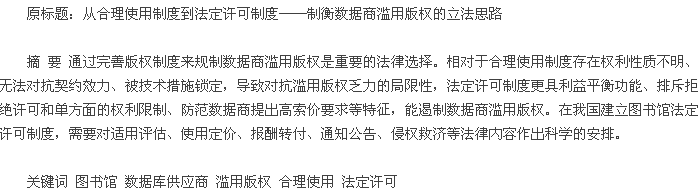
图书馆为公众在版权扩张的法律环境中自由获取知识和利用信息保留了难得的空间。然而在数据商滥用版权的背景下,图书馆保存与拓展这种空间力不从心。私法是规制数据商滥用版权的重要法律选择,其中版权法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完善版权制度来消弭数据商对版权的滥用,既符合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协议)等国际条约对版权的定位,又与我国私权行使的民法原则要求一致,还能避免反垄断法等公法与私法的冲突和矛盾,所以更具合理性、可行性。
合理使用制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版权利益平衡因素,是对版权的“绝对限制”.但是,面对规制数据商滥用版权的实践需要,合理使用制度屡现尴尬。与此形成对比,尽管对法定许可制度有着“扩大与缩小”“存在与废除”的学术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国家的版权法已经出现了将传统的合理使用的某些类型转化为法定许可,拓宽法定许可适用范围,用法定许可替代合理使用的新动向[1].韩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版权法针对图书馆设置有专门的法定许可制度,目的是制衡版权,提高授权效率,保障权利人利益,关照公众诉求。鉴于法定许可制度蕴含的“平衡基因”和体现出的反版权垄断的独特优势,其消弭数据商滥用版权的价值受到重视与挖掘。在我国建立图书馆法定许可制度,既要分析立法的依据和法理性,又要对制度架构与内容作出科学的设计和安排。
1 合理使用制度抗衡数据商滥用版权的不足
1.1 合理使用法律性质的定位不利于对抗滥用版权
对合理使用的法律性质问题,至少存在“权利限制”“侵权阻却”“使用者权利”等不同的理论。“权利限制说”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并被许多国际条约、国内立法肯定。“侵权阻却说”的不足在于对合理使用的“合法性”视而不见,既然是合法使用,就无所谓“侵权”与“侵权阻却”.“使用者权利说”的弊端是无法解决一个特定义务主体面对众多不特定的权利主体的矛盾[2].我国版权制度没有“合理使用”的概念,无论是现行 《着作权法》,还是“《着作权法》 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都将“合理使用”涵盖于“权利限制”范畴。版权是法定赋权,使用者对抗滥用版权需要拥有相应的权利。法律对合理使用性质的定位不利于图书馆等作品使用者应对数据商滥用版权的挑战,甚至在权益受到损害时找不到反击的利器(如诉讼)。所以,应当使合理使用“权利化”,让滥用版权具备可诉性,使用者可以合理使用“权利”受到滥用版权侵犯为理由提起控诉[3].
1.2 现行合理使用制度的法律效力低于契约的效力
“合同”是数据商滥用版权的“帮凶”,因为合同的契约效力高于合理使用的法定效力。比如,美国版权法规定,图书馆应承担其收藏的作品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的合同义务,欧盟 《信息社会版权指令》 则倡导图书馆通过约定解决版权问题。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第七条“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暗含合同排除合理使用的有效性。虽然按照《条例》 第十条的规定,图书馆可以置“事先声明不许提供”的法律规定于不顾,而根据 《条例》 第七条设置的原则行事,但不能杜绝数据商以约定方式禁止图书馆按照第七条规定使用作品的可能性,除非 《条例》 第七条成为“强行法”.又如,为加强对版权的垄断,数据商从作者、出版社获得的权利通常是“独占许可”,由于我国《着作权法》 未对独占被许可人的义务与责任作出规定,数据商就可能拥数据库待价而沽,拒绝在图书馆未能满足其提出的条件时怠于行使权利,拒绝许可。
1.3 技术措施的数字锁定效应使合理使用形同虚设
“数字锁定”(digital lock)是指权利人采用技术措施使版权物权化,规避版权限制与例外而造成的一种“无法律秩序”,或者说一种“技术为王”的秩序和状态[4].由于技术措施具有“认同一切,排斥一切”的“全有或者全无”功能,使得未经授权的所有利用作品的企图被挡在“技术围墙”之外,包括合理使用制度变成一纸空文。
美国图书馆协会指出,“一招致百式”的单一技术使图书馆基础业务和读者服务全面受到压抑[5].面对被技术措施加了“锁”的作品,图书馆笼罩在“寒蝉效应”之中,既动弹不得,又动辄得咎。因此,美国国会在 《消费者、学校和图书馆DRM 接触法》 立法议案里要求扩大数字作品的合理使用范围,保障图书馆等的技术措施知情权与自由选择权[6].《条例》 规定了 4 种技术措施例外,但图书馆不是适用主体。即便是公有领域资源,一旦附加技术保护措施,图书馆就无能为力。目前我国图书馆消除“数字锁定”的办法主要是合同约定,但合同往往不是赋予而是否定图书馆的技术解密权。比如,Elsevier 在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签订的 《许可协议》 规定图书馆不得对被许可资源采取的任何技术措施实施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分解[7].
2 法定许可制度消弭数据商滥用版权的优势
2.1 更有利于平衡版权利益关系
利益平衡原则在版权制度中起着核心与实质性的指导作用。相对于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保持了对权利人财产权的尊重,所以更具平衡价值。为了使权利人得到创作回馈,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版权法规定经济补偿的权利不能放弃。为了突出利益平衡理念,法定许可制度不仅采取“多次付酬”的设计,有的还设置“保留权”条款,权利人认为不能达到其利益诉求时可以“选择退出”,重新采用“授权许可”.有学者认为,法定许可制度是网络条件下利益协调的新准星[8].图书馆建立法定许可制度就是奉行“折中思维”,既满足图书馆利用作品的需求,又使数据商等权利人的权利降格为获得合理的报酬请求权。合理使用是版权制度最复杂的部分,关联因素较多,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征,规则复杂,图书馆难以厘清和掌握;而法定许可的适用条件简单而清晰,不需要作出任何主观的判断,这同样增加了其在图书馆的适用性。此外,法定许可制度侧重于考虑图书馆、公民素质教育等涉及公众利益的某一行业,而不是个人[9],这也是法定许可制度在图书馆立足的一个理由。
2.2 排斥数据商单方面的权利限制
法定许可是“非自愿许可”,是公权力通过对私权力流转的强行干涉,促成版权交易条件的法定化,从而排除权利人的授权意愿,作品使用者无需理会权利人可能施加的限制条件,更不必顾忌陷入被拒绝使用作品的窘迫境地。显然,法定许可制度对图书馆反制数据商利用合同限制图书馆的权利,或者在不满足其条件时以拒绝许可相威胁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法定许可制度的“保留权”条款却建构了一种立法悖论。因为设置“保留权”条款的初衷是平衡权利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关系,但是把“保留权”的行使作为能否适用“法定许可”的前提条件,无疑是给使用者开了一张可能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收不到“鱼和熊掌兼得”的立法效果。我国法定许可制度存在的“法定”逊位于“意定”之法理矛盾,导致这项制度存在先天性的理论缺陷。世界上只有少数大陆法系国家的版权法定许可制度设置“保留权”条款,如德国、西班牙等国家的版权法。因此,笔者建议立法删除我国法定许可制度的“保留权”规定,还法定许可制度的本来面目,以符合国际立法的大趋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