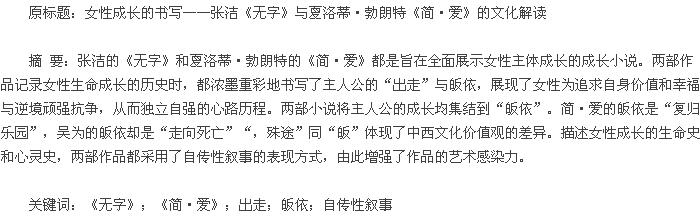
1986 年秋天,利用去欧洲进行文学作品交流的机会,张洁专程前往英国约克郡游览,因为那里是蜚声中外的着名作家勃朗特姐妹的故乡。参观完勃朗特的故居,张洁情不自已,随后赋诗一首———《到呼啸山庄去》:“……铺上她已经长满青苔的,屋舍和院落。将生者带进死者的坟墓,讨论爱情的必要或无稽,在如此绵长的雨中。”[1](P396)通过小诗张洁寄予了自己对勃朗特姐妹深深的怀念和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同为女性和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生死” 等诸多人生问题感同身受的况味和惺惺相惜之情。
于张洁而言,夏洛蒂·勃朗特显然是她很早就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1984 年张洁在锦州文学报告会上不无赞叹地对读者说:“布朗特姐妹写出了《呼啸山庄》和《简·爱》这样不朽的世界名着。” [2](P58)张洁对《简·爱》的接受在其文学创作中有突出表现。1980 年张洁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它的主题和《简·爱》一样也是从女性意识的角度来探讨爱情的真谛,在中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说“:没有文学影响的过程,即一种令人烦恼并难以理解的过程,就不会有感染力强烈的经典作品出现。”[3](P6)这种识见用于夏洛蒂·勃朗特对张洁的影响称得上恰如其分。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启了这种影响的序幕,那么时隔 20 多年,张洁创作出了 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无字》,无疑将这种影响做了更丰富鲜明的回应和呈现。
一、出走:成长的法门
“成长小说”是叙述主人公经过多种世事、多重历练而不断获得关于社会、人生和自我的认识而逐渐成长的一类小说,内容除具有亲历性的特征外,还突出表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女性成长小说”除了具有属于一般成长小说的特征外,还有其独特性———即“女性”这一性别前提所内含的性别特质。
所以,学界普遍认同“女性成长”的小说“主旨在于全面展示女性主体的成长过程”。[4](P232)波伏娃强调“女性成长”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5](P8)意思是“女性成长”小说在按时间的线性发展来叙述女性的个人历史和事件的同时,她的历程中还会出现特别的性别生存境遇的内容。她们的生活场景和心灵感受的聚合,既是个体千姿百态的生命史,也勾勒了女性作为社会“第二性”所具有的普遍和整体存在的心灵成长史,是跨越时空而共有的明确而切肤的感受。
《简·爱》和《无字》记录女性成长的历史采用了基本一致的模式化的叙述结构:不幸的童年→出走→遭遇爱情→认识人生和回归自我。前三项生活经历按线性发展,并且每每在经历人生这些重要阶段的时候,女性主体意识会逐渐强化和清晰。无论是“不幸的童年”还是“遭遇爱情”,在面临个体生活成长的特别阶段,女主人公都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于是频频“出走”成为联结人物生命历程最重要的环节。简·爱和吴为通过“出走”不断改写自己命运的轨迹,而且还促使其日益独立自主、自尊自爱。
从盖茨海德“窗台上的孤女”到“桑恩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简·爱通过四次“出走”,完成了一个女性主体角色的转换。第一次出走是童年时逃离盖茨海德府。简·爱有着不幸的童年,父母早逝,被舅舅收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舅妈里德太太和她的孩子一家经常无理打骂和虐待她,甚至把幼小的她关到恐怖的“红屋子”里。简·爱孤独而无助,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台”上。小小的她反思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想采取“出走”或“从此不吃不喝,让自己饿死”的办法来反抗。最终简·爱取得了“胜利”———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得以离开舅母家。第二次出走是离开罗渥德学校。罗渥德学校的 8 年时光,简·爱从童年走进少女时期,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眼界的开阔和自信心的确立。她凭着自己的友善和努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重,还有海伦的友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中的简·爱渴望闯进“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忧虑、激动和兴奋的变化多端的天地”,于是她通过报纸找到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而达到了远走高飞的目的。第三次出走是离开桑恩菲尔德庄园。在桑恩菲尔德庄园,简·爱体验到了对罗切斯特的爱情,但因为对自己的相貌和经济地位等方面的不自信,对这份情感的不确定感始终困扰着她。当婚礼受阻并得知了关于罗切斯特第一次婚姻的详情后,简·爱的情感世界在一瞬间坍塌瓦解,她的道德感不允许自己作为一个不合法的“妻子”继续生活在桑恩菲尔德庄园,所以尽管深爱着罗切斯特,但自尊心极强的简·爱选择了离开。第四次出走是离开沼屋。沼屋是简·爱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在明白了圣约翰对自己的爱情只是为了为上帝服务后,视爱为生命的简·爱理性复苏,迸发出对罗切斯特的强烈情感。在爱的召唤下,简·爱踏上了寻找罗切斯特和爱情的旅途。
《无字》是一部家族四代女性的生命史,第三代女性吴为的“出走”是整部作品最跌宕起伏的一幕。童年时期,为了生计为了寻找爸爸,吴为跟随着母亲叶莲子“打起行李就出发”,辗转于北京、陕西、武汉、广州、香港、桂林、柳州等临时的栖身之所。
耳闻目睹母亲遭受的苦难与屈辱,以及父亲还有小学赵老师等给予她灭绝人性的暴力虐杀,吴为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她善良怯懦、多愁善感但又倔强自尊。在人生的路途,吴为一直跌跌撞撞,不断出走。读小学四年级的吴为,因为长期被赵老师等“教育”,所以“总是从学校后的高坡翻出墙外,一天到晚从不停歇地在山野里跑来跑去”。[6](P311)面对父亲顾秋水,吴为“背上自己的行囊一分钟也不多留,一声再见也不说,头也不回地走了。她知道,到死,他们也不会再见了。”[7](P325)韩木林,吴为的第一任丈夫,把她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所以吴为“只带着她不多的几件衣物出了门,连禅月的生活费都没要”,就在街道居委会果断地办完了离婚手续。那个仲夏的雨夜,他们无话可说地告别“,从此一别,再未相见,今生也不会再见”。[8](P13)至于与胡秉宸二十多年的感情纠葛,吴为曾若干次出走。正如小说中所描述:“满脸是揩也揩不完的泪,却硬硬地不肯回头。走向汽车站那短短的几十米路上,她的人生似乎又有了一个转折。她现在已是日薄西山,她将独行。”[8](P385)为了逃避自私恶心的虚情假意,吴为选择经常去往国外,并且长时间逗留不归;要么就是当吴为受到胡秉宸和白帆的作弄和攻击,对爱和生活极度失望的时候,她会不远千里奔向“最爱的森林”和“塬”这样的故地,在大自然的怀抱寻找情感和精神的慰藉。
综观简·爱和吴为生命里的几次“出走”,都和她们在女性成长的生命历程中追求“自我独立”、“婚姻自由”等个性解放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中外知识女性主体意识逐渐成长的姿态。这种姿态具体有三个层面的表现:一是对暴力和压迫的反抗而勇敢出走。简·爱和吴为都有非人待遇的童年境况,这些早年的苦难磨砺使得她们很早就萌生了与不平命运斗争的反抗精神。二是为情感自由而出走。这是女性作为一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与认同的核心,情感的独立意味着男女平等和人格独立。三是为自由空间而出走。现实社会为达到对女性的规训往往不为她们提供合理的生存空间,为此简·爱和吴为努力拼搏奋斗,她们对自由空间的思考和向往已然超出了男女平等的性别层面而直指社会。
《简·爱》和《无字》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女性“出走”的积极意义,并且揭示了撑起这种心灵成长的两个重要内因:一是知识给予成长的力量,二是经济独立促成个体独立。“出走”,不仅意味着有能承受因超离社会规范而带来的身心痛苦的力量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实现经济独立。对此伍尔夫非常赞同,她说:“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9](P96)所以“出走”不仅是女性对现实生存境遇保有的清醒认识,确保其追求新生活时行动不盲目,而且是女性自觉规划未来人生和主动践行的体现。
二、皈依:成长的走向
在“出走”的成长旅途,简·爱和吴为尝尽了生活的千般滋味,历经了人生的重重考验。汗水和着泪水,她们的生命之河不舍昼夜向前流淌。从懵懂无知走向稚嫩青涩走向理性成熟“,出走”再“出走”,迈过生命的道道阶梯,终于停下了漂泊的脚步,将自我“皈依”到一种尘埃落定的命运。但简·爱和吴为出走后的回归,已不同于以往中外作家笔下的娜拉式、子君式、萧红式重归现实原点的“返回”,而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抵达个体生命生长至高点后的皈依,是回归女性自主的家园。历经多次“出走”的简·爱“复归乐园”———在芬丁庄园与罗切斯特幸福相守相依;吴为选择“走向死亡”作为最终的皈依地———“先是发了疯”,而后“拔掉了赖以支持生命的所有管子”。一个走向希望,一个走向绝望;一个是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一个是花落人亡的悲剧告终;尽管曾经的“出走”景况惊人相似,但在“皈依”的时候,方向和方式却大相径庭。《简·爱》和《无字》在“皈依”层面出现的“天壤之别”,耐人寻味。同是展示女性成长的生命史,简·爱和吴为在同“皈”时却走向“殊途”,这种书写差异究其实质是因为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持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而导致的。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 19 世纪的英国,基督教文化早已深入人心。《圣经》被英国社会奉为道德和法律准则,是民众信仰的总纲、处世的规范和行为的指南。并且夏洛蒂成长于一个牧师家庭,从事牧师职业的父亲经常给儿女布道授课。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影响,使得夏洛蒂成为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和情绪必然会渗透到作家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简·爱》这部小说的叙述、对白和独白中有 60 多处引用或化用了《圣经》观点和素材,行文中直接用“上帝”的名义或启示的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简·爱面对罗切斯特陈述爱情的平等的宣言时,就带着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特征:“上帝若赋给我一些美,许多钱,我会使得你难以离开我,就如你现在使得我难以离开你一样。我不是在藉着习俗、惯例,甚至不是藉着可朽的肉身来和你谈话;———是我的精神向你的精神谈话;就如同我们都从坟墓中复现,我们站在上帝的脚旁,两人平等,———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10](P307)简·爱的皈依,作者意图非常明显:夏洛蒂·勃朗特把住在芬丁庄园的罗切斯特和简·爱类比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与夏娃,把作品中主人公的世俗幸福提升到受上帝恩宠、得基督祝福的高度,反映了一种深沉的基督教情结。
荒林评论《无字》说“:成长这个概念基本上用于生理和心理,很少用于观念更新和智慧更新、对生命态度的更新,只有在最后一种意义上,成长才具有特别个人的价值和写作学的价值。”[11](P98)吴为从“出走”的激情叛逆走入一种精神失常和自杀的极端沉寂和遮蔽,这样一种皈依的安排,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实是真正的更新了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认识有了新的观念与智慧。如果说在无边和无端的苦难面前,吴为在生命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只是被动地“承受”、容忍地“服从”、善良的“宽恕”,这与一开始受到命运不公平待遇就知道奋力反抗的“简·爱”不一样的话,然而,随着生命历程的前行,当残酷的现实一次一次击碎她心底残存的梦,那种潜藏的强烈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女性人格就被激活,她用“疯癫”和“死亡”的遮蔽态度拒绝了与男性的共存与和解,用貌似无奈、沉寂的方式对无望世界的做着无声而壮烈的反抗。海德格尔认为,“遮蔽可能是一种拒绝,或者只是一种伪装”。[12](P274)无论是“伪装”还是“拒绝”,吴为对自我的可塑性已产生了致命的怀疑,那么,当女性应有的社会地位得不到尊重和肯定时,绝望和虚无的情绪就不可避免。“天高了,云淡了,夏天过去了。树还绿着,吴为却要走了。这就是死亡……我死了,不会有人为我流泪,只有屋后树上的蝉儿,为我失声悲鸣……”[8](P421)带着对生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渴求,美丽的吴为参透了生死的大义,向死而生“,破茧成蝶”,涅盘重生! 这体现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古自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和“舍生取义”的高洁情怀。虽然惨烈,但这恰是以吴为等为代表的中国女性完成一个作为独立的“人”所走过的血泪史!
从“出走”到“皈依”,《简·爱》折射了西方文化为自由和平而自强不息的生命观,简·爱正是践行这种生命观的女性,她成为了尊严与价值的“ 精神贵族”。《无字》反映的是中国文化对待生命的宽容和舍身取义的特质,吴为这个以死抗争命运的“烈女”,寄寓的是中国女性绝不在男性创造的所谓神袛前低头跪伏的高贵品格。同为女性成长题材创作,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表现出来的“和而不同”特点,充分地显示了中外作家在文学活动中的“文心相契”,也证明了张洁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有着世界级文学地位的作家的良好素质:既能虚心吸收和借鉴中外其他作家的影响,又能主动与其疏离。
三、自传性叙事的艺术追求
成长小说一般都具有自传性叙事的形式特征,小说中的自传体内容,往往是事实和虚构紧密结合的一种艺术呈现。作家善于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将自己独特的感悟用文学的方式传达出来,自然而然,就会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提取一些重要素材融合到创作中。写作心理学认为,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是人的个性形成的重要阶段, 这些时期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境况会给作家个性的形成打上鲜明的烙印。作家的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会给作家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作家个性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对此,张洁说“文学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在回答张英关于能否把《无字》称为自传体小说时,她肯定地说:“作家的每部作品,都可以看做是他们灵魂的自传。”“小说除了名字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13](P93)夏洛蒂也有类似的表达,她说“:我决不会用自己未曾体验的东西去影响读者的感情。”[14](P188)《简·爱》和《无字》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都把作家的生平经历植入其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到处可见作家的身影。简·爱有不幸的童年,父母双亡;而夏洛蒂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简·爱被送到罗伍德慈善学校学习,受到非人待遇,两个好朋友活活病死;夏洛蒂四姐妹也曾被送到“牧师女儿学校”柯文桥,在那里过着衣裳单薄、食物匮乏、备受虐待的生活,她的两个妹妹因此不幸病死。简·爱在偏远的乡郡生活过,而夏洛蒂也在英国遥远的约克郡居住;简·爱后来做了家庭女教师,而夏洛蒂在专职写作前也曾做过家庭女教师;简·爱爱上了一个大她近 20 岁的、有个“疯老婆”的罗切斯特,而夏洛蒂爱上了自己尊敬的老师“黑天鹅”埃热先生。《无字》中吴为的一些生活遭际与张洁何其相似:吴为自小被父亲抛弃由母亲一人带大,张洁自小父母离居,是由母亲张珊枝独自将她抚养成人。吴为的童年居无定所,战乱之中随母亲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张洁从小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吴为是国内外的知名作家,张洁同样如此。吴为的女儿禅月在海外工作,张洁的女儿唐棣现居美国。吴为与长她 20 多岁的副部级官员胡秉宸十年苦恋终成正果,张洁的前夫曾是国家机械部的一个老领导。小说中吴为的母亲死了,她与胡秉宸最终也离婚了,张洁的人生正好也经历了这两次变故。当然,成长小说的自传性叙事毕竟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传,它存在艺术的虚构。所以简·爱和吴为的生活不能完全等同作家。比如,夏洛蒂和埃热先生的感情就没有简·爱和罗切斯特的浪漫诗意,更没有如小说中美满幸福的结局;而张洁没有吴为那样悲惨的结局,她过着宁静自由的生活。
除了人物生平经历具有很鲜明的自传特征外,人物的形象、气质和性格也极具自传色彩。盖斯凯尔夫人谈到第一次和夏洛蒂见面时情景时说“:她又瘦又矮;柔软的棕色头发,不很黑,眼睛很好,富有表情,坦然直接看着你,同头发一样颜色;嘴大;前额方宽……一个邻人正好来访,见到夏洛蒂,他说夏洛蒂小姐使我想起她自己的《简·爱》。她看来比一向更矮小,那样安静无声来回活动,正象一只小鸟,象罗契司特说简·爱一样。”[10](P12)生活中的夏洛蒂也和简·爱一样坚强勇敢、不懈奋斗,为了自己的幸福她与旧势力和旧观念不屈斗争。她的作品《简·爱》最初是用“柯勒·贝尔”这样一个典型男性化的笔名发表,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固然是为作品出版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对现状的无奈。
但是,心灵深处她极力争取着女性享有的平等地位。1850 年 1 月 19 日夏洛蒂致信给乔·亨·刘易斯:
“亲爱的先生:我将告诉你,为什么看了《爱丁堡》上的评论我那么不高兴。并不是因为它的批评尖锐或者它的责备有时候严厉;并不是它的赞美有限,而是因为我已经诚恳地说过,我希望评论家把我看作一个作者,而不是一个女人,但是你却那么粗鲁地———我甚至认为是那么残酷地———处理了这个性别问题。”[15](P382)《无字》中吴为的人生跋涉与情感履历异常悲壮:父亲顾秋水在精神深处和意识潜层毁坏了她作为人的尊严、自信和正常追求,成为她一生拂之不去的沉重的生命镣铐。与胡秉宸的恋情,在点燃了她的生命之火的同时又最无情地断送了她的一生。即算成长环境如此恶劣,也无法阻止一个坚强勇敢、奋斗不息的女性保持自己冰清玉洁的操守。所以作为主体意识完全觉醒了的吴为,作出了骇人一搏,自我毁灭当是她最华丽的转身。了解张洁的读者,一定能理解,吴为就是张洁的代言。在张洁的成长和成才的路上,“父亲”这一重要角色始终处于“缺席”状态。她对“父亲”所谓一家之主的传统观念不仅从来没有任何感觉,反而因为“父亲”这个“男人”对妻子、女儿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出不屑与仇恨。于是张洁一反中国文化传统,随母姓而非父姓,在对婚姻失望后她毅然绝然地走上了离婚和独自抚育培养女儿的道路。
故园是生命成长中最诗意的印象,是夏洛蒂和张洁最深切和亲切的记忆。夏洛蒂在《简·爱》中深情地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石楠荒原”“:我知道我到了什么郡;是北部中心的一郡,荒野苍茫;峰峦突起。在我的后面和左右两方,都有着大片的荒原。路向东南西北伸展———发白、宽阔、荒凉;它们都穿过荒原,石楠都茂密地生到路边了。”“我摸触石楠:草是干的,可是夏日的热还使它温暖着。我看望天空;天空是清净的;一颗慈爱的星正在峡谷的顶上闪着光。露水降了,但很是温柔;没有微风发响。我觉得大自然仁慈善良;我想她爱我,虽然我是无家可归的人;从人只能预期到疑惑、拒绝和侮辱的我,却怀着孝心的爱紧依着她”。[10](P397-298)当简·爱遭遇痛苦困顿感觉孤苦无依时,她就会回到荒原,因为在那个万物之母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她永远是被关爱的孩子。现实生活中夏洛蒂家屋后就有一片荒原,荒原上有弯结多枝的石楠植被,欢快鸣唱的各种小鸟,奇形怪状的嶙峋岩石,潺潺而流的山涧小溪。荒原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天天陪伴着自己心爱的孩子,夏洛蒂和妹妹弟弟经常在那嬉戏游玩,自小失去母爱的她从荒原的怀抱里获得了感情慰藉。荒原带给夏洛蒂最多的爱和快乐的同时,也赋予她最丰厚的生活启示和创作灵感。
《无字》中张洁用大量的笔墨尽情描绘了故乡的自然风景,“塬”是其中最美最独特的风景,也是吴为最钟爱的地方。“她从黄土的叠层或裸露的断层上,渐渐阅读出而不是塬对她叙述出的,无从装饰、无从营造、无垠无际,比史前更久远的苍凉以及那摄人魂魄的神秘和宿命”。“黑暗中,她的塬以一尘不染的纯净包裹着她、护卫着她,并从另一个世界招回许多远走的灵魂,陪伴、翻飞在她的周围,使她自小在光明世界中受到的惊吓消散地无踪无影”。[6](P370-371)“塬”这道风景显然与与《简·爱》中的“荒原”有着类似的神韵———苍凉、辽阔。同时它也和“荒原”一样是有温情和生命的另一个世界,与女主人公关系深刻。当吴为累了失望了的时候,它会用博大的胸怀包裹着她、护卫着她。借助对家乡自然环境的描绘,张洁寄予了自己关于生命归途的思考和理想家园的向往。
总之,从各自成长的经验出发,围绕女性成长的生命史和心灵史,张洁与夏洛蒂·勃朗特通过《无字》和《简·爱》两部作品,塑造了以简·爱和吴为为代表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深入探讨了女性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法门,在现代不断高涨的女性自我身份确认的全球化语境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洁文集·散文随笔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何火任. 张洁研究专集[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美)哈罗德·布鲁姆着,江宁康译. 西方正典[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荒 林,王光明. 两性对话———20 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5](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着,陶铁柱译. 第二性[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张 洁. 无字(第一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张 洁. 无字(第二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8]张 洁. 无字(第三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