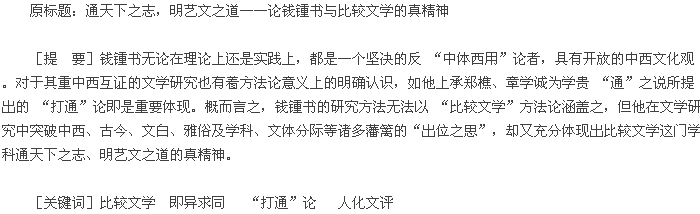
钱锺书的学术生涯始于 20世纪 30年代,当时还有不少老辈文人对西方文学的价值缺乏认识。如民初大诗人陈衍就曾向尚在清华外文系攻读英国文学的钱锺书提出过疑问:“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①从表面上来看,这一说法固然体现出作为旧诗人兼旧式批评家的陈衍对 “外国文学”(基本等意于西方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借鉴意义缺乏了解,而从深层来看,它又显示出陈衍心目中根深蒂固的 “中体西用”意识。因为,根据钱锺书的记述,陈衍对学 “理工或法政、经济之类有实用的科目”者 “懂外文”并无异议②,换句话说,他并不反对在实用性的学科上 “向外国去学”,只是不赞成在非实用性的学科如 “文学”上借鉴“外国”(主要指西方)。这表明,陈衍仍然抱着精神文明是中国的好、物质文明是西方的好之类老套观念,其思想境界实未超出洋务运动时期的 “中体西用”论者如冯桂芬、孙家鼐、张之洞之辈。与此形成对照,钱锺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坚决的反 “中体西用”论者。他在 《谈艺录》初版序中就明确提出了 “取资异国,岂徒色乐器用”③这一与 “中体西用”论针锋相对的观念。而他对 30年代中期 “本位文化”论者的批评,则显然可以视为其反 “中体西用”立场的自然延伸。
此外,钱锺书对其重中西互证的文学研究也有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如他上承郑樵、章学诚为学贵 “通”之说所提出的 “打通”论即是重要体现④。需要说明的是,钱锺书提出“打通”论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将其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区别于 “比较文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钱锺书排斥 “比较文学”研究。例如,他曾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时概括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他的 “专业”,“比较文学”是他的 “余兴”⑤。并且,他还多次肯定了 “比较文学”的意义,并对 “比较文学”的一般方法以及如何发展中国 “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多有论述。以笔者之见,钱锺书之所以不愿将其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等同于 “比较文学”研究,也不愿被视为 “比较文学”学者,固然与某些所谓 “比较文学”论文牵强比附、水准不高以及该类学术曾被视为 “资产阶级文艺流派”⑥等内在、外在的原因有关,但究其主因,当是钱锺书不愿将自己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囿限于 “比较文学”的范围内。
概而言之,钱锺书的研究方法确实无法以 “比较文学”方法论涵盖之,但他在文学研究中突破中西、古今、文白、雅俗及学科、文体分际等诸多藩篱的 “出位之思”,却又充分体现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的真精神。本文拟对钱锺书的治学之道与比较文学的错综关系进行较全面的梳理,藉以阐明钱锺书的治学精神与方法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与启示。
一 、钱锺书 “打通非比较”之说的内在精神及理论渊源
钱锺书在文学研究中常常以 “外来之观念与本国之材料相参证”,不少研究者因此将他定位为 “比较文学”学者,并致力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考察他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成就与贡献。
钱锺书本人对此颇不以为然。⑦笔者注意到,钱锺书将打通 “中国诗文词曲”与 “小说”的方法解释为 “以白话小说阐释古诗文之语言或作法”,而究其实,则是以 “白话小说”与 “古诗文”的 “语言或作法”相类比、相 “参证”。例如,《管锥编·毛诗正义·卷耳》一则 (67-9),即是以章回小说 “话分两头”或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说明 《卷耳》一诗 “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的意境;又如,《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一则 (164-166),乃是以 “后世小说、剧本”中的 “对话独白”体,拟之于左氏在历史叙事中 “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的 “代言”方式;再如,《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鲁仲连邹阳列传》(321)一则,为了说明 “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一语中的 “乃今然后”四字看似 “堆叠重复”,实则 “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已之心思语气”的修辞效果,乃以 《水浒》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一语中的 “自此方才”四字与之 “连类”。
如果说,“打通” “中国诗文词曲”与 “小说”,实则是指 “白话小说”与 “古诗文”的“语言或作法”相类比、相 “参证”,那么,与此相应, “打通” “中国文学”与 “外国文学”,则主要应指以 “外国文学”与 “中国文学”相类比、相 “参证”,这在 《管锥编》以及 《谈艺录》、《七缀集》等其它钱着中处处皆是:如以西方现代主义流派 “达达派”所创的 “同时情事诗”体,《堂·吉珂德》第二编第五章中的一个情节,《名利场》中有关滑铁卢一役的 “结语”,与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 “人异地而事同时”的情境相类比、相 “参证”(《管锥编·毛诗正义·卷耳》)⑧;以华兹华斯、雨果、施莱格尔等浪漫主义诗人以 “向不入诗”之 “字句”、“事物”采取入诗的作法,与唐韩愈、清末黄遵宪等中国诗人的 “以文为诗之意”相类比、相 “参证”(《谈艺录·三》)⑨;以大仲马等西方作家擅于在 “每章结束处特起奇峰”的小说笔法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 “回末起波”的手法相类比、相 “参证”。 ⑩前文提到,钱锺书提出 “打通”论,乃是为了将他的研究方法区别于 “比较文学”。那么,“打通”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打通”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层面要比 “比较文学”研究丰富。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指超越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而打通研究则不仅包括语言、国界或学科界限的超越,还包括对文体界限、古今界限的超越瑏瑡。因此,从研究层面来看,“打通”研究可以说是涵盖了“比较文学”研究。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 “打通”研究之 “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这一层面虽然近似于比较文学中的 “平行研究”,但也存在着微妙差异:比如,对中外文学的 “打通”研究往往止于罗列 “外国文学”现象以印证 “中国文学”,而 “平行研究”则还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分析,或辨别异同,或双向阐发,或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再次,从目的论上来看,“打通”研究与 “比较文学”研究固然都试图通过越界对话以求有所新发明 (“拈出新意”),但一则专务 “求同”,一则兼重辨异,差别是显然的。
如果从中国学术史的角度着眼,钱锺书的 “打通”论与传统学术思想中尚 “会通”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但由于钱锺书在其论着中只提到了宋郑樵与清章学诚有关 “会通”的议论或观念 (如郑樵 《通志·七音略序》中 “宣尼书不过拔提河”之慨,章学诚 “文史通义”之说),因此,笔者在此着重介绍郑樵与章学诚的尚通之论。
郑樵是南宋着名史学家,长达 200卷的 《通志》一书是其代表作。在该书总序的开头部分,郑樵明确提出了 “会通之义大矣哉”的口号,他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基于这一观点,郑樵对《史记》作者司马迁赞赏有加,因为后者能够继承孔子修 《春秋》的义例,贯彻治史的 “会通”准则,并编写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 《汉书》作者班固却因断代为史,失去 “会通”之旨、“相因之义”,而受到严词斥责。由此可见,郑樵是以 “会通”作为治史的准则,并用它来评判古人着书的是非得失。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郑樵在内的传统学人的尚 “会通”的观念,固然与 “通史” /“断代史”之争密切相关,但并不限于这一层面。郑樵谈 “会通”,就既从纵向贯通古今的角度着眼,又从横向融通文史的角度着眼,他所谓 “总 《诗》、 《书》、 《礼》、 《乐》而会于一手”,所谓“会 《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即明横向融通文史之义。此外,郑樵又明确谈到:“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
这表明,他已具有超越地域、时代界限以寻求 “普遍规律”(“道” /“理”)的理论自觉。到了章学诚,则更为突出横向融通文史的一面,他所提出的 “六经皆史”说,即为融通文史、融通经史子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而在 《释通》一文中,他又首揭 《大易》“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之说,进而发挥道术求通的思想,为郑樵张目。
显然,钱锺书的 “打通”论与郑樵、章学诚的尚通之论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如前所述,钱锺书主张在文学研究中 “打通”各人文学科,这与郑樵、章学诚以横向融通文史为尚的立场是一致的;其次,钱锺书还主张在文学研究中超越 “古今町畦”,这与郑樵、章学诚提倡纵向贯通古今的立场,基本精神却是相通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钱锺书在其论着中分别提到了郑樵与章学诚有关 “会通”的议论或观念,但对其 “打通”论有着更为直接和明显影响的则是章氏的 “会通”思想,因为,钱锺书曾明确指出,“打通”论的基本精神即在于章氏所谓 “文史通义”。
在钱锺书看来,唯有不囿限于 “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范畴而注重东西之理、南北之学的 “打通”(“通以骑驿”),才可 “语于”章学诚所谓 “文史通义”。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钱基博对其子喜 “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着述之隐”的评价。
二 、钱锺书的 “比较文学”论及其方法论自觉
事实上,钱锺书并不排斥 “比较文学”研究,他除了承认 “应用过比较文学里的一些方法”之外,还对 “比较文学”的学术意义有着明确认识。他指出:
比较文学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
这段话揭示了 “比较文学”研究的三重意义:“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
我们知道,“比较文学”是超越民族、国别与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不同民族或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而阐明某种文学现象。这里所谓 “比较研究”,既可以是指借助他国文学理论或术语阐发本国文学现象或观念,也可以是指以他国文学现象与本国文学现象相对照,如钱锺书曾提到:“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歌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 “比较研究”,都是他者与本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它一方面使我们在他者的参照下,对本我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另一方面,也能增进我们对他者的了解。因此,“比较文学”研究在作为不同民族或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一层面上,就如钱锺书所揭示的那样,不但 “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也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此外,由于这一研究模式乃是超出个别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范围的文学研究,因此,往往可以由此总结出带“普遍性”的、适用于东西方文学的文艺理论或范畴,以此为基础,便有可能建构起一种为许多比较文学学者所向往的 “共同诗学”。
我们看到,钱锺书是从 “发展”轨迹和 “艺术”品性这两个层面来谈论各国文学 “异同”的。在钱锺书看来,各国文学既在 “发展”轨迹上存在着各自的 “特色”和彼此间的 “共性”,又在 “艺术”风格上存在着各自的 “特色”和彼此间的 “共性”。这种认识可以说是 “比较文学”学者的 “共识”。以中西文学的比较为例,一般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在文类的产生上均经历了由诗歌而戏剧而小说的演进过程,这是中西文学在 “发展轨迹”上的 “共性”,而中国古典文学由诗而词而曲的演进路向,又是中国文学在 “发展轨迹”上的 “特色”;再从中西文学的 “艺术”品性来看,“通感”手法和 “诗可以怨”的功能论可以说是体现了中西文学的 “共性”,而 “比兴”手法和 “意境”理论则可以说是体现了中国文学的 “特色”。
此外,钱锺书还对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有着深切体认。在他看来,“文艺与哲学思想”是 “交煽互发,辗转因果”的。综观钱着,借重哲学 (含伦理学)、“心理学”之处甚多,如老子、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狄尔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伦理学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等等。另需说明的是,钱锺书还对超媒体研究 (跨艺术门类的研究)、译介学研究等不同类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有着明确意识,其 《中国诗与中国画》、 《读〈拉奥孔〉》、《林纾的翻译》、《汉译第一首英语诗 〈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等文,均堪称以上领域内的经典之作。
我们看到,钱锺书在指出各国文学在 “发展”轨迹和 “艺术”风格上既有 “特色”又具“共性”后,接着强调,研究者在对各国文学的比较中,应善于从异中看出同 (“即异而求同”),从同中看出异 (“因同而见异”),这样才能使 “文艺学”具有 “科学的普遍性”。这一观点其实可以解析为两个层次:第一, “比较文学”研究乃是文学研究走向 “普遍性”的前提之一。这一层意思按照钱锺书所引法国着名比较文学家艾田伯 (REtiemble)的说法就是:“没读过 《西游记》,正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去讲小说理论,可算是大胆。”
艾田伯的意思是说,如果只局限于考察某一地区 (如西欧)的小说创作,而不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小说创作 (包括中国小说、俄国小说在内)有一全面了解,便不应奢谈 “小说理论”。因为,以某地区小说或某地区文学为依据所总结出的所谓 “小说理论”或 “文学理论”,往往是片面的、缺乏 “普遍性”的,因而也是不足为凭的。第二,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乃是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这一层意思显然已超出比较文学是否有学术意义或学术价值的问题,而已涉及到“比较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其实,对于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钱锺书有着明确定位。众所周知,他曾借用法国已故比较文学学者伽列 (JMCarre)的话指出:“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
笔者以为,钱锺书的上述看法对误用或误解 “比较文学”方法的人均具有纠偏意义。显然,那些热衷于 “抽取表面相似的中外文学作品”、“为比较而比较”的所谓 “比较文学”学者,属于误用 “比较文学”方法的人;而那些将 “比较文学”研究等同于 “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的学者,则属于误解“比较文学”方法的人。不过,由于不少所谓 “比较文学”论文确实存在着 “牵强比附”、 “为比较而比较”等问题,因此,其他领域的学者对 “比较文学”学科有所误解和怀疑,也是不足为怪的。可以看出,钱锺书相当重视中外文学的异同分析,并将其视为 “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
而他所谓异同分析,实则包含两个层次,首先是初步区分出不同文学的相似处或相异处;然后是因同见异,即异求同,也就是从初步区分出的相似处看出差异,或从初步区分出的相异处看出共性。显然,中外文学的异同分析只有从第一层次推进到第二层次,其所得结论才是可靠的和有深度的。以中英古典诗歌比较为例,在韵律层面,可以拈出不少相异处,如中国诗讲平仄,英国诗讲轻重音;中国诗的 “停顿” (caesura)位置较固定,英国诗的 “停顿"位置较灵活,诸如此类。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相异处的背后存在着共性,即,它们都是服务于音韵和谐和便于吟诵这一美学目的的。显然,讲平仄或讲轻重音,“停顿”位置较固定或较灵活,只是中英古典诗歌的表面区别,而追求音韵和谐和便于吟诵,才是中英古典诗歌之普遍规律。
这表明,深层次的异同分析既能使 “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又能使人认清所谓 “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到底是 “枝叶”之异还是 “根本”之异。
需要说明的是,钱锺书在突出强调作为比较文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异同分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比较文学方法的 “多样性”。如他曾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的一次双边讨论会上指出:“比较文学,同时也必然比较比较文学学者,就是说,对照美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中国对等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他随后以肯定的语气反问道:“是否比较文学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呢?”
我们知道,比较文学曾有 “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之争,美国学派以韦勒克为代表,提倡以审美分析、价值判断为主旨的 “平行研究”,而法国学派则更注重建立在 “事实联系”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由于不少中国学者了承袭传统学术重 “实证”、重考据的学风,因此,他们在涉及到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走上了 “法国学派”的路子。
因此,考察 “美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 “中国对等学者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便至少可以区分出 “平行研究”和 “影响研究”这种研究类型,以及与此相应的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分析和中外文学关系的实证考察这两种研究方法。钱锺书一再指出,“学说有相冥契而非相受授者”。
这就意味着,在钱锺书看来,中外文学中某些相似处的存在是出于不谋而合 (“相冥契”),而未必是受到了某一方的影响 (“相受授”)。而平行研究即以中外文学中不谋而合的相似处为研究对象,影响研究则主要考察中外文学中存在渊源关系的相似处。这就意味着,无论是 “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无论是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分析还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实证考察,都离不开异同分析,因为,我们对中外文学中不谋而合处的揭示,实际上就是一个 “即异而见同,因同而见异”,进而总结出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即共同 “文心”的过程;而我们对中外文学渊源关系的考察,则必然应以对中外文学中相关文本的异同辨析为前提,否则,诸如异国之间 “相受授”双方的 “文学姻缘”,接受者的因袭与变异,以及因袭与变异背后的文化根源等等,均无从谈起。
除了对 “比较文学”的学术意义和基本方法作了一般性论述,钱锺书对如何发展中国 “比较文学”还有许多切实的建议,这对国内的 “比较文学”学者以及 “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理论”等领域中兼重中外文学与文论的研究者而言,始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重提钱锺书的有关论述,并根据新出现的材料而有所增益,大约不算多余之举。
钱锺书有一个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耳熟能详的观点,即, “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
钱锺书还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而 “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他指出,进行这项工作必须深入细致,不能望文生义。因为,同一术语在不同的人用起来含义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别分明,必然引起混乱。此外,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大多数是实践家,兼 “能作”与 “能评”于一身,因此,要了解其理论必须同时读其诗文。
显然,钱锺书早期的 “人化文评”说,可以视为 “比较诗学”领域内 “导夫先路”的重要成果。钱锺书指出, “人化文评”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 “特点”。所谓 “人化文评”,指的是 “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 (animism)”,也就是以 “气骨神脉”等等人体的 “机能和构造”来评论诗文。如刘勰 《文心雕龙·附会篇》所云:“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曹丕 《典论·论文》所云: “孔融体气高妙”,锺嵘 《诗品》所云:“陈思体骨气奇高,体被文质”,均是传统 “人化文评”中的显例。概而言之,传统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术语如 “气”、“骨”、“力”、“魄”、“神”、“脉”、“髓”、“文心”、 “句眼”等,作为 “人化”的诗学范畴或 “生命化名词”,均是 “人化文评”的体现。随后,钱锺书从 “西洋文评”里找出了若干带有 “人化”色彩的 “代表性例子”,并把它们 “分为三类”,而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 “人化现象”,作了 “由浅入深”的 “逐类辨析”,以指明西方文评中带有 “人化”色彩的术语或命题与中国传统文评中的 “人化现象”往往 “似是而非”、“貌同心异”。如法国文论家布封的 “风格即人”说,表面看来类似于 “人化文评”,但究其实质,两者存在着明显差异,因为,布封所谓 “人”,是指 “人格人品”,不过 《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见”一节的意见,并不指 “人身”人体。又如,罗马大雄辩家兼修辞学家西塞罗曾云:美有二种:“娇丽者”,“女美也”;“庄严者”,“男美也”。这无疑契合于中国传统文评中 “阴柔”“阳刚”之美的区分,但在各自所指的对象上又有所不同,因为,西塞罗 “根本是在讲人体美”,而并非说 “文章可分为阴柔阳刚”。
总之,通过对中西方文论或文评中类似现象的深入比勘和辨析,钱锺书既充分论证了 “人化文评”乃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又明确界定了 “人化文评”的内涵。如果说,钱锺书的 “人化文评”说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而言具有 “导夫先路”的意义,那么,其晚期的 《诗可以怨》一文,则堪称中西 “比较诗学”领域中的一篇具有典范性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钱锺书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和西方都认为最动人的诗是表现哀伤或痛苦的诗,很多诗人和理论家在说明这一点时不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语也常常巧合,这就指出了东西方诗学中一个根本性的规律。此外,钱锺书还认为:“语言比较也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大的部门”,并特别指出,他 “对此曾经花过心力。”
通观 《管锥编》,可以看出,钱锺书确实极为重视 “语言比较”。如 《管锥编》开篇之 《论易之三名》一则,即在论证 “一字”而 “融会相反两意”这一语言现象时,以古汉语中的 “易”字兼训 “不易”,“乱”字兼训 “治”,“废”字兼训 “置”,与德语中 “奥伏赫变(aufheben)”一词兼训 “灭绝”与 “保存”二义相对观,从而既推翻了黑格尔断言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依据,又显明了一字而 “融会相反两意”这一语言现象的普遍性。再如,为了说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钱锺书列举了十多位中外哲学家、文人 “责备语文”的观点 ,如黑格尔所谓 “语文宣示心蕴既过又不及”,尼采所谓 “语文乃为可落言诠之凡庸事物而设”,故 “开口便俗”,歌德所谓 “事物之真质殊性非笔舌能传”,陆机所谓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所谓 “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黄庭坚所谓 “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诸如此类。又如,为了表明中国诗家惯用之 “回鸾舞凤”格乃修词通例,钱锺书以古希腊修词学所谓 “丫叉句法”与之对观。
那么,钱锺书何以对 “语言比较”格外重视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对此进行分析:首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如试图从根本上把握文学活动的 “普遍规律”,便无法绕过语言研究,尤其是对语言特性、语言现象 (包括修词现象)的比较研究,而钱锺书的基本学术旨趣即在于抉发东西方共同的 “文心”、 “诗心”,因此,他主张 “语言比较”应为“比较文学”一大 “部门”并为之付出 “心力”,便是很自然的事;其次,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这种 “转向”亦波及到了文学研究,而钱锺书对西方现代学术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理论一向感知敏锐,因此,他对语言研究及 “语言比较”的格外重视,也很可能和 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的 “语言学转向”有着一定的关联性。
综括而言,在钱锺书看来,“清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相互阐发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术语”,“语言比较”乃是中国 “比较文学”发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务。事实上,这三项任务对发展中国的 “外国文学”研究,“古代文论”研究以及 “文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