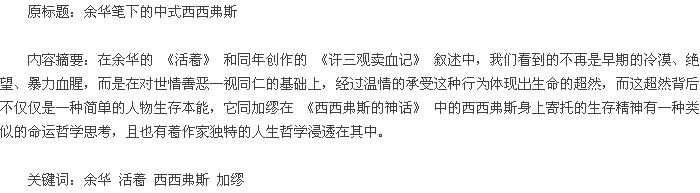
一、 《西西弗斯的神话》 和《活着》 文本概况
《西西弗斯的神话》 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一部哲学随笔集,原书的副题是“论荒缪”.其中西西弗斯的形象是一个各个身体部位都高度紧张,十分吃力的在一个陡坡上推动巨石移动的健硕而又伤痕累累的人,他的目标看似很坚定,然而当把巨石推上顶峰之后,又重新陷入了命运的轮回:
巨石还会从他的手中滑落,滚到谷底。这种以永罚的形式存在的永无休止,不仅是展现出这个世界的荒诞,更体现了处于荒诞世界的生命个体的自我选择,荒缪不存在于人之中,也不存在个人身上,存在人与世界的共同作用之中。西西弗斯是甘愿一次次的承担这种命运的荒谬的,在被压制的状态下,他懂得在每片尘土,每粒细碎石屑上用自己的力量使巨石每次移动时所呈现的不同的有着微妙差异的生命状态。
《活着》 中的富贵先是败掉了祖宗遗留下来的的所有财产地契,从赌嫖豪奢的行为过渡到家穷四壁,为生计发愁,接下来便是无穷无尽的死亡接力:父亲终在无法释怀的变故后死在茅厕上、母亲穷困中染病死去、懂事而又天真的有庆在帮助他人时献血过度而死、哑巴凤霞在嫁了好人家开始幸福的时候因难产而死去、贤妻贾珍在最后的精神稻草凤霞死去后也步入黄泉、而女婿二喜在工地上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以致再无法拉扯自己的孩子苦根、最后由于贪吃豆子这种平时少吃的食物苦根也离富贵而去,最后只剩下与富贵一样老的黄牛作伴,继续安详地在农田里耕种,停停歇歇。作家使文本中环绕在主人公周围的角色一个个死去,在初读时觉得这是作家有意而为之来表现生命中的大悲苦,这种偶然性极高的死亡突发事件罗列起来,是为了阐释一个主题:生之艰难。富贵的苟活也被这样不负责任的读者定义为麻木的活着,被痛苦侵袭习惯之后的坦然。然而随着对文本的深入,会发现曾经的阅读体验会被认知基础上的一些形而上的一些思想推翻。余华的 《活着》 和 《许三观卖血记》 都是简洁凝练的短篇,然而被叙述的故事的结构及其故事本身给人无限的绵延之感,这种绵延之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于生命哲学的表述与思考。人作为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从生命之始的个体性,慢慢衍化到群体性,然而最后又会在这条路上回归生命的本真:个体性。因此余华的众多死亡叙述不是为了表现弗洛伊德似的“死亡本能”,虽然余华在自己的死亡叙述中表现了有机体从生机勃勃走向最终的无机状态,但是叙述中的死亡个体自身并没有带着对这个世界其他个体甚至对自身的毁坏冲动与冲击本能,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反倒是像加缪的 《西西弗斯的神话》 中的西西弗斯一样,得出了类似的生命结论:现实的“荒诞”是人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人是这个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绝现存世界,却又不愿离开它,反而为不能更多地占有它而痛苦。”
二、富贵和西西弗斯生命哲学的相通之处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富贵和西西弗斯都在以痛苦而又清醒的方式咀嚼生命,看清了痛苦也看清了幸福。富贵在一生中都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推动着命运给予自己的每次重压---每次亲人的死亡;他也像西西弗斯一样有过在征服山顶时片刻的欢愉---家珍并不嫌弃富贵的现状带徐有庆回家、富贵在经历战争的浩劫后幸存回到家乡与心心念念的家人重聚、不会说话的凤霞也嫁给了一个老实的城里人,像普通女孩子一样过上了向往中的婚姻生活。这种经历不断逝去的死亡苦痛与现存的偶尔零星幸福相互穿插,相互交织,构成了富贵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富贵不同于一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是被历史大潮流推动着向前的所有平凡人中的缩影。这些“小人物”在生命的历程中,没有侧重描写其外在的政治环境与历史现象,也没有具体描绘富贵在度过每段生命困境具体的生命体验,他只是在以自己认为最自然的方式生活着,经历着,承受者。在这里叙述的富贵与西西弗斯很大的相同之处是在于二者处于相同的苦难循环中:我们总要解决无尽的苦恼,在看似解决了的背后,其实下一个烦恼正在逼近。对于苦难的态度:都忠于自己的生活选择,因此在为自己的选择基础上的现实承担责任。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破裂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就应该是幸福的。两个主人公都在生命的流逝中学会去接受自己的命运,富贵是在安详的晚年中和耕种的老牛共同生活,这份生活带着对过去所有苦痛以及也是最大的幸福残留的记忆:老牛拥有多重身份、多个名字:家珍、有庆、凤霞、二喜、苦根,同时也带着对未来前途的无期待亦不完全冷漠的态度,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本身。活着本身已经需要太多的精力力气,这对一个饱受苦难的孤寡、暮年人来说会更加懂得生存的含义。最初以为生命追求的是激情与崇高,在阅历增加,泪流使皱纹的沟壑布满脸庞时才知道,生命的琴键之音应该降低、降低。从相似的创作 《许三观卖血记》 里同样可以领略生命的这个哲学:生命的重压,使生命的符号---血液从人本身剥离,但是精神上的忍受---活着本身是人本身最具有韧性的展示。活着不是没有绿洲的荒漠,也不是一片蓝色的汪洋,活着本身就让主人公获得了充实。为了寻找理由而活着,一致认为是一种活着的理想状态,但这种生命状态在中国的余华和法国的加缪笔下都得到了相应的否定,以虚构的文学文本 (余华自身对这个故事的虚构性也做了否定,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时,我忍不住会去怀疑自己真实的现实是否正在被解构) 和相应的荒诞理论做了指向:“我看到有些人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或幻想而丢掉了性命。所谓活着的理由,也就是死的极佳理由。”西西弗斯的韧性以一种更为乐观,享受处境的态度展示,由于文化语境不同,作者或者后人的阐释不同,所以与我们在余华笔下看到的主人公富贵、许三观在相同之中又有着众多差异。
三、二者不同的文化语境造就的不同生存解读
西西弗斯不仅是在苦难中承受重压的人,他的承受自身就在进行一种捍卫尊严的反抗。就如加缪以西西弗斯为例所解读的荒诞那样:荒诞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把他贬压,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权利都全部给他了“.西西弗斯他在浑身沾满泥土,伤痕累累的状况之下,在把脚下经过的每片土地,每颗土粒当做自己欣赏、征服的世界的同时,这种表面上的妥协已经暗自向一种最大的反抗转化。永无止境的困境中永不停下的脚步,活在自己的激情世界,是对永罚的幻化。加缪的”荒诞原理“将面对荒诞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生理上的自杀,二是哲学上的自杀,三是反抗。
第三种态度反抗中的激情是对西西弗斯的评价,因为西西弗斯拥有现在与种种现在之延续的不断的意识,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并且最后以超越精神成了人道主义的象征。对于余华的《活着》 的主人公富贵则不同,许多人认为富贵对于生命采取的态度过于消极,过去的经历使富贵麻木了,这实则是未被作者的创作初衷的。在用加缪的理论和西西弗斯作比较时,发现富贵的生命哲学也较符合加缪的”荒诞理论“,荒诞的三种结果:我的自由即是指一种摆脱除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事物的自由体验,这是一种对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毫无责任的感觉。这种自由符合富贵最终作为活着本身的活着,它不是在”自由“的名义下美化悲观厌世的哲学,是一种接近于非理性状态下的,在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小人物“的主观生存动机。在中国博大沉稳的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是以这种生存状态在活着的。生活的众多波澜对于一个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以致毫无反抗力量的家庭是致命的打击,但最终都在风雨中继续飘摇。生活还是要继续的,生存中的重压并不比所有的死亡都来得更容易,更为轻松的让人接受。生活中不缺乏扼住命运之喉、在苦难之还游弋的勇士伟人,而组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是那些甘于默默承受的人,以缓慢的步伐行走在人类的历史中,走向自己最终的目的地。
富贵和西西弗斯以及类似于他们的文学形象,沉淀着创造者赋予他们无限的精神力量与生命之思。与人类历史和存在没有任何固定意义或目的,却仍然在这个荒谬世界中从事活动问题的人对话,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先见与启迪。
参考文献:
[1] 余华: 《活着》, 《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5月
[2]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 《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1日
[3]加缪: 《西西弗斯神话》,张清、刘凌飞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3年1 月1日
[4]唐虹: 《传承与超越---余华小说中的存在主义意识审视》, 《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12月第10卷第6期
[5]白雪: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先锋性》, 《内蒙古师范大学同等学力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7月
通过对两部作品中生命意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见海明威和余华在对待生命和死亡时态度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