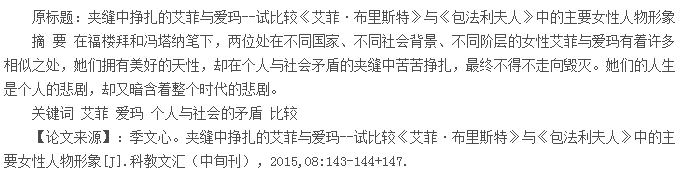
19 世纪中期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作家福楼拜完成了他最具批判性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轰动了当时的法国文坛,塑造了极富魅力的女性人物形象---爱玛。而 19 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在《包法利夫人》的影响下,德国作家冯塔纳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艾菲·布里斯特》,同样"小说女主人公艾菲这一形象可以列入世界文学最优美的女性人物之列。"[1]
这两位女性都拥有美好的天性,然而她们的悲剧命运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本文试从她们的个性、爱情观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分析两位女性人物形象。
1 艾菲与爱玛的个性比较
《艾菲·布里斯特》和《包法利夫人》都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主人公艾菲是个美丽纯情的女孩,出生于普鲁士容克的贵族家庭,17 岁那年她嫁给了 40 岁的殷士台顿男爵,他是凯幸县县长,也是她母亲的旧情人。然而,婚后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殷士台顿忙于公务,忽视了对妻子的关心,艾菲受到了花花公子克拉姆巴斯的引诱与他发生了婚外情,6 年后殷士台顿知道了妻子的隐情,选择与她离婚。而艾菲最终在柏林孤独地死去。
小说中艾菲的个性首先体现在她自然率真的天性上,艾菲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她自己也认为"可是我……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永远像个孩子".[2]
连孩童玩耍的秋千也让她着迷。艾菲好玩乐,爱幻想,对万事万物极具好奇心和新鲜感,无法忍受枯燥无聊的生活。她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总得换换花样,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目标,她并不了解爱情,对感情的期待也只是变换花样。艾菲另一个个性特点则是爱慕虚荣。她并没有爱上殷士台顿,甚至对殷士台顿说出了自己与他结婚的真实原因。"你根本不了解,我是多么热爱名誉和地位。老实说,我所以肯和你结婚,也完全是出于热爱名誉和地位。"[2]
艾菲出身下层贵族,受其家庭影响使得她对上层贵族的生活十分渴慕,于是她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殷士台顿。
《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富裕农家姑娘艾玛深受父亲疼爱,曾被送去修道院接受过良好教育。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可是她的两度偷情非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却使她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积债如山,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尽。
爱玛同艾菲一样也是天真可爱的,小说中也描述她"有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情".
但在爱玛身上更能看到一种艺术情结。这种艺术情结是少女时期的爱玛在修道院形成的,爱玛十五岁时就迷恋上了当时的消极浪漫主义小说,"书上写的,无非是两情相悦,情男情女,……躁动的心,山盟海誓,哭哭啼啼,眼泪与吻,月下扁舟,林中夜莺……"[3]
受小说的熏染,爱玛逐渐养成了多愁善感的个性,以及对艺术化生活的追求。爱玛也是爱慕虚荣的,只不过这种虚荣心一方面是出身农家的爱玛对贵族生活的深深向往,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浪漫小说的影响。有幸参加舞会的爱玛终于见证了小说中的贵族生活,她居然对舞会中的一个糟老头不禁敬佩,"人家可是在王宫里待过,而且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啊!"[3]
爱玛身上另一个特点就是她的独立人格。爱玛有着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愿望,这种反抗意识体现在她对爱情生活无休止的追求,既然在夏尔身上找不到感情的共鸣,就可以去找其他男子。
可以说在个性上,艾菲和爱玛是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她们天真美丽,爱好幻想,性情不太稳定,但情感世界却异常丰富,她们不堪忍受枯燥的家庭生活,渴望生活的激情,又爱慕虚荣。她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艾菲是个有着孩子般自然天性的女性,愿意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爱玛则是有着艺术气息、浪漫却有着种种欲望的女人,这些欲望激发了她对生活的无穷想象与渴望,也使得她对爱情执着追求,极力把幻想变为现实,不断冲破道德的屏障。爱玛的这种独立人格在艾菲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艾菲较爱玛更为安分守己,更为软弱,她对爱情没有强烈的追求,对社会的不公也没有去反抗,艾菲在临死前原谅了殷士台顿,说明了她对普鲁士社会和道德规范无意识的维护与认同。
2 艾菲与爱玛的爱情观比较
艾菲和爱玛的个性影响着她们的爱情观。如前文所述,艾菲嫁给殷士台顿是因为虚荣,而"她自己对爱情并没有多少感受"[2],充其量是读到报刊上的爱情文章,以及从好姐妹荷尔达那儿听来的,这样也就使得艾菲对接下来面临的婚姻生活并无多少准备。冯布里斯特夫人也预言到"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她那种贪图享乐和喜欢冒险的脾气是不是也得到满足了呢?……殷士台顿很不善于使一个热情奔放的小丫头一天里面获得几小时的娱乐和消遣,不善于使她战胜她的死敌---无聊。"[2]
婚姻生活确实没有满足艾菲的全部需要,"因为她朦朦胧胧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并不美满,实际生活中还缺少殷勤、激情和无微不至的关心。"[2]而殷士台顿也未注意妻子的感受,而是忙于公务,此时懂得女人心的克拉巴姆斯出现了,在一次郊游中,克拉巴姆斯说道:"生活的乐趣在于不断地变化口味。"[2]
这正是艾菲梦寐以求的生活目标。于是在克拉巴姆斯的引诱下,艾菲跨越了道德的界限,然而她对克拉巴姆斯并无爱意,只能说是她的自然天性对于新奇事物的好奇,以及不能忍受生活的无聊而已。爱玛的爱情生活则比艾菲复杂许多,其中爱玛的艺术情结起到了重要作用。爱玛认为":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无所不知,多才多艺,启迪你领会激情的力量,生活的情趣和种种奥妙吗?"[3]
然而毫无情趣的夏尔只带给爱玛平静的生活,却无法欣赏她作的画、弹的曲、唱的情歌,爱玛对艺术化生活的种种追求在真实生活中处处碰壁,她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天啊,我干吗要结婚?"[3]此时莱昂出现了,他同爱玛一样爱读小说和诗歌,而且多才多艺,至于对莱昂的感情",她并不想知道自己是否爱他。在她想来,爱情应当骤然来临,电光闪闪,光彩夺目……把整个心儿带往深渊。"[3]
正是对小说中轰轰烈烈爱情的向往,爱玛"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发生什么事情。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寂寞的生活中搜寻".[3]于是与莱昂擦出了爱的火花。后来爱玛爱上鲁道夫也是因为他身上散发的味道让爱玛想起了那次宴会上的子爵,而他的甜言蜜语也与小说中的贵族男子相仿。沦为鲁道夫的情妇后,爱玛不禁心花怒放":我有情人啦!我有情人啦!"[3]因为在爱玛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贵妇都有情人!
艾菲和爱玛都对婚姻生活的激情和乐趣充满了向往,却又都没有从各自的丈夫那里得到满足。于是爱玛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找她的激情,艾菲则被动地接受了旁人带给她的激情。爱玛沉浸在激情的欢愉中不能自拔,艾菲却因承担不了激情的后果而终日惶恐。
爱玛受修道院教育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她的爱恋是带有虚幻性质、朦胧性质的。她厌恶夏尔的平庸,子爵的形象实际上是爱玛渴慕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物。
她之后的爱恋对象不管是莱昂还是鲁道夫无一例外地都具有消极浪漫小说中贵族男主人公的特征,满足了她自己的艺术情结对于爱情的种种幻想。爱玛同情人的爱更多的是想让自己的浪漫幻想和满腔激情有所寄托,然而俗不可耐的男性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她的幻想。
艾菲的爱则是简单的,她甚至还不明白爱的含义,她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努力按照社会要求生活,她并不厌恶自己的丈夫,甚至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然而她还是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她要的只是符合她天性的激情与乐趣,然而这在枯燥压抑的凯辛县却无法实现,于是天性压倒了理智,被克拉巴姆斯引诱,她的行为一时满足了她内心的愿望和对激情的追求,然而对婚姻的不忠并没有使她获得任何幸福或精神上的安慰和自由,恰恰相反,罪过和自责一直重压在她心头。
3 艾菲与爱玛所处的社会环境比较
艾菲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前后,即小说是以具体的普鲁士国家机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及精神文化为背景的。"18 世纪时普鲁士国王有意识以训练军队的方法培养官员的职业道德,把军队中服从、尽职、节俭、准确的作风渗透到国家岗位上。"[4]
无疑殷士台顿这个人物可作为普鲁士社会文化的代表。殷士台顿的理智、克制、原则性与艾菲的自然随性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婚姻的矛盾。艾菲曾对妈妈说道:"殷士台顿始终是个出色的男子……他身上总有一点叫我感到陌生的东西,连他对我的温存体贴也有这种成分。……有时候我还感到害怕。"[2]可以说这种陌生的东西则是普鲁士道德规范在殷士台顿身上打下的烙印。
除了要求基本一些品质和素养外,普鲁士官僚制度还要求官员注重国家和整体利益。"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不仅是单独的个人,他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我们得时时顾及这个整体的利益,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它而独立存在。"[2]从决斗前殷士台顿与维勒斯多夫关于整体和个人关系的谈话中可看出,维护整体利益和个人荣誉是普鲁士国家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中,只有国家的幸福才是个人的幸福。"然而扞卫名誉崇拜的殷士台顿也终究成了荣誉的牺牲品,在与艾菲离婚以后,"他感到极为痛苦:世界上确有幸福这个东西,他过去曾经有过,而今他已经没有了,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再有。"[2]
小说中爱玛所处的时代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法国处于政治平稳时期,工商业有了较迅速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追求落到了物质层面上。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才可能生活得有滋有味,比如药剂师奥梅先生,全书最后一句写道:"他新近获得了荣誉十字勋章。"[3]不得不说是对资本主义庸俗生活的巨大讽刺。
如果爱玛的艺术情结符合真实的生活,最终悲剧自然不会发生。但遗憾的是,爱玛周围的环境是封闭平庸而又恶浊麻木的,独有她留恋精神的云端。当然爱玛的艺术情节中含有消极意义---即对享乐糜烂生活的向往,但是修道院教育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整体已经被金钱和物欲腐蚀得俗不可耐。
可以说爱玛的死,是对突如其来的真相没有足够的准备,她不是因为受到良心的谴责,忏悔赎罪,而是所有外力加在一起,这些外力就包括勒赫先生的威逼,爱玛接受了勒赫的谄媚与贷款,却看不透他的险恶用心。更深层次地说是一切以利益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把爱玛推向了绝路。
从这两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人生活的。女性们一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遵守社会规则,另一方面自然的天性也无法泯灭。艾菲是率真自然的,却在以崇尚责任、父权、义务和个人荣誉的 19 世纪德国社会中压抑自己的自然天性;爱玛是有艺术气息而浪漫的,却在 19 世纪资本主义金钱当道的法国苦苦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两位女性的美好天性与社会的严酷性构成了反讽。
4 结语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都是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冷漠和她们所处社会扼杀人性的本质。自然天性与社会规范的矛盾、艺术化生活与庸俗社会的矛盾在两位女性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们时时处于一种夹缝状态,她们的人性、情感和生理需求在压抑心灵的社会中不仅得不到满足,甚至遭到破坏和毁灭。可以说艾菲与爱玛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余匡复。德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 (德)冯塔纳。艾菲·布里斯特[M].韩世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3] (法)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钱治安,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4] 谷裕。试析冯塔纳小说的疑难结构[J].外国文学评论,2003(4)。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俄狄浦斯因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被抛弃,他试图逃离命运却被命运之神一步步牵引入命运的圈套,最终通过刺瞎双眼,流亡国外来赎罪。《海边的卡夫卡》中15岁主人公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
虽然安娜与早月叶子都是高举“女性意识”和“自我抗争”大旗的先驱女性, 但她们始终都没有脱离过女性的从属地位———从属着家庭, 从属着婚姻, 从属着男性的经济———从来没有独立地进行过彻底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