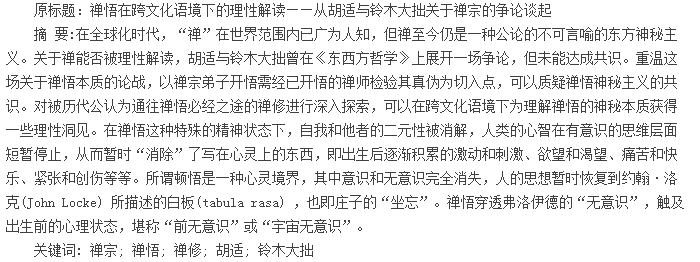
“禅”,一个过去只为中国人和亚洲人所知晓的词汇,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已广为人知。自20 世纪初以来,禅在世界各地备受瞩目,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从哲学家、心理学家、宗教领袖到科学家及各个领域的专家,甚至还有普通百姓; 同时,除中国和日本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在修禅。
禅甚至对西方人的生活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一家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则趣闻轶事: 一些禅修者声称,当他们集中修禅时,华盛顿的犯罪率竟然急剧下降了。
尽管当今的“禅学热”要归功于诸如卡尔·荣格(Carl Jung)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 、埃里克 · 弗洛姆 (Erich Fromm) 、卡伦 · 霍妮 (Karen Horney) 、麦斯特 · 埃克哈特(Meister Eckart) 、爱伦·沃茨(Allan Watts) 、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 、梅尔福特·斯皮罗(Melford Spiro)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等世界级思想家、学者及艺术家的推广,但我们必须承认,禅学在西方最初引起关注是西方公认的最伟大的禅学家———铃木大拙的功劳,他倾尽其毕生之力成就了禅的普及,以至于“禅学热”在西方曾被称为“铃木效应”。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铃木一生虽然不断在向世界宣扬禅,但他始终坚持认为,禅是理性和智力所不能把握的。至于禅悟———禅修的核心,同时也是禅修的终极目标,铃木则在其著作和演讲中反复强调,人的理智完全捉摸不透它; 它的非逻辑性、非理性,使其“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而他这种论断在 20 世纪被大多数思想家所普遍接受,荣格就曾说,禅悟是“一门艺术和一种开悟的方式,欧洲人几乎不可能领会”。荣格似乎生怕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他进而赞同另外一个日本学者的观点,即: “任何企图解释或分析禅为何物,开悟为何物的行为皆是徒劳。”
弗洛姆尽管不同意荣格的那种带有族群中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完全附和铃木的看法,认为开悟是一种绝不能通过智力传达的体验,“这种体验再怎么解释和论证也无法传达给别人,除非那人之前就有类似的感受。如果开悟能够通过某种解析,从而让那些从没有过类似体验的人也能对其有所体会,那么,开悟便不能称之为开悟了。因为这样的话,开悟将脱离自身的概念,不再成为禅修的一部分。”
另外,他还表明: “我未曾开悟过,也就只能肤浅地谈论禅,而非以应有的、出自完全体验的方式来谈论。”
此类被诸多学者所接纳之有关禅的理念,看似言之凿凿,却无法使我们深信不疑。例如,梦在人们看来也是不符逻辑和不合理性的,但是弗洛伊德的解析,有力地证明了梦境能够被人的理智所洞察,能够通过符合逻辑和理性的语言来解释。铃木坚持认为禅悟须出自亲身体验的观点固然可以接受,但过于强调个人体验似乎暗示了禅将会永远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修行者才能开悟(即使在现在的日本,也只有极少数人被认为实现了心灵之顿悟) 。此外,当个人体验被不恰当地过度强调时,就相当于认为一位精神分析师无法完全理解神经症、癔症或精神错乱,除非他自己也深受其害。我们的意思是,那些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人类理智能力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在医学界,一个医生不必患上某种疾病后,才能了解和描述其性质。
由于这种不可知论的观点一直是主流,所以对于禅,尽管对其西方有大量的研究和强烈的兴趣,但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学者自身,禅至今仍是不折不扣的一种不可言喻、且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东西。与禅有关联的描述总是“秘传的”、“不可言喻的”、“异国情调的”、“神秘的”和“奇异的”等语词。荣格对修禅初学者的忠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从一开始就深深浸染在充满异国情调的朦胧的禅学轶事中,并始终牢记顿悟是神秘的、不可言传的,就像禅学大师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其就禅悟和西方神秘主义体验所作之比较研究,是加强而非解开了禅的神秘性。亨利克·杜姆林是西方最先研究禅学的学者之一,他苦心孤诣地写了整整一本以禅悟为主题的书后,在“后记”中自嘲似的写道: “禅是修行,是体验,是生活———无须解释、说明、研究或者诡辩。正如中国古代的大师们所言,所有的言论最多也就是指月之手指罢了,手指不是月亮,无法将月亮摘下来。”
这些观点显然与铃木的毕生信念相契合。
然而,这些公认的观点却无法使人信服,因为它们似乎都违背了禅修进程中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即当一个禅宗弟子开悟后,他(她) 会被自己的师父反复盘问以证实是否确实开悟。如果一个人能够证明他人的顿悟是否为真,那么这就表明禅悟是能够通过理性和智力来理解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那种公认的观点是站在不可知论的立场上所发表的,它完全否认了人类主体之间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而本文试图重温胡适与铃木大拙关于禅悟本质的论战,质疑禅悟神秘主义的观点。我们将对古老的禅修,这种被历代公认为通往禅悟的必经之途进行深入探索,以图在理解禅悟的神秘本质方面获得一些理性洞见。
再议胡适与铃木之争1953 年 4 月,胡适,这位享有盛誉的中国学者,同时亦为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学生,与铃木大拙在《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 上就“禅悟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辩论的主题一句话即可概括: “禅悟可以被理性解读吗?”尽管二者的争辩最终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却影响了了后世学者们对禅的理解及研究禅的路径,所以,此次争论对我们理解禅仍然有着深刻的意义。胡适与铃木都是此领域的权威人物,胡适曾是使用敦煌写本研究禅宗佛教的先驱者,而铃木的声望足以影响西方世界对禅的理解,所谓的“铃木效应”正是基于此。
尽管铃木执著地推动对禅的研究,但至死,他仍持有禅既不属于宗教也不属于哲学的观念; 认为禅既无逻辑又非理性、超越了人类的智识理解的极限,“如果我们拿常识的观点去判断禅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它的基础在我们的脚下坍塌。我们所谓的唯理主义思维方法,在衡量禅的真伪方面,显然是毫无用处的。禅完全超越我们理解的极限之外。因此,我们对于禅所能说明的只是: 它的特点在于它的非理性或者说是非我们逻辑理解所到之处。”
铃木否定人类具有理解及鉴估禅宗的智能,这一点是胡适不能接受的。于是,他直接反驳铃木的不可知论,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 “禅学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国佛教史又是中国一般思想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只有把禅放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这与中国哲学其他任何宗派一样,都必须放到它的历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才行。”
胡适采用这种充满强烈的历史观的研究方法,着手对禅宗进行研究,并得出了结论: 禅宗是从一个开端开始的,此开端“只不过是中国人在佛教内部的改革或革命”;而且,禅宗的修行路径是一种“亦即让学者透过他自身的努力和逐渐扩大的生活体验去发现事物的实相”的授导手段。
对于胡适的否定,铃木立刻反唇相讥,他针对胡适从历史学角度来研究禅的方法提出异议,认为禅学乃历史学家研究所不能企及的领域。另外,他还提出,在与禅直观相对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心理: “第一种能够了解禅,因此有权对它做一些谈论; 另一种则完全不能领会禅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分别是本质的差别,因此没有调和的可能性。”尤其是,他明确地表达出这样的观念: “就我的意见看来,胡适代表着第二种心态,还没有适当的资格来就禅论禅。对禅的了解,应该抛开历史因素,从内部去了解,而不能从外部。”
60 年后,我们重温这次意义非凡的争论,不得不说,两位学者的论点皆有其有根据及有价值的地方,但二者的观点又不完全正确。排除铃木那显而易见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那不可知论的观点就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仅从智性分析,是不能解释禅的。由于智性是关于语言文字与观念的,它永远不能接触到禅。”
事实上,若真如铃木自己所言,那么,我们便可试问: 他写了这么多关于禅学的著作,难道不是用语言文字来解释禅学吗? 这么说来,那铃木倾尽毕生精力来解释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可将他的论点简述为一种循环论证: “禅即禅,知则知矣,不知则为不知。”尽管如此,支撑其第二个观念的要素却可言之凿凿地表述成: “我坚持认为,禅必须先从内部来领会,只有在获得过这种体验之后,才可以像胡适那般,去研究禅的历史外观。”与胡适历史学的方法相比,铃木所认同的“禅应从内部而不是外部去了解”的观点确实有根有据。事实上,胡适与铃木对禅学的解释各持一端,如同二人各自握着一个棍子的两端,彼此相持不下,而这个棍子代表着禅宗阐释学的过程。我们若冒昧地将禅学比作一个文学文本,那么胡适的历史学方法就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对其来龙去脉的解释,这是表层意义上的; 而铃木的研究可以被视为旨在挖掘文本含义内部途径。历史学的方法能够解释内容的前后关系,但不通过对细节的把握,深层含义就不能够显现出来; 深层研究能够深入文本,但少了上下文的关系,就很有可能走入死胡同。诚如美国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所言: “意义包含在语境中,而意义的语境却是无限的。”
值得肯定的是,铃木一再强调: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禅本身是什么,就必须从内部去掌握它。”
但其内部研究的方法,却因其认同禅超越文字,不受智力支配的理念控制的不可知论观点而显得不很严谨。诚如他自己所言: “严格意义上来说,世上不可能有‘如如’哲学,因为‘如如’无法用截然无误的言辞作为一种观念的定义。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观念来了解时,就失去了它; 它变成了一个影子,而任何建立在此之上的哲学都将成为空中楼阁。‘如如’或‘只这是’是一种个人必须自己从内在去体验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妨说,只有具有此种体验的人,才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暂时性的思想体系。然而,有这样心灵的人,往往宁愿沉默,而不喜欢言谈或用智性化的符号去表现。他们不想去冒被人误解的危险,因为他们知道,指月之指极易被认作所指之月。”反之,他让我们满足于“就是如此,除了‘只为如此’仅此而已”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禅恰恰就是禅本身,你要么体悟到了它,要么没有。”铃木在禅学入门中提到,他学习几个世纪以来禅学大师们的做法,即: 要么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谈论禅,要么采用隐喻性的话语,譬如“指月之指”、“石壁栽花”、“无底篮子拾菜”。
铃木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也不是一种内在理解的路径,至少不够彻底。下面,我们不妨将禅学比作一个黑匣子,胡适只顾向我们展示盒子是如何出现在那儿的,而铃木关心的则是描述盒子看上去如何。但二者都未曾打开盒子,窥探其中奥秘,并传达出他们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什么。而且,他们都有不打开盒子探视的理由,在胡适看来,只要描述了盒子出现在那儿的方式,人们就能推测盒子里面的内容; 而铃木则认为打开盒子这件事压根就不在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所以,二者的方式都无益于对禅悟的理解。
从禅修实践来理解开悟我们希望表明,人们能够通过智性活动达到对禅的领悟,禅学也可通过理念和观点来传达。除却本身所代表的含义,理念和观点的确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一种形式,但它们就好比是“指月之指”。是的,“指月之指”不是月亮,也不能将月亮摘下来; 但它作为一种指引,能准确无误地向另一个人表明月亮的所在之处,而古老的禅修就充当了这样一个指引的作用。既然从概念层面去探讨禅学原理又将是个长篇大论,在此,我们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仅梳理历来人们如何通过禅修达到开悟,而这种梳理有便于我们破解禅悟的本质。
禅宗与印度本土佛教不同,这体现在禅宗将修行作为主要信条。“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四句短语相互联系,完美地诠释了禅悟的过程,它们不仅构成了禅宗的教义,更为禅修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指导方法。可是,为何禅宗摒弃了语言这个途径呢?
诚如现代思想家所言,那是因为,语言使人远离本我。例如,尼采就有把语言比作“牢笼”的著名论断。海德格尔也曾表示,并非是人类用语言来诉说,而是语言诉说着人类,因为是语言使人及整个人类社会成为了有意识的存在。拉康则认为,人类已然是语言和话语的附庸,因为语言先于主体,并为主体思考,从而使有意识的自我区别于无意识的自我。
这种语言本质观是对存在进行探讨的中心命题,是西方的思想家通过繁琐的哲学探索才艰难获得的洞见。但这种观念在东方却并不稀奇,尤其是常见于禅师们的授导和修行中。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对语言本质的这种理解,禅宗便不注重创立教义、传授教义、刻苦读经这些行为。尽管如此,禅宗还是认为使用语言是一件不得已的坏事,由此设计出一系列旨在摒除语言干扰,寻找真我与非我的无中介联系,并最终能达到开悟目的的修行方式。以下三种就被推崇备至: (1) 坐禅; (2) 公案; (3) 问答。历史记录显示,这其中每一种方法都曾成功地帮助修行者达到了心灵的顿悟。
1. 坐禅: 一种自我启动的通往开悟的方法。坐禅采用一种叫做莲花坐的坐姿,这种姿势要求修行者将双腿弯曲交叉于臀部之下,紧闭双眼,两手互相握住,排除脑海中所有杂念。在威廉·詹姆斯著名观点中,大脑以意识流的方式运作,这样就几乎不可能完全摒弃所有意识思维。六祖慧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 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
但他在得出与现代意识流观念相同的认识之后找出了通向禅悟的康庄大道: 开悟的关键是无念,即通过真正地切断意识流来达到心灵的虚空: “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 即是法缚……。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他把无念的状态也看作是一种新生: “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
如何才能达到心灵的虚空? 为此,禅师建议修行者要从内部凝视肚脐的方向或注视眼睛合上时隐现的微光。我们大胆地推断,坐禅中的这些细节旨在模仿胎儿在子宫中的存在。任何看过胎儿在子宫中生活图片的人,都不难注意到所描绘的坐禅的姿势和胎儿的姿势的相似。
胎儿悬浮在子宫中,双眼紧闭,双手互相靠近,双脚交叉接近莲花坐的姿势。当我们看到连着婴儿肚脐的脐带,就不难想到为什么坐禅者在脑海中要凝视自己的肚脐。肚脐是切断脐带后留下的伤疤,在子宫里,脐带是连接胎儿和母亲的生命线。它为胎儿输送营养,帮其排泄废物。
如果在子宫中胎儿能够感觉到什么,首先一定是脐带。肚脐是在婴儿生命中创伤性事件(即出生和与子宫分离) 的遗留物。凝视肚脐,有没有可能是禅宗的先驱们在直觉上认识到,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脐带的遗留物上,人们可以退回到宁静的精神状态,引起回到失乐园的幻觉呢? 至于清空脑海中有意识思想的要求,子宫里的胎儿不具备有意识的思维,有的只是感觉和可能的知觉。对于一个打算达到胎儿般安宁的精神状态的人,当然绝对必要摆脱任何有意识的思维。可问题在于,有意识的思维几乎不可能摆脱。如果有人一旦成功地摆脱了有意识的思维,他已处于开悟的边缘,或者已经实现了顿悟。
一般认为,禅来自于印度,但坐禅冥思可能并不单单起源于印度。因为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式的冥思早已存在,被称为“坐忘”,这在据说是孔子和他的学生颜回之间的对话中有详细记载:颜回曰: “回益矣。”仲尼曰: “何谓也?”曰: “回忘仁义矣。”曰: “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 “回益矣。”曰: “何谓也?”曰: “回忘礼乐矣。”曰: “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 “回益矣。”曰: “何谓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 “何谓坐忘?”颜回曰: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 “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 丘也请从而后也。”
这段对话来自《庄子》内篇,学者皆已认定此为庄子(公元前 369 - 前 286) 本人所著。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冥思的行为便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远在普遍认可的佛教最初传到中国的时间(公元 1 世纪) 之前。在此,我们不想争论坐禅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中国,我们的目的在于表示: (1) 庄子所描绘的坐忘与禅宗的开悟是如出一辙的: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禅宗开悟的主要特征; (2) 坐忘是很难获得的精神状态,甚至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心甘情愿地拜自己开悟的学生为师; (3) 如果坐禅最早的渊源来自两个不同的、独立的文化传统,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因此它一定首先起源于古代大师们对回归本源(即子宫) 的人类无意识欲望的直觉的感受。这点也许证明了我们的推测: 冥想最初是由模仿胎儿的心理状态而来的。
禅宗的许多理念与道家思想并无多大本质性差异。有一本道教书籍《光之轮: 金花的体验》提出了类似坐禅的技巧: 端坐,调整呼吸,减少感官活动,全神贯注于内心,凝视肚脐等等———这一切都在于模仿胎儿的存在状态。在该书的一节中,修炼所谓内丹的技术与那种无意识的欲望,即希望回归到未受打扰的平静和安宁的最原始状态,其相似之处是如此异乎寻常。正如日本学者黙仙目幸(Mokusen Miyuki) 在一篇道教研究文章中指出的: “在内丹理论所述的‘打坐’练习中,一个人所有的心理能量被转向内部,聚焦于个性最深处的核心,即自我。
这被象征性地表达为对绝对的静止与消极的纯阴的回归,这又产生了纯阳的创造力,并因此形成了微型宇宙的新循环。”我们需要注意诸如“回归”、“绝对的静止和消极”、“微型宇宙”等词语,它们表达了对胎儿存在的直观理解。
2. 公案: 为了摒弃语言而使用语言。在禅修中,有一位修行者得到一个记载下来的公案,他当全神贯注,竭尽所能去理解它,直到如禅语所说———“一超直入如来地”(his bite gives a-way) ,这意味着他放弃了理性的思考,进入了悟的超理性非逻辑的领域。以中国明代的文人画家董其昌为主倡导的南北宗理论,也借用了禅宗的此类观念,来为当时的文人画正本清源。
正如杜姆林所描写的,“强化的公案练习促进了禅悟,在练习中所有的身心能量都被指向虚无。身体呈端正的莲花坐,精神的努力与身体的努力相结合。在最紧张的时刻,壳破了,宇宙打开了。”这种无逻辑、非理性的公案思维,迫使修行者在认识自我和他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完全放弃理性的和逻辑的方法,直到此人不再意识到自我和环境的区分,这样就能进入自我和他者融为一体的精神状态。几位禅宗学者也如此描述了公案的作用: “公案并不是需要敏捷的才智来理解的谜团。
它不是一种使修行者分裂的自我达到某种稳定的语言心理技艺。在我们看来,它也不是似是而非的一种悖论,只有外人才如此认为。当公案解决时,修行者会意识到它是一个有助于唤起有意识状态的简单明了的陈述。”因此,公案只充当突破意识思想的途径,正如中国禅师无门在其《禅宗无门关》序言里所说,它们就像“敲门瓦子”,“历代祖师……根据弟子的能力因材施教的工具”。
历史上的禅宗大师们大多厌恶语言。迦叶(Kasyapa) 对佛祖拈花一笑,意味深长; 维摩诘(Vimalakirti) 以沉默来表现自己的彻悟,慧可用无语的鞠躬来回答菩提达摩(Bodhidharma) 的诘问———这些著名的案例都说明,对于禅宗的核心概念如佛性和开悟的理解,语言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语言是禅悟的根本障碍。
的确,语言无可避免地使主体与自身产生异化。禅宗的核心教义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正如学者们认为的,这句箴言不仅证明了禅独立于语言,而且将语言当作看到真实自我的绊脚石。如果语言被认为是一种不够充分的方法,一个障碍,或尼采(Nietzsche) 所称的“牢笼”,那么摆脱它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沉默。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的名言所述: “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
但是沉默也会被理解为无反应和未理解。伯兰特·佛尔(Bernard Faure) 见解深刻地指出,一言不发或答非所问都可被利用来“让那些无话可说的大师们假装自己正在仿效维摩诘的沉默。”因此对那些打算皈依禅门的信徒来说,沉默可能是欺世盗名而令人气恼的。
所以,到了中唐,语言被禅宗大师们当作不可避免之恶,并被赋予了暂时的价值,就如路标或“善巧方便”,这就催生了公案。一些学者认为,公案是中国禅宗传统中一项重大的发明,它的重大意义在于,禅师们认识到,尽管语言作为媒介疏离了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但也能起桥梁和催化剂的作用,促进通向开悟的心理反应。比如留下影响巨大的《碧岩录》的禅宗大师圆悟克勤就强调语言文字在实现明心见性这一禅宗的基本目的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引导作用。他曾就立与不立文字有过这么一段话: “须知向上一路不立文字语言。既不立文字语言,(心) 如何明得? 所以道,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由此可见,用与不用语言文字并非绝对,禅宗的终极目标是明心见性,恰当的文字语言对于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也许是必要的,就看如何化不利为有利,把阻拦人们明心见性的障碍变成穿越高墙的一个通道。但语言文字的作用何在呢? 这就得从语言与主体的关系来看了。美国著名禅宗研究者佛尔在研究禅宗对语言的使用时有一段精辟的概括: “普遍的看法是,觉悟始于语言和心理功能的终结。对觉悟的反复描写是‘语言的道路被切断了,一切心理功能都熄灭了。’然而,语言还被视为拥有无限的深度。所以,在语言内部发生觉悟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这就是说,语言与禅悟有一种二重性关系。
语言对禅悟的二重性可从形成主体的语言来理解。探讨主体性的语言方法认为,主体是一种语言构建,不是实质性的本体存在。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 令人信服地指出,主体性“只是存在内部的语言基本性质的表现。成为自我就是说出自我”。例如,代词“我”是一个无意义的能指,因为当某个人使用这个词时,它只能涉及一个具体的人。它使说话者将自己构建成主体并使用语言为话语。但是藉此形成的主体性只是一个语言的幻觉,不是现实的本体存在,因为这种主体只是一个修辞。这种“形而上的主体”,即尼采所批判的笛卡尔式的幻觉,错误地存在于根据语法习惯推理出一个代理人,一个活动背后的“著名的古老的自我”,即思维活动背后的思想者。有关主体的语言理论可能会产生一些对理解禅悟有用的洞见。如果自我,主体和主体性是语言构建的,我们就能通过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来摆脱它们,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忘记语言这个产生主体的机制来摆脱它们。这正是禅宗大师们告诫弟子们要做的事。
这种对语言能量的认识具有心理学的基础,就是拉康所称的语言的“钩子”功能和其启示的能量:也许我能这样表达,就语言的本质而言,与他者钩联并不陌生。毫无疑问,语言是主体和他者间的调和,这暗示了在调解中他者的形成。他者形成的一个必要元素就是将我们和他者联合起来的语言能力。……话语还有另外一面———启示。启示,而非表达———无意识只能通过变形、能指的移置、扭曲和转运来表现。
在禅宗传统中语言的使用日益增多,可能是因为禅宗大师们从直觉上认识到,禅宗寻求的东西无法被象征。进一步而言,恰恰因为禅悟无法被象征,处于所谓真实界(拉康的 Real Order) 的空间中,人们才必须依靠象征界(拉康的 Symbolic Order) 的概念,即能指的权威的概念。这意味着我们被抛回到了话语系统,通过此系统我们达到自我的主体性。在此系统里,我们产生意义,创造理解和知识,或如拉康所称的当一个人试图为了禅而抛弃语言系统时,同时产生的“基于欲望的真实效果”。
进入象征界之后,儿童的欲望,对遗失乐园的无止境追求,必须经过隐秘的象征界的通道进行疏导,就像流经一条地下河一样。这就有可能使那些缺席的事物通过语言而在场,这些如迷宫般纠缠的通道仿佛如拉康所说,像“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项链”。
人,生于语言; 也永远不能逃避语言。即使沉默或沉睡,我们也受到语言意指的控制。这样说来,语言成为了一个外在的“牢笼”。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禅的静修在实质上不存在声音或文字,但是在隐喻上是隐藏了许多看不见的意指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被看成有潜力结束意指过程并暂时帮我们逃离“语言的牢房”的能指。罗兰·巴特在日本短暂停留后,在《符号帝国》中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顿悟: “禅的一切……都表现为巨大的实践力量,这种力量注定要制止语言,堵塞那种不断向我们发送的内心的无线电似的信息,甚至在我们睡眠时,……抽空灵魂中的不可压抑的喃喃话语,使之呆若木鸡,使之欲语忘言。”
对于巴特来说,顿悟“只是语言的一种没有理由的中止,这种语言的空白推倒了符码对我们的统治,打破了构成我们人格的内心的吟诵”。佛尔在对巴特的解读中,直接地指出: “在《符号帝国》中,禅的成功是不是因为禅的静修本身已成为范例性的能指?”
作为一个能指,静修是语言和会话的另一形式,属于象征界的维度。它和发音的会话具有同样的突破性的作用,能够暂时消除自我和他者、主体和客体、象征界(Symbolic Order) 和想象界(拉康的 Imaginary Order) 之间的障碍,引导进入真实界(Real Order) 。时常,静修在引起顿悟方面要更有力和更有效,正如禅宗大师们喜欢提到的一个矛盾的表述: “雷鸣般的沉默”。
3. 问答: 这种修炼常常伴随其他方式,诸如棒喝。这是通过外在辅助的形式来达到禅悟的一种途径。
禅师和弟子间的对话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悟禅方法。这让我们想起精神分析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和分析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者都使用语言来突破心理压抑的障碍,但他们的相似之处是有限的。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分析者让分析对象以自由联想的方式谈话,分析那些语言并将其解释成看似合理的情结,再让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进入意识,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而在禅宗对话中,师傅要么向弟子提出似非而是的问题,要么对弟子提出的问题作出非理性的解答,旨在破坏后者习惯性的理性思维。而且这种练习建立在绝对必要打破二元性障碍的基础之上。
大慧宗杲(1089 -1163) ,中国宋朝时著名的禅宗大师,就心性二元的两个方面作出了区分:心充满了有意识的精神活动,如感觉、知觉、思考和表象等等,而性是一个人静止不动的基础。他主张像慧能一样,用停止所有意识活动的方式来达到人心彻底的宁静。他相信能够通过意识层的突然塌陷和随后进入原始的心理状态来体验禅悟: “将思量计较之心坐断,不于空寂处住著,内不放出,外不放入,如空中云,如水上泡,瞥然而有,忽然而无。只向这里翻身一掷,抹过太虚。”
大慧在传道实践中使用了一种方法,即对一个公案常常似非而是的问题反复询问,以打破所有习惯性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目的是触发深刻的见解,让人在困境中获得一种新鲜而自由的洞察力。同时,大慧还提到了赵州和尚对公案“狗子佛性无”的解答,他明确地表示,开悟表现为消除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从而达到统一的状态: “凝气聚神———倏尔,如梦初醒、如莲之盛开,如拨云见月,是时,即自得统一。”
除了这种强烈质询的方式,禅宗法师们还会求助非语言的交流如棒喝来达到同一目的: 震撼和唤醒。这也是一种恢复被压抑的出生前和学语前的统一存在的方法。顿悟是被束缚精神的突然释放。它常由某种提示引起,这些提示是语言的或动作的,视觉的或听觉的。在此值得提一下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开悟的体验。根据传说,芭蕉在蛙鸣声中突然体验到了禅的真相。
罗兰·巴特提到: “芭蕉从这种喧闹声中发现的当然不是‘启悟’这类主题,也不是一种敏感的符号性表现,而是语言的一种终结: 在一瞬间会出现语言的休止(这种时刻要经过多次修炼才能够出现) ,这种无声的断裂立即建立起……禅宗的真理。”
确实,我们读到关于顿悟的各种各样的描述,有铃声,雨声,鸟兽叫声,某人的大喝,敲钟声,木棍的突然重击———这些行为都是触发性的刺激因素。这些刺激能够激起记忆机置,诱发在习得语言、自体客体分化和出生的创伤性事件之前的被长期遗忘的体验。这种催化引出了自由舒畅的体验: 自我和他者、主体和客体的融合,万事万物归于虚无。
禅悟的本质依据心理学的理论,所有的感觉都已在脑中留下痕迹。简而言之,就是所有的感受从未被遗忘。但我们想表明的是,禅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在此状态中,依据自我和他者的二元性,人类的心智暂时在有意识的思维过程中停止,从而暂时“消除”了写在心智上的东西: 即出生后逐渐积累的激动、刺激、欲望和渴望、痛苦和快乐、紧张和创伤等等的痕迹。按庄子的话来说,那个瞬间称作“坐忘”。而巴特则用其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将这种自由的体验称为一种“非语言(a-lan-guage) 状态,阻塞了过多的能指内容的无限添加,打破了语言的有害的无限性”。语言和思维的瞬间暂停就可能在一瞬间回到失去的出生前和学语前阶段的“乐园”,但这种返回与婴儿或胎儿的思想状态不同。弗洛姆将修禅者和儿童感知到的现实作比较,并指出两者的不同,这也许能作为一种有力的证明:禅修的目的在于开悟:即时地、不经考虑地把握现实,并不受污染、不经理性思考地意识到自我与宇宙之间的联系。这种全新的体验是在理智干预前,瞬间把握到儿童状态的一种重复,当然,这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是人的理性、客观性及独立性的全面提升。儿童体验的及时性和单一性存在于异化的体验和主客体的分离之前,而禅悟则存在其之后。
弗洛姆直接把禅悟的机制看成解除压抑的过程,在这个没有压抑的状态中,“人再次感知到直观而未被扭曲的现实,那是种孩童才有的单纯和自发性”,并且重新连接意识和无意识。然而,像大多数他们同时代的人一样,他相信无意识是最深层的思想维度,是本我的沸腾的大锅,其表面是有意识的自我,“必须要突破它才能到达无意识”。我们则倾向于认为,禅悟采用的方法目的在于打碎(尽管是暂时的) 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别,从而在一个人真正的存在中摒弃异化,进入暂时的忘却。我们的观念不是基于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家所理解的弗洛伊德的观点: 从位置的角度(in thesense of locality) 来使用“无意识”,而是拉康理解的弗洛伊德所谓的“无意识”,即“我的历史中空白的一章”,“被审查删除掉的一章”。但是这一部分可以通过身体症状、童年记忆、话语风格、民族神话和传说,以及归根到底,“他者的话语”———一种“类似语言结构的复杂的心理模型”等,进行解密。如果一个人能够抓住那“被审查删除掉的一章”,并且哪怕是短暂地破坏它,他就可说是实现了顿悟。东西方的禅宗学者们的观点正如铃木大拙一样,即顿悟是“对无意识的洞见”。
我们倾向于认为,所谓顿悟是一种心理状态,在其中意识和无意识都完全消失,从而使人的思想暂时恢复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 所描述的白板(tabula rasa) ,好像一张白纸。但这时的白纸与新生儿的心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代表着长时间游离和遗忘的精神状态的迅速回归。这种观点可为理解唐代青原行思大师所说的禅修三种境界提供了新的角度: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
人们将这三种境界理解为禅修者从无知状态进化到充分理解生命意义及人之存在的三个阶段。
我们的观点则截然不同,认为公案应从反方向去理解。在我们看来,三种禅修的方式并非来源于从单纯无知到经验丰富、智慧无边,而是一种反方向的回归,即从有意识到前意识再到无意识,这恰好与弗洛伊德的“心理三层次说”所契合,即: 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但我们的观点比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向心理深层更进一步。我们认为,禅悟穿透弗氏无意识触及出生前的心理状态。由于没有合适的词语描绘,我们不妨称之为“前无意识”,这是婴儿在出生前的心理状态。禅悟就是成人短暂地回归这种“前无意识”状态。从这个意义上便不难理解开悟之人所说的那些似非而是的话了: 开悟之后,他所见的山与水,与之前所见的既相同又不相同。
青原禅师的禅修三境界使读者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 是否所有的开悟体验都一样? 目前,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以评价是否真正开悟或哪种开悟的方式更为高级,由此,心理学家认为开悟是一种主观状态,一种自我发生的如痴如醉的恍惚心态。即使是对禅极力推崇的荣格也说: “我们决不能说,那人是否真的‘开悟’或者‘解脱’了,抑或那只是他自己的想象。我们没有所能依据的标准……一个开悟或声称自己已开悟之人,认为所有事物都曾引发他的开悟。即使他是在说谎,他的谎言也是一种精神事实。”
事实上,禅修者经常将某些情绪上的狂喜误认为是开悟,甚至有人将“走火入魔”的幻觉误认为开悟。然而,声称达到开悟境界的人,其体验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们冒昧地说,开悟要经历三个阶段: (1) 初级觉醒: 精神成功地进入语言前的状态,达到无念; (2) 次级觉醒: 成功进入前自我的精神状态,感觉身心无异,意识到统一性和整体性; (3) 三级觉醒: 精神处于出生前状态,与宇宙合二为一,达到宇宙性的无意识。只有经历了这三个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六祖坛经》中,慧能一再提到他多次开悟的情况。
一个人一旦进入了开悟的第三阶段,他便从所有的情感负担和心理负担中解脱出来,其自由的灵魂就能够像庄子笔下的鲲鹏那样展翅飞翔,了无牵挂,这样,他便能以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而存在,进入一些开悟之人所说的无冕之王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