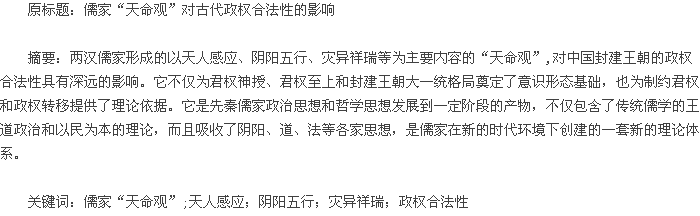
引言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当人类历史出现阶级以后,政治便成为人类社会进行自我组织和管理的形式,而政权便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先秦时期一般都将“政”和“治”分开使用,“政”指行政权力、法律和规章制度;“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治理人民,让人类社会处于安定祥和的状态。《尚书·毕命》载“道洽政治”一语,大意是治国有方,国民安居乐业;《周礼·地官》也有“掌其政治禁令”一语,是指治理国家的一切权利。可见,中国古代所谓“政治”便是指君主通过建立国家行政机构,颁布法令,经过治理而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而“政权”便指君主建立国家,设立官制,颁布法令的权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一直是国人的崇拜对象,古代的“天”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气层,而是自然神和人格神双重含义的宗教信仰对象。“天”不仅是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也拥有决定二者兴衰存亡的终极权力,所以人世间君主的政治活动要上承天意,才能得到上天的庇护,“法天而行”也因此成为历代君主治国的官方政治思想。“法天而行”的思想源起可以追溯到西周,当时西周统治者依据天地四季建立了六卿制度:“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司徒,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在先秦各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终于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天而行”思想,既包含了富有宗教色彩的新儒学天命观,又是儒家政治话语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1 传统“天命观”的衰落
天命思想的源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先秦文献对此多有记载。《礼记·表记》载:“夏道有命,殷人尊神”;《诗经 · 商颂》载:“帝命式于九围”,意思是上天命令成汤掌管九州;《尚书·汤誓》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时的“天命”不仅用来解释自然界与社会的运作变化,而且也是统治阶级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做出的宗教性诠释。商纣王残暴,势力弱小的周人通过长期的努力,终于领导各部落灭商,这种暴力性的政权更替很容易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周人一方面通过贬低商纣王,美化周文王来论证灭商的合理性,一方面提出了“天命”得失与人间统治者是否失德相一致的理论,这是他们构建的一个伟大的理论。
新的理论在当时不仅为巩固政权和收拢人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为后世统治者敲响了警钟。西周初的周公旦曾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下庸释于文王受命。”他敦促周成王及其大臣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敬天保民”价值标准的威力在这段话中甚至超过了天,这从客观上降低了“天”的威信和作用,重人事轻天命,这对西周以后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重民思想的来源,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历史依据。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天人关系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倾向和变化。
首先,周初的“天”作为至上神的观念受到了冲击,各种关于“天”的理论不断萌芽,“天命观”开始衰落。这一时期“天道”、“天地”等范畴较为普遍地出现,不仅是指至上神或它的意志、命令,而且具有多种涵义,如“天道”,既指天意、天理,亦指春夏秋冬的轮换和天体运行的规律,人格化的“天”开始褪色,着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开始做出自己对“天”的定义,强化“天”的自然属性。
伯阳父认为:“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国语·周语上》)单襄公认为:“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下》)春秋后期的军事家在《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的天时、地利、人和对战争具有重要性的影响,他说的“天”是指风雨雷电、春夏秋冬四时变化的自然现象。范蠡提出了“天因人,圣人因天”的重要观点,他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国语·越语》)范蠡提出的“天”指以天象和气象为中心的自然现象,即指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化,四时交替,阴晴风雨等,从比较客观的角度探讨了自然行为与人的行为及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天生万物的自然思想观,如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这些材料都突出了天生万物的生殖功能,这时候的“天”既是神学的崇拜对象,也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天”的自然化便是对至上神“天”有否定意义的尝试。
其次,“重人轻天”的思潮开始出现,甚至出现了人们“骂天”和“恨天”的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开始退化,安逸奢华的生活逐渐腐蚀着周朝大小贵族,“敬天保民”在政治实践上根本无从谈起。底层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周边少数民族也严重威胁着边疆的安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并没有促使统治阶级惕励自省,周代先祖构建的一整套理论体系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天命”的可信度急剧下降,人们纷纷质疑“天命”的真实性,到了西周末年,一场“骂天”和“恨天”的思潮终于爆发了。《诗经》里面出现了大量内容,开始明确否定“天”的明察,讽刺以德配天的荒诞,以至于开始“恨天、骂天”.这种思潮具有深远意义,说明周的天命观开始动摇,走向衰落。到了周幽王时期,随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收场,周朝的政治权威终于因为政治军事实力的下滑而崩溃,大小诸侯也失去了对周室的最后一丝敬畏,周代所宣扬的政治宗教理念也开始瓦解。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郑国星占家预言郑将发生大火,人们劝子产用玉器祭祀,以避免火灾。子产回答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他对“天”的作用提出了质疑。《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国出现了彗星,按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这是齐国将有灾祸的征兆。齐国的国君十分惶恐,派遣使臣祭祀上天以求宽恕,大臣晏婴却对齐王说:“天道不謟,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这种思潮的另一个影响便是重视人事,当时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把“天意”和“民意”联系在一起。公元前706年,楚国入侵随国,随候认为自己祭祀神灵时十分忠诚,神将会协助随国取得胜利。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这种“夫民,神之主也”的说法是古代理论家否定神权的第一次积极尝试,季梁毫不客气地讽刺了随候盲目信神的荒诞行径,认为“民意”才是处理政治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彻底否认了神对世俗生活的主宰权力,这是古代无神论挑战有神论的重要事件,标志着先民们开始摆脱神权天命的束缚。《左传》中曾记载齐国讨伐鲁国,鲁庄公认为只要自己在祭祀时十分虔诚就可以一战,但曹刿认为不可,而当鲁庄公认为自己不仅关心民生疾苦,而且不因所爱而滥赏、不因所恶而加刑时,曹刿认为这才是可以作战的资本。《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也曾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殷商时期的神人关系颠倒过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天命”的主宰性和权威性的否定。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大小国家战乱纷起,灭国立国不知凡几,自诩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周朝已经奄奄一息,而衰落的周朝和被灭国的诸侯哪个没有祭祀过天神?可是天神的庇佑却不见踪影,“天命观”由此逐渐衰落下来。政治上的混乱从而导致了思想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天命”问题也成为各家各派争论的重要问题,涵义更是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倾向,殷周以来的多种观点依旧向前发展,但是又出现了系统化的认识和解释,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也受此影响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
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天命”观念具有自然和人格双重性,《论语》中谈论“天”、“命”和“鬼神”的句子不多,而且多是感叹和发表议论的话,属于认同的有“五十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天子”、“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属于感叹议论的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并由此提出了“知天命”和“畏天命”两种“天命观”.由此可知,孔子对于“天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承认其存在并且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淡化其主宰色彩,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他很少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在孔子谈论“天”的句子中,多是出现在他遇到了危险,受到了冤屈,或者是由于心爱之人去世的时候。例如,公元前481年,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英年早逝,而孔子对他的离世万分悲痛,不禁哀叹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这些都可以归于人之常情。孔子关于“天命”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冲破至上神的束缚而走向自然和人的历史趋势,虽然孔子由于出身和怀旧等原因,未能突破西周“天命”论的束缚,但是他主张人类应当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轻视虚妄的宗教世界而重视现实社会,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孔子对于“天命”和“鬼神”的模糊态度,形成了后世儒学发展的两个方向,一是被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儒家人士发掘,突出了“天命”中“天”的人格色彩,强化了“天命”的神学性,推动“天命”观向神学发展,为封建政权的合法性做出了理论依据,最终形成了流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的“谶纬”之学。二是被孟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学者强化了“天命”观的哲学意义,逐步形成了对后世影响甚大的理学和心学。
2 “天命观”的重建
秦朝初建,皇帝制度刚刚稳定下来,虽然秦始皇自称为“受命于天”,但皇帝与天命的关系尚不明确,皇帝不仅不把“天命”放在眼里,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支配“天命”.例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封禅泰山,儒生阻止始皇坐车进山,唯恐损坏草木惹怒山神,秦始皇大怒,不仅坐车上山,而且命令禁军砍伐草木示威。结果封禅完毕,秦始皇下山时遇到狂风暴雨险些丧命,只好躲到树下避雨,并因此封避雨之树为“五大夫”.“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在巡游湘山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是在其他封建王朝,狂风暴雨阻挡封禅巡游,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十分严重的天意谴责,但是秦始皇并不认为这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多大影响,在朝野也没有形成任何政治波动。甚至在民间也缺少对“天命”的敬畏,无论是项羽和刘邦的“大丈夫生当如此”,还是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体现了其对“天命”的蔑视。无论在统治阶级,还是在民间,秦朝“天命观”远没有汉朝“天命观”令人信服。
西汉建立以后,统治阶级面临着三大社会问题:一是社会经济恢复问题,天下残破,民众饥寒交迫,恢复因为战乱而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是汉代统治者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二是匈奴问题,严重威胁新生王朝的安全;三是地方分裂势力问题,各个诸侯王与中央政权日益分离,隐约有叛乱之势。为了迅速恢复国力,统治者从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出发,制定了以恢复民生经济为主要目标的内外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黄老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通过与汉初的社会现状相结合,成为汉初政治的主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恢复,经济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然而,黄老思想也有自身的不足,即擅长于安抚社会却无法彻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致使汉初几十年的各种规章制度漏洞百出,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在统治阶级内部,官僚贵族骄奢淫逸,彼此争权夺利,同姓诸侯王实力膨胀,进而觊觎皇位;在民间,一些民众暴富,甚至富比王侯,而一些民众却无立锥之地,社会贫富矛盾日益尖锐。伴随着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社会秩序也日益混乱。汉景帝时期发生的“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王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大量贫穷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凸显;北方匈奴虽然接受和亲,但仍然不时南下掠夺边境。出现这些问题,除了实力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便是思想问题,在这些危及社会安全的团体或者个人的思想里,基本不存在真正的上下等级、尊卑观念,他们蔑视礼仪制度,缺乏对中央政权的敬畏感;“七国之乱”的诸侯王多数是皇帝的长辈,在日常生活中常无视君臣之礼,举止张扬,多有僭越。原有的黄老思想显然已不能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给出更为合适的设想和解决方法,一种新的治国理念迫切需要出台。葛兆光教授指出:“时代的需要,使思想逐渐趋于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一个从终极意义到实用技巧、从知识技术到法律制度可以涵盖一切的意识形态。”
终于,新的理论体系登上历史舞台,它以汉武帝前后伏胜的《洪范五行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翼奉的《齐诗》为开端,两汉间蔚为壮观的纬书将其推向高峰,后汉章帝时白虎观会议产生的《白虎通义》则是其理论的终结。
汉代前期,儒家面对复杂的思想背景,时代的需要和学说自身理论不足让儒学理论急需弥补。而如何弥补自身的不足,建构一个涵盖天地万物的理论框架、解释自然人间各种现象的知识系统和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可操作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使儒学在这种社会环境变幻莫测的时候成为国家政权乃至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便成为儒学在汉代最重要的目标。
这一任务并非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至少在汉初,陆贾便接纳了黄老之学、阴阳五行思想,甚至包括术数方技等一些基础性哲学思想,开始构建儒学的理论系统,如他在《新语·道基第一》中说“天”的时候,一开篇就论述“天”、“地”、“人”的关系:“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这里的“天”就是万物的根本依据和效法目标,随后他进一步论述了“天”的自然性: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霜雪,养育群生,一茂一亡,润之以风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节气,降之以殒霜,位之以众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新语·道基第一》)这段话重点论证了“天”的自然性,但是也有天人感应之义,所以陆贾说:“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动之以生杀,悟之以文章。”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的结论。董仲舒也是在前人“天命观”的基础上,结合先秦各家和汉初儒家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政治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不仅被统治阶级所接受,而且得到了广大下层阶级的认可。董仲舒指出上天之意志绝对不是毫无章法可循,天地万物与上天互相感应,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都会被上天所感应,而上天通过灾异祥瑞来表明对人类活动的态度。若只从历史影响力来看,董仲舒是先秦以来儒家“天命观”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着作《春秋繁露》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天人一体,同类相感
董仲舒首先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阴阳五行观”.他认为天、地、阴阳、五行、人为十端,阴阳五行的变化影响万物,是天人相互影响的媒介桥梁;他通过人的身体特征和社会活动强加附会,提出了“人是天的物质派生”这一观点,这就是“天人相副”、“天人同类”,而天人感应的基础便是所谓“人副天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他还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具体论述了天对人的决定性地位:“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无论是意识形态功能还是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儒学的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构的影响,在中国文化体系内的地位开始发生动...
古代中国,军国大事主要体现在战争和祭祀方面。而祭祀与思想家的天命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古代各种政治活动中,天神崇拜和祖宗崇拜与之密切相关。舜承尧位及武王伐纣时,皆以天命来论证其新政权的合法、合理性。不仅如此,在之后的中国封建历史中,每...
现代新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20世纪表现出多方面的走向,从社会哲学的观念史角度说,可以归结为围绕着动力与秩序这两大观念作多重演化。前者促使其开掘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以应对外来的动力式文明的挑战,获得主体性的自觉与开展,展现出努力由被动...
周予同先生有一个说法:经学的时代结束了,经学史的时代刚刚开始。虽然说是经学史研究,但周先生及弟子朱维铮先生对于经学基本是否定的态度,这很难说是客观、公允的研究。如果我们今天还是采用这样一种态度,还是周予同、朱维铮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自绝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