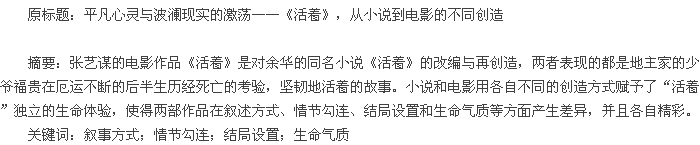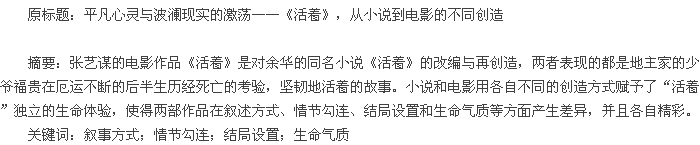
“当我们与现实抗争到无能为力时,便只能选择活着。”作品《活着》让电影大师张艺谋与文学巨匠余华在面对人如何承受生命苦难之时,产生了思想的火花与交集。小说与电影用各自擅长的方式娓娓道出平静心灵与波澜现实产生的激荡,让读者和观众去思索一个人和他生命以及一个人和整个时代的关系。
一、叙述方式的变化:从温情的倾听者到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
在小说《活着》中,故事的叙述者“我”到乡村收集民间歌谣,在田边碰见福贵老人,于是与其坐在田埂上倾听福贵老人平静地叙述他波澜的一生。之后的整篇关于“活着”的故事,便是由福贵老人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出来,而“我”便自动转换为一个平凡的倾听者。有人认为,虽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对于福贵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 “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同时也是福楼拜所谓的“冷漠性”。
而我却并不这么认为。故事的讲述是一种需要双方参与的过程,有讲述者,则必然要有倾听者。即使面前的对象只是安静地侧耳坐着,无论是否以说话的方式进行互动,只要有眼神交流或是心灵的内在碰撞,便是一种对对方的应答。况且,在文字作品中,有多处“我”因老人的叙述而对眼前之场景或是记忆中的画面阐发联想和感悟的段落。老人的故事在感染着“我”,“我”的虔诚的倾听也使得老人继续叙述自己的遭际。“我”并不是冷漠的第三者角色,“我”的感动、“我”的真诚、“我”的怜惜也在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体验。作者与读者之间不是冰冷的隔墙,而是有温情的暖意在流动。
而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叙述方式便产生了变化,由温情的倾听者转化为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导演删除了“我”这个个体的存在,直接把福贵的故事推到荧幕之上,真实地活在观众的面前。福贵是在活着自己的故事,毛茸茸的生存质感便与之融为一体。导演站在镜头之外,无法影响主角的生存线索。而导演的喜怒哀乐却通过画面的颜色、背景的音乐、人物的阴暗色调等表现了出来。声与色的交融在小小的影院中铺天盖地而来,观众或多或少被导演的情绪所影响着。然而福贵的故事却还在屏幕上继续,观众们可以通过理智的思考去感受福贵的一生,去冷峻地思索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电影带给观众们的幸运:电影冷静客观的旁观视角使得观众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在锤炼着他们在面对苦难时的情绪表达。
对于小说而言,“活着”的经历是在泥土里,在血液里,甚至是在人的心里。苦难纯粹而透彻,坚持着活下去的本能让人艰难的生存状态贯穿始终,普通生活中的一个普通百姓过着波澜而平凡的人生,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在电影中,“活着”在不同年代里对于同一个人有着不同的含义:是战争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侥幸,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的无奈,是在愚昧思想和精神动荡夹击下的清醒,更是真正作为“人”而活下来的新的生活。从小说到电影,叙述方式的变化,不仅使得读者的阅读体验和观众的观影感受发生变化,也使得不同媒介下的生存故事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内涵。
二、情节勾连的艺术:从自然到精致
小说《活着》的情节发展基本上都是依靠福贵老人对自己一生遭遇的讲述。历经时代考验的老人在回顾过往的时候,是平实而冷静的。然而,故事虽然以“活着”为名,却是以身边人的死亡来穿插剧情:地主龙二反抗公社运动,拒绝交出地产,被五发子弹枪毙;好友老全在战场上搜寻弟兄时被无辜打死;十几岁的儿子有庆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死;妻子家珍长年操劳,患上软骨病,医治无效而死;战友春生及其妻子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不堪屈辱与虐待,自杀身亡;女婿在工地上搬水泥板时,被坚硬厚重的水泥板当场夹死;外孙苦根一个人在家里吃豆子不幸撑死。死亡环环相扣,贯穿了福贵老人的后半生。平和的叙述反而让死亡的主题愈发深重,是怎样一种活着的力量让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忍受坚持到现在。作为一个生存个体,福贵的故事就通过他自己的口自然展开,没有刻意的渲染,但读者分明就能感受到故事里悲切的呼号与苍凉的心绪。
电影到底是一种画面与声音的艺术,大致相似的情节在荧幕上的呈现却是另一种精致的精彩:
首先,明晰的年代线索让福贵的命运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在小说中,作者是以福贵生命的自然过程为线索,时代背景只是人物命运展开的背景,赋予了情节一种现实化的支撑。简单来说,小说的线索就是福贵坎坷的命运。而在电影《活着》中,导演直接将影片分为四个部分: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及以后。这些数字便是时代最好的标志:40 年代,解放战争时期,福贵赌钱输光地产,从地主家少爷变得一无所有,借皮影出门讨生活,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从炮火和死人堆中侥幸活下来,两年后方与妻儿团圆;50 年代,全国大炼钢铁,福贵靠给钢铁工人唱皮影谋生,儿子却被下乡考察的区长的车子撞死,丧子之痛让福贵活着的最大最好的希望泯灭;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战友春生被打成走资派欲寻死,福贵鼓励他活下去;哑巴女儿凤霞与瘸子女婿二喜结婚,福贵生活有了新希望,然而女儿却因产后大出血而死,留下刚出身的外孙馒头;70 年代及以后,福贵依旧局促的生存着,希望新的时代能给儿孙带来更好的生活。明确的时代线索,将不同的事件划归到了不同的时间维度之中。导演的设计会自然让观者去思考苦难人生与时代的关系,有庆是 50 年代的牺牲品,凤霞是 60 年代的牺牲品,两个定格的年轻生命诠释着在特定年代下“活着”的简单愿望并不是轻易能达成的事情。普通的人物心灵不得不在波澜的生存现实中激荡,除了忍受现实继续活着,别无选择。
其次,细节的安排使得情节的发展更加精致和细腻。第一个细节安排便是皮影。当龙二将皮影的工具箱借给给福贵时,皮影的戏份便正式上演。给解放军唱皮影时,福贵是希望皮影能保全他活下来与家人重逢的;给炼钢工人唱皮影时,福贵是希望一家四口好好的生存下去;给儿子唱皮影时,福贵是想表达自己对儿子的亏欠和深沉的父爱;文革破四旧的时候,皮影被烧象征着对普通百姓生活的打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毁;最后,皮影没了,而放皮影的箱子成了外孙养小鸡的窝,含蓄地显示出福贵及其一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皮影是电影中的亮色,夜幕降临,普通百姓围坐在昏黄灯光下的幕布周围,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乐趣,也是他们努力追求生活的简单方式。另一个细节便是关于“鸡长大了变成鹅,鹅长得了变成羊,羊长大了变成牛,牛长大了便有好生活”的历经几代人的故事。在电影中,这段话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福贵背着有庆送他去炼钢铁的路上,父子俩的对话温暖人心,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希望。然而这却是父子间最后一次对话,当天下午有庆便被车撞死,空留当时的欢笑与热度。第二次是福贵作为姥爷逗弄外孙时的对话,只是最后变成牛长大了之后馒头变也长大了,福贵此时比第一次平静得多了,他相信迎接外孙的新生活该是真正的好日子了。这个流传了至少三代人的故事或许就是福贵他们一家生活下去的信仰吧。
最后,偶尔插入的幽默镜头让情节在紧张与轻快间张弛有度。有庆为了报复巷子里的调皮小孩欺负姐姐,在食堂吃饭时特意打了整整一大碗装着辣子的面条,生生浇在那个领头孩子的头上;家珍为了缓和福贵和有庆的矛盾,鼓励儿子调制了一碗又酸又辣的茶水送给福贵,福贵喝下后一口吐在了皮影的屏幕上;凤霞结婚时,二喜煞有介事地向墙上的毛主席像呼告:“我把凤霞接走了!”也引得围观的群众开心一笑。虽然整部片子的基调是深沉浓郁的,但间或也有微弱的光照亮人心。
三、结局设置的内涵:从孤单而不孤独到局促而微暖的陪伴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我知道黄昏正在转瞬即逝,黑夜从天而降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小说的最后的画面是福贵与老牛渐远的背影,就像老人自己戏称的“两个老不死”的。亲人们都离开了,苦难的生活也过去了,最终只剩下福贵一个人与老牛相依为命。谁都不知道福贵还能活多久,老牛还能活多久,然而活着就是幸运不是么。虽然福贵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但我却认为他不是孤独的,他有有庆、家珍、凤霞、二喜和苦根的陪伴,每日与他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远处的炊烟仿佛是家人在召唤着福贵回家。村子里的男人女人都在平凡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福贵来说,他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农民。
电影的结局和小说略有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导演与作者对于活着的理解不同。影片最终呈现的是一幅局促而微暖的陪伴的画面:福贵、二喜、馒头围着皮影箱子吃着馒头,家珍坐在一边的床上微笑地看着地下的祖孙三代,房子的空间很局促,但温暖确是浓郁而阔大的。
小说隐含着看透人生的淡然,悲惨生活的烙印让人觉得多活一天都是生活的恩赐,因而老人是平静而安详的,生命的流变让他接受着世事的变迁,这是痛过之后的坦然。而电影最终还是用类似大团圆的结局赋予了一个小家庭部分的圆满,生活清苦而希望仍在。与小说相比,其刺痛感与悲剧性便被大大削弱。导演对新生活的希望直白在屏幕上表现出来,而作者的思考却在字里行间隐现着含蓄的生命之光。生命在死亡的深渊中显示了它的韧性,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人性光辉的事物在过去的年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并且又将怎样走下去。
四、生命气质的融入:从对人文关怀的坚守到对时代历史的反思
阅读小说《活着》和观赏电影《活着》是不同的审美体验。小说和电影各自作为一个带有创作者温度的独立的生命体,蕴含着的是不同的生命气质。小说《活着》之所有充满着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他把目光投射在人心,关注人的精神状态。他毫不避讳残酷的人生,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他在努力地接近着生活的真实。面对死亡,活着就是有力的武器。尽管作者在小说中不断重复死亡,但他依然剖开死亡,直指生存的欲望。时代的悲剧或是个体的悲剧,天灾或是人祸,物质的灾难或是精神的动荡,人生存的终极价值并不在于生命之外的身外之物,而恰恰在于生命过程本身,人就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作者始终关注着普通百姓的心理状态,希望用文字坚守一份人文的关怀。人在苦难中不轻易绝望,内心的力量鼓舞着人继续走下去。
从张艺谋的作品《活着》来看,他更侧重的是对时代历史的反思。40 年代、50 年代、60 年代……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小标题,使得政治因素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作品。战争究竟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的是和平还是更大的痛苦?大炼钢铁的决策是正确还是错误?文化大革命是促进新文化的建立还是对传统文化的毁灭性打击?普通百姓能否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生活?……人是社会人,无法摆脱时代历史背景而存在。面对历史,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盲目的肯定或者否定;理智地看待时代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勇敢地接受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机遇。从小说、电影中广泛接受不同创作者生命气质的熏染,也是有助于读者或观者培养自己对于生命的关怀,增强自己的生命体验。
参考文献:
[1]余华.活着.作家出版社,2008年.
[2]余华,杨绍斌.文学谈话录——“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
[3]廖青鹏《.活着》之小说和电影的跨学科研究.电影文学,2012年第6期.
[4]梁言.论《活着》的小说和电影异同.北方文学,2011年六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