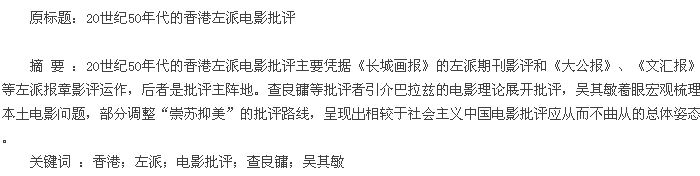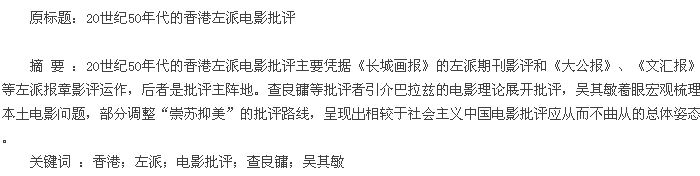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冷战格局下的香港“作为西方阵营渗透‘竹幕’和新中国打破围堵的缺口”是“海峡两岸三地里唯一的‘公共空间’”,不断上演意识形态的左右颉颃,电影生产者和电影批评者“为求生存,必须选择立场,投入左派或右派阵营”(罗卡语)。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新联与右派电影公司永华、亚洲、电懋、邵氏较量高下,左派影评阵地《长城画报》、《文汇报》、《大公报》等与右派影评阵地《中国学生周报》、《新生晚报》、《南国电影》等两相对峙,港英政府则刻意塑造不偏不倚的“中立”形象,任其“自然”。“在左翼文学家和文化人纷纷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时候,右翼文艺界和新闻界则在国民党全面败退中南来香港。……而五六十年代香港文艺界和新闻界鲜明的左右对垒,也自此形成。”由于诸多南下影人干将离港北上,香港左派电影批评日渐式微,吴其敏、查良镛、陈君葆等接续前行。
一 、《长城画报》的电影批评
司马文森等左派电影工作者被迫离港后,香港“电影界中的左派力量一落千丈”,电影批评自是日渐衰敝。“民主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仍是奢侈品”在艰厄窘况中,秉持“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的左派电影批评者,举步维艰。
值得提醒的是,相较于同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批评的“政治主导”,即过分强调和突出政治功利性,将电影视作“时代的‘晴雨表’和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倪震语),殖民地生存的香港左派电影批评“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再刻意追求慷慨激烈的辞锋犀利,不再彰明较着地鼓吹“进步思想”,而淡化政治色彩,注重“提倡健康,导人向善”,“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努力开辟电影的新天地。”
《长城画报》(1950-1962)即是香港左派电影工作者开辟的一个新阵地,亦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左派电影批评最重要的期刊根据地。1950年8月创刊的《长城画报》,不仅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的官方刊物,而且是凤凰影业公司、新联影业公司等左派电影公司的宣传阵地,“居电影刊物销售之冠,尤其在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力很大”“,研究香港电影史……不能不看《长城画报》”。
相较于《文汇报》和《大公报》影评影响的逐渐式微,《长城画报》影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则不断增拓。自1952年港英政府驱逐左派人士开始,《长城画报》的电影批评,总体上扬弃阶级斗争的激进话语,有意识确立“爱国进步”、“健康写实”、“导人向上”、“导人向善”的弹性表述。尽管其电影批评空间有限,但《长城画报》还是刊登不少精彩电影批评,“批判坏电影·推崇好电影”。这些电影批评,既有电影问题的探讨,也有电影作品的评论。前者的影评主将,是日后成为文学大家金庸的查良镛(笔名林欢、姚馥兰、姚嘉衣);后者的影评则未有主将,零星上阵。
1953至1958年,《长城画报》刊发查良镛的电影批评超过50篇,所论问题之广泛远胜“粤片集评”乃至“七人影评”:论述电影基本元素问题,如《电影艺术浅说》、《谈电影音乐》、《电影中的音响》等 ;论述电影叙事问题,如《谈倒叙手法》《、电影中的冲突》、《谈电影的结尾》等 ;论述电影与文学关系问题,如《名着的改编》、《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短篇小说式的电影》等 ;论述电影演员问题,如《谈演员的戏路》、《谈电影中的配角》、《义演和我们的工作》;论述电影观众问题,如《观众们的意见》、《电影观众的年龄》、《对少年儿童的影响》;论述电影本土化问题,如《民族遗产与电影》、《谈中国风格》《、古装电影的要旨》等 ;论述外国电影问题,如《谈亚洲各国的电影》、《美国影业的衰退》等。
这些电影批评中,所述电影问题最广泛的是《电影艺术浅说》,在《长城画报》分四期连载,即《电影艺术浅说之一》(66期)、《电影艺术浅说之二——学看电影》(67期)《、电影艺术浅说之三——脸的表情》(68期)《、电影艺术浅说之四——镜头的角度》(69期),其批评思路直接或间接援引社会主义阵营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的电影美学主张,某种程度上暗合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电影美学建构思路,颇值细读。
查良镛归纳电影诞生初期的戏剧思维弊病——公式化“闹剧”的横行、全景景别的单调乏味、演员们“十分夸张的”表演,直接借用巴拉兹的表述,称其“只是舞台式表演的拍摄”,“真是滑稽之极”。查良镛指这些不足“有电影而无艺术”,并与批判资本主义挂钩 :“盲目的蜂涌追逐,也正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利润的疯狂追求,内在自有一种心理因素。”继而,查良镛通过辨析电影不同于舞台戏剧之种种,套用巴拉兹的四点总结,指出“电影艺术的特点”:“一场戏被分割为一个个的镜头”,“一个镜头与另一个镜头之间,互相的连续会发生特殊的效果”,“观众与一场戏之间的距离经常在变动”,“观众看的角度常常不同”,由此阐述电影的镜头、剪辑、景别、角度观念。针对电影接受,查良镛提醒看电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欣赏力”,并结合巴拉兹的表述和格里菲斯的实例,指出“隐晦的、比喻的、间接的表现方法”的“精微细致”。
而后,查良镛详述“电影艺术的特长之一”的“善于运用脸部表情”,并结合多部中外电影实例,包括其编剧、香港左派电影《绝代佳人》和《不要离开我》,指出演员“脸部的表情是最深刻、最复杂、也最细致的”,这正是巴拉兹提出的“‘多音的’面部表情”“、微相学”概念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查良镛所述外国电影,不仅有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波罗的海代表》,而且有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美国电影《不可容忍》、英国电影《雾夜情杀案》,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电影”并未一味否定,甚至称其中某些“影片都是具有民主性的”。这一论断的理由在于,电影作为“新事物”具有“进步性”,“从这种新的艺术之中,必定会产生进步思想,那是必然之理。”
巴拉兹提出的“电影艺术的第二个重要创作方法”的“变化多端的摄影方位”,查良镛运用丰富实例进行说明。通过英国电影《孤星血泪》例证“同样的风景,气氛却完全不同了。这种不同之处,主要是用镜头角度的转换来表现。一般说来,表现恐怖、紧张等感情,常常是用不平常的角度来拍摄的”;通过美国电影《鸳梦重温》例证“角度不变的重现”“常常用来去表现回忆”;通过美国电影《狂夫淑妇》《、蜡炬成灰泪始干》例证“倒影与反映的角度会变化情调”;通过美国电影例证镜头角度的“暗示与象征”;乃至直接照搬巴拉兹分析苏联电影《伊凡》的表述,表示电影“角度变换所产生的效果”。
尽管查良镛的《电影艺术浅说》电影理论上的独立创见甚少,基本袭用巴拉兹·贝拉的《电影美学》,但查良镛结合包括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的大量电影实例,使得《电影艺术浅说》更适合中文语境中的观念传播。同时,由于当时巴拉兹·贝拉的《电影美学》尚无中文译本,《电影艺术浅说》亦具理论引介之功,使得内地电影刊物《中国电影杂志》几乎对其全文转载,可见其在左派电影观念夯实上的实绩。
而《电影艺术浅说》所揭橥的本土情怀,在查良镛的电影本土化影评中,自是更加凸显。如在《古装电影的要旨》中,自豪声称“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与文学作品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并以电影编导身份,称其所编《绝代佳人》“遵照《史记》的记载”,“有一个原则 :不可以歪曲当时的历史事实,也不可以把现代的思想和意识,硬装到古人头脑中去。”
这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乃至消解同时期社会主义中国鼓吹的“主题先行”、“工农兵电影”电影观念。查良镛敏锐意识到的时代精神不等于现代精神,这和内地“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对电影文本进行定向读解,可以为形象赋予某种政治含义,再对这种意义确定政治性质,展开政治批判”(胡克语),亦即将所谓“现代精神”强加于历史叙事的批判思路,泾渭分明。由此,查良镛明确提出“古装电影的要旨”,“在于表现当时的历史精神。……要抓住那个时代中一个深刻的矛盾问题,用现代观众所了解,所喜爱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对于时代意义的强调,同样体现在查良镛的《谈古装电影》——“对一部古装片的评价,主要是看他表现的历史意义是对的还是错的。”某种意义上,这一思路指向对于历史叙事过度政治化阐释的消解,建构着不同于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批评的香港左派电影批评意识。
值得提醒的是,查良镛乃至诸多《长城画报》影评作者,抛弃内地影评的“唯心史观”铡刀,但其“反封建思想”却和内地影评颇多一致。略察即知,“反封建”是五四运动的成果,香港左派电影批评者自可高举这一旗帜,颂扬电影中的“反封建”。如查良镛称《梁祝》是注定的封建社会悲剧,“和所有反对封建的人的心灵就更为息息相通”,称誉《梁祝》“反抗的是整个封建势力,……《梁祝》的结局是化蝶,是反抗者在死亡中得到胜利,他们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至死不屈。”
这种相较于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批评应从而不曲从的立场,正是1952年后《长城画报》电影批评的主流姿态。查良镛的《什么是好片子》,正是基于此前提的电影价值判断,其中指出“好片子”的必要条件“必须有一个主题,而且是正确的主题”,而“正确”是倾向于“大我”重于“小我”,“公利”大于“私利”,例如“长城”出品的左派电影《方帽子》,即有“受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而不是求自己的名利”的“正确的主题”。这样的电影价值判断,不独是查良镛的个人立场,而是《长城画报》乃至香港左派电影公司的集体立场。正因于此,《长城画报》亦刊出马国亮专论“坏片子”的电影批评,使得二元对立的影片“好”与“坏”的分野更加明晰 :好片子有主题,有正确主题 ;坏片子没有主题 ;好片子反对个人主义,坏片子歌颂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无视别人利益的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始终是一个英国殖民地,这儿的左派导演无法赤裸裸地宣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纵然想拍亦无从拍起”(汤尼·雷恩语),某种意义上,这种“好坏片子”左派电影价值观念的确立,正是对于当时内地通过政治运动推动的“人民电影”乃至人民美学观念的革命话语的香港化改造,将前者置换成“大众电影”的“进步话语”,此话语策略相当程度上接续着国共内战时期胜负局势明朗前的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的“进步话语”。
《长城画报》电影问题批评作者阵容中,主将查良镛之外,颇值注意的是“粤片集评”宿将吴其敏(笔名望翠)。其电影问题批评着眼于当下问题的切实阐述和宏观审视,呈现出明确现实关怀意识。如其推崇“新长城的崛起”,肯定“它带来了一股充沛的力量,使国语电影在港更呈欣欣向荣之势”。又如其阐述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海外片厂“丰富的行旅”,“结合《孽海花》打头阵”,发掘其中对于香港电影生产的意义,“这虽然是一个影片公司负责人对于自己业务所推进的改革与发展的行动,但显示的意义并不只此,行动严正地接触了港制电影和国外影业的联系与交流的问题,也表现了如何采集他人之所长,补助自己之所短,对制片工作不断求进的精神。”
再如其整体审视一年间香港电影发展,凸显左派电影的实绩,——如梳理1954年香港“国片概况”,比较各个出品公司的制片数量,指出“以长城为第一位”,“在影业被不景的云雾所浓掩密盖的今天”,左派阵营的长城电影公司独占鳌头 ;如梳理1955年“一年来的香港国语影坛”,指出长城电影公司的《大儿女经》“是港产片票房收入的冠军”,而“赢得舆论上广泛好评、和观众热烈拥护的”国语影片,仍由左派电影主导,譬如“‘长城’的《视察专员》、《不要离开我》,‘凤凰’的《闪电恋爱》、《一年之计》”等等。
值得提醒的是,吴其敏在这种年度电影梳理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问题发掘,如追问“昔日的观众那(哪)里去呢?”观众“最通常的选择方法”有哪些?“低潮下的上乘收入”情况如何?并逐一解答 :“经过数年的禁运,凡百事业,几乎没有一行好景,这就必然影响到中小市民的收入了。”他们节省日常开支,自然影响观影数字 ;观众选择电影“其一是纯粹以寻求消遣为目的的,……又一是以欣赏艺术、接受教育为目的的”;低潮下“内容决定一切”,“素材良好,主题积极,和现实生活有切肤之痛的”电影引领风骚 ;吴其敏由此融合事件线索和问题探索,确立20世纪50年代香港左派影评在年度电影批评书写上的高度。
相较于电影问题批评,《长城画报》的电影作品批评则明显逊色。尽管有组织12名评论者痛揭长城电影《一家春》缺点的“集锦批评”壮举,但《长城画报》的作品批评总体上成绩平平,陷于“新片推介”的广告式影评窠臼。如水公称赞《门》通过三个段落的“门”巧妙连接“一个关于婚姻的故事”,“我憎恨这一道一道的门,因之我深深地喜欢国亮兄那个《门》的作品。”或如志霄称赞《娘惹》“这个发生在华侨身上的故事,便希望成为一首恋爱与婚姻的斗争的史诗。”
二、左派报章的电影批评
1952~1962年间,香港左派电影作品批评的主要阵地不在《长城画报》,在哪里?答案是 :在左派报章,即《文汇报》《、大公报》(包括其子报《新晚报》)。这一电影批评的基本格局,类似于国共内战时期由《电影论坛》杂志主导电影问题批评。由《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主导电影作品批评的左派电影批评结构,称得上是一种整体性影评结构的继承发展。
正因如此,《长城画报》电影问题批评主将查良镛,在《文汇报》、《大公报》则是电影作品批评主将,和陈君褒等其他左派电影批评者一道,对“七人影评”和“粤片集评”在香港报章开辟的作品批评传统,继往开来。
这些左派电影作品批评,接续“七人影评”和“粤片集评”的本土关怀意识,对于香港电影和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持续关注和肯定,着意阐发其中的“思想价值”。如查良镛称道“长城”出品的《姊妹曲》“是一部好电影,因为它指出了美丑之间的分野,叫观众明白,穿漂亮衣服、美容、出风头并不美,美的是辛勤的劳动、对别人的帮助和同情、良好的品德。”这样一种将道德判断施加于审美判断之上的评价思路,正是“主题第一”批评策略的具体演绎。查良镛强调电影的工具性,“作为一种教育工具,电影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帮助观众明白事物的价值,明辨是非善恶。”
由此,观看电影是接受教育,“看电影明理”,看《姊妹曲》则明白“这部影片中表明,真正的美不是外表上容貌与衣饰之美,而是灵魂之美、人格之美”。
再如,查良镛肯定朱石麟导演的《乔迁之喜》“在我们看来就有特别一种亲切感”,指出其教育意义是“批评了用剥削与侥幸来解决经济困难的办法,指出一个人只要有一双手,肯定劳动,总饿不死”,并鼓吹“本片教人勇敢地抬起头来,不对贫穷屈服。”
又如,查良镛推崇社会主义中国制作的电影《祝福》,“夏衍的剧本、桑弧的导演、白杨与魏鹤龄等人的表演,体现了鲁迅先生所写这个悲剧的深刻意义。对于封建社会的一切,我想不出有甚更强烈的控诉和谴责。”
或如赞美《梁祝》:“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电影,但没有一部比这部更让我感动。……这样强烈地打动人心,实在是电影史上的一个大杰作。”阐释其故事是“自始就注定了的(封建)悲剧”,主题是“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反抗着封建的黑暗势力。”
查良镛自言“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喜欢《梁祝》中那样一切表现得含蓄”,钦佩梁祝“对爱情的深挚和对封建社会宣战的勇气”,“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凸显本土关怀意识的应然性与有效性。或如文化名家陈君葆评价电影《阿Q正传》“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而在思想性上存在“电影过于集中在表现阿Q个人,较少注意到表现那个时代的环境与其他人物”的不足 ;评价电影《雷雨》“整个来说……是成功的,从头到尾没有一些松懈的地方”看此片“你也许得承认世界上许多角落,仍有不少(周朴园)这样的老奸巨猾”,同样是一种作品思想性批评主导的影评模式。
本土关怀意识之外,查良镛等对于“七人影评”的“崇苏抑美”的批评路线,并未因循守旧,而是根据语境变迁而有所调整 :对于苏联电影,褒赞为主,批判为辅 ;对于美国电影,贬斥为主,肯定为辅 ;对于英国电影,倾向于肯定而非批判。
这一姿态,不再一味臣服于苏联电影,夏衍所声称的“对于苏联片……从来都是带着上课一样的心情去看的”的自我矮化已然不再。尽管查良镛等继续称赞苏联电影,如称《大歌舞会》“说明苏联艺术与人民的关系 :艺术为人民服务,同时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出来的”,或称《罗密欧与朱丽叶》“银幕上有巨大的群众场面,很正确地刻画了人民的形象,表示普通人民对这两家望族无聊的世仇存在着很大的愤慨,表示作者的意愿是与普通人民相一致的。”但是,同时亦批评苏联电影“教育意义是很强的,意思很好,可是总感到想象力不够丰富”,或称《第十二夜》“这是一部有趣的影片,虽然不怎么深刻”。
胡克表示,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联电影体系与观念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对于准共产主义的浪漫想象”。而身处充斥批判否定苏联消息的香港,查良镛等左派电影批评者面对苏联电影,自然更加冷静平和。而美国电影的优点,亦得到香港左派某种有限肯定。在社会主义中国,朝鲜战争后“停止放映一切美国影片”;而在香港,美国电影基本上畅通无阻,“香港的电影,一向是以美国影片为主”美国金援的亚洲影业公司20世纪50年代隐晦传播反共意识,美援刊物“公开提倡美国文化、美式民主和西方生活方式”,左派电影批评者亦更全面审视美国电影。如查良镛评价金·维多导演的《战争与和平》“在改编上的缺点是,过于忠实原作,以致变成了不够忠实。”或称《无比敌》“影片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因为电影用了小说的情节,然而忽略了小说的精神。”或称《刁蛮公主》“在美国的歌舞片中还算是品质比较高的”,尽管如此“,本片如果还值得一看,那主要是因为莎士比亚的缘故”。
总的来说,“这部《刁蛮公主》只采用了原作的一些情节,没有深入地表现莎士比亚的含义,就戏剧的艺术性而言,是一种比较肤浅而庸俗的解释。”这样一种对于美国电影有赞有弹的左派批评,相较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空白和沉默,尤显可贵。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保护英国片,而定了(香港)七十天必须演七天的配额以后,英国片名字出现的机会多了”(胡春冰语)。而左派电影批评者对英国电影自难刀戟相加,倾向于宽容待之。如查良镛称道《百战忠魂》“编剧与导演都不是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制作了一部好影片,因为他们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各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尊重每个人爱自己乡土的情感。”或如肯定《理查三世》“是一部值得比较详细谈谈的影片”,对原着“是一个成功的改编”,导演颇具匠心,如处理除掉希史丁斯一幕,“导演处理这场戏时巧妙地运用了一张长桌,使出席会议的人一个个地离开他。后来,希史丁斯孤零零地处在长桌的一端,另外的人都聚在另一端。观众一瞥之下,就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对于英国电影的批评姿态,是香港左派电影批评者的一种现实生存需要,是其夹缝中存在的策略化选择。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冷战高峰,无意中也让香港在文化上扮演中国与外界的沟通、转口及中介地点”,而1952~1962年间“长凤新”的香港左派电影平台,基本上是香港和内地电影交流的唯一通道。“长凤新”“开启了建国后香港和内地电影产业互动的通道”,社会主义中国成立前三十年“长凤新”是“打通这一通道的唯一执行者……还开通了内地观众和香港电影之间的心理通道。”
内地电影对“长凤新”电影有所关注,如具有政治标杆意义的《人民日报》即刊登评论长城电影《新寡》的影评,称其“在内容是、在艺术处理上,还是能吸引住我们。”而如其所述,查良镛等香港左派电影批评者对于内地电影更是积极肯定。另一方面,此间左派电影批评亦持续看齐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批评观念,“打造一个以导人向上为善,认同祖国为目标的梦工厂。”(黄爱玲语)如伍觉的《鲁迅怎样看电影》,基于毛泽东确定的鲁迅“他的思想、行动、着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立场,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鲁迅电影观念,溢美鲁迅是“最有鉴赏力和批评力的观众,在看电影上,他走在我们的前面。”又如查良镛在评论电影《战争与和平》时,联系“胡风事件”表示,“世界观与作品之间的矛盾和统一问题,自从文艺界对胡风事件展开批评以来,到今天还在热烈地讨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要评论这部电影,又不能不接触到这个基本的关键。”
20世纪50年代,面对右派阵营不断壮大,“香港左翼文艺阵营也努力因应,但似乎资金较短缺”,“如无中国幕后支持,恐连较为弱势的经营也无法维持”,左派电影批评者步履艰辛。尽管如此,由于左派批判观念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六十年代中期之前的香港……绝大多数的制造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量廉价的劳工投入其中,而他们换回的却是最微薄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左倾思潮在香港乃至东南亚社会无疑具有广泛的市场。”
总体而言,在香港左右电影批评的“唇枪舌战中,左派占了上风”,查良镛等左派批评者的电影问题批评和作品批评,续写并革新夏衍等左派批评先驱开辟的影评路向,建构着新的时代的左派电影批评标准和批评范式,不断发出有效的、进步的、爱国的批评声音。
参考文献:
[1]参见郑树森.香港在海峡两岸间的文化角色[J].素叶文学,1998(64):15.
[2]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10.
[3]罗卡.传统阴影下的左右分家[A].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M].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12.
[4]陈野.夏衍与香港电影[J].电影艺术,2000(6):25.
[5]李镇. 行走镜中——电影文本的细读[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224.
[6]林欢.电影艺术浅说之一[J].长城画报,1956(66).
[7]查良镛自白,“贝拉巴拉兹写过一部《电影理论——一种新艺术的性质与长成》的书,这书有英文译本,其中有许多精辟的独到之见。”(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54.)其《电影艺术浅说》(署名林欢)在《长城画报》四次连载完。
[8]林欢.古装电影的要旨[J].长城画报,1953(28).
[9]姚嘉衣.谈《梁祝》与《铸情》[N].大公报,1954,12(15).
[10]关于“人民电影”问题,可参见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1949-1966年》(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有称“早期伦理型人民电影”是在“和好莱坞帝国主义霸权斗争中成长”(蓝爱国. 后好莱坞时代的中国电影[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的,《长城画报》树立的“坏片子”的典型,亦是好莱坞电影,例如其刊出的《邪恶的“鬼风”来自“人间的特区”——谈“好莱坞风气”》,几乎将好莱坞斥作人类罪恶之源,妖魔化表述态度激进:“这半个世纪间,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邪魔,便是好莱坞的蛊惑性的光芒……电影这东西原非妖魔,可是在好莱坞却被制成了迷魂丹……四十年来的中国电影界,除了有意地接受了好莱坞的艺术方式之外,也无意地受够了‘好菜坞风气’的感应”(绿云.邪恶的“鬼风”来自“人间的特区”——谈“好莱坞风气”[J].长城画报,1951(7).)。查良镛的《好莱坞的悲剧——十年来的黑名单》,亦侧面佐证香港左派集体批判的“好莱坞之罪”。查良镛强调,“十年之中,美国政府从未停过向影剧工作者进行迫害。政府、右派团体、与电影公司联起手来,开列了包括数百人的‘黑名单’。凡是榜上有名的人,从此就受不到美国所有电影公司的雇用。”并联系美国电影价值标准问题,发掘黑名单事件“最最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大批有进步思想的艺术家永远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使电影以及其他文艺作品中,不敢再有任何进步的意识,使美国电影中充满了不真实的粉饰、歪曲、说谎,和污蔑。”(林欢.好莱坞的悲剧——十年来的黑名单[N].文汇报,1957,7(27).)进而联系抹黑中国形象事实,批评“向政府告密”的爱德华德米特里克“到香港来拍了污蔑新中国的《江湖客》”,“清楚地”说明其“变得多么可笑和低能”。(林欢.好莱坞的悲剧——十年来的黑名单[N].文汇报,1957,7(27).)
[11]望翠.袁仰安开拓海外市场[J].长城画报,1955(49).
[12]望翠.一年来的香港国语影坛[J].长城画报,1956(59).
[13]吴其敏.一年来的香港国语影坛.[A]吴其敏.吴其敏文集②.香港:文坛出版社,2001:276.
[14]志霄.论《娘惹》的思想性[J].长城画报,1951(7).
[15]姚嘉衣.评《姊妹曲》[N].文汇报,1954,7(31).
[16]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四)——五十年代(上)[M].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2000:195.
[17]朱虹.闪耀在同一星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31.
[18]姚嘉衣.谈《梁祝》与《铸情》[N].大公报,1954,12(15).
[19]陈君葆.电影的《阿Q正传》[N].文汇报.1958,11(25).
[20]陈君葆.关于电影的《雷雨》[N].文汇报.1961,6(1).
[21]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76-131.
[22]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87.
[23]罗卡,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4.
[24]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36-168.
[25]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22.
[26]银都机构.银都六十[M].香港:三联书店,2010:6.
[27]胡克表示,“新中国的电影理论基础由三个来源组成。首先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指导思想,……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从事进步电影积累的经验,包括左翼电影经验,抗战时期电影经验、抗战胜利后进步电影经验。再有是对苏联电影观念与理论模式的全面引进和借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形成社会主义电影理论,……构成一个庞大而完备的体系。”(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84.)
[28]金庸.金庸散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40.
[29]银都机构.银都六十[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