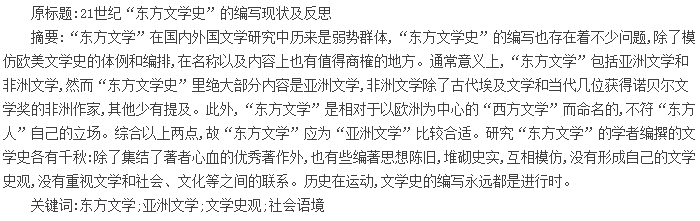
“东方文学”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历来是弱势群体,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东方文学在大学外国文学课程里或作为选修课,或直接被忽略不计;外国文学等于“西方文学”,外国文学史就是欧美文学史。只有不多的大学本科院校把“东方文学”作为一门必修课或进行专门研究。自然,这一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除了模仿欧美文学史的体例和编排,在名称以及内容上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编撰的各种外国文学史,编写模式通常是欧美文学+亚非文学。欧美文学部分在前面分为十几章,有的还分成上下编,详细介绍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而且,这里的“美”专指美国。美国一个国家和欧洲一个大洲相提并论,占据外国文学史的大部分篇幅,亚洲和非洲两个大洲挤在一起,很少能占到全书五分之一,有些书里面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至于其他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其他国家完全不见踪影。这种不合逻辑的不对等一直张扬地存在着,并没有被质疑和修改。而今,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亚非文学史部分的改写成为可能并已经付诸行动。自然,改变的过程没有十全十美,限于篇幅,本文仅对21世纪十几年来出版的亚非文学通史编著(包括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中的亚非部分)进行讨论。
问题一:“东方文学史”?
随着学术的发展,亚非文学慢慢受到国内学人的重视,关于此部分的研究逐渐细致和深化。21世纪以来,除了和以往一样包括欧美文学和亚洲文学的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之外,专门为这一区域撰写的文学通史先后出现,书名里大都有“东方文学”字样。如《东方文学史》《新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简史》《简明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论》《东方文学概论》以及《东方文学史话》等等。
由欧美文学史的附属和绿叶成为独立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并且有了新的名称,证明亚非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地位明显提升。然而,有人对这种名称转换提出了质疑。王向远认为,“东方文学”与“亚非文学”并不等同。他解释说,东方文学包括亚洲文学和属于中东文化的北非地区文学,而不是整个非洲文学。这是因为,“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在近代以前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近代以来在政治、宗教、语言、文学等各方面,更多地接受西方的支配和影响,是不宜把它划分在‘东方’的范围内的。”另外他还说,“亚非文学”容易让人想起曾经风行一时的“第三世界”的“亚非拉”文学,有着涂抹不掉的政治色彩。有了这个认识,他把1994年初版的《东方文学史通论》收入2007年出版的著作集时,做了大量的改动,把原来的非洲部分删去,只在最后一节保留了对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介绍。
事实确实如此,现已编撰的东方文学史主要研究对象是亚洲文学,北非地区只有埃及忝列阿拉伯文化一员。且在几乎所有的东方文学史里,除了上古时代专设一节讲述以《亡灵书》为其代表的古埃及文学之外,就是在当代专列一节介绍马哈福兹,除此之外,再无关于非洲文学只言片语。
实际上,“东方文学”这个名称是相对于“西方文学”存在的。国人习惯把欧美文学称为西方文学,那么,和欧美相对的亚非自然是东方文学了。
然而如果仔细地想想,事情并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既然有东西方之分,就存在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即以谁为中心来确定东西方向。在封建中国,自然是以泱泱华夏为中心,其他乃蛮荒之地,未开化之族。所以,早在《说文解字》就有“南方蛮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敢情这些地方的民族在祖先眼里都与狼虫虎豹这些动物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盛唐时期,疆域辽阔,“东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世界上最安宁、最文明的国家。……几百万中国人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而同时代的欧洲和西亚散居的人们还住在茅屋、小城堡或恐怖的山寨里。这时的西方人正苦于神学禁锢的黑暗中,中国人却思想解放、精神宽松、富于探索。”都城长安成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它的200万居民里2%是外国人。“从亚洲各处来的人———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都前来长安或留学、或经商、或旅行等等,有些人就在中途结婚生子,安居下来,甚至进入了唐代的官员阶层。印度在中国西面,其时名为天竺,故高僧玄奘是受帝命去“西天”取经,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即《西游记》。
直到清朝末年,受尽了外国侵略之苦的有志之士们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东渡扶桑,西去欧美,是为留学“东洋”“西洋”。由此可见,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前,中国人的东西方概念是以己为中心来确定的。
到了近代,随着欧洲的兴起,东西方的概念有了变化。欧洲成了世界的中心,经济落后,政治处于殖民半殖民状态的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成了欧洲眼里的“东方”。然而,这是有色眼镜关照下的东方:“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它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成了“一个被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的地方”;“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在这种社会语境下,“东方”完全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是欧洲和美国强加在亚洲地区的称谓,附带了浓郁的被殖民色彩。由此,再把欧美文学称为“西方文学”,把包括本国在内的区域称为“东方文学”,就有些不合时宜了。作为亚洲主场的中国学界在研究亚洲文学时自然要有当仁不让的主人翁姿态:立足本国,打量世界,自觉主动地发掘和传承世界上最古老的大河文明,并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中脚步坚定,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把本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
既然“亚非文学”名实不符,“东方文学”他者身份,为什么不叫“亚洲文学”呢?如此一来,既实事求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是客观地按照地理位置划分,如“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且刚好包含了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文化为中心的三大文化圈,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问题二:写什么?如何写?
21世纪以来编撰的外国文学史里,有一部分沿袭了之前的编排模式,把亚非文学放在欧美文学后面,用寥寥几十页最多上百页的篇章介绍了整个亚非文学史。基本分为三章:“上古文学”,介绍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代希伯来文学;“中古文学”,讲解印度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阿拉伯文化的《一千零一夜》;近现代文学,以日本和印度为主,代表人物是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学史通常是作为教材使用的,至少封面或内容介绍上是这么写的:“高等院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理工类大专院校外国文学教材”,等等。有一本“高等学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共十二章,只在最后一章“亚非文学概述”里用了百分之三的篇幅做了简之又简的介绍。
有些编著与时俱进,编者以全球化的眼光把整个世界文学(实际上仍然仅仅是亚非文学和欧美文学)融为一体,以时间为经纬编写整个世界文学史。从这部分编著里可以看出,上古文学和中古文学部分基本上是亚洲文学的天下:上古文学除了古希腊罗马神话、英雄史诗和古埃及的《亡灵书》之外,其他古巴比伦、古希伯来、古印度文学都属于亚洲;中古时期除了欧洲的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阿拉伯文学、波斯文学和日本的和歌物语文学大放异彩。然而到了近代,从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开始,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拨接一拨儿的文学运动先后在欧洲和美国上演,基本上没有亚洲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文学什么事儿。虽然有些编著会在最后一章介绍“正在崛起的非洲文学”,分析一些作家,比如沃尔·索因卡、纳吉布·马哈福兹以及纳丁·戈迪默等。只是,如果他们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他们代表的非洲,他们还会在当代文学史上挤得一席之位么?而诺贝尔奖分明正是“西方”文学界对他们的认同。
这其实就是一个“东方文学史”里“西方”仍旧权威的例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亚非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水平。美国人承认,“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里胡乱砍伐树木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学会阅读他们祖先的知识遗产了。”亚洲有世界上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规模最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一部寓言故事集《五卷书》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等等。然而,这些都只是辉煌的历史,今天的亚洲文学失去了自主言说的话语权,导致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学遗产无法为世界人民了解和欣赏,无法像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一样影响深远。世界瑰宝的地位若已如此,可以想象近现代的亚州文学,在邯郸学步和亦步亦趋中艰难地恪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想方设法地在世界文学中求得生存,其成果不是被忽略不计就是沦为笑谈,成为“西方”猎奇的对象。
对于这种现状,有人无可奈何,有些学者义愤填膺,道出大家明白却置之不理的事实:“有人认定东方近代文学落后了,很大程度上是用西方的标准加以衡量的结果。跨文化交流和交往的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以尊重多元文化为前提,不能用一种文学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另一种文学并做出价值判断。”“在西方侵入东方的两三百年间,东方作家,东方文学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剧烈的文化冲突中,在民族存亡的血与火的历练中记录了社会的巨大变迁和心灵的剧烈震荡。……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东方近代文学,不但具有西方文学所不具备的独特的美学价值,也具有西方文学所不具备的重大的文化价值与文献价值。”其心也忧,其情也切。这番话也许能给后来的外国文学史编撰者新的选取史料角度和自我警醒。毕竟,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学语境里,如果只有欧洲和美国文学声音一枝独秀,孤芳自赏,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来说,并不是什么前景乐观的事情。尤其作为同样被人认作“他者”的中国学界和经济政治上稳步上升的“东方”大国,应该当仁不让地揽起推介亚洲文学的责任。不可否认,语言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史料匮乏是无法逃避的困难。惟其如此,才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相比之下,单独成册的“东方文学史”内容丰富详实得多,这归功于学者们皓首穷经的努力。早在1987年,季羡林编写的《简明东方文学史》就已经做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典范,让人感受到功底深厚的学者“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境界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书里不但详细地介绍了各个时期各个区域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更重要的是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尝试着对东方四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发展理出了一个似乎规律性的东西”。后学者也不示弱,编撰出各有特色的文学史。郁龙余和孟昭毅编写的《东方文学史》,介绍了不少国内不太熟悉的亚洲现当代作家,如日本的野间宏、朝鲜的李箕永和韩雪野、印度尼西亚的普拉姆迪亚、伊朗的赫达雅特等;还把印度古代的文艺理论作为世界上三大文艺理论之一进行了推介。孟昭毅和黎跃进编写的《简明东方文学史》在每一章最后都单列一节论述这个时期的东方文学交流,“给读者一个双向互动的整体感,在拓展了学术视野的基础上便于发现和总结出东方文学史总体发展的规律性。”黎跃进的《东方文学史论》在对“东方文学”纵向发展进行总体论述的基础上,重点对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日本文学和其代表作家分别进行研究,并对中印民族诗歌的共同宗旨、日本启蒙文学与中国“新小说”的关系以及普列姆昌德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作了专题介绍。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亮点是对古代流散文学的研究,这个主题和当代因各种原因远离家乡却在异地没有归属感的人文现象很是契合。
有的学者另辟蹊径,把“东方文学”或“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王向远在《东方文学史通论》里,“根据东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并且适当考虑与西方文学的对应关系”,把“东方文学史”分为信仰的文学时代、贵族化的文学时代、世俗化的文学时代、近代化的文学时代和世界性的文学时代五个阶段。后来,曹顺庆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和王向远2004年出版的《比较世界文学史纲》都在尝试用比较的方式把世界文学融为一体,把同一个历史层面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民族文学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综合,比如世界起源神话的比较和互相影响等。与种类繁多内容却大同小异的欧美文学史而言,“东方文学史”的书写真正是花团锦簇,各有千秋。
尽管如此,有些文学史的编写还是免不了新瓶装旧酒,书里的内容只是史实的罗列,数字的堆积:作家简介、作品内容、艺术风格、主题分析、价值意义、阶级意识等等。无论再怎么标榜“本教材多次印刷,由全国十几所院校资深任课教师合编,点面结合,史论结合,条分缕析,追摹几千年来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也总有互相模仿、重复之嫌。
有一本教材的西亚、东南亚的现当代文学,各自只有四五行文字介绍,古代巴比伦和希伯来文学也只有五六行之多。这种过于言简意赅的文字不会在读者心里留下多少印象;而且,对这些内容不熟悉的读者很快就丧失了对这本书甚至书中所写历史的兴趣。究其原因,除了编者本人的治学态度外,就是对史料的掌握僵而不化,没有自己的见解和认识,无法形成个人的文学史观。“文学史观是文学史著的灵魂”。梁启超认为,应该“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历史不是抽象的,它是“历史学家在对历史文件、记录、统计、以及其它能反应这些事件的材料进行考察以后所形成的对于过去的解释和说明,可以被读者和其他的人当做“真实的”而加以接受。”这就意味着文学史的编撰者应该对历史有所反应,根据自己对史料的见解,尽量科学地阐述历史的变迁、流派的交替以及文学传统的每个链条等。这样编写的文学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彰显了个人风格,也帮助读者从不同角度思考。
另外,文学史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先后呈现的历史;文学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不是作家闭门造车的产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概论”中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文学史要全方位多视角地分析文学与各种外界因素的关系,如文化传统、时代背景、政治运动、读者群体、科学技术、对外交流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等等,把文学史置于社会大背景下,把握文学作品和思潮产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尽量还原和复活历史,以便客观公正地解读。
“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文学研究范型。”在这方面,《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值得借鉴。这部以时间为顺序的美国文学通史在讨论每一段时间内的文学事件时,总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紧紧相连,以优美流畅引人入胜的文字带领读者走进文学史,和文学史里有血有肉的作家交流。编撰者尤其注意当时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学形式的发展,决不会把文学流派紧紧限定在准确的年月日里,一如国内欧美文学史的流派划分。
历史是在不断运动的,每个年代应该有每个年代的文学史,亚洲文学史也不例外,因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以阶级分析为特色的文学史已成明日黄花;一直以来亚洲文学史没有受到重视的事实貌似还在维持现状,但种种努力已在涌动,独立成书的各种亚洲文学通史、断代史,亚洲国家国别史、专题研究等就是证明。同时,非洲文学史、大洋洲文学史、拉丁美洲文学史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的国别文学史也陆续有人在做。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如此丰富而便捷,共同利益让人类必须学会互相关心和了解,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应该受到忽略和歧视,何况曾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亚细亚,现在依然拥有自己的优势和魅力,亚洲文学史的再书写永远都是正在进行时。
参考文献:
[1]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二卷)[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93.
[2]许慎.说文解字[M].长沙:岳麓书社,2006:78.
[3]黎跃进.东方文学史论[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456-457.
[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5]约翰·梅西.文学史纲[M].孙青玥,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3.
[6]王向远.中国的东方文学理应成为强势学科[M]//王邦维.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25-26.
[7]季羡林.简明东方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3.
[8]孟昭毅,黎跃进.简明东方文学史·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何乃英.东方文学研究会与东方文学学科建设[M]//王邦维.东方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9.
[10]佴荣本.文学史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1]埃默里·埃利奥特.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M].朱通伯,等,译.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12.
[1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96.
底层文学是21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而中国文学又是东方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相比西方文学,讨论东方文学视域下的底层文学对中国文学更具亲缘性和启发性。从东方文学史来看,从上古埃及的劳动歌谣到中古印度的故事文学以及阿拉伯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