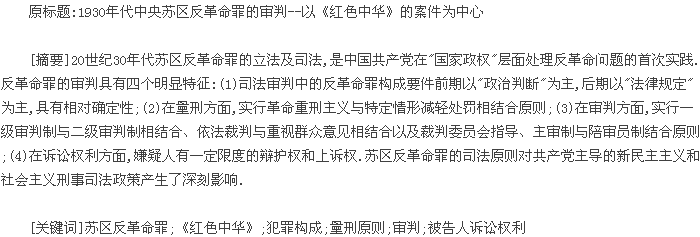
1930年代,中共领导的苏区政府①鉴于复杂而严峻的社会形势,颁行了一批以惩治反革命罪为中心内容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②、《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⑤(下文引用该个法律文件时不再标注)等;以法律文件规定与现实犯罪情形为根据,苏区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治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反革命分子的司法行动,此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层面处理反革命罪的首次实践,此际反革命罪的立法与司法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对于刑事司法的探索成果,其中的司法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法制建设依然有借鉴价值.
当前学术界对于1930年代前期中央苏区的反革命罪研究,鲜有专题性学术论文,主要是法制史专着的章节性解读,张晋藩总主编、张希坡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第十卷(新民主主义政权)⑥一书是代表性的成果,该书"工农民主政权的刑事法规"、"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机关"、"工农民主政权的诉讼制度"、"工农民主政权的新型监所制度"四章内容涉及到反革命罪立法的实体性与程序性规定.其他亦有一些革命根据地法制史专着涉及到此类问题,如卓帆《中华苏维埃法制史》⑦一书"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部分地解析了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立法与司法的特点.此类研究成果基本上附属于教科书式的法制史专着,力求完整而全面,宏大叙事风格明显.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拟以《红色中华》⑧登载的反革命案件为基本资料,同时联系苏区法律文件和司法环境,着重从司法审判中的犯罪构成、量刑原则、反革命罪的审判以及被告人诉讼权利四个方面进行解析,以探求1930年代苏区反革命罪审判之特质.
一司法审判中的犯罪构成
何种行为构成反革命罪,也就是反革命罪的构成要件,这自然是反革命罪立法和司法的首要问题.
1931年《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与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下简称《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关于反革命罪构成要件的根本性法律,也成为苏区政府审判反革命罪嫌疑人的效力最高的法律依据.
《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即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该法律文件效力自1931年12月开始,到1934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宣布废止其效力.也就是说,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多数时间内,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是基本性的刑事法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规定的主要是反革命罪程序性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则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合体.六号训令对于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只是宣布了纲领性的、概括性的处罚原则,文件号召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反革命的组织和活动,要给他以彻底的消灭","对于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首要分子,应该严厉处置(如宣告死刑等),对于从工农贫民、劳动群众出身而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分子,以及附和的分子,应该从宽处置(如自新释放等)".
在此情形之下,苏区反革命罪审判实践中的构成要件,只能适用(借用)中共革命政策的"政治判断",当然必须依据第六号训令的基本精神.当时的判决书一般逻辑为:第一步列举被告的反革命事实,第二步根据第六号训令来判决;没有说理充分的"判决理由"部分.如1932年5月5日作出的瑞金县苏裁判部第八号判决书("谢步升反革命案件")在叙述了谢步升的反革命事实之后,"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双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①.1932年5月24日作出的瑞金县苏裁判部第十六号判决书就"钟同焕反革命案件","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钟同焕处以死刑.倘若双方不服,在一星期内可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司法观念之下,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带有浓厚的"政治判断"色彩,或许司法者认为当事人反革命行为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详细阐述"判决理由",故出现类似"独断论"式的判决书结构.
如上所述,反革命罪的构成要件委之于中共革命政策的"政治判断",司法实践中反革命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并非混为一谈."朱多伸反革命案件"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与反革命案件区别的典型案例,1932年6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21期刊登了临时最高法庭对此案的"法字第十七号"批示意见:
瑞金县苏裁判部第二十号判决书关于朱多伸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伸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及冒称宁石瑞三县巡视员等等,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伸曾组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七十二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此批瑞金县苏裁判部.
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六日③本案件清楚地表达了临时最高法庭的立场,普通刑事案件与反革命案件在司法审判中是能够而且应该区别处理.本案件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声音,更准确地划分了反革命罪与普通刑事犯罪,有利于更好地孤立少数反革命分子,给予普通刑事犯以恰当的处理①.
1934年《惩治反革命条例》承接了六号训令的法律效力,该条例明确地提出了"反革命行为"("反革命罪")的概念,其第二条规定:"凡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法,都是反革命行为."②此处的"反革命行为"也就是"反革命罪",反革命罪的犯罪客体是"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苏维埃政府"即是国家法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从逻辑关系分析可以说是社会法益.该条文可以视为反革命罪概括性的构成要件.《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至三十条规定了反革命罪的28种行为类型,有军事行动、反动宣传、破坏社会利益、危害苏区经济等诸多方面.在列举28种反革命犯罪的行为类型之后,该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本条例所未包括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相类的条文处罚之."在定罪科刑方面,本条款明确规定允许以类推适用的原则来处理反革命犯罪行为.综合《惩治反革命条例》全部条款,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本条例确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与刑事类推相结合的司法原则③;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具有确定性(为主)与适度开放性(为辅)结合的特点.
1934年《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定了反革命罪的构成要件,以"法律规定"方式代替了第六号训令时期构成要件的"政治判断",亦可说是反革命罪构成要件的"政治判断"之"法律化"表达.
反革命罪构成要件关系到嫌疑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在现实司法审判中又是如何呢?
反革命罪内的此罪与彼罪区分问题,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可能没有区分的必要,在留下来的司法文书中没看到相关记录;反革命罪与普通犯罪的区分,如前所述,苏区最高司法机关进行了强调和规范.
嫌疑人的罪与非罪问题,才是反革命罪构成要件的实质内容,现有司法资料非常匮乏,整体评估苏区的司法实践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1932年10月的《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则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该报告汇总统计数据如下.
全苏区各级裁判部七、八、九三个月所判决的犯人列举如下:
一、枪决的:二七一人,二、苦工的:三九九人,三、监禁的:三四九人,四、罚款的:一四一人,五、无罪释放的:四八一人,六、共计:一六四一人.……所判决的这些犯人,政治犯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普通的刑事犯占百分之三十④.所谓"政治犯"即是反革命犯,故该报告可以用来分析反革命罪的审判实践问题.分析该报告,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这一段时期,"无罪释放的"占所判决人数的29.31%,比重还是相当高的;这说明苏区反革命罪的审判注意把握犯罪构成要件,准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二反革命罪审判的量刑原则
苏区反革命罪审判的量刑原则,较有特色的有:
1.实行革命的重刑主义1931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规定:"对于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首要分子,应该严厉处置(如宣告死刑等)."六号训令并没有明确哪些行为该判处死刑,1932年10月15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写给寻邬县苏裁判部的指示信指出:"此次判决的蓝昌绪,据保卫局的控告、审判记录及判决书所载,如(一)组织暗杀队,吃血酒发誓,(二)不要从红军要从白军,(三)开会要杀政府及共产党的人,(四)敌人进攻时,鼓动群众不参战,做反宣传.有一二项事实即应判处死刑,以镇压反革命的活动,不料你们只判处他半年苦工."①此封指示信可以看作一份苏维埃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反革命罪死刑犯量刑的意见,提供了一个判决死刑的大概标准.
根据前述1932年10月《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全苏区各级裁判部7、8、9三个月所判决的犯人,政治犯约占总数的70%,普通的刑事犯占30%;判处死刑(枪决)的占到受审判人数的16.51%,占受处罚人数的23.36%.所谓的"政治犯"即反革命犯,此种比例基本反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关于反革命犯的执行死刑情形.应该注意的是,此处的数据是经过裁判部审判的人数.从法规条文和实际情形分析,尚有一部分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等机构直接处死的反革命犯人.
2.未遂犯、附和犯、胁从犯等情形以及自首分子、自新分子减轻处罚原则1934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二条确定了未遂犯和附和犯减轻处罚原则,附和犯可以理解为现代刑法学的从犯.该条例第三十三条确立了胁从犯及主观上缺乏违法性认识的情形减轻处罚原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减轻处罚的量刑原则,幼年犯人应接受感化教育一类的保安处分.该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凡犯本条例所列各罪之一,未被发觉,而自己向苏维埃报告者(自首分子),或既被发觉而悔过,忠实报告其犯罪内容,帮助肃反机关破获其他与谋犯罪者(自新分子),得按照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该条款确立了自首分子、自新分子减轻处罚原则.自首分子、自新分子的从轻处罚原则在当时司法活动中大量适用,成为一种分化犯罪分子团伙的有力武器.
3.工农分子和有功绩的人减轻处罚1931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号训令强调处理反革命分子"一定要分别阶级成分",这是苏区反革命罪量刑的基本原则.1934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工农分子犯罪,而不是领导的或重要的犯罪行为者,得依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量减轻其处罚."重申区别阶级成分的司法原则,这意味着工农分子与地主资产阶级同罪异罚.当时的司法判决坚决地贯彻了阶级路线,如1933年9月24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针对"宜黄县裁判部的判决书"的第十三号批示,作出以下改判:"欧尚求一年监禁太轻.查被告人勾引红色战士反水去投降白匪,虽未达到目的,而其计划已实行,本应处以死刑,但念他为雇农,着处监禁三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一年.""涂老细判决苦工六个月不能照准.查被告人是雇农,在欧土豪家里做长工时,带红军去反水,完全是受欧土豪婆指使之所为,同时又是雇农分子,加以教育感动即可释放,原判苦工着即取消."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批示中,欧尚求本应处以死刑,但考虑他的雇农身份,判决监禁三年;涂老细被释放,"雇农分子"是主要理由之一.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跟欧尚求、涂老细一样的工农分子犯罪得到了减轻处罚的待遇.
工农分子减轻处罚原则也并非绝对,如果工农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变节,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力量,此原则就不会采用.如临时最高法庭第一百一十八号批示(1932年10月15日)对于"寻乌县苏裁判部第五号判决书"指出:"蓝昌绪一名,成分虽是贫农,但根据政治保卫局的控告及审判记录和判决书所列事实,实系叛卖阶级坚决反革命分子,亦应处以死刑."①石城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第五十一号布告《宣布反革命的侦探谭智春死刑》(1933年4月公布)指出:"该犯虽系贫农,他积极做反革命活动,出卖阶级利益,成了我们工农群众的死敌人.为着要巩固政权向外发展,要保障工农革命的胜利,将该犯捆赴刑场,执行斩决."②工农分子减轻处罚原则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的政权性质相吻合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③.尽管从法理上,工农分子减轻处罚"这一规定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④.但在当时情景下,书本的"法理"必然要让位于革命的"情理".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法庭以镇压地主资产阶级为目的,对于工农分子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国民党法庭以镇压工农阶级为目的,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犯罪则一般处置较轻,法庭的作用完全给政权的阶级性决定了."⑤毛泽东从政权阶级性角度论证了当时苏区司法的阶级路线问题,可谓一语中的.
1934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功绩的人减轻处罚的原则.此原则应用最典型者,要算"季振同、黄仲岳反革命案件".
1932年8月10日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写道:
根据季、黄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者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故对于该案特作如下的决议:
(一)季振同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计算起;(二)黄仲岳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计算起;(三)朱冠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计算起;(四)张少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计算起;(五)高达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计算起;监禁期满后并剥夺公民权五年.
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萧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中,季振同、黄仲岳、朱冠甫、高达甫、张少宜等五人由于领导或参加宁都暴动的原因,被改判较轻的处罚,充分体现了有革命功绩的人减轻处罚的司法原则.
三反革命罪的审判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审判权,1931年《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第一项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之后以原告人资格,向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或裁判部)提起诉讼,由国家司法机关审讯和判决."此项规定适用于"成熟区域"和"半成熟区域".在"新发展区域",县或区政府的司法机关审讯反革命分子,拟具判决书,报告省司法机关作最后之判决,但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罪恶昭着,经当地工农群众要求处决者,当地政府得迅速执行处决之,无须得省政府许可(1931年六号训令第五条).在"暴动区域","当地革命群众"有直接处决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权力(1931年六号训令第六条),这意味着"当地革命群众"直接行使对反革命分子的审判权及执行权①.可见,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司法审判(成熟区域和半成熟区域)、司法审判和行政手段并用(新发展区域)、革命手段(暴动区域)等三种.司法手段、行政手段、革命手段构成了苏区政府终局处理反革命分子的三种基本方式,此一"三足鼎立"之执法格局贯穿苏区时期.
关于反革命案件的司法审判,苏区政府的制度设计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一级审判制与二级审判制结合1932年6月9日公布的《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级裁判部的权限":区裁判部审理一般不重要的案件,其判决处罚强迫劳动或监禁的期限,不得超过半年(第三十条);县裁判部是区裁判部所判决案件的终审机关,同时又是审判有全县意义的案件之初审机关,有判决死刑之权,得省裁判部的批准之后才能执行,只有与省政府隔断的县苏裁判部,不得省裁判部的批准,可以执行死刑(第三十一条);省裁判部为县裁判部所判决案件的终审机关,同时又是审判有全省意义的案件之初审机关,有判决死刑之权,但须送临时最高法庭批准而后执行,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省裁判部有最后处决案件之权(第三十二条).依据本条例,案件有初审和终审,死刑原则上由上级裁判机关批准②,只有县或省与上级政府隔断情形例外.《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规定是对1931年六号训令的具体化落实,二者的基本法制精神是一致的.
1934年4月8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宣布废止1931年六号训令和1932年《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对反革命的审判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依据本司法程序,区裁判部、区肃反委员会,有权审讯和判决当地一切犯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之权,对于新区边区等特定地域或紧急动员时期的反革命及豪绅地主之犯罪者,有一级审判之后直接执行死刑之权(第二条);省县两级裁判部、肃反委员会、高初两级军事审判所,均有审讯、判决与执行判决(包括死刑)一切犯人之权(第三条).各级裁判机关的权限极为广泛,拥有了包括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权力,死刑批准制度事实上被取消,二级审判适用范围相当一部分让位给一级审判.概括地说,在前期,苏区反革命罪处理以二级审判、死刑批准为基本原则,后期则转变为一级审判扩展与二级审判式微的局面.
2.裁判委员会指导、主审制与陪审员制相结合1933年5月30日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第六条明确指出:"每个案件先经过裁判委员会的讨论,讨论一个判决的原则,给审判案件的负责人以判决该案件的标准,使判决上不致发生错误."①该条款确立了裁判委员会对案件进行指导的司法原则.
1932年《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法庭须由工人组织而成,裁判部长或裁判员为主审,其余二人为陪审员."关于陪审员的产生,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陪审员由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出来."在《红色中华》登载的所有案件中,皆能查阅到法庭关于主审和陪审员的组成名单,如1932年9月11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审理"赖子春反革命案件"法庭组成人员有:主审傅源标,陪审员谢增荣、廖友贵二人②;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对"谢步升反革命案件"上诉审的组成人员有:主审梁柏台,陪审员:邹武、钟文芳二人③;可见主审与陪审相结合是当时的基本审判制度.
1932年10月的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认为,陪审制表明"苏维埃法庭,就是群众的法庭,在工农群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法庭审判人员必须由司法机关裁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体现了一定的司法民主性因素.该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主审与陪审员在决定判决书时,以多数的意见为标准,倘若争执不决时,应当以主审的意见来决定判决书的内容."主审的意见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是决定判决书内容的关键因素,条例规定了主审负责制的审判原则.陪审制与主审制度结合,体现审判权的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与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内在逻辑是吻合的.
裁判委员会指导、主审制与人民陪审员制相结合的审判制度是共产党人革命性的创造,在中外司法审判制度史上相似者并不多见.
3.依法裁判与重视群众意见相结合1931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强调:"各级苏维埃政府,接到本训令之后,应严格地遵守执行,如果违背本训令所规定的原则,须受严厉的制裁."可见,第六号训令确立了严格执法、依法裁判的原则.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刑事法规亦规定了重视群众意见的条款,司法裁判中渗透了群众路线的思维.同样在1931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第五条规定,"在新发展区域,即在革命政府的建立尚未满六个月的地方","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罪恶昭着,经当地工农群众要求处决者,当地政府得迅速执行处决之,无须得省政府许可"."工农群众要求"成为当地政府"执行处决"的主要条件之一,一定程度可以取代"省司法机关最后之判决".从文本的逻辑关系分析,尊重"工农群众要求"正是六号训令文件所规定的"严格执法"、"依法裁判"的应有之义.
1933年4月2日,石城县苏政府裁判部关于"宣布反革命赖裕香、曾瑞珍、熊流民、温善珍、许向华等死刑"的布告典型地表达了当时的司法精神,该布告宣布:"根据多数群众迫切要求,我们为了坚决保障工农利益起见,将该犯赖裕香、曾瑞珍、熊流民、温善珍、许向华等五犯捆赴刑场,执行斩决死刑."④"多数群众迫切要求"成为执行死刑的基本 "根据"之一.
根据1931年第六号训令的基本精神,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对于罪恶昭着,事实确凿,群众要求处以死刑的阶级异己分子,应速即执行死刑,然后报告上级裁判部备案"(第一条)."群众要求"成为对阶级异己分子速即执行死刑的要件之一.该指示第三条明确规定:"解决任何案件,要注意多数群众对于该案件的意见.""多数群众意见"成为审判案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第二条规定:"新区边区,在敌人进攻地方,在反革命特别活动地方,在某种工作的紧急动员时期(例如查田运动,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等等),区裁判部、区肃反委员会,只要得到了当地革命民众的拥护,对于反革命及豪绅地主之犯罪者,有一级审判之后直接执行死刑之权.""当地革命民众的拥护"成为区裁判部、区肃反委员会对于反革命及豪绅地主之犯罪一级审判之后执行死刑的重要条件.
1934年3月20日出版的第164期《红色中华》第3版有一则"瑞金壬田区枪决反革命:三个宣传迷信破坏苏维埃的坏蛋"的报道,该报道说:
县裁判部在群众的要求下,于本月九日判决了该三犯的死刑,当日在壬田执行枪决,并公布了三犯的罪状,大略如下:
一、李永昌,男性,现年五十六岁,瑞京壬田区刘垅乡人.
二、余万隆,男性,现年六十一岁,瑞京壬田区竹塘乡人.
三、钟广婆,女性,现年五十一岁,瑞京壬田区竹塘乡人.
以上三犯的反革命事实,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领导反动迷信,进行反革命阴谋,串通一般无赖之徒,大造封建迷信谣言……该李、余、钟三犯应处以死刑,以保障苏维埃政权,以保障群众的利益.
在本报道中,"县裁判部在群众的要求下,于本月九日判决了该三犯的死刑","群众的要求"成为判处该三犯的死刑的基本依据,倒没有说明判决的具体法律依据,这充分说明了群众意见在苏区审判中的分量.
四反革命犯人及嫌疑犯①的诉讼权利
在国家机关追诉和审判过程中,反革命犯人及嫌疑犯有限制性的辩护权,1932年《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被告人为本身的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法庭的许可."汇总《红色中华》登载的全部反革命案件,从裁判机关的"判决书"和国家保卫局的"控诉书"的文本分析,没有一例反革命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案例.这可能是基于反革命罪的敏感性和对敌斗争的严峻性,苏区法庭行使司法裁量权"不予许可"犯罪嫌疑人的委托辩护.
反革命犯人及嫌疑犯在一定范围内有上诉权.1931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第二条规定:"中央区及其附近的省司法机关,作死刑判决后,被告人在十四天内得向中央司法机关提出上诉."被告人只有此种特殊类型的上诉权,其他的情形并没有规定.
1932年4月20日签发的临时最高法庭第二号训令对于江西省裁判部第一号第二号判决书(1932年4月3日作出)纠正道:"该两案的判决只在该本级裁判部是最后的,但该案的被告人在十四日内应许有上诉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第二项内已明白的规定."②临时最高法庭训令再次强调了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于1932年4月3日作出的第一号判决书,就"朱××等三人AB团反革命案件"作如此判决:"他(朱××)是最坚决的一贯反革命到底的分子,应处以死刑";吕××"应监禁三年,自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计算起,又从监禁之日起,剥夺选举权五年";"杨××应监禁三年,自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计算起,又从监禁之日起,剥夺选举权五年";"以上三犯,判决是最后的,没有上诉权"③.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于同一天作出的第二号判决书④,就"萧××、颜×二人AB团反革命案件"判决道:"该犯(萧××)的反革命事实与罪恶,已经昭着,应依照肃反法令着予处决";颜×反革命"事实昭着,本法庭根据肃反法令着予处决";"以上被告人等的判决,是最后的没有上诉权".江西省裁判部第一号第二号案件包括了两种情形:一是死刑案件,如朱××的死刑和萧××、颜×二人的被处决,根据六号训令文本的直接含义,自然可以有上诉权;另一种情形是非死刑案件,如吕××和杨××的三年监禁判决,在此种情况下,临时最高法庭第二号训令强调被告人的上诉权,则是对六号训令上诉权条款的拓展性解释.
临时最高法庭训令对六号训令中被告人上诉权的拓展性解释在1932年6月公布的《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得以验证.该裁判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级裁判部所判决的案件,在裁判书上所规定的上诉期间内,被告人有上诉权."该条同时规定"上诉的期限规定为二星期,由审理该案件的法庭,看该案件的内容而决定上诉的日期".可见本章程规定的是弹性的上诉日期,最多不能超过14天,1到14天范围内是当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1932年5月24日作出的瑞金县苏裁判部第十九号判决书就"钟盛波反革命案件","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钟盛波,处以枪毙,倘若双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限内可以向临时法庭上诉"①.1932年9月11日作出的福建省苏裁判部第六十八号判决书就"赖子春反革命案件","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被告人赖子春(即老六子)处以死刑.倘若不服,限三天期限内,可向临时最高法庭提起上诉"②.同样依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号训令,两个案件的上诉期限分别规定了"一星期的期限"和"三天期限",上诉期限的相对法定特征至为明显,与现代刑法的上诉期限绝对法定不同.
关于上诉权问题,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第五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上级批准制度,实行上诉制度.犯人不服判决者,准许声明上诉.并规定声明上诉之期最多为七天."③由于形势紧张,此处上诉的最高期限由14天减为7天.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第五条同时规定:"在新区边区,在敌人进攻地方,在其他紧急情况时,对反革命案件及豪绅地主犯罪者,得剥夺他们的上诉权."该条款剥夺了特定区域和紧急情形中反革命犯人的上诉权,以应付日益严峻的苏区社会态势.
20世纪30年代反革命罪的审判是苏区革命政权的基础性工作,因为这关系到确定罪犯、分清敌我的政治大局;苏区各级裁判机关肩负重任,不辱使命,严格执法,出色地履行了岗位职责.由于革命情境的复杂性,处理反革命罪亦出现一些偏差④,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问题时指出:"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⑤此处"错误的处理"包括职务的撤免,或者刑事的追究甚至反革命罪的处罚.
苏区反革命罪的立法与司法是中共以"执政党"身份积累的第一笔治理国家的刑事诉讼经验,苏区的司法原则如处罚加重与减轻结合、裁判委员会制、陪审员制、重视群众意见等,对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央苏区的医疗卫生法治化建设与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环境相结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医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建设过程中重视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思想政治教育,及注重对伤病军人的优待工作。...
随着中央苏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的深入,必然导致中央苏区法制史渐成独立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