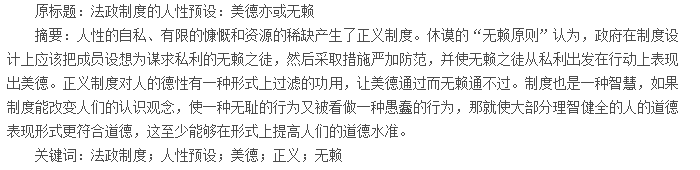
休谟是西方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思想家,他将西方传统的肇始于柏拉图的唯理主义转向为经验主义,在经验主义基础上将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道德观转向为情感主义道德观,并在情感主义道德观的基础上将西方传统的法政人性预设由“美德”转为“无赖”,这种转换体现了休谟的法政智慧,如老子所言的“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休谟的“无赖”预设绝非是他对“无赖”情有独钟,而是他对“美德”有着清醒现实的认识,他是通过对“无赖”的预防来为“美德”开拓出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这是法政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高超智慧。休谟这位“无赖原则”的始作俑者也是追求“美德”的满腔热忱者和实现“美德”的超强能力者。
一、自私和有限慷慨的人性
自休谟之后,西方的法政逐渐步入正轨,这印证了休谟“政治可以解析为科学”[1]5的预言。休谟认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基础,人性本身是“这些科学的首都和心脏”[2]7,法政科学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的科学之上。休谟强调人的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2]8,而反对在此之前的两种人性假设:(1)以洛克为代表的、诗人虚构的“黄金时代”,物质极大丰富和人心极大善良,财产、责任、公正和不公正这些概念也随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果人的慈爱和大自然的供应都是无限度的,那么作为正义前提的利益计较和产权区分也就不必要了,“把人类的慈善或自然的恩赐增加到足够的程度,你就可以用更高尚的德和更有价值的幸福来代替正义,因而使正义归于无用。”[2]535例如,父母对年幼子女慈爱到足够程度,就不会起诉年幼子女说那件衣服是“我的”;大自然所恩赐的空气极其丰富,没有人起诉说哪里的空气是“我的”。(2)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哲人设想的“自然状态”,物质极大匮乏和人心极大邪恶,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不断战争,是人类自私和野蛮的本性未受约束的必然后果。例如,强盗对受害者毫无慈爱之心,也不会起诉受害者说那件东西是“我的”而是直接抢劫那件东西;对于大自然根本就没有的东西,也不会有人起诉说这东西是“我的”。休谟认为这两种假设对于人性的认识都是不适当的,这样一种人性状态是否总是存在,假若它确已存在,能否延续相当长一段时期以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状态,这是完全值得怀疑的。这两种假设在法政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卫国阶级都具有金银铸造的“美德”,卫国阶级不可以有任何私人财产,因为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另一方面,法西斯暴政则信奉“丛林法则”,实行赤裸裸的强权法政,对人性做了“恶魔”预设。
对于绝对的“美德”,根本没有必要用正义规则加以防范;对于绝对的“恶魔”,任何正义规则也无法发挥规范作用。但人性的准确描述不是“美德”也不是“恶魔”,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无赖”,“无赖”人性预设对正义规则提出强烈的呼唤。休谟认为“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供应”[2]536,“稀少的供应”是自然的性质,“自私和有限的慷慨”是人的性质。
人性的这两个特点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通过彼此之间的限制而不使另一方极端化,有限的慷慨对自私的限制使其不至于下滑为兽性,而自私对有限的慷慨的限制使其不至于升华为神性,只有介于神性、兽性之间的人性和自然稀缺性质的结合才诞生正义规则。公道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状况,如果根植于人类胸怀中的或者是完全的温良和人道,或者是完全的贪婪和恶毒,就会使正义变成完全无用的。
人性就是介于善恶之间的“无赖”,这与西方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还有所不同,因为在“无赖”中,魔鬼与天使并不是分为两半,而是交织在一起,至于最终显现出来的是天使还是魔鬼,那就仰仗制度保证了。在这种人性预设基础上,休谟提出“无赖原则”的法政宣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督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说,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1]27休谟是说,古往今来,一个不变的人性是,除极少数的高尚君子和卑鄙小人外,占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谋求私利是行动的主要目标,但“有限的慷慨”之存在也能够使他权衡利弊,遵守正义规则,使自己的自私行动不至于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危害,而是有益于社会公益的。正因为人性中“有限的慷慨”,休谟对西方基督教自私“原罪说”也持批判态度:“自私这个性质被渲染得太过火了,而且有些哲学家们所乐于尽情描写的人类的自私,就像我们在童话和小说中所遇到的任何有关妖怪的记载一样荒诞不经,与自然离得太远了。”[2]535有研究者因此把休谟当做“西方传统中少见的性善论者”[3]233,笔者也是不赞同的,因为在休谟的人性中,有限的慷慨终究是第二特征,自私作为第一特征与西方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而非“革故鼎新之举”[3]233,休谟整合这两个相对立的人性特征,就表明休谟既不是性善论者也不是性恶论者,休谟这个观点类似于孔子人性观“性相近习相远”,而区别于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休谟和孔子承认人性中所蕴含的善恶对立统一的矛盾,是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构成了法政社会的人性基础。如果人性中没有恶的一面,人们是极大的善良,那么用以区别“你我他”的正义法律也就没有必要诞生了。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单单性恶导致不了正义法律,动物也是恶的,动物界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绝无法律规则可言。我们固然不难看到动物之间的“亲子之情”,动物中的父母也可以为子女做出牺牲,但那是一种本能而非善性,动物也不可能将这种本能扩展到血缘关系之外,因此,动物不可能遵守以一定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规则,哪怕这种一定自我牺牲的遵守规则会带来更大的长远利益。动物既然不可能遵守规则,因此动物界也不可能诞生规则。
人类和动物相比,人性高于兽性的地方正在于“有限的慷慨”,也就是相比恶性而言要稀薄得多,但毕竟还有善性,这就避免人性的“极大的邪恶”,使人类之爱超越动物的本能、超出动物狭小的血缘关系,人类因此能够遵守以一定的自我牺牲为前提的规则,而这种一定自我牺牲的遵守规则会带来更大的长远利益。大部分“有限的慷慨”的人都因此希望在一个规则的调整下,不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同时也希望别人同样地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正义规则因此被制定和遵守。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人和动物的区别正在于人是能够遵守规则的动物。
因此休谟从情感主义论述了正义规则的产生:“这样,正义就借一种协议或合同而确立起来,也就是借那个被假设为全体所共有的利益感觉而确立起来;在这种感觉支配下,人们在做出每一个单独的正义行为时,就都期待其他人也会照样行事。”[2]538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发扬“有限的慷慨”的善性一面,以暂时牺牲一点利益来遵守规则而获取长远的更大利益,改变动物界“弱肉强食”的本能性活动,变成遵守善良规则的意识性活动,在极大丰富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精神世界。两个强盗从绞刑架下经过,甲对乙说:“没有绞刑架该多好,我们可以放心做强盗。”乙回答说:“如果没有绞刑架,人人都去做强盗,那才糟糕呢!”乙的认识是深刻的,正是法律的威慑作用,大部分人才放弃做强盗的兽性,强盗成为个别现象,而不像动物界那样强大者吃掉弱小者成为普遍现象。尽管人性无法改进,但社会制度可以改进,好的制度可以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彰显人性善的一面,从而使人类在道德本质并无改进的情况下,道德的表现形式却大有改进。
二、“美德假设”机制下的无赖和“无赖假设”机制下的美德
休谟的“无赖原则”表明,政府成员善与不善,并不主要取决于政府成员本身,而在于民众是否具有防范的自主性:如果民众把政府官员当做无赖之徒并有着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一个政府成员即使本质上是无赖的也必然是表现良好的,否则就会被“无赖假设”机制淘汰掉。
在“无赖假设”机制下,“无赖”是墓志铭,“良好”是通行证,纵是本质上的无赖之徒,从理智和自身利益出发,也没有理由不表现出良好。反过来如果民众把政府成员当做天使、恩人而丝毫不加防范,那么,一个政府成员即使本质上是良好的也必然是表现无赖的,否则就会被“美德假设”机制淘汰掉,在“美德假设”机制下,“良好”是墓志铭,“无赖”是通行证,纵是本质上的善良人,从理智和自身利益出发,也有理由表现出无赖。
“无赖假设”机制是指,政府在制度设计上,把每一个官员当做自私自利的无赖,然后对这种无赖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无赖行为在理智计算上是不利的,必然会被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所抛弃,哪怕该员的道德修养不怎么样。在“无赖假设”机制下,无赖之徒出于利益的考虑也会有较好的道德表现形式,只要他还没有丧失理智。
在这种机制下,官员的贪婪是“有贼心而无贼胆”,因为这种机制对腐败处罚严厉,腐败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这种机制对腐败的查处严密,通过公布财产、阳光作业等措施编制密网,使腐败分子很少有漏网之鱼,从而打消官员在腐败问题上的侥幸心理;腐败无异于跳崖、自残和引火烧身,只有精神病和过于侥幸的官员才会做出这样的愚蠢之举。“美德假设”机制是指,政府在制度设计上,把官员当做道德模范而不加防范或疏于防范,官员的腐败行为若得不到严惩就对他是有利的,自利的本性使他把腐败当做理智和利己的行为,整个官场逐渐为腐败分子所控制住,清廉的官员反而被当做另类而失去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官场生态,官员很难有好的道德表现形式而是成为活生生的无赖了。
有人说,人性如水往下流,官员的腐败是必然的。这句话在“美德假设”机制下才是符合逻辑,在“美德假设”机制下,官员满口仁义、好话说绝;但同时满手肮脏、坏事干尽;美丽的光环掩盖丑恶的真相,这正是“美德假设”机制下有腐败的“一体两面”。如果我们改变这种机制,就发现这句话在“无赖假设”机制下才是不符合逻辑的,在“无赖假设”机制下,官员说少做多,做得比说得好,不可能出现美丽的光环掩盖丑恶的真相,因为无真相可被掩盖,这正是“无赖假设”机制下无腐败的“一体一面”。固然人性如水往下流,但如果政府机制也是这样,那就会出现萨达姆、卡扎菲这样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在“美德假设”机制下都曾是全民歌颂的领袖,谁敢不歌颂他们就会人头落地,他们行使权力就像水往下流一样不受任何限制,直至他们被推翻。但是在动力机器下,水又由下往上流,“无赖假设”机制就相当于那台动力机器,使政府官员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必须按照机器所要求的轨道逆流而上行使。也就是说,这种“无赖假设”机制就能使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使不是水往下流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水往上流满足公众的利益。如果这个机制才是民主法治的机制,每一个民众都是监督官员行为的主人,每个官员不过是民众监督下的雇员而已,不好好干就被淘汰出局!
休谟的无赖原则被人类的法政曲折发展史反复证明,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员、领袖,如果我们进行的人性预设是“美德”因而不进行制度上的防范,那么他们绝大部分最终都会原形毕露为“无赖”和“恶魔”。我们相信,在原则上大部分人是好的,而面临实际的利益选择时,如果缺乏正义制度的约束,遵守正义规则不利而违背正义规则有利,大部分人都不会遵守正义规则而变坏的;如果正义规则的约束到位,遵守正义规则有利而违背正义规则不利,大部分人会遵守正义规则而变好的。如果说自然科学提升了人们获取资源的能力,那么人性科学的法政设计则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美德”水准,尽管这种提升仅仅是外在的、形式上的,缺乏康德所说的内在动机,被康德称做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康德认为,道德是纯粹无功利的,“在交易场上,明智的商人不索取过高的价钱,而是对每个人都保持价格的一致,所以一个小孩子也和别人一样,从他那里买的东西。买卖确乎是诚实的,这却远远不能使人相信,商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责任和诚实原则。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这有利于他。”[4]13在康德看来,商人不是出于纯粹责任而是出自利己的诚实,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道德价值的。那么官员不是出自纯粹责任而是出于利己的诚实,也没有什么道德价值。显然,我们不能说康德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对人性的估计和要求过高,无论是官是民,有多少人是出自纯粹责任而表现出诚实的道德品格呢,只有极少数道德君子才能做到,而且不管什么道德运动,都不能使道德君子由极少数变为大多数,康德所要求的这种不计功利的纯粹道德是很不现实的,其实践价值也极其有限。那么,退而求其次,在不能做到出自责任的诚实之外,无论官民,出自利己的诚实不也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吗,不也能够带来社会利益而成为一种称道的品质吗?所以,一个好的制度,不是无视和消灭利己自私,而是正视和调整利己自私,使人的利己自私行为符合正义规则的要求,符合社会公益,带来社会利益,“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刺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2]535
在正义规则的调整下,自私能够发挥勤奋、节俭、拼搏、成就等积极面,激发人们的工作和创新热情,并能遏制懒惰、奢侈、懈怠、平庸等消极面,打消人们通过歪门邪道发财致富的幻想。休谟也承认,高尚的道德能使正义归于无用,但是人性并不是高尚的道德,而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道德君子从来都有但也都是凤毛麟角,对于大多数人和社会来讲,正义比道德更为必需和有用。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就会解体,回到野蛮状态;而遵守正义规则,则会给人和社会带来无限的利益。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回答千万种,在休谟看来是人能够制定和遵守正义规则,动物则不能。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协作提高能力、分工增长才干、互助减少偶然意外事件的袭击,从而使人在和动物竞争中胜出,并促进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文明。
因此,通过正义规则对利益的调整,使诚实的行为有利,不诚实的行为不利,那么理智正常的人都会放弃不诚实而走向诚实,尽管这种利己的诚实如康德所言缺乏道德价值,但对人类的法政文明来讲是必要的和珍贵的。所以高全喜在研究休谟的政治哲学时指出:“一个人的行为可以从他的动机来考察其善恶的本性,但是如果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那么善恶问题就被正义问题所取代了。”[5]107也就是说,在这种人性预设的法政设计里,人的道德本质不会改变,人内心的贪婪、自私和少量同情心的秉性依然如故,但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大为改观:贪婪不仅依然是无耻的,更是显得弱智,所以不是这种设计里有理性人的明智选择,也就无从表现出来。自私的目的是利己,但这种设计里惟有利人才能利己,损人必将损己也是必须放弃的不明智选择,所以自私也是以不违背美德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再变得面目可憎了。休谟非常自信地认为,不是人之善,而是制度能够使坏人也可为公众的幸福服务。人性并不乐观,但立基于人性的法政设计却使我们有理由乐观,在民主法治国家的健全制度下,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首先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健全理智的人都不会做的,就是这种制度提升了人们的道德表现形式,而这种制度又是建立在预防人的道德“无赖”上,这就是我们制度认识上的“二律背反”。
公仪休很喜欢吃鱼,当了鲁国的相国后,很多人向他送鱼,都被他一一回绝,“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也就是说,公仪休拒不受贿,并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很高尚,毫无自私利己之心,出自责任而表现出诚实,而是因为他受到正义规则的调整,出于自私自利而表现出无私和诚实,完全符合老子所提出的“反者,道之动”和“无私故能成其私”的观点。可以说,绝大部分商人和官员的诚实,不一定和不仅仅出自道德修养的要求,更是理智功利的要求。只要制度健全,正义规则调整到位,自私的人也会表现出无私,在道德本质上只具有有限道德的人却能够在行动上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即使那些自私贪婪的官员也会在行动上理智地选择廉洁,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腐败,内心贪婪的官员和清正廉洁的政府并行不悖,就在于立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设计出的遏制贪婪的正义制度。
正义制度有赖法治的保障,法治就是依法治理,法律规则在本质上是诚信,诚实信用是民法的霸王条款,法律规则保护诚信行为,制裁不诚信行为。如果诚信的规则被谎言的潜规则取代,那将是什么状况?握权的官员、掌刀的医生、分配好座位的小学班主任都能够发挥极致地以权谋私,面子工程、数据工程、豆腐渣工程总是吸引人们的眼球,假文凭、假职称、假身份乃至假离婚打造着全民造假大军,地沟油、瘦肉精、毒生姜腐蚀普通民众的心灵,人们面对谎言节节败退直至缴械投降,越是做着见不得人的事,越是用动人的言语去掩盖,谎言如无限发酵的泡沫一样攻城略地,直至诚信的阵地尽失。
人们在精心编织谎言的谋人中哪能够诚实谋事呢,日计有余岁计不足,一群群本是精明的人却做不成实事。
规则是利益的公正调整,意味着为了他人和社会的更大更正当利益而放弃一己的不正当小利。规则具有逻辑可持续性,某人在某次遵守规则中损失一点私利,必然在他人的遵守规则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回报。这是一种以德报德的高尚行为,当别人也以德报德时,这种高尚行为又演变成明智的有利行为,其结果是人际交往的诸方“诸赢俱好”。可以说,没有正义就没有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人们遵守正义规则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甚至每一个人在核算起来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得到了利益;因为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入野蛮和独立的状态。”[2]538
正义规则使人们放弃舍远求近的狭隘目光,愿意为了长远的利益而遵守正义规则并牺牲眼前的一些利益,如别人的东西不偷不抢,公家的东西不贪不占,否则社会就会乱套,社会公益没有了,个人的利益也没有了。在正义规则对利益的有效调整下,“社会上每一个成员都感觉到这种利益:每个人都向其他的人表示出这种感觉,并且表示决心,愿这种感觉来调整他的行为,假使其他人也照样行事的话。”[2]538也就是说,一个人遵守规则是以其他人也遵守规则为前提,这就要求正义规则的普遍有效,这也是法治社会的真谛,惟有法治社会规则才会得到普遍遵守。“履行许诺”
被休谟称为正义三原则之一。所谓履行许诺就是遵守已经制定的规则,通过相互为对方服务而达到双赢。“因此,我就学会了对别人进行服务,虽然我对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好感;因为我预料到,他会报答我的服务,以期得到同样的另一次服务,并且也为了同我或同其他人维持同样的互助往来关系。因此,在我为他服务了、而他由我的行为得到利益以后,他就被诱导了来履行他的义务,因为他预见到,他的拒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2]561-562这就是说,虽然人是自私的,遵守规则会有一点眼前和暂时的利益损害,但对于可获取的长远和更大的利益是有利的,遵守规则也就成为理性人的明智选择,并不需要多么高尚的道德。
规则盛行,谋事不谋人,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单个规则行为的于己不利放在大社会这个宽阔的视野里都是有利,在“利”他人又被他人所“利”的良性循环中,任何人都只是规则偶然的失利者却是必然的得利者,遵守规则都是一时的输家和最终的赢家;守规则的这种既道德又明智的行为却被讥讽为迂腐,也是源自鼠目寸光的人生哲学,只想着这次的“失之东隅”,却没想到下次的“收之桑榆”,一时的“小失”遮蔽了长远的“大得”。
当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时,遵守规则不利而遵守“潜规则”有利,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除了少数执着的君子外,“潜规则”会成为人们行为的信条,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谎言遍野、恶事丛生,绝大部分人处于不利地位而要求变革,重新树立规则的权威和效力,“潜规则”的盛行是张扬人性恶的一面,是法治的反面,也具有暂时性。规则有效而潜规则无效时,遵守规则有利而遵守潜规则不利,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遵守规则受到道义和利益的双重嘉奖,遵守潜规则受到道义和利益的双重惩罚,潜规则在冷落中溜之大吉,除极少数道德极败坏的人外,规则成为人民信奉的教条,黄钟歌唱瓦釜哭丧,诚信遍布、好事丛生,绝大部分人处于有利地位而维护规则的权威,规则盛行是张扬人性善的一面,是法治的正面,具有持久性。通过“无赖原则”设计而导致政府遵守正义规则的美德,是有利于人类整体利益和每一个公民的正当个人利益的,最终会成为每个选民、政府、官员的必然选择,低调的人性预设带来乐观的政府美德。
三、余论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马克思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6]82除了极少数道德君子外,占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有逐利的行为取向,这是人的本性,不可改变的,绝不可能通过一场“斗资批修”的思想道德运动就能够将人们自私自利的本性消灭掉,这种道德乌托邦运动的危害性已有前车之鉴。所以马克思又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103
虽然腐败表现为谋取私利,但清除腐败并不在于抛开利益,而在于正视利益,通过健全公正的法律利益调整机制,使腐败和利益逆向,而清廉和利益同向,官员还是从利益出发,自觉地抛弃腐败而选择廉洁。一旦腐败不利,清廉就不再被嘲笑为迂腐的呆子行为,而是一种深谋远虑、大智若愚的精明行为,那么官员清廉的内在动力呈几何级增长,腐败就不再是不可医治的癌瘤,而是药到病除的小病。显然,这种“药”就是法治。在前法治社会,腐败是不可能根治的,而法治社会是一种全新的利益调整机制,这种机制里,没有腐败生存的土壤。例如,北欧的小国芬兰,曾是腐败盛行的国度,现在却成了最清廉的国家,根除腐败也是靠民主、法治、制衡、监督、公开、透明、教育等,但是做得很彻底、很到位。官员如果有吃、请、受贿等腐败行为,基本上意味着仕途的终结;企业如果有商业贿赂等行为,立即丧失信誉,成为其他企业不愿打交道的孤家寡人,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公款请客,从总理到科员,何人、什么菜、多少钱,都要上网列清单,让阳光杀死一切病菌。在芬兰,腐败之愚蠢不亚于一个在十层楼上的人看到楼底下一堆黄金而纵身跳楼,只有神经病才会这么干,只有神经病的官员才会腐败。因此,尽管芬兰的官员和其他国家的官员一样自私自利,但那种机制下,他们是通过清廉来实现自己的自私自利的。芬兰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库西马基任职30年里,没有一个人以任何形式向他行贿。这说明,在法治社会,法律最大,权力服从于法律,就不会有腐败,消除腐败在法治社会绝不是天方夜谭,相反,在法治社会,腐败成了稀少的不正常行为。在法治社会,清廉亦或腐败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理智判断问题,理智正常的官员,不管内心如何龌龊,在行动上必然是干净的,内心的无赖转化为行动上的美德,法治是反腐败的最佳选择。
但中国只是处于“法治进行时”,腐败依然是全社会瞩目的大问题。令人警醒的是,道德滑坡已经从官场向民间蔓延。山东潍坊地区农村,长期使用已被禁用的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生姜。因为有毒,他们自己不吃这种毒生姜;也因为检验严格,他们出口的姜并未使用“神农丹”农药;吃上这种毒生姜的就是不知情而又没有严格检验做保障的国内同胞。毒生姜事件呈现给我们道德滑坡的表象,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益机制的调整出了问题,使“见利忘义”成为人们切实可行的行为准则。例如,检疫机制形同虚设。假如我们矫正了方向,使“无义有利”寸步难行,“有义有利”大行其道,行为的义与不义并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素养,而是利益机制的调整方向,理智正常的人不论其道德品质的优劣,都会选择“有义”而不是“不义”之举,因为这种选择对他们有利[8]。
如果制度设计为无赖,那就有一种防范无赖的措施,反而使其无法无赖,表现出一定的美德;反之,如果设计为美德,就不会防止其无赖的一面,最终表现为无赖。实际上,人的美德与无赖是交杂并行的,只是在某人身上美德多一些,在另一些人身上无赖多一些,制度对人的德性有一种形式上过滤的功用,让美德通过而无赖通不过。因此预设无赖的好制度下无赖很少,预设美德的坏制度下美德也很少。应该说,制度只是过滤器,不会提升或降低一个人的道德;但是制度也是一种智慧,如果制度能改变人们的认识观念,使一种无耻的行为变为一种愚蠢的行为,那就使大部分理智健全的人的道德表现形式更符合道德,这至少能够在形式上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
参考文献:
[1](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5]高全喜:《休谟的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