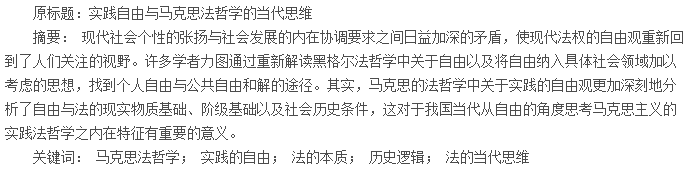
随着对社会学现代诊断的逐步加深,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和解、个人权利与公共秩序的兼容以及法在其中的应然作用,黑格尔的法哲学尤其是其"自由意志"的思想重新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和讨论,而事实上马克思对自由的深度解读以及由此建立的丰富而深刻的法律思想更是值得我们反复研读、揣摩和深入思考。
一、现代法权自由观及马克思的批判继承
尽管人们对自由与正义的追寻由来已久,但明确提出"自由"是天赋人权思想的是近代契约论者。启蒙思想家的自由观奠定了现代法权的基础,也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民主平等的理论渊源。霍布斯认为: "自由人……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办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碍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1],而自由的特征在于"法不禁止即自由"[2].卢梭进一步区分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从自由观的角度来说,即人们通过让渡一部分自由,订立社会契约,实现超越自然体力和才智不平等的法律和道德的平等,以防个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或曰共同利益。"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 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3]
黑格尔接过现代法权的大旗,批判继承了契约论者的自由观,在其法哲学思想中明确提出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是"作为理念的自由"[4].同时,黑格尔又指出,自由意志"在定在中进入了量的范围和质的规定的领域,从而与此相应地各有不同",也即自由意志和人格都不是只停留在抽象的思维中,而应该在其"具体而明确的定在"[5]中理解。黑格尔将自由视为绝对价值,又试图将对自由的保障纳入复杂具体的社会领域,体现了对现代法权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扬弃,成为现代法权自由思想的重要里程碑。但他并没有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剖析自由的经济制约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特征,而是脱离伦理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将国家视为伦理通过自然的发展而完成的统一。国家的本性不在契约关系之中,它既不是"一切人与一切人的契约",也不是"一切人与君主或政府的契约",而是"伦理理念的现实"[6],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7],从而深陷国家神秘主义的窠臼。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复兴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霍耐特结合对社会病理的现实诊断,致力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将黑格尔法哲学重新解读和诠释为"规范的正义理论",关注黑格尔对于个体自由和普遍的自由意志之间关系的描述,以期寻找个体自由得以实现的社会和制度条件,建立"以一元道德为基础的多元正义"[8].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时期,非常认同现代法权自由与理性的价值理念,并以此为武器激烈批判当时德国的保守政策。他认为德国的《书报检查令》违反了自由的原则,"问题不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新闻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9].可见这时候他对于自由的理解基本上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但是,随着马克思逐渐接触到底层民众的生活,他开始认识到观念、理念的背后存在着的现实利益。在生活的实践的推动下,马克思从经济学维度出发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法哲学乃至整个现代法权的质疑和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直至旷世巨著《资本论》,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从表面上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自由而平等的,交换主体拥有交换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无产者只有将劳动力卖与谁的自由,并没有卖与不卖的自由。在生产和资本循环的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强加给工人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收益,"交换领域的自由与平等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马上就会变成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10].经济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必然带来政治和观念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仅仅是私有财产的自由,平等也不过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基础上的平等,形式的自由掩盖了实质的不自由,人沦为物的奴隶。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揭露了现代法权自由观的抽象性和空洞性,以及现代法权思想推动下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建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虽然自由和平等无比神圣,但是,自由与平等如果不能根植于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市民社会的利益制约中,就只能是理想化的抽象概念。
可见,马克思接受和继承了现代法权对自由的价值追寻,但又将其扎根在社会实践的坚实土壤中,强调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国家和历史特征对自由实现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的自由观可以称之为"实践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哲学理论也一定是关注现实、从实践出发的"实践的法哲学"."启蒙的现代性法权哲学的确具有崇高的人类精神,体现了对人本身的关怀。但这种对人的关怀并不能单纯依靠抽象的法权观念去获得,现实的人的利益的实现只有在现实的斗争中才能达到。"
二、实践的自由和法的本质
市民社会是自由与法的现实基础。自由是利益占有基础上的权利展望,而非仅仅是道德领域的价值追求。特权社会必然产生等级制度,拥有生产资料进而掌握政治权力的特权阶级确实会视自己为人,但却难以尊重无权阶级为人。因此"视自己为人并尊重他人为人"的自由在等级社会难以实现,直至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才为自由的充分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2],其实质是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和实现,核心是自由交易、等价有偿、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以商品的交换为生产目的,因此首先承认对财产的私人占有。私有制使市民社会的成员相互认可为商品的所有者,并以此为基础自主决定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民社会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体现出来的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平等交易等原则都是对自由最大限度的张扬。
法为这种自由意志的充分行使提供了秩序的保障。它虽然表现为制约和强制,但这种强制并不是对自由的反动,相反的,正是规则的划定和秩序的建立使主体在体现自己自由意志的同时不会损害他人的自由意志,避免了因为社会成员各自为争取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和社会失序。"市场经济天然地包含着尊重人,将人当人看待的现代社会文明思想和人文观念,包含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契约观念,包含着弘扬法律平等与自由的法治观念"[13].
市民社会为法和法律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首先,市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意义上法和法律的出现。市民社会的交换建立在自由和自愿的基础上,换言之,交易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使用暴力和掠夺的手段获得利益。因此市民社会的法是真正以保护自由和正义为其价值目标和本质属性的,这一点使其与等级社会捍卫特权,以镇压和威慑为目标的传统法律迥然有别,人类的民主进程也由此展开。其次,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法律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市民社会的良性发展依赖法律对私有制和财产权利的有效保护。当私有利益发展为社会成员普遍的权利要求时,法律的作用也随之表现为对民权主张的支持,即对"权利"的捍卫和对可能侵犯和干扰人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抗衡。法律显现出了"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内在本质要求。第三,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法和法律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分工使得独立的职业法学家阶层以及独立行使法律的司法部门渐渐发展起来。前者使法和法律获得了理论思辨和概念区分的可能,后者使法和法律获得了专业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机会,在二者的合力下,法和法律逐渐与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相分离,成为拥有独特内涵特征、价值理念、逻辑过程和外在表现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
表现为国家意志的法律体现了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协调。在自由意志和利己主义的呼唤下,市民社会拥有了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发展规律和价值追求。这些规律是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构成了对政治力量和"特权"强力干预的反对和否定。因此,"守夜人政府"的消极立场成为启蒙思想家普遍认可的理想社会模式。市民社会的成员力求使自己自由的人性得到承认,并将这种权利要求称之为"人权".但是,人权并不是赋予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 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产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14]
现代社会机器化生产带来的社会分工使得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利益活动通过交换得以实现,由此形成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利益分化和共同利益。囿于天然禀赋和自然条件的不同,人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在追求人权的过程中对利益的占有和共同利益分享的能力也并不相同,在利益争夺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逐渐激化。"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15].为了缓和这些矛盾和冲突,需要找到一种普遍认可的方式,既能"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又能将这些利益控制在共同利益的范围之内"[16],国家以及表现为国家意志的法律应运而生。在政治国家中,统治阶级需要捍卫其作为统治者的共同利益,并将这种利益扩大为全社会认可的一般利益,以维护其统治秩序。这种利益既不同于社会成员的个人意志,甚至也不同于统治者内部个人的主观意志,因为"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17].可见,法律是社会成员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个别意志相互协调、相互妥协而形成共同意志的产物,是对体现共同意志的公共自由或曰社会自由的捍卫。而法的本质则在于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这两种自由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则可能互相冲突。当法的内在本质通过一定社会统治者的强制性设定,以法律的表现形式固定于外时,追求个性自由的人权精神也就淹没在实现公共自由的国家机器之中,法律的价值不仅体现自由和平等,更体现公正和秩序。
其实,即使将个人自由协调一致为公共自由,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这种自由也可能是不自由的。在市民社会发展的最成熟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成员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实现了政治地位的人人平等,因此,实践中存在的现实社会等级区别只能根据占有财产的多寡划分。在赤裸裸的经济利益面前,人们越来越屈从于对金钱和物质的膜拜。商品、物质和金钱异化为市民社会的主导性因素,吸引或者强迫人们的行为乃至思想,人渐渐沦为物的奴隶,在蝇营狗苟的物质追求中彼此倾轧,相互分离。
现代社会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各种公益性质、非营利性质的民间社团和民间组织作为第三方力量,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市民社会的内涵压缩为追求社会公益的非官方组织。市场、市民社会、国家隐然三足鼎立,分别以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追求目标。至此,公共自由也应划分为体现社会成员集体意志的社会自由和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自由。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的冲突和协调更为复杂。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应然之法以国家强制力的实然之法律表现出来时,更需要增加这一调和的作用,既要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实现,又不能以牺牲社会自由和社会发展为代价,还要行使国家专政的职能,维护统治秩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自由。
亚细亚生产方式下自由和法的独特历史逻辑。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迥异于欧洲的东方社会,分析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普遍存在于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国家和法律发展的深刻影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所有制形式是"把土地看做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18]
也就是说,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以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并且这些财产归共同体所有,实际上是归共同体的代表即君主所有,而社会成员个人并不享有财产所有权,顶多是财产的占有者,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君主制使得东方社会缺乏私人利益产生和追求的主体参与因素,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无需经常性地依赖他人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使得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交换无法充分发展起来,整个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的封闭小农经济之中。这样的经济结构强力制约着东方社会自由意志的成长,也决定了东方社会法律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逻辑。
一方面,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人们没有对自由的需求,或曰对自由的向往程度较低。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使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以通过自己得到,商品价值不必精确计量,对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等价有偿和契约自由等观念的需求并不迫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社会交往的层次较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超稳定的社会要求的是"守旧"而非"革新",是"本分"而非"自由"."给东方国家带来的是极其顽固、冷漠的小农意识。这使得东方社会的个人既没有关注自身和他人权益的市民意识,更没有关注公益和政治权利的公民意识"[19].
另一方面,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法律不是对自由的捍卫而是对专制制度的保障。土地的君主所有制为专制政体提供了坚实的土壤。由于不承认个人的财产所有制,法律不可能以保护私人财产以及由此衍生的个体自由为其价值目标,而只能为君主专制政体服务。以中华法系为例,其本质属性是捍卫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以威慑力维护君主的统治权。在高压的法律氛围下,百姓对法律的情感是畏惧和疏离的; 其核心精神是彰显德行,维护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律的儒家道德主体构建的宽容平和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法律精神的熏陶下,人们崇尚容忍和退让,而非纠结于是非曲直本身; 其价值目标在于以诉讼为手段,实现"无讼"的和谐社会秩序; 其法律信仰是建立在对"明君"或"清官"的信任和膜拜的基础上,实现的实际上是"人治"前提下的主观正义。凡此种种,都与以捍卫公民权利为核心,强调张扬人性,实现正义和自由的现代法治精神迥然有异。在传统的东方社会,法不是"自由的定在"而是专制的打手。
现代意义上自由和民主的观念只能在以交换和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现代法权思想也只能伴随着反封建的思想和政治革命的隆隆炮声而被提出。古老的东方社会只有打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推翻专制体制,尤其是消除思想和观念上保守而固步自封的小农意识,才能迎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和对自由意志的肯定。
三、马克思法哲学的当代思维
马克思的法哲学建立在对现代法权的批判继承之上,既反对基于抽象自由观,无视法权之现实基础,发生现代法权异化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哲学,又反对全盘否定现代法权,因而对自由的一般概念也加以拒斥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哲学,"既划定马克思法哲学与作为现代性形态的近代形而上学法哲学之间的原则界限,又划定马克思法哲学与作为乌托邦形态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原则界限"[202].马克思法哲学的当代思维从其实践的自由观出发,应当定位于"实践的法哲学".
社会主义法的实质是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自由意志的现实要求。古代罗马法律文化中的权利观念主要体现在私法领域中对个人经济权利的保障,包括权利主体制度、所有权制度和债权制度。近代契约论者掀起"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说,是个人权利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扩大和延伸。马克思的法哲学进一步将权利看做是法的重要价值属性。
法的本质及其价值属性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专制社会的君主所有制下,君主意志必然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法和法律为贯彻和巩固君主意志,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对自由观念的钳制和对等级秩序的维护,强化作为统治阶级实现专政目的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权力能力,表现为权力制约权利。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崛起,使平等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实现了社会成员政治上的平等,人权主张和自由意志通过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资本主义社会"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就是为了实现权力制衡,防止国家的权力滥用侵犯了个人权利的主张。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基础决定了不同的主体拥有财产的多寡不同,因此实现权利的能力不同。大的财产所有者可以凭借对财产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更强力的调动将其意志凌驾在无产者和小的财产所有者的意志之上,他们的权利要求转变成了权力压迫,无产者和小的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变成了屈从于财产压力之下的不自由。
共产主义社会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解放,私有制的消亡使人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权利与权力高度融合。在当代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和公有制为主体使人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法是全体人民权利主张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法与法律,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基本统一。
但是,由于市场和商品经济仍然存在,私有财产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人与人的现实差异也不可否认地存在,自由和权利主张的实现还是会发生一定的异化。因此,社会主义的法以权利制约权力,不仅指的是平民意志对抗贵族意志,更主要指的是普通民众对抗特权阶层。这既要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府职权接受社会民众监督,还要求法律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和保护,以尽力消减因财产占有的差异带来的人的异化。
社会主义的法体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和解。现实的自由包括三个层面: 体现为个性张扬的个人自由、体现为国家意志的国家自由以及体现为社会公德的社会自由。个人自由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自由追求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社会自由追求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发展。因此从社会成员个人的角度来说,法和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其实就是主体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而当法和法律保障国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时候,无疑会相应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其实就是主体在法律上应当履行的义务。如果说权利是社会成员从社会中获得的福利,义务则应该是其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福利与责任是相对应的,因此,权利与义务理所当然应该是对等的,这也是现代法权要求下法已经被公认的基本原则之一,实际上是对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包括国家自由和社会自由) 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要求。
但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难以实现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的一致或曰和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使市民社会的成员以私人利益为目标,所谓人权也主要是对个人自由无障碍实现的权利要求。过分强调和支持抽象人权,可能会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被侵害为代价。尤其是随着市民社会的深入发展,一些私人财团获得了更加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国家和社会的干预和影响能力越来越强大,公共自由被迫进一步向其个人自由让步,市民社会就会异化,法的价值随之分裂。
个人自由和公共自由,尤其是社会自由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问题的主要症结之一,也是社会学界越来越关注的课题。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建设,是对传统市民社会的超越,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新型社会。
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统治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和政治国家的利益追求统一起来。巩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法因此实现了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的和解。不仅如此,当代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人格培养,要求从狭隘、自私的市民进化到公民。这里的公民不是指法学意义上拥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而是哲学层面上"通过教育的不断启蒙而建构的一种'人格',即第欧根尼寻找的'真正的人'".这样的人不满足于获取私人利益,更关注社会的公益,其视野不局限在私人领域,更投向社会的公共领域,宁愿放弃一部分私利换取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的道德和信仰推动了公民在法和法律中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人权和公民权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的法和法律对人权的保护通过对公民权的保护完成,由此,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也找到了和解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的法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法。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亚细亚所有制下法律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深刻剖析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法哲学的构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和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历史发展绝不可能是孤立的,必然与社会的文化传承有不可割裂的联系。因此法和法律的移植一定要与其本土法律资源相结合,而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现代的法的理念。
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秩序格局,维护社会秩序主要依靠三种权威力量: 政府权威、伦理权威和法律权威。政府权威和伦理权威都是为等级制度服务的,而表现为中华法系的法律制度以礼法为其核心,"出礼入刑"的法律原则证明中华法系从来就不是"自由的定在",而是专制的工具。
从夏商周直至清末,中国一直没能萌发出自由的思想和对自由的要求。近代中国畸形的社会还是不能为自由提供发展的土壤。因此中国是缺乏自由的传统和追求自由的勇气的。时至今日,中国人其实仍然习惯于将自己的意志屈从于某种权威之下,期待由外在的力量替自己做出决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简单地引入自由观念和现代法权思想是不现实的,不仅可能使自由流于空谈,甚至可能犹如给一个不懂火之危险的孩童玩火的权利,带来严重的危害。当人们认识到了自由的可贵,却没找到实现自由的正确途径时,自由可能会被某些人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式的随心所欲,等同于无视政府管理,无惧道德规范,无视法律规则,挑战一切权威,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范。
所以,虽然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历史潮流注定自由和民主是当代中国法哲学构建的必然基石,但自由的深入人心和良性运作却有一个逐步引导的过程,是现代法权思想的辩证继承与中国本土法律传统相契合,随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从传统逐步走向现代的过程。
参考文献:
[1][2](英)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黎廷弼译。 商务印书馆,1985: 163,164.
[3](法)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80: 30.
[4][5][6][7](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2010: 36,99,82,253,29,96,75,257.
[8]王凤才。 黑格尔法哲学: 作为规范的正义理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 19 -2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1995: 167,443.
[10][11]武建敏。 马克思对现代性法哲学的批判与超越[J]. 法学杂志,2011(1) : 61 -64.
[12][15][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人民出版社,1960: 41,37,378.
[13][16][19]秦国荣。 市民社会与法的内在逻辑[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1,214,38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M]. 人民出版社,1957: 143.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卷[M]. 人民出版社,1979: 472.
[20]刘日明。 当代境域中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4) : 48 -53.
[21]李朝东,王金元。 教育启蒙与公民人格建构[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10.
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有一个伴随其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学者们基于不同的思考问题的视角,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
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从其早期作为理想主义法学的承继,到其实现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哲学观的演进,直至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全面形成,始终包含着新与旧、成熟与不成熟各种观点的矛盾复杂和尖锐冲突。所以,找寻合适的视角对于在历史情境中探索青年马克思法...
马克思法哲学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就不是教条式套用文本,而是在把准马克思法哲学精神的基础上,针对我们的历史语境和具体问题,确立法治建设的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