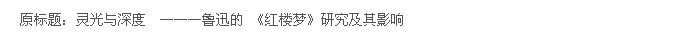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鲁迅的学术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他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学术观点、使用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红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很大。对此,“鲁学”研究界和“红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在鲁迅的《红楼梦》研究是否自成体系方面还存在一定分歧。本文无意对这些分歧进行辨析,只是认为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值得从学术思想发展史角度进行梳理,这种梳理不但有助于加深对其学术思想体系形成和发展演变的理解,也有助于深化对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一、鲁迅《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贡献
毋庸讳言,发端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是在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其中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西方学者惯用之思维方式的借用以及一些新术语的引进介绍,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基础。从文学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和发展的角度看,鲁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也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针对中国古代文学缺少真正悲剧所提出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就《红楼梦》研究而言,鲁迅提出的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断、概念如“人情小说”、“悲凉风格”等,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其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后来者继续深化对《红楼梦》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术方法的演进,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鲁迅在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优秀古典小说的研究中,始终具有清醒、自觉的史家眼光和文学史意识,将其纳入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之中,并在总结概括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进程中审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基于此,鲁迅给予《红楼梦》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鲁迅的高度评价,奠定了《红楼梦》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心目中不可动摇的“经典”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红学”的发展。特别是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就一方面将高鹗之续书与前八十回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给予续作较高评价;另一方面辩证地看待问题,看出了其他续作硬写一个拙劣的大团圆结局的致命缺点。鲁迅在比较原着和各种续作后指出:“《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
……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
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①其次,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并不局限于对作者作品的分析,而是站在审视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高度,将作者生活的时代和作品产生的有关历史文化背景纳入其小说史研究框架中,给《红楼梦》一个准确的定位,使其研究做到以点带面,从局部走向整体,具有深广博大的特色。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红楼梦》是在第二十四篇,但早在第十九篇鲁迅就在“人情小说”的名目下论述《金瓶梅》,因为他看到了此书对《红楼梦》的深刻影响。而在第二十六和二十七篇,在论述清代狭邪小说和侠义小说时,仍注意到它们所受《红楼梦》的影响,这就给读者以十分清晰的发展演变线索,是真正具有文学史眼光的分析论述。
再次,鲁迅在《红楼梦》及其他古典小说研究中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框架模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和框架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红楼梦》研究为例,鲁迅在整整一章的篇幅中,既有对作者生平和作品产生之时代背景的论述,又有对作品流传情况和版本的分析研究,由此可见鲁迅深知“知人论世”之法。他的论述既有对作品主人公形象的分析,也有对整部作品故事情节的概括,更有对作品艺术特色的论断等。其中鲁迅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精到分析及独特判断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及“爱博而心劳”等语,早已成为不易之论。再如他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仅露‘悲音’,殊难必其究竟”②以及对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③的比较性分析评价,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鉴赏品味和对作品思想意义的深刻理解。
最后,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所提出和使用的一系列名词术语,均具有学术独创性和示范性,尽管有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在今天看来不够周密、严谨,但在那个时代代表了此类研究的最高水平。例如他提出“人情小说”概念,并称《金瓶梅》、《红楼梦》等为“人情小说”之代表作,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类型划分范例。“人情小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作为和“神魔小说”、“讽刺小说”等平行的概念提出的:“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④所谓“银字儿”,是指宋代说话人所讲述的小说故事,因讲述这些小说时以银字管吹奏相和,故有此称。鲁迅在论述明代之人情小说时把《金瓶梅》列为代表作,在论述清代之人情小说时则视《红楼梦》为代表作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①由此既可看出鲁迅对这两部杰作之内在联系的认定,也可看出鲁迅对“人情”或“世情”之内涵的认定。不过,对于“人情”与“世情”两个说法是否完全可以互换,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
在笔者看来,鲁迅提出这些概念重在题材差异,意在区分小说类别,并不看重同一类别中作品的艺术水准是否一致。如在人情小说中既有《红楼梦》这样的巨着,也有《玉娇梨》、《平山冷燕》这样的平庸之作,而在神魔小说名下也不乏《西游记》这样的杰作。认真考辨鲁迅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似乎“世情”小说侧重于展示社会风貌和针砭时弊,而“人情”小说则更侧重于刻画人物情感世界,重在对人性的揭示。如《金瓶梅》和《红楼梦》都被鲁迅视为人情小说的代表作,但鲁迅对前者的评价是:“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②而在谈到《红楼梦》时,他的重点始终在于阐释他对宝黛悲剧的理解、对贾宝玉内心悲凉情怀的剖析以及对曹雪芹感时伤怀之“自叙”性创作的肯定:“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③这“在先”的人情小说,显然包括《金瓶梅》。对此,陈平原在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有专门章节论述鲁迅如此分类的学术意义及对后世影响,如“后世的小说史家几乎无不借重鲁迅的小说类型设计;……正是在与前代和后世的小说史家的对话中,鲁迅的小说类型理论确立了其独立地位。”④鲁迅把《红楼梦》视为“人情小说”代表作的意义,还在于这是对中国古代小说一贯将其中荒诞不经、鬼神狐妖的内容视为当然的一个“反动”、一个拨乱反正。《红楼梦》正是在借描写日常生活传达人生哲理方面达到极高造诣,才为鲁迅看重:“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⑤鲁迅在这里最为强调的,应是曹雪芹如何能够将普通平庸繁琐的日常生活素材,改造加工为焕发出浓郁诗意的文学巨着。鲁迅晚年在一次大病初愈后曾写过一篇《“这也是生活”……》,其中有一段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会对《红楼梦》所写的普通生活有那样深刻的理解:“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⑥的确,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和表现,不仅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红楼梦》的创新性研究,还在于他在冠以“清之人情小说”的标题下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分析《红楼梦》,从作品版本到作者生平,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同类作品的影响。这种论述形式对后来的文学史撰写影响极大,以致后来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专着,都把《红楼梦》作为专章论述。当然,有些文学史在论述《红楼梦》时没有冠以“人情小说”的名目,但都给了《红楼梦》整章的篇幅。
在谈到《红楼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时,鲁迅特别注意从小说类型演变角度以及社会生活角度进行分析,如分析《儿女英雄传》及其作者所受《红楼梦》影响时,鲁迅把目光放在《红楼梦》所表现“人情”之影响演变方面:“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文康晚年块处一室,笔墨仅存,因着此书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亲历,‘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并序语)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①这里鲁迅从作者身世及思想境界角度评判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深得社会历史批评真髓,当是此类批评的范例。
关于《红楼梦》的主旨,在蔡元培的“索隐说”和胡适的“自传说”之间,鲁迅原先颇倾向胡适的自传说,后来有所改变而更加强调文学创作的虚构性。而作为胡适、鲁迅共同之好友的俞平伯,原先赞同胡适的观点,后来有所变化,转而接近鲁迅的看法。
如俞平伯在1940年已经认为:“《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②其实,无论是鲁迅还是俞平伯,他们对胡适的批评不仅在于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涉及对胡适在所谓“科学方法”指引下去“整理国故”的看法,认为这样做有局限性。为了进一步体会鲁迅观点的深刻,再看另一位“红学”名家吴宓的观点。在其《〈红楼梦〉新谈》中,吴宓运用西方近代小说理论,对《红楼梦》有这样的概括性评价:
“《石头记》(俗称《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中,亦罕见其匹。西国小说,佳者固千百,各有所长,然如《石头记》之广博精到,诸美兼备者,实属寥寥。英文小说中,惟W.M.Thackeray之《TheNew-comes》最为近之。自吾读西国小说,而益重《石头记》。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③吴宓同意美国学者的意见,认为结构谨严是仅次于作品主旨的衡量小说是否杰作的必要条件,而《红楼梦》恰恰符合此点。相比之下鲁迅似乎没有对《红楼梦》的结构给予格外关注,更多地赞美其语言特色。吴宓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说理论为价值尺度,其对《红楼梦》的分析不乏精彩之处,也开创了运用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先河。但整体而言,他的研究有生套西方理论之嫌,有些分析也显得牵强。
此外,笔者以为还应该格外关注鲁迅在论述宝玉形象时所提出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一论断之价值,及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风格研究的影响。悲凉作为美学范畴有两层涵义,一指作品风格,一指作者心态。
至于悲凉作为文学人物或作者之心态,导致其产生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第一,由于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黑暗势力面前无能为力而产生悲凉感。第二,由于对自己一向认为神圣、视为生命的事业(如学术)感到失望从而导致人生理想破灭而走向悲凉。第三,对自己置身其中又深深迷恋的文化传统感到失望而又无力拯救的悲凉。第四,对宇宙永生、人生短暂而又无力改变这种结局所产生的悲凉。第五,由上述各点导致对自身存在、人类存在的价值感到怀疑、痛苦但又无法解脱而产生的悲凉。从主体角度看,只有真正具有孤独感的人才会感到悲凉,悲凉与孤独往往是同时出现于心灵之中。因此,无论个人多么痛苦绝望,但只要他还能创作,他就不会走向颓废或死亡,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宝玉的悲凉,也正是曹雪芹的悲凉,诚如其所言:“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①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表现人生之死亡的大书,当为确切之辞。笔者以为,如此看待鲁迅针对宝玉所使用的“悲凉”一词,才比较接近鲁迅的用意。
鲁迅这近于盖棺论定的说法极大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且不说有多少研究者使用“悲凉”概念分析人物心态、界定作品风格,也不说有多少研究者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冠以“悲凉”特色,单单“悲凉”一词对于20世纪中国文人思想情感的影响,就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诚然,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文化日趋衰败的状况,为文人提供了创作悲凉之作的生活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从根本上切断文人进入统治集团的合法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悲凉”传统,也会对那些虽已接触、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但情感上依然对传统文化高度认同的中国现代文人产生深刻影响。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立的双方,虽然文学观念截然对立,但其作品的风格却都趋于深沉悲凉。更有甚者,是那些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五四”之后经历的迷茫和失落,更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无可掩饰的悲凉与荒寒。
因此,可以说鲁迅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这一传统对20世纪中国文人的深刻影响。加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就使得“悲凉”这一概念不仅具有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更具有思想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意义。
以下我们再简单评述王国维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以进一步对比映照鲁迅相关观点的学术思想史价值。王国维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他借用叔本华哲学于1904年所写的《〈红楼梦〉评论》,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运用西方哲学理论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论文,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纵观王国维此文,其最大学术价值在于运用叔本华哲学,断定《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一部悲剧中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与鲁迅一样,认为宝玉是体现《红楼梦》悲剧精神的唯一人物:“彼于缠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脱之种子,故听《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读《胠箧》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则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渐决,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读者观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实,其解脱之行程,精进之历史,明了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②他的说法与鲁迅论宝玉的“悲凉之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整体而言,王国维论《红楼梦》更多是从哲学角度,而鲁迅则更侧重于从文学史角度进行评价,这是他们的不同之处。
二、“红学”与“鲁学”视野中的鲁迅《红楼梦》研究
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如资料搜集的限制,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些关于作品版本、作者生平等方面的具体观点和见解,在今天已经过时或者不够全面,但他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所作出的整体判断依然有价值。
笔者曾对“红学”界一些研究者的论着以及常见的中国文学史中有关《红楼梦》部分的论述进行过统计,发现在众多的研究论着中,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述最常被引用的应为以下五处:
1.(宝玉)于外昵秦钟蒋玉函,归则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荣公府虽煊赫,而……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①
2.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②
3.《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
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止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③
4.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④
5.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⑤此外,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中有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红楼梦》的评价,也常为学界引用:“人情小说萌发于唐,迄明略有滋长,然同时坠入迂鄙,以才美为归,以名教自饰。李贽、金喟虽盛称说部,而自无创作,亦无以破世人拘墟之见,但提挈一二传奇演义,出于恒流之上而已。至清有《红楼梦》,乃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⑥在20世纪后半叶影响较大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和“红学”研究者专着中,均有对鲁迅上述论断不同程度的引用。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论述《红楼梦》的第八章第三节的结尾,引用了上述五段中的第二段,这也是该章唯一一次引用现代红学研究者的成果。相形之下,该章在提及其他红学研究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等人观点时均不提具体人名且持批判态度,而将鲁迅此段引文放在该卷第三节的结尾,具有盖棺定论的作用,由此可见作者对鲁迅论断的重视。又如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也是在第三卷专门论述《红楼梦》的第七章第五节,在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时也引用这一段,是该章中唯一一次引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同样是对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观点予以不点名的批判。
周汝昌是20世纪中叶以来“红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这样评价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只要细读《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代人情小说———红楼梦》,就会看出,鲁迅在蔡胡两家之间,作出了毫不含浑的抉择:弃蔡而取胡。并且昌言指明,‘自传说’开端最早,而论定却最晚。应当体会到,鲁迅下了‘论定’二字是笔力千钧,他岂是轻言妄断之人?……更应着重指出的,是鲁迅并非照抄别人的文字见解,他自己作了更多的探索,而且有超越别人的识见。这才真正够得上是‘学’的了。”①20世纪50年代初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爆出名的李希凡和蓝翎,在其论着中更是不止一次引用鲁迅的有关论述,作为他们文章的立论出发点。如李希凡的《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中,就多次引用上述数段鲁迅的论断作为自己评价《红楼梦》的理论基础。在该书的《极摹人情世态之歧》一文中,李希凡写下这样高度评价鲁迅研究的话:“鲁迅给予《红楼梦》以如此高度的评价,而且是早在二十年代,的确显示了他的小说史家的深邃、卓识的眼光。”②另一位“红学”研究名家蒋和森,曾在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红楼梦》的长文中两次引用鲁迅的话作为理论依据,③不过没有一次是鲁迅评价《红楼梦》的内容,而是鲁迅就其他话题所发表之议论。这本身颇耐人寻味,因为就蒋氏此文的题目看,他所评述的内容,本该很适合引用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断。那么,这是否说明他对鲁迅的“红学”研究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而且,从蒋和森其他“红学”论文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如“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歌颂爱情,虽历千年而不少衰,发展到明清更是广及于戏曲小说。但那些作品虽然各有冲击封建社会的意义,却总是跳不出一个范围,即大都不脱‘郎才女貌’、‘夫贵妻荣’、‘五花诰封’这类爱情理想和人生追求。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才完全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格局”。④蒋和森这段话虽没有明指,但显而易见脱胎于鲁迅的那句“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⑤当代学者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谈到清代小说时,也是引用鲁迅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作为对《红楼梦》的最高评价。⑥至于其他学者之引用和评价,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自然,由于鲁迅特殊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领袖地位,很多学者都会对鲁迅的《红楼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也会在相关研究中引用鲁迅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所以,要正确判断鲁迅研究的价值以及对“红学”研究的影响,还是要回到学术研究本身,具体分析鲁迅的研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为此,看看作为“新红学”代表人物的胡适、俞平伯如何评价鲁迅的有关研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尺度。①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话文学史》“自序”里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研究:“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②1936年11月,胡适的学生苏雪林致信胡适,攻击鲁迅。胡适在12月14日的复信中却高度评价了鲁迅:“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③不过,对于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观点,胡适似乎没有什么评价。
再看俞平伯,首先要注意他与鲁迅的“师友渊源”关系: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是鲁迅老师章太炎的老师,因为此段关系,俞平伯曾把自己小时与俞樾的合影照片复制品赠送给鲁迅。其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引用了俞樾有关《红楼梦》的两段评述。再就是《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时,鲁迅将俞平伯当时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观点列入书中并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俞平伯对于鲁迅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小说史研究持怎样的态度呢?
1923年秋,俞平伯应聘到上海大学教授中文,负责中国小说的讲授课程,为了备课,他想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索要一份《中国小说史》讲义。④当年8月5日,他写信给周作人:“下半年拟在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此项科目材料之搜集颇觉麻烦,不知先生有何意见否?鲁迅先生所编之《中国小说史》讲义,不知能见赐一份否?”⑤俞平伯应该没有从周作人处得到此讲义,因为这时周氏兄弟已反目成仇,而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俞平伯尚不知情。后来俞平伯是通过孙伏园从鲁迅处借到《中国小说史》讲义,看后又由孙伏园归还鲁迅。当年9月2日,俞平伯返回上海前写信给周作人:“我明日拟偕绍原南下,因事冗路远,未能再走诣一次,至歉!《小说史》讲义在鲁迅先生处借得一册,觉得条理很好。
原书仍交伏园奉返,请您晤他时为我致谢。”⑥这个“条理很好”虽是正面性评价,但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准师生关系,也不算是很高的评价。
至于俞平伯对鲁迅《红楼梦》研究的态度,应该是属于抽象肯定而具体忽视。俞平伯在其红学专着中,基本没有提及鲁迅,没有对其“红学”研究观点进行肯定性评价。⑦综上所述,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胡适和俞平伯对于鲁迅的小说研究成就给予较高评价,但对于其《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论断并未给予特别关注,这既与鲁迅没有专门的“红学”论着及主要成就为文学创作有关,也与他们两人在“红学”研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大概他们感到自己已站在群山之巅,所以对于其他人的研究,多少都抱着俯视的态度。
至于“鲁学”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鲁迅的学术成就评价较高,但实际上并未给予足够关注,这只要看看数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可以明了。唐弢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把鲁迅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所有作家中只对鲁迅用了两章篇幅进行论述。但即便如此,它们阐述的重点仍是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就,而对其学术研究却论述甚少,对于《中国小说史略》则更是一句带过,没有具体评价。考虑到二者的文学史属性,自然会把论述重点放在作家作品和相关时代背景的讨论,但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处理如此简略,不仅反映了作者所受时代背景制约的局限,也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整体上忽略鲁迅的学术成就这一状况。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和发展演变的角度,鲁迅本应列入被重点考察的对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因此,从学术思想发展史角度,审视鲁迅的《红楼梦》研究以及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现代学术视野,并分析他的相关研究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产生的影响,是一个较为迫切的工作。
三、鲁迅“作家”身份与治学关系及其现代学术意识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小说家,也是艺术鉴赏力极高和理论分析能力极强的文学理论家。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和视角,对其学术研究有着复杂深刻的影响。整体而言,这有利于鲁迅准确深刻地把握《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性,特别是他对《红楼梦》艺术特色的体悟和分析,确实有只眼独具之处。这也给后世一些主要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者以宝贵的启示,如鲁迅之后的张爱玲和近年来刘心武、王蒙等人对《红楼梦》的研究,其实就体现了他们作为作家的独特视角和经验。且不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是否正确、深刻,单单考察他们的“红学”研究是否受到鲁迅影响以及如何受到影响,就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鲁迅对《红楼梦》的语言评价极高,对其写实性风格评价也很高,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多次对其他小说的语言特色给予格外的关注和评价,这其实与鲁迅自身的小说家身份有极大关系。对此已有学者给予注意,如台湾学者龚鹏程就曾特别论述鲁迅的小说家身份对其治学影响:“《小说史略》中对小说的文字功夫,讨论极多,如谓《孽海花》‘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作风固然如是矣’;……详看这些评语,我们就会发现它确实是一位作家写的小说史。里面对于‘如何描写’着墨甚多,金针度人,不乏甘苦之谈。比起一般只从主体意识、社会背景、渊源影响论小说史者,确实掌握了文学的特性,不愧为小说之史。”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此类评价,对20世纪几部文学史的写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我们稍作对比: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它所具有的那种不见人工痕迹的反映生活的本领。天然无饰,或者说巧夺天工,这是曹雪芹的一个很大的天才特色。在《红楼梦》中,一切是显得那样的血肉饱满和生气勃勃;一切是显得那样的纷繁多姿,然而又是那样的清晰明朗。生活,在《红楼梦》中的再现,好像并没有经过作家辛苦的提炼和精心的刻划,只不过是按照它原有的样子任其自然地流到纸上,就像一幅天长地阔的自然风光,不加修饰地呈现在我们的窗子面前一样。其实,这都是经过作家的惨淡经营才能达到如此的境界。②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③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①虽然所引第一段没有直接引用鲁迅的论述,但显而易见受到了所引两段鲁迅论述的影响。
此外,鲁迅对《红楼梦》中有关内容的摘引以及摘引方式也值得关注,不仅显示出鲁迅很高的文学鉴赏水平和小说家特有的欣赏角度,而且能看出其别致新颖的学术视角和善于从第一手资料中加工提炼出内在主旨的学术眼光。《中国小说史略》中对《红楼梦》中有关宝玉的大段摘引有两段,一段是为了说明宝玉的“爱博而心劳”,所引内容为戚本第五十七回中宝玉去看黛玉,因黛玉休息不敢造次,遂与其他丫鬟谈笑,反遭黛玉冷落以致伤心流泪事。另一大段则是为了阐释“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的观点,所引内容为戚本第七十八回中宝玉因晴雯之死想去吊唁却未能如意,遂往黛玉、宝钗处寻求慰藉也未能如愿,最终遂将满腔悲愤绝望及因晴雯之死所产生的痛惜悲凉之情,倾泄于为“姽婳将军”所做挽词中一事。从前八十回看,这两回对于塑造宝玉的性格以及表现宝玉的悲凉孤独心境和对旧传统的反叛思想非常重要,鲁迅摘引这两段确实极有眼光。
实事求是地看,很多文学史和小说史对《红楼梦》整体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分析评价,特别是对作品艺术特色如人物性格心理的分析和语言特色的阐释,对作者创作心态的分析,并未超越鲁迅。鲁迅的学者身份对其文学创作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宝玉这一形象和《红楼梦》“悲凉”风格的界定和认同,必然会影响他个人的文学创作,在大致同时期酝酿和写作的《野草》,其美学风格就不仅受到西方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也明显受到弥漫《红楼梦》全篇之悲凉氛围的影响。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鲁迅在对《红楼梦》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所体现的学术独创性和自觉性,也值得给予足够关注。在此仅从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发展角度,简单阐释鲁迅的重要贡献。
1931年,陈寅恪在谈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状况时曾表示不满:“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持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②可见,陈寅恪是从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从建构既接受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又承继古代优秀学术传统之中国学术体系的高度看当时学术界的状况,所以认为问题甚多。其实早在20世纪初叶,学术界一些远见卓识之士就意识到建构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性。如陈寅恪就针对在引进外来文化和承受传统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买珠还椟”①(即只接受其合理内核,抛弃其不合中国国情之形式)、“新瓶装旧酒”②等原则性意见。王国维也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照搬外来文化、学术研究的“无用之用”及学术独立等发表过很多真知灼见,其对中国古代戏曲史和甲骨文的研究等更是将中西学术观念和学术研究方法结合的典范,具有开创性意义。陈寅恪从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角度对王国维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着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③其实陈氏对王国维的评价,正可以用来评价鲁迅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贡献,因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正是一部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同样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着作,是一部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强调个人独到见解的杰作。鲁迅之前,冠以“小说史”等名目而出版的着作不是没有,如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蒋瑞藻所编的《小说考证》、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静方的《小说从考》以及1920年泰东书局出版的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等。但这些着作要么只是简单的资料长编,要么只是照搬西方小说理论而对中国小说发展缺少系统和深入的了解。④因此,鲁迅的着作一出即受到学术界的一致称赞,并引起相关的学术探讨。如陈寅恪就曾以“间接对话”方式对鲁迅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工作给予关注。当时,胡适、鲁迅等人都对《西游记》中孙悟空等人物形象原型的来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陈寅恪也写了《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表明自己的观点与胡适、鲁迅不同,并特意注明是“此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⑤陈氏此文发表于1930年,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于1925年,并在1930年修改后再版,所以陈氏所言应是有所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的古典小说研究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且在当时达到了一流水平,才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整体而言,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是重大和深刻的,但由于其辉煌的创作成就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影响,致使其学术成就无形中受到忽视冷落。
诚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鲁学”和“红学”长期都保持较高的研究水平,但二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一直较少,而且对鲁迅的学术成就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忽略。无论是《红楼梦》还是鲁迅,其文学地位和思想地位都曾被过度拔高,使部分研究者对鲁迅的《红楼梦》研究产生偏见和抵触,从而使鲁迅的观点要么成为确保“理论正确”的挡箭牌,要么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鲁迅被引用最多的几段关于《红楼梦》的论述,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整体性,引用方便,不仅适用于评价《红楼梦》,也适用于评价其他文学现象甚至文化现象。久而久之,人们反而忽视了鲁迅论断的具体内涵和学术价值。
“红学”界对鲁迅的“红楼研究”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忽略”的态度,有其复杂原因。鲁迅在其《红楼梦》研究中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等论断指出了作品的思想价值,重点放在分析宝黛爱情悲剧特别是贾宝玉个人精神世界上,而没有过多谈论其反封建思想意义。囿于1949年后某段特殊时期的文学研究环境,相关研究者不得不更加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过分强调其反封建色彩。此外,单从贾宝玉这个人物看,鲁迅强调更多的是宝玉的内心感受,是“爱博而心劳”,是其无奈的一声叹息。而后人更多看重的是宝玉的叛逆思想和行动,是所谓的呐喊和反抗。另外,在对作品版本和具体内容的考证上,鲁迅也没有更多更深入的跟进性研究,也使得他的观点难以对后来的“红学”界产生具体而实际的影响。
诚如很多文学史研究者和鲁迅研究专家所言,中国小说自古无史,有之,则从鲁迅始。而20世纪的“红学”,尽管在鲁迅同时期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研究,但鲁迅依然能够独树一帜,提出很多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其对作品的理解和概括性论述对后来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早已超出对《红楼梦》进行阐释的范围。至于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笔者以为可以分为直接(或显性)影响和间接(或潜在)影响两种方式,两者比较,后者更为重要。所谓直接影响,就是鲁迅的研究直接而具体地影响了他所在时代以及后来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如他对《红楼梦》悲凉风格的概括、对宝黛爱情悲剧与人类终极命运的追问等,都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红学”研究、小说研究。所谓间接影响,就是鲁迅在《红楼梦》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概念等以及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所形成的研究模式和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路(如他多次提及的对中国文学史写法的思考等),都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建构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只是这些影响长期未能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有些研究者虽从鲁迅的研究中获益良多,却因种种原因不愿或不敢直接提及自己所受鲁迅的影响。此类间接影响的另一种表现就是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在经历时间的考验后,早已和他的其他学术思想、文学创作等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对“鲁迅”这个文化符号的全部想象。提及鲁迅,自然会提及他的小说、杂文,他深刻的批判与启蒙思想,也会提及他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爱博而心劳”等关于《红楼梦》的天才评判,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鲁迅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总之,鲁迅在对《红楼梦》和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过程中所使用和提出的一些学术理念和观点,证明他在那时就已做到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为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诚然,如果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要求看,还不能说鲁迅的《红楼梦》研究已自成体系,但其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且框架初成。然而,迄今学术界对鲁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虽已有要提升到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高度进行研究的共识,但具体成果依然甚少。加之“红学”研究界和鲁迅研究界之间的沟通尚存在很多不足,使得相关研究进展缓慢。为了更好地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进行总结,就必须对这些不足加以改进,对此我们有理由给予乐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