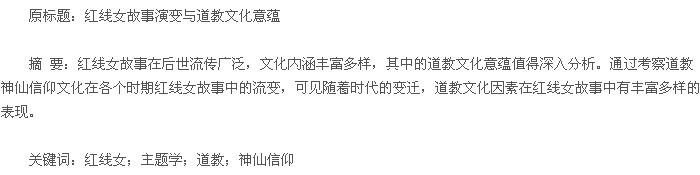
红线女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除唐传奇以外,该故事在诗歌、小说、杂剧、传奇、史料笔记等领域都有文本流传。红线女原为唐潞州节度使薛嵩侍婢,她明理识体,为主排忧,通过夜窃金盒的举动起到了警告和震慑敌方的作用,使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不敢出兵,从而平息了一场战争。
一个弱女子,轻松进入重兵把守的敌军阵营,成功盗走敌军将帅枕边金盒,技艺和本事超乎寻常。故事中,红线女不仅“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繍短袍,系青丝轻履”,额上还书着“太乙神名”,穿衣打扮处处显露出浓厚的道教气息。本文运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挖掘道教神仙信仰文化在红线女故事中的嬗变过程,并探寻其内在动因。
一、红线女故事的文献版本梳理
唐代《甘泽谣》为目前能查到的红线女故事最早版本:唐潞州节度使薛嵩有青衣名“红线”,善弹阮咸,又通经史,掌管牋表,号曰“内记室”。一次军中大宴,红线女听出“羯鼓之声,颇甚悲切”,一问,原来击鼓之人妻子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放归”。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成立了一支拥有三千名高手的卫队,号曰“外宅男”,意欲吞并潞州。田承嗣实力超过薛嵩,曾扬言,潞州的气候于他的身体健康更有好处。薛嵩得知后,日夜惶恐不安。这时,红线女主动请缨,潜入魏城,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盗取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当薛嵩派人送还金盒时,田承嗣“惊怛绝倒”,枕边取金盒无人知觉阻挡,取首级也是易如反掌。因此不敢再作吞并潞州之想,一场战争得以平息。忽一日,红线女辞去。原来她前世本为大夫,因用药误杀孕妇及腹中二子,今世降为侍女。如今因功,“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薛嵩苦留不住,广为饯行,红线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在《甘泽谣》里,唐代道教神仙信仰讲究功成身退、不慕富贵的特点已经有所体现。
《白孔六贴》卷 24 也收录有红线女故事。红线开始只是潞帅薛嵩手下一名不起眼的歌妓,得知主人忧虑后,“红线曰:‘此易耳,妾愿一到彼观其形势,初夜首途,三更可还。’出户忽不见,未晓果复至,取承嗣寝所金盒来,嵩即遣使持送盒遗承嗣,书曰:‘有客从彼来,云自元帅头边得此金盒。’承嗣大惧,散外宅男,河北遂宁。”关键时刻红线女展露非凡自信,运用绝世武功,在两地飞速往来,完成使命,令人击节赞赏。
宋元时期,对红线女故事的记载都是寥寥数语,有的甚至连盗盒这一重要情节都没提。编入话本小说集《醉翁谈录》妖术类中有《红线盗印》,现已佚。看题目可知,话本中应有红线女盗盒的情节,但把红线女的才能归为妖术,也可见编者歧视之心。
明清时期,红线女故事流传和创作都进入鼎盛阶段,基本情节和内容沿袭《太平广记》,除文言小说外,还有传奇、杂剧、白话小说、诗歌等多种体裁。值得注意的是,从唐代红线女故事产生开始,创作者都是在用文言传承故事,一直到明代凌濛初,才第一次以白话的形式、拟话本的体裁重新演绎了红线女故事。《初刻拍案惊奇》卷 4《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入话开篇,提到许多剑侠女子,第一个就是红线女。与文言小说相比,拟话本的红线女故事有三个特点。一是语言生动、鲜活、口语化,使得故事更加喜闻乐见。如云“田承嗣一见惊慌,知是剑侠,恐怕取他首级,把邪谋都息了”,完全运用口语,简短精练。二是把红线女定位为绝技者,说红线女盗盒成功,是因为“弄出剑术手段,飞身到魏博”,对红线女的超凡技艺加以渲染,可以看作是明代商品经济推动下,作者和书商满足读者猎奇心理,吸引读者阅读兴趣,提高书刊效益的一种手段。三是突出社会教化功能。明清的劝惩之说盛行,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 12 说自己的写作态度:“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谈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强调红线女最后修成神仙,是因为她除恶扶善、功德圆满,以此劝诫读者多行善事,必定会有善报。
戏剧方面,留存下来的有明代梁辰鱼的杂剧《红线女夜窃黄金盒》,全剧正名为“薛节度兵镇潞州道,田元帅私养外宅儿。红线女夜窃黄金盒,冷参军朝赋洛妃诗”,结尾是红线女功成升天,道教色彩浓厚。
明代胡汝嘉的杂剧《红线金盒记》并未佚失,该剧题目正名为:“莽节度潜窥泽潞军,红粉侠暗掌销兵计。”剧中红线女本是上真弟子,因“功行有亏,罚向人间”。一次,她在梦中受董双成、萼绿华二仙点化,得知田承嗣企图,盗盒退兵后,重返天界、证果朝元。更生子的传奇《剑侠传双红记》,记载侠士昆仑和剑仙红线并谪凡尘,在人间为奴为婢,修行圆满返回天庭。另外,明代程守兆所作杂剧《金盒记》、李既明所作杂剧《金盒》,还有无名氏所写的《双红记》,今均已佚。
二、唐代红线女传奇中的道教神仙信仰
刘勰《灭惑论》云:“案道家立法,厥有三品,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这里概括了道教的大致特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神仙信仰。神仙信仰由神仙、仙境和成仙方术三方面组成,在长期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和神话传说,尤其是在成为道教的中心教义之后,吸收了封建宗法思想,并借鉴佛教关于佛国净界的教义,体系日渐完备。唐以前的道教神仙信仰,追求肉体上的长生,关注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延续,讲求人如何能够得道成仙,魏晋六朝以来,在道士们的推动下,炼丹服食在士大夫阶层中颇为流行。
到了唐代,道教为御用宗教,道教神仙信仰广被社会民众接受。唐代许多人孜孜不倦追求得道成仙的人生理想,神仙信仰在唐代达到鼎盛。道教神仙信仰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追求“栖心物外、自由逍遥”,崇尚精神上的永恒、超脱,更加关注人的精神品味和境界。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就自认老子李聃为李家宗祖,欲借道教的神威来抬高李家的权威,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于是道教在皇室的保护下不断光大,并居于儒释道三教之首。唐代道教的神仙信仰与老庄哲学紧密结合,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老庄学说中自然素朴、清静无为,追求超尘脱俗,以达精神绝对自由的思想。这时期的道教神仙信仰纳入了道德人格的修养,认为形体只是人的暂住体而已,关键是从精神上理解成仙,超越自我,获得心理和生理的绝对怡悦、自由。
唐传奇中的红线女身怀绝技,但是府中无人知晓她的武功,她自己也是深藏不露,以致薛嵩一开始对红线女能否完成这样重大的任务心存怀疑,后来红线女不负众望建立奇功,完成使命,使两地平息干戈,百姓免于祸乱。在庆祝的宴会上,红线女不贪慕荣华富贵,只愿“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到山林中隐居修炼,超脱俗世,结局是拂袖而去,“遁迹尘中,遂亡其所在”,整篇作品充满着自然无为、恬淡空灵的气息。这也符合唐代小说的结尾特点,即侠客向往的是独立自由的精神,他们在行侠成功之后都不贪恋功名,而是拂袖而去,如兰陵老人、义侠都是如此。这也是唐代道教神仙信仰对唐传奇小说结构模式的影响。
三、明代红线女故事中的道教神仙信仰
宋明以后道教神仙信仰又有新变化,尤其注重道德内涵,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修养是成仙的重要条件。全真道就将心性修炼作为修行的根本,强调“性命双修性为本”,强调践履道德对于修道成仙具有重要意义,修道应着重从积累功行方面下功夫。
明代红线女故事的结局多是得道成仙,道教仙化观念明显提升。《初刻拍案惊奇》中的红线女因为平息了一场战争,震慑住了田承嗣侵略潞州的野心,做了善事,所以“修仙去了”。凌濛初赞曰:“红线下世,毒哉仙仙。”
明代梁辰鱼杂剧中的红线女也是一身道服,渴慕成仙,功成之后“主公之恩已酬,林壑之念遂决”,送别宴席之后,红线女就飞上了仙界:【太平令】早来到神都蓬囿,去寻个道侣仙俦。免不得参辰卯酉,那里管笺书章奏。我呵!从今离歌楼舞楼,便飞上麟洲凤洲,呀!看身穿九霄云窦。
在明代,道教与皇权关系密切,但神权位于皇权之下。明代戏剧中,身穿道服修成神仙的红线女还要拜谢朝廷,这里所表现的忠君思想,也是宋明以后道教神仙信仰强调伦理道德的体现。
胡汝嘉杂剧中,出现许多道教神仙,有金母娘娘、西王母、东王公、许飞琼、董双成、绿萼华等,主人公红线女也是道教上真弟子,因“功行未至隔仙久,不得团圆”,在平息战争,保全两地百姓性命,“功成行备”之后,终于能够返回天宫,受到众仙恭迎。“青鸟已传金母信,紫鸾应返玉皇家。”从此,红线女便“无萦无绊,无系无拘,无虑无忧”,受用些“仙馆、仙台、仙乐、仙厨、仙桃、仙酒”,要过那神仙的快乐生活。更生子的传奇《双红记》里的红线女,“当初离紫宸到人寰,忍辱行满功成,香云缭绕,双双复返天庭。飞仙自入飞仙队,剑侠还将剑侠寻。”最终,功德圆满,与磨勒重列仙班,返回天庭。
宋明以后道教神仙信仰认为道德水平和心理状态的提升与完善即是神仙。“历劫—悟道—升仙”成为明代红线女戏剧创作的普遍模式。红线女身怀绝技,之前不显露,是因为必要时候方可挺身而出,实现“功成”的人生价值;之后选择“身退”,是为了让生命在宁静、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养育,上升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红线女大功告成后得道成仙的结局模式也反映了佛、道、儒三者的融合。“功成身退”是整个中国文人的至善至美的完满的人生观。
四、红线女故事所表现出的其他道教文化因素
红线女故事流传的过程中,除了道教神仙信仰的内涵在不断演变之外,还有一些道教文化的因素在历代红线女故事的流传中始终是稳定不变的。
(一) 服饰装扮具有道教意味
红线女故事中,在红线女出发时,描写她的神态装束很是细腻,突出了此次行动的重要性:(红线)乃入闱房,饬其行具。乃梳乌蛮髻,贯金雀钗,衣紫繍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再拜而已,倏忽不见。
道教早期,道士服饰并无定制,魏晋南北朝刘宋时期,道士陆静修订立了服饰仪制。此时的道教法服仪制是权力等级的象征。此后,经过不断增修,到南北朝末,道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服饰制度,其基本形制为:上褐、裙、外罩帔。这里,褐是指用粗麻制成的短袍,裙是一种围在腰部以下的服装,帔是一种披在肩上的服饰。到唐代时,道教服饰制度进一步完善。此时,修道者的服饰已演化为按道士入道年限及学道的深浅分为七种等级,并对每种等级道士的衣服、冠巾、靴履及其所用颜色、尺寸、款式、质地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品第越高,服饰越华丽、复杂。故事中,红线女头插金雀钗,身穿紫繍短袍,系青丝轻履,应该在道士中品第不低。
(二) 武功技能的施展和兵器法术的运用具有道教意味
隋唐时期成熟的内丹术,使武功至唐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各种武功,大都是在内丹术的基础上糅合各种技击本领而成的。
武侠小说所写的武功主要有四种:轻功、气功、剑术、药术。武功描写的出神入化也是受道教文化的影响。
在红线女故事的文本流传中,都提到了红线女执行任务时胸前佩戴的龙文匕首,这说明红线女身怀剑术。在《初刻拍案惊奇》中红线女被定位为“剑侠”,能弄出剑术手段,飞身到魏博。明代胡汝嘉杂剧更是直接点明,消除兵刃之争,全仗红线女“一剑行事”,红线女当场舞剑,“忽地里龙吟虎啸,一霎时雨惊云落”,飞沙走石,惊心动魄,剑术气势极其威猛。古文献及道教仪式对剑都有神化宣扬,如《庄子·说剑篇》《吴越春秋》的“越女剑术”,《越绝书》《史记》等对剑的精彩叙述,甚至在魏晋志怪小说《搜神记·三王墓》《搜神后记·比丘尼》中,剑已成为神奇武艺的象征。而在道教科谯仪式中,剑也渐渐被用作驭神驱邪的法物,如《三水小牍·李龟寿》中的剑即被当作禁咒式的神器。正是由于剑带有如此神性,它便成了身怀绝技、神出鬼没的豪侠们的宝物,剑术也成了他们的看家本事。
豪侠们的弓矢、剑术等武艺总是与飞行、隐遁等法术相联系的,虽然他们所用兵器多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剑,但取胜多靠法术。道教极重视神仙方术的演绎,如《云笈七签》卷 29 至卷 31 就录有隐身变化的各种方法,而《抱朴子》则对腾云游空、分身隐形、千变万化等各种方术都做了鼓吹。田承嗣的寝室四周安排了三百名重兵防守,“侍人四布,兵器交罗”,要想轻松拿到床头金盒,红线女当然得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红线女助薛嵩,用的应该也是飞身、隐遁之法,不然她不可能“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经五六城”,“飞鸟似一般”来去自如,这些轻功是从道教的乘侨术变化而来的。
(三) 具有道教意味的行侠必成、无往不胜
唐代小说中,主人公昆仑奴、聂隐娘、贾人妻、荆十三娘、僧侠师徒、车中女子,往往飞身隐遁,神出鬼没,大异常人,并且最终都能成功,不像司马迁笔下的侠士绝大多数以悲剧为生命结局,这是道教信奉肉体长生思想的表现。道教不承认来世、转世、轮回,而只信奉肉体本位的长生与长存。这种肉体不灭的本领,使得红线女能够行侠必成、无往不胜。
唐传奇中,对于令节度使薛嵩日夜忧虑、计无所出的重大战争,在红线女的眼中,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一桩小事,她表现得胸有成竹,非常自信:红线曰:“此易与耳,不足劳主忧焉……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使,具寒暄书,其他即待某却回也。”嵩曰:“然事或不济,反速其祸,又如之何?”红线曰:“某之此行,无不济也。”
尽管平时薛嵩对红线的才能颇为看重,然而此次“事系安危,非尔能料”,他认为红线女无法解决这么重大的难题。在半信半疑中,薛嵩回到房中焦急等待,平时饮酒,不过几杯的酒量,这一晚他连喝十几杯都没有醉意。忽然薛嵩听到外边有叶子坠落的声音,惊而起问,原来是红线女回来了。明梁辰鱼杂剧、胡汝嘉杂剧中的红线女也是本领高强,胜券在握。最终的结局都是红线女施展奇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危急的军国大事。红线女作为修道升仙的人物,肉体长生思想自然在红线女故事中有所反映。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孔传.白孔六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黄仕忠.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 姚燮.今乐考证[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4]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 沈泰,邹式金.盛明杂剧[M].北京:中国书店,2011.
[6] 李昉,等.太平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道教脱胎于原始宗教,以道家老庄思想为理论基础,后又杂糅神仙方术思想和民间信仰,于东汉末年正式形成本土宗教,因此与民间鬼神信仰和巫术有着天然联系。早在秦汉时期,有关神仙方术的思想就已相当发达,后来在迎合历朝君王求长生愿望下,得到迅速的发展。《...
引言《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将传记小说夸张的笔法和寓言故事讽刺的语言风格,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这部小说获得第二届红楼梦奖和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第一章钟馗题材小说创作原因钟馗传说和信仰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钟馗传说的来源主要集中在摊仪说、木棒说、人名说三种说法。钟馗信仰的产生与钟馗传说是密不可分的,二者互为表里。魏晋至唐五代是钟馗信仰形成的重要阶段,宋元时期是钟馗信仰与民...
纵观关羽形象的整个演变过程, 从历史还原给我们一个勇猛之武将, 发展到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忠勇之儒将, 再到宗教信仰中的神像, 关羽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固化成一种文化符号, 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