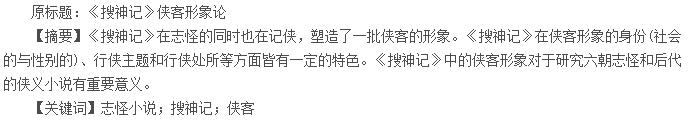
干宝的《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在古代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地位。该书大约在宋代就已经散佚,现今所传,是明代胡应麟的辑录本。该本20 卷共464 则正文故事和34 则佚文故事,今以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最为流行。小说“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以神灵精怪为主要表现对象,干宝也因此博得“鬼之董狐”的美名。但以往学者似乎并未注意到,《搜神记》在志怪的同时也在记侠,塑造了一批与鬼怪斗争的侠客形象,为满纸荒唐神怪故事、充满阴森诡异气息的小说增添了许多“人”气,使之更具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早期小说的杰出代表,《搜神记》对于后代小说起着不同寻常的先导和示范作用。唐宋以后蔚为大观、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侠义小说,与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许多作品中的侠客形象、侠客的行侠主题及其行为模式,都可以在《搜神记》里找到雏形。《搜神记》对于研究六朝志怪和后代的侠义小说,具有重要意义。
“侠”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侠客的活动及其相关记载。从古到今,记载和表现侠客活动的作品不计其数。“侠”又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后人对“侠”的认识和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最早为侠客树碑立传,他把侠客的基本特征概括为: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 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无论后人对“侠”作如何表述,都以太史公此说为主要的立论基础。本文所讨论的《搜神记》侠客,即是指作品中具有上述相关特征、又符合约定俗成的欣赏习惯的奇行异能者。
一、《搜神记》侠客的身份
侠是一种行为,不论职业、门派、阶级,“蒿莱明堂之间”,只要愿意有所担当者,皆可挺身为侠。
因此,《搜神记》中的侠客,社会身份颇为复杂,有官员、武士、书生、道士、民女、自由职业者等,其中又以官员、书生、武士为多。
《搜神记》侠客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官员。如大旱之年,不惜血肉之躯,自焚求雨的谅辅(271《谅辅》是广汉郡太守的五官掾(属官) ,此前也曾先后供职佐史、从事史; 为寡妇苏娥昭雪沉冤,把亭长龚寿绳之以法的何敞(384《苏娥》) ,为交州刺史; 其他如郅伯夷(427《到(郅) 伯夷》) 乃北京督邮,葛祚(275《葛祚碑》) 为衡阳太守,谢鲲(429《谢鲲》) 是“谢病去职”的卸任官员,汤应(439《汤应》) 是公差使节,等等。这类官员要么是为民请命,要么铲除妖魔和邪恶,其举动已超越了官员的一般职守,侠义的性质强于职守的行为。如谅辅之舍身求雨,就不是他的职务要求; 何敞为鬼魂办案,并不在自己管辖的治域内,甚至跨越了阴阳、人鬼两界。这些官员的行为,无疑正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等侠义品格的体现。他们的侠行义举,彰显了正直官员的威严和侠客的热血。
促使他们成为侠客,成就他们的侠行义举的决定因素,是超越常人的精神、气质和道义担当,也就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搜神记》中的书生侠客虽然不具备官员侠客所拥有的权威,但面对妖魔鬼怪时的从容优雅、淡定自信,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大贤(426《宋大贤》) 、安阳南亭书生(438《安阳亭书生》) 都明知亭馆闹鬼,却毫无惧色,刻意会之,伺机除害,见义勇为之心昭然。宋大贤“夜坐鼓琴,不设兵仗”,鬼怪现身时,仍“鼓琴如故”; 最后徒手相搏,恶鬼竟然不堪一击。安阳书生面对好心人的劝阻,不改初衷,信心百倍: “无苦也。吾自能谐。”执意夜宿亭楼; 其夜“端坐诵书”,直至天明,既令妖怪无从落手,又摸清了对方的底细; 天亮以后,一举铲除了三个长期作祟害人的妖怪。大敌当前,鼓琴诵书,气定神闲,可以说是书生侠客内在气质、素养的表现,也是其精神和力量的源泉。这类侠客成竹在胸,从容不迫的儒雅举止及其克敌制胜的手段,显然由这种内在的气质、素养所决定和支撑。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文人侠客,或琴棋书画,或羽扇纶巾,风雅倜傥,克敌降魔于玩赏谈笑之间,在《搜神记》的书生侠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影子。
《搜神记》中的武士侠客著名者如养由基、更羸(264《魏更赢》) 、古冶子(265《古冶子》) 等。熊渠子(263《熊渠子》) 是西周时楚国的国君,但小说对于他的记述,并没有刻意凸显他的国君身份,纯以勇武示人。《搜神记》中的武侠要么勇力过人,要么武功高强,表现得极为神勇。如熊渠子误以卧石为虎,弯弓射之,箭头竟然深陷石头之中; 养由基、更羸两位都是神射手,百步穿杨自不用说,即使是拉弓而不发箭,也会令猿猴抱木而哭,大雁应声栽下;古冶子绝对是一位力士,庞然大物般的老鳖衔走了骖马,他入水追凶,杀了老鳖,“左手持鼋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水面) ”。他的神勇孔武,无与伦比。
《左传》、《战国策》等史书对上述诸人均有记载,但其人其事已带有较多民间传说的色彩。《搜神记》对武侠的记载和刻画远没有官员及书生侠客那么具体,除了古冶子入水追凶杀鳖之外,其余的人仅是展示他们的神奇武功,形象刻画注重“神似”。一方面,小说重在表现形象的力量、精神和气质,而不是作为侠客的侠行义举,因此,小说中的武侠几乎是一个形象符号: 英武盖世,无人匹敌,是威慑力、征服力的一种象征; 另一方面,武侠的超强武功都被神化。他们虽然是历史人物,但事迹显然脱离了历史,脱离了真实,形象特征几近神人。《史记》、《汉书》等正史记载的“史家之侠”,都是以气节而不是勇力武功立世,唐以后则“以武行侠”的观念盛行,小说中的侠客大多武功高超,或飞檐走壁,或剑术、拳术出神入化,取人性命如探囊取物。《搜神记》中的武侠形象,以历史人物为原型,武功又超凡入神,史家之侠与小说家之侠的特征都兼而有之,史家之侠向小说家之侠蜕变的行迹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这表明,在《搜神记》中,侠已由史家社会意义的价值诠释开始走向文学人格精神的艺术创造,这对后世侠观念的形成和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上三类侠客,从数量上构成了《搜神记》侠客形象的主体。由此可见,《搜神记》侠客的官方特征是很突出的。上述诸武侠,除了熊渠子是楚国的国君之外,养由基、更羸、古冶子分别是楚王、魏王和齐景公的御前勇士。作品虽然没有交代他们的职务,但他们活动在国君左右,効力于朝廷,其官方的身份或背景不容置疑。书生侠客的官方特征虽然没有那么显著,但其人其事也颇具官员的气质和色彩。封建时代的书生多是后备官员,《搜神记》中的书生侠客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过人的胆识、智勇兼备的素质,都初具正直官员的风采,颇得群众的信赖。在此,不妨把书生侠客视作官员侠客的初级版。
将绝大部分的侠客与官方扯上关系,其实是时人心灵深处迷信官府、权力的一种表现。这种权力迷信,与魏晋时代甚嚣尘上的神鬼迷信性质相似,也遥相呼应。人们在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同时,也为虚幻世界中的精怪魑魅和现实世界中的邪恶败类制造一个正义、强势的对立面和一种制衡的力量。此举与其说是为了维持客观世界的安宁,不如说是为了求得心理的安宁和平衡。统治者都以社会秩序的守护者自居,在现实生活中,官员也的确操控着狱讼生杀、赋税征敛、事体兴废、价值评判等话语权。就像无法认识神鬼的虚妄无稽一样,人们也无从认清封建官吏自私、欺骗的本质,从而对手握公权的官员寄予厚望,对权力产生了崇拜甚至迷信。于是乎,有匡扶正义、济世安民之心的侠客,便多以官员的身份或借官方的背景出现,倚仗官方的威望和权杖行侠布义,从而形成了《搜神记》侠客身份的一大特征。侠客以官员的身份或官方的背景出现,折射出动荡、黑暗的魏晋时期,人们的心理期盼和思想、文化意识。
《搜神记》中的官员侠客如此之多,也与现实环境中侠客的地位和影响有关。在秦末的农民起义军中,游侠是一股重要的力量。汉高祖刘邦之得天下,颇为倚重游侠之力。汉政权建立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张良、彭越、英布之类大小之侠,或者裂地封侯,成了高祖的股肱之臣; 或者官挂州县,权倾一方,成了地方上的豪强。因此,汉初六十多年,侠风之盛,前所未有。有官员身份的豪强之侠立强于世,甚至“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豪侠活动范围之广、人数之众,其权势和影响力之大,可以想象。
《搜神记》中的大多数官员侠客,如前文所见的谅辅、何敞、葛祚、汤应等,都被明确交代是汉代官员。
他们可以说是汉代豪侠的一个侧影,他们的行侠活动,正是汉代豪侠现象的一种反映。汉代的豪强之侠有操控公权、扰乱法纪、作威作福的习气,备受时人谴责,但《搜神记》中官员侠客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仗义行侠,展示汉代豪侠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这也表明作者在传述官员侠客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性蕴涵着审美的判断和取向,后世小说对于侠客形象的塑造、刻画,多以正义、公正和利他为归趣,这与《搜神记》审美取向的启发和影响有很大关系。
在古代小说史的人物画廊中,侠客形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群体。大体而言,这个群体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依附于官府或有官方背景的官侠,另一类是游离于主流社会、活动于法外之域的江湖之侠。《搜神记》侠客身份的官方特征于文学史而言,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最早为古代小说人物画廊推出了官侠这一艺术类型,率先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中国古代侠客与官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为后世小说家所效法。承魏晋志怪而兴的唐传奇,其所塑造的侠客,身份特征与《搜神记》如出一辙。如郭元振(《郭元振》) 、许俊(《柳氏传》) 、古押衙(《无双传》) 等,都是官员侠客; 书生侠客则有柳毅(《柳毅传》) 、赵中立(《荆十三娘》) 、李靖(《虬髯客传》)等; 聂隐娘(《聂隐娘》) 是魏博大将军聂锋之女,红线(《红线》) 是为潞州节度史薛嵩“掌笺表,号曰‘内记室’”的私人秘书,其他如昆仑奴磨勒(《昆仑奴》) 、红拂女(《虬髯客传》) 等,都与官方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在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中,更有江湖之侠与官侠合流的趋势,如《三侠五义》、《施公案》、《小五义》等作品中的侠客,许多都归顺官府,谋得一官半职,在清官的旗帜下行侠布义,除暴安良。
古代小说中这种官侠同体、官侠相连的现象,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景观。它的产生自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化心理; 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搜神记》开风气之先,引发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意义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
先秦两汉的侠士皆为清一色的男性。《搜神记》侠客的性别构成,仍然维持着男侠居绝对多数的格局。唯一不让男侠专美的,是东越闽中的少女李寄(440《李寄》) 。她不惧凶恶、勇刺蛇妖、为民除害的义举,是《搜神记》中最令人回肠荡气的侠义故事之一,李寄也因此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少女英雄形象。在几乎是男性独步天下的侠世界中,李寄形象的出现,透射出许多新的思想文化信息,表明女性有能力并开始跻身这个充满凶险的世界,她们的行为也已为人们所接受。在唐代小说里,女侠异军突起,完全可以与男侠平分秋色。聂隐娘、谢小娥、红线、红拂女等,一个个豪气干云、血肉丰满,成了唐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亮丽景致。而在这些形象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女侠如李寄般英雄盖世、性格鲜明、光彩照人。因此,李寄堪称唐前女侠的代表。
她引领女侠在文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叱咤风云,在这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男性世界嵌入一股女儿情怀,为侠骨柔情这个古代小说历久不衰的主题开辟了道路。
二、《搜神记》侠客的行侠主题
《搜神记》中的侠客主要有三大行侠主题: 一是仗义除害,救人危难; 二是替人复仇; 三是显示技艺。显示技艺的行侠主题主要体现在武士侠客的身上。这类作品描写武士侠客的技艺武功,显示其神奇勇武、气概不凡的英雄本色,以此来张扬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可惜作品对其侠行的描写过于简略,情节未能予以适当展开; 对形象的刻画过于平面单薄,主题未能得到深化。所以,这里不打算对此作更多的讨论,而把笔墨放在除害救危和复仇两大主题上面。
司马迁指出游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救人于厄”。救人危难,就势必要直面天灾人祸。因此,驱邪去恶、仗义除害,便成了侠客的天职和信条,也是《搜神记》侠客行侠的第一主题。在《搜神记》中,为民除害,平息鬼魅灾殃,救百姓于水火,还一方平安,是侠客事迹中数量最多的。这些侠客的侠行义举,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为除自然之灾,二为除鬼魅之祟。
前者以“谅辅求雨”为代表。大旱之年,日似炎火,“万物枯焦”,黎民百姓了无生计。身为太守属官的谅辅先是向山川祈祷,继而代太守悔过,向上天谢罪,最后欲以自焚的极端方式向上天祈求降雨。其以生命为代价的诚意和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天,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驱除了肆虐多时的旱灾。可以说,谅辅是《搜神记》官员侠客中最具人格魅力的一个。他与民休戚与共,舍身求雨、感天动地的侠行义举,给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在这个形象身上,忠于职守、为民请命,百姓利益高于一切的为官信念和“不爱其躯”、重诺轻身、救人危难的侠义品格完美结合,反映了古代人民渴望德操高尚的官吏的良好愿望。作品似乎有美化封建官吏的倾向,但不可否认,在封建时代,受“兼济天下”、“修身治国平天下”、“杀身成仁”等思想的浸润,赤胆忠心、为人民谋福祉的官吏虽说不多,但也绝非没有。在谅辅身上,正直官吏的使命感和侠义精神找到了契合点,两者相辅相成,从而促使他做出了顺合民意的举动,成为《搜神记》官员侠客的突出代表。
以除鬼魅之祟为行侠主题的故事,如郅伯夷、葛祚、谢鲲、汤应、宋大贤、安阳书生以及道士寿光侯(32《寿光侯》) 、谢非(444《丹阳道士》) 等人的义举侠行,都写得阴森诡秘、离奇异常。最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者当推“李寄斩蛇”。东越国闽中郡的崇山峻岭之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嗜食女童,若嗜欲不能满足,则作祟不止。当地的官吏苟且偷安,草菅人命,连年募索女童喂蛇,以求暂时的安宁。少女李寄挺身而出,“怀剑,将犬”,以过人的勇敢和机智斩杀蛇妖。李寄斩蛇的故事,其首要意义当然是褒扬平民少女为民除害、慷慨赴难、无私无畏的侠义精神和行为。与此同时,作品中也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批判意义。篇中的官吏,非但没有为民除害,反而助纣为虐,其无能、荒唐和残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为可恨; 蛇妖作祟历经多年,先后已有九位少女葬身蛇腹,面对一幕幕血淋淋的场景,男人们竟然集体失言,没有一个挺身而出,张显男人的勇武和血性———是为可悲。九个成为牺牲品的少女,其悲惨遭遇值得同情。无良官吏的行径固然令人发指,但少女自身的愚昧和懦弱,不懂得抗争、自救,也是陷她们于万劫不复之境的重要原因。对此,李寄亦有深刻的认识,她对着九个女孩的头骨说: “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为哀愍。”妖怪穷凶极恶,官吏无良残忍,男性乡民人性冷漠乃至血性缺失,同龄人愚昧懦弱,李寄行侠的环境是何等的恶劣。作品通过对现实中这三组人的批判,既深化了为民除害的行侠主题,也突出了李寄孤独英雄式的侠客形象。
复仇是后代武侠小说的基本主题。在《搜神记》中,复仇主题的侠义故事也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情况下,侠客的复仇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是为亲友复仇,二是为同门复仇,三是为他人仗义复仇。
第一类是基于血缘或情感的原因,第二类则是出于学(艺) 缘的关系,两者都有沾亲带故、个人恩怨的性质。《搜神记》的侠客复仇则属于第三类,如《三王墓》(266) 、《苏娥》(384) 等名篇中的侠客,他们与受援者之间都是素昧平生、非亲非故,甚至是阴阳相隔。他们替人复仇,纯粹是基于道义的考量,个人的利害得失并不计较。
《三王墓》(即“干将莫邪”) 的故事最早载刘向《列士传》,又见曹丕的《列异传》。《搜神记》的记载与两者大体相同,但增加了许多细节和具体场面的描写,显得更加生动,故事也因之在古今广为流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楚王怒而杀干将,莫邪独力把儿子赤比抚养成人。赤比立誓报仇,楚王悬重赏缉拿。山中侠客为赤比设计了复仇计划: 让赤比自刎,侠客持其头献楚王,伺机刺杀楚王。楚王果然上当,“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坠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坠汤中。”
与对手同归于尽,以死亡来实现复仇的目的,这是《搜神记》中最悲壮的侠义故事。故事强烈地揭露和控诉了统治者的凶恶残暴,歌颂了人民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和复仇精神。山中侠客的举动,也把慷慨仗义、重诺轻身的侠客精神发扬到了极致。
他与干将、莫邪一家素昧平生。之所以挺身而出,为之复仇,表明他认识到这不仅仅是干将、莫邪一家与楚王的私仇,而是善与恶、正与邪的冲突,他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性。他的复仇方式是玉石俱焚式的,有很强的悲剧感。以暴制暴、血债血还,手起刀落,瞬间身首异处、鲜血淋漓。尤其是三个头颅在同一个镬里翻滚,那是何等的血腥和悲壮。
三个头颅与一个头颅相比,也许代价过于沉重,但这正是邪恶势力与无辜百姓力量对比的真实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侠客出现,以锄强助弱,除天下不平事。山中侠客想必是考虑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才选择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复仇方式,由此又可见他血性冲动中的理性和智慧。悲剧产生的原因,往往是邪恶势力的过于强大。山中侠客这种独特的复仇方式及其悲剧结局,显然有它的必然性。
这位山中侠客,又是《搜神记》侠客中最具神秘感的。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姓名、身份、职业、行踪、居所,还有他的生存状态,我们都毫不知晓。他的出现,如从天降; 他为赤比设计的复仇计划,似乎早有预谋; 但他舍身取义的心路历程,却又无迹可寻。他如掠过夜空的流星,燃烧自己的生命,光耀穹苍,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这样一个浪迹江湖,充满神秘感的“职业”侠客,迥异于《搜神记》中的其他侠客,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苏娥》篇讲的是一个凄美的复仇故事。寡妇苏娥外出经商,暮宿鹄奔亭,亭长龚寿乘人之危,图谋强奸并杀人越货。三年之后,交州刺史何敞夜宿此处,苏娥的鬼魂向其诉说冤情。而何敞明查暗访,终于昭雪沉冤,把龚寿绳之以法。
本篇被后人视为文言小说中较早的公案故事,它通过交州刺史何敞侦破的一件凶杀案,曲折地表现出人民的复仇精神。从案件发生到何敞入宿已历三年,逗留鹄奔亭的人想来不会太少。何敞或许不是第一个遭遇鬼魂诉冤的人,却是第一个接受申诉、同情被害者、拍案而起的人。正直官员的责任心和锄奸除恶、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在此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官员侠客,他既有官员的明断、慎密,又有侠客的果敢和疾恶如仇。其他人遭遇苏娥的冤魂,或吓得魂飞魄散,或觉得无稽,或漠然置之。而何敞听完对方申诉后的第一反应便是:“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这表明他对事件的真伪、是非已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之后,验尸、缉捕疑犯、审讯、查证、定罪,侦查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也按他自己设定的轨道进展,这些细节清晰地展现了何敞当机立断、精明干练的办事作风和性格特征,给人以深刻印象。
何敞又是《搜神记》侠客形象中最为复杂的一个。破案之后,以包庇的罪名处死凶犯全家,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一种过度杀戮、无法可依的行为,但仍然坚持为之。这就显得少了几分清官的理性和冷静,多了几分莽侠的盲目和疯狂。后世小说中的复仇者,为解一己之恨,常有滥杀无辜的现象,如《水浒传》中的李逵,抡起大斧,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一气,与此何其相似。在正义的幌子下处死罪不当死者,其实也是一种野蛮、罪恶的行为。这反映了何敞形象应该批判的另一面。何敞形象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行侠主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魏晋以降,传述侠客故事的小说蔚为大观。但总而观之,侠客的行为大体上仍在上述三大主题的框架之内。陈平原先生认为唐宋传奇侠客有“仗义”、“报恩”和“比武”三大行侠主题,后世的武侠小说大都依此为本。
这三大行侠主题与《搜神记》侠客的三大行侠主题可谓“貌离神合”。表现比武的作品如袁郊的《赖残》、段成式的《京西店老人》、《僧侠》、皇甫枚的《嘉兴绳技》等,着眼点都在侠客神奇的技击本领上,与《搜神记》中显示技艺的作品当属一类。所谓仗义类的传奇,则与《搜神记》中除害救危、复仇主题的作品相类。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洪迈的《解洵娶妇》、薛用弱的《贾人妻》等篇中的侠客,其仗义锄奸的性质不容置疑,但复仇的意味也是很浓厚的,这部分作品显然未出除害救危和复仇两大主题的范畴。唐传奇中报恩的侠客,如红线、昆仑奴、聂隐娘、古押衙等,他们的侠行虽未必都有锄恶之功,但都有救困扶危之实。如红线不流一滴血便替薛嵩制服了田承嗣,主观上固然是出于报恩,但客观上却化解了一场军阀混战,解救了无数濒临战火、危在旦夕的生灵。由此可见,报恩的侠行中,也包含有除害救危的主题。如此说来,后世小说中的侠客,其行侠主题依以为本者,实乃《搜神记》。《搜神记》侠客的三大行侠主题,为人们认识侠客及其行为的性质、特征提供了标本,不仅对后人侠观念的形成、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为后世小说的侠客规备了基本的行为模式。后世小说中的侠行义举尽管千姿百态,但都以此三大主题为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搜神记》为后世小说家之刻画、塑造侠客形象,演绎侠义故事,开创了最主要的几种类型。
三、《搜神记》侠客的行侠处所
《搜神记》侠客的行踪遍及亭馆、宫廷、官府、庙宇和山野河津等地,但除了亭馆以外,其余处所都是偶尔出现。在亭馆中发生的侠义故事,恐怕要超过其他地方的总和。如在前面论述过的宋大贤、安阳书生、何敞等人,其行侠的处所就分别在南阳西郊亭、安阳城南亭、苍梧鹄奔亭。其他如谢鲲除鹿怪的地方,为豫章郡空亭; 汤应勇斗猪怪、狐精处,是庐陵郡都亭; 北京督邮郅伯夷以头巾、帽子盖脚假寝,让妖精上当,从而将妖精除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狐狸精经常出没的无名亭馆……《搜神记》侠客的行侠处所主要集中在亭馆,这种现象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
西汉时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东汉后,这种设置逐渐废除。亭有配套的亭舍(馆) ,供过往旅客停憩、留宿,《搜神记》侠客的行侠处所,便是这种地方。由此也可知,亭馆遇鬼逢怪一类的故事,都应产生于汉代以后。作为一个流动人员停留、交会的场所,南来北往的旅客鱼龙混杂,盛旺时的亭馆必定是治安问题的多发地点,废弃后也多变成盗匪藏匿、作恶之所、坑蒙拐骗、谋财害命、淫人妻女之类的罪恶在这里不断酝酿和滋生。因此,亭馆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现实社会的魔窟,一个时刻“闹鬼”的地方,是丑恶现实的一个缩影。《搜神记》的侠客,多是作为邪恶的对立面出现的。因此,魔怪、邪恶出没频繁的亭馆,就成了侠客仗义行侠、驱邪惩恶的主要活动场所。
多以亭馆作为行侠处所,也与侠客的身份有关。前面已经论述过,《搜神记》中的侠客,以官员和书生为最多。官员因为公务,书生因为游学,都不可避免地要远足旅行,这就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光顾亭馆,成为那里的常客。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以亭馆为行侠处所的侠客,不是官员就是书生;在亭馆上演的侠义故事,无一不是官员或书生与牛鬼蛇神正邪交锋,最终邪不敌正、束手待毙的故事;官员和书生侠客的浩然正气和大智大勇,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到更多、更充分的展现。
《搜神记》对亭馆没有具体的描述,相关信息只在叙述中稍有透露,如宋大贤“尝宿亭楼……至夜半时,忽有鬼来,登梯与大贤语,聍目磋牙,形貌可恶”(《宋大贤》) ; 郅伯夷入住亭馆后,“传云: ‘督邮欲于楼上观望,亟扫除。’须臾便上。未暝,楼鐙阶下复有火。”(《郅伯夷》)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大概样貌: 三两层陈旧失修的阁楼,狭窄陡峭的楼梯,数间晦暗简陋、散发着霉味的房子。房间灰墙剥落,垢迹斑斑,老鼠、蟑螂等肆无忌惮地出没其间。在世人心目中,鬼魂精怪之类的污秽物,就寄居在这种阴森、污秽的处所。这样的场景对于侠客来说,更显得他正气凛然,艺高胆大。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气氛更加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满足他们喜欢猎奇、寻找惊险刺激的心理,收到“游心寓目”的效果。
由上可见,亭馆成为侠客、尤其是官员和书生侠客的主要行侠处所或背景,无论在故事的生成还是在叙事的修辞上,都是合乎逻辑的。亭馆伴随着侠客的活动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它既成就了侠客仗义除害的业绩,又因侠客的活动而被赋予新的功能和内涵,从而成为《搜神记》侠客行侠的一个典型场景,已具有相当固定的象征意义。
由于官办的性质,亭馆可以说是官府衙门的一种延伸,仍然是主流社会之一隅。活动于此的官员和书生侠客自然表现出独特的特征和文化品格。
正如前面所述,他们有着显赫的身份或受人尊崇的地位,行止也有较强的规律性。由于亭馆还处于官府权威的辐射半径内,亭馆之侠事实上还活动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面对妖魔鬼怪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强势,除了自身胆识、人格的力量外,恐怕与这一特定的活动场所也不无关系。而另一方面,亭馆也是固有秩序的一种象征。在这里,亭馆之侠无法超越自我,也无法超越现实,像活动在法外之域的江湖之侠那样随心所欲,有着天马行空式的潇洒和自由。活动被限制在相对固定、狭小的空间内,也使得他们的行侠故事比较单调,甚至类同,远不如驰骋于荒山野渡、游走于民居古刹的江湖之侠那样多姿多彩。这些都表明,《搜神记》中的亭馆,是官员和书生侠客赖以显示身份、品格和特征的合理空间。他们的侠行义举在此得以实现,情性得以显示,但同时又受之制约,它和侠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制约的关系。
小说中情节展开、人物活动的背景与空间谓之环境。环境既是特定社会历史风貌的展示,又是人物形象的补充、性格的外化。《搜神记》中,一般的人物活动场所都比较模糊而且分散,唯有亭馆是一个相对比较明确而且集中、固定的场所。它所展示的特定的人地关系、鲜明的时空特征和人物行为,已初步具备小说环境的意味和内涵,这在“粗陈梗概”,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魏晋志怪中,是难能可贵、令人瞩目的。在亭馆发生的故事虽然都荒诞不经,但人物活动的环境具有很强的、独特而鲜明的空间感,从而令故事演绎得逼真可信,在虚幻中透射出真实,显示出小说的艺术特质和魅力。这无疑为后世小说家营造人物活动的典型场景、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人物与环境、情节与环境关系的和谐统一,是小说成熟的表现,也是一种艺术追求,因此,小说家都比较注意经营这些关系。《搜神记》以亭馆为侠客的主要活动场所,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未必是自觉和刻意为之,但它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意识,事实上已为后世的小说创作起了示范的作用。
明以前的小说,对人物、情节与环境关系的处理都比较粗疏,明清之际的小说家才比较自觉、娴熟地处理这些关系。这说明,在小说创作中要达成这两种关系的和谐统一,历程是比较漫长的,也是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也才更显出《搜神记》示范作用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