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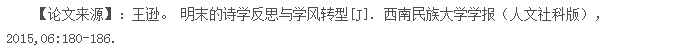
每一时代文学与诗学的发展总是建立在对前代遗产的继承与超越之上,故而,对先前已有充分发展的文学创作潮流或主张进行系统的总结,尤其是对其弊端的认真反思,就成为每一接续者的必备功课,新的文学创作潮流往往由此孕育,新的文学主张也每每就此发端。论及明清之际的诗学发展时,学人充分注意到清初士人对于明代文学、诗学的弊端进行了系统反思,并通过此一过程开创了清代文学、诗学的新局面,蒋寅认为"通过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清人愈益明确了自己的理论目标。清初诗歌观念的重建,正是对症下药、在反拨明代诗学的基础上完成的"[1].清初诗学固然别开新天,但许多工作并非由清初人肇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横跨两个时代,虽说他们的不少观点入清后方形诸文字,但若追根溯源,不少思考早在明末就已萌发,渗透着他们身处明末文学、诗学环境中的独特体验。
一、明人的文学反思意识
一代文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自会有人对其发展、演变史进行梳理和评判。自易代之际以来,对明代诗文进行总结的工作便代不乏人,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奠定了此后认识模式的当推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四库馆臣等人,详考诸家的种种论述,不难发现某种共同的倾向。如钱牧斋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渝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警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2](P.567-568)
而朱彝尊则如此描述他对明代诗歌发展史的理解: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3](P.636)
又《明史·文苑传》云: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为幽深孤峭。[4](P.7399)至《四库全书总目》,可谓集大成,《御定四朝诗》提要云:明诗总杂,门户多岐。约而论之,高启诸人为极盛。洪熙、宣德以后,体参台阁,风雅渐微。李东阳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阳已崛起与争,诗体遂变。后再变而公安,三变而竟陵。[5](P.2658)《明诗综》提要则论之更详,云: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
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相互左右。[5](P.2662)上述诸家对于具体流派、诗人、诗作的评价颇有差异,学者论之已详,但就其思考方式而言,却无不将明代诗文的发展史描述为"矫弊循环论"[6],即后一派的兴起往往是缘于矫正前一派的弊病。今人多半因袭了这一理解模式,或是着眼于其中的"对立",将明代文学、诗学的发展史描述为台阁、茶陵、七子、唐宋、公安、竟陵等派的斗争史,有些时候则根据其诗论倾向径直归纳为"复古---革新"演变史,进而批评明人党同伐异、互相攻击;又或者着眼于"矫弊",淡化各流派间的对立色彩,强调其观点内在的"互补".这两种理解方式自然都难免有所不足,故而有学者倡议"突破钱、朱批评的理论,……更多地关注明清诗文的创作和复杂的文坛现象"[7].此论有极大的开示意义,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了"矫弊"说的价值。
"矫弊"模式的建构并非是钱谦益等人的独创,王世贞也曾有过类似描述,云:国初诸公承元习一变也,其才雄,其学博,其失冗而易。东里再变之,稍有则矣,旨则浅,质则薄。献吉三变之复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厌。勉之诸公四变而六朝,其情辞丽矣,其失靡而浮。晋江诸公又变之为欧、曾,近实矣,其失衍而卑。故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先秦之则,北地反正,历下造玄;理学之逃,新建造基,晋江、毗陵藻梲;六朝之华,昌谷示委,勉之泛澜。[8](P.139)
考诸典籍,此种论调遍及有明一代,凡对诗史予以总结时无不沿袭了这一思路,就此可见时人认识的倾向性。再者,持"对立"说者为的是批评明代"霸道"的学风,此论偏颇处甚多,自应反省,笔者将有专文详论,此处暂付阙如;"互补"说强调复古、革新二者间的关联实是为了反拨当下推重革新、贬斥复古的观念,寻求理解明代文学发展的新线索,此中的积极意义不当忽视。此外,假如我们超越了上述两种视野,即不专门针对特殊流派或对象,亦不计较彼此的功过得失,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的话,"矫弊"观念的出现正说明明人始终具备鲜明的反思意识,他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问题并积极予以调整。
郭绍虞先生论王世贞称"他也正看到格调派的流弊,徒摹声响,不见才情,所以他要有些转变"[9](P.178),说王世懋乃"格调派的转变者"[9](P.190),胡应麟则是"格调派的修正者"[9](P.191).具体观点或不无可商榷之处,但他揭示出的现象或倾向却非虚辞。公安派方面,激烈如中郎,晚岁思想日趋成熟之时,也对早年的偏激之论多有反思;至于小修更是以公安派修正者的面目出现,他对乃兄创作中的问题并不回避,并对能矫其兄之弊者大为赞赏,称"今之功中郎者,学其发抒性灵,而力塞后来俚易之习。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10](P.462),在他看来,兴衰相继,后人对前人的反思与超越本就是必然规律。当然,基于立场、视角等因素的制约,很多反思的力度尚远远不够,但这至少说明他们并非一味盲从。
明末文人无疑继承了这样一种传统,对既往的七子、公安、竟陵这三股文学潮流所产生的弊端进行了积极反思(涵盖针对对立面的批判、自我反思以及超越派系论者的检讨三个层面),他们或是严厉批判七子的模拟、剽窃,或是强烈谴责钟、谭的幽眇峭独,他们认为,诸家阙失的表现特征虽然不一,究其根源,皆可归之于"空疏不学".吴应箕认为王、李文章"千篇一律"、"生气索然"乃是因"其言于经术甚浅"[11](P.545),其对公安、竟陵也有批驳,云:如近日某某方自谓其诗有性情,自予观之,直不成语而已,天下岂有目未读一寸之书,胸中无十古人名姓,但用几虚字作一二聪明语,便曰此见性灵之诗也,有是理哉?"[11](P.546)亦是标举学问之意义,钱牧斋则论之更苛,云"自近世之言诗者,以其幽眇峭独之指,文其单疏僻陋之学"[12](P.960),认为竟陵派所谓新风格的提倡只是掩饰自身"粗疏"的手段。时人对"诗"与"学"的联系多有认同,似成共识,如谢肇淛云:……不知作诗如采花成蜜,醸蘖为酒,胸中无万卷书,咀嚼酝酿,安能含万象于笔端,罗千古于目前?故未有不明经、不读史、不博古、不通今而能矢口成章者,皮肤影响,终非实际。[13](P.3500)从"学"的思路出发,他们对七子、公安、竟陵诸家的诗学流弊予以了深刻检讨,进而促成了明末学风的转变,并为其后诗学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二、诗学空疏的表现及反思
详考七子、公安、竟陵诸家的创作与理论,确有失学、废学的倾向。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不学"需区分创作的空疏与诗学的鄙陋两个层面,虽说这两种情况彼此联系,效果或影响却稍有不同。创作中的疏陋,如钱谦益批评"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14](P.312),又或如顾亭林批评《诗归》"尤为妄诞",并一一摘书中改字之例,"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15](P.1077)此类问题系由诗人读书粗疏、学问鄙陋造成。
至若诗学之鄙陋,虽与诗人自身学问的粗疏紧密相连,但它却不是表现为对知识、典故的无知或误解,更多的是"识"出现了巨大偏差,呈现出一种忽视或拒绝"学"的倾向。因对"学"理解之不同,诸家立论颇有歧异,个中是非得失亦需分殊。
所谓"学",首先可作"学问"解,在不少文人看来,学问与诗文存在较大的歧异,学问的介入将会影响诗歌的创作水平。如李攀龙有"视古修辞,宁失诸理"[16](P.394)之说,公安派的先导李贽云"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17](P.98),袁宏道则称"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18](P.463),而竟陵派提倡"真诗",其实质显然"也是一种妙悟说,而把它更缩小在狭窄的境界内,与'诗有才,非关学也'的说法,并无异致"[19](P.184).以上诸家所理解的学问亦有多种内涵,李攀龙所谓"学"系指理学,他出于对唐宋派论文道学气太重,"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以致于有"重道轻文"的倾向,才发出此等论调;卓吾所谓"学"亦系指理学而言,不过他对"理学"的反对原因与于鳞不同,主要针对的是当时道学的虚伪,受此蒙蔽,"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着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17](P.98).
此二者就其初衷而言确实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都不免"矫枉过正",预设了一定的理论漏洞。陈平原指出,公安派"批评前后七子将'学问'与'言语'分离因而无法自立,却是击中要害。……将一个文学运动限制在'法式'层面,并与思想、学说完全隔绝,其命运可想而知",因为"模仿秦汉之文,而又不愿涉及诸子百家丰富而且深邃的思想学说,所谓'复古'便只剩下雕琢词句了"[20](P.144).袁宗道在反思七子模拟之弊时就已然表达过类似意思,云"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21](P.285).
所谓"学"还可指前代的文学积累。诚如我们所知,后代文学都是对前人遗产的继承与超越,对前人的模仿本就是创作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而中郎前期的诗论则基于反七子的立场透露出无视传统的倾向,拒绝对前人的学习与模仿,宣扬"不拘格套,独抒性灵",这一观点虽有其现实性与针对性,却也的确造成了极大的弊端,牧斋云"驯至于今,人自为学,家自为师,以鄙俚为平易,以杜撰为新奇,如见鬼物,如听鸟语"[12](P.993),自然要在深刻反思中予以修正。
公安派崇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自然对"学养"颇不以为然(后期转变则是另一个问题);就七子派而言,李攀龙虽有"宁失诸理"之说,流露的也只是对道学的不满,却并没有忽视学养的意义。虽说时人及今人多批评他们"空疏不学",但他们的学识以及对"学"的重视却并非像今人描述的那么不堪,王世贞这样的博学巨子且不论,即使是李攀龙,王世贞云:
于麟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风神,大抵其体不宜多作,多不足以尽变,而嫌于袭。[22](P.1063)这里虽是批评他对西京、建安的效法未能臻至拟议而变化的高度,但"临摹帖"、"袭"说明于鳞对古乐府及西京、建安诗的理解确有一定的造诣。黄宗羲对七子的空疏多有批评,但也有回护之辞,称"攻北地、太仓者,亦曾有北地、太仓之学问乎?"[23](P.70)对七子的学识尚有所肯定。七子派的文学纲领被概括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对于自己所推崇的对象必然要有深入、系统的研习、体悟。
七子派诸子未必学识不佳,一应见解亦是出于涵咏前贤典籍所得,在此引导下断不至沦落为"空疏不学",但现实却是"单疎僻陋",原因即在于建立在一定学养基础上的诗学理论因其表述方式和接受效果而客观上造成了"废学"的倾向。万历中期以来,其后学就已有所反思,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如胡应麟云:明兴,庆阳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踪三古之上,经秦纬汉,出宋入唐,……拟议之则滞焉弗镕,采蓄之程隘焉弗广,两都而外,诵法靡征,六季以还,见闻旋废,以致缘情者病其剽敚,多识者陋其拘挛。[24](P.802)又如屠隆称:李、何从宋元后,锐志复古,可谓再造乾坤手段。近代后生慕效之,涉猎西京,优孟《左》、《史》,不读古人之全书,不识文章之变化,亦李、何启之也。[25](P.444)七子派论诗主要标举汉魏晋盛唐,其中固然有个人偏好的因素,然而汉魏晋盛唐确系诗歌创作的典范,且这种典范意识的确立是建立在广泛的研读、辨析基础上,七子派诸子就曾"经秦纬汉,出宋入唐",严羽固然称"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天宝以下人物"[26](P.1),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有赖于依次取汉魏诗、晋宋诗、南北朝诗、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诗、开元天宝诸家诗、李杜二公诗、大历十才子诗、元和诗、晚唐诸家诗、苏黄以下诸家诗熟参,"真是真非,有不能隐者"[26](P.11).换言之,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建立在深厚学识的基础上,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学识才能领悟其真谛。
但在所谓的"文学主张"里,却未曾融摄这"熟参妙悟"的必备过程,推崇的典范固然优秀,但仅仅拘泥于狭隘的对象本身却无法完全领悟其魅力,所谓"不读古人之全书,不识文章之变化".李维桢多次强调学习前人要善于甄别,他对《顾李批评唐音序》一书大为赞赏,原因就在于:今观是编,而唐人之所从入,与其格之分初盛中晚,献吉之所以能为唐诗与其不合于唐诗者,其大致可窥也已。[27](P.493)没有广泛的阅读以及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行的比较,根本无法找到"靠近"典范的途径,所谓的"学古"终究将沦为"泥古"、"摹古",通过"窃取"古人的字句、用典、音律、法式来获得所谓的古人面貌,形成字模句袭、千人一面的状况。
上述诸家已然对七子派诗学纲领的狭隘及流弊多有警醒,王世懋也意识到了这一层面的问题,且论之更详,并明确凸显"学养"来完善格调论诗学主张的不足。其云: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傅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然使诵其诗,果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当上宗,论诗亦莫轻道。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晚唐诗人,如温庭筠之才,许浑之致,见岂五尺之童下,直风会使然耳。览者悲其衰运可也。故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28](P.779-780)按照王世懋的见解,想要实现格调派的诗学理想,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真情实感,二是真才实学,这二者本是七子派诗学的题中之义,却因种种因素而被忽略,故而他才要大力表彰。明末诸人或许不能认同七子派的"格调论"主张,但他们对七子派的反思却大体沿袭了上述思路。如钱谦益对七子攻之甚烈,多处以"俗学"视之,但他并非只是针对具体的人事,更多的在于他看到了七子派文学主张,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等观点产生的流弊,其云: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敝,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弘治中学者,以司马、杜氏为宗,以不读唐后书相夸诩为能事。夫司马、杜氏之学,固有从来。不溯其所从来,而骄语司马、杜氏,唐以后岂遂无司马、杜氏哉?务华绝根,数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谓复古者,盖亦与俗学相下上而已。[12](P.992-993)
俗学之"俗",与学术之弊类似,时人仅仅阅读一些简单的删割本,而未曾寻根溯源,系统、完整地研习经典,于古今学术之传承与流变缺少综合的认识,他们对古人的理解因缺少此一功夫,故往往只得皮毛而不识要领。通过完整地阅读、细致地比较,才能体悟最终的结论,而七子派的诗学主张却无形中舍弃了重要的经典涵养过程,即忽略了学养的重要意义,执着于一个空洞的口号,不免流于教条。郭绍虞曾批评严羽"他不拿这方法教人,而偏拿他所认为实证实悟自家开辟的田地去教人,那是嚼饭喂人,便不合于禅了"[9](P.69).七子之失近于此。
不唯牧斋,艾南英也有类似意见,其与陈子龙论文时云:及在舟中见足下谈古文,辄诋毁欧曾诸大家,而独株株守一李于鳞、王元美之文,以为便足千古,其评品他文皆未当,不佞心窃叹足下少年,未尝细读古今人之书而颠倒是非,需之十年后足下学渐充、心渐细,渐见古人深处,必当翻然悔悟。[29](P.204)
在千子看来,卧子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的造成就在于他简单地接受了七子派的偏颇主张,未曾全面、系统地研习前代典籍,因学识的不足导致了论断的错误。可以说,牧斋、千子的观点正是对七子派后学的强调与深化。由此亦可明证,所谓"晚明"思潮不可仅以"革新"视之,诸种矫正之方已然孕育并得以继承发展,终至成为一时风尚。此外尚需注意的是,牧斋与七子、千子与卧子之间存在严重的观念对立。千子认为卧子"未尝细读古今人之书",即学养不足,因而才会信奉七子的主张,若果真笃学而有识,自会发觉七子之非而转向。牧斋也认为但能读书反思,便能发现七子的谬误。
牧斋、千子对七子"不读古人之全书"的批评甚为有见,但他们的上述结论,看似言之凿凿,却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七子诗学观念之形成,也系得自于他们对经典之涵养,只是彼此立场对立,所学虽同,所得有异。陈子龙并非不学之人,纵是不学之人,一番穷究,也未必就能赞同牧斋或者千子的主张。但问题在于,此时的文坛"学诗者,知空同、元美而已矣。其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知空同、元美之汉、魏、盛唐而已矣……学者冥行倒植,不见日月"[12](P.925),甚而"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辞华浓丽,绚烂夺目,细按之,一□□耳"[29](P.210),对于"学",或者说得明确一点,对学养、学识的淡忘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千子对卧子的批评未必完全妥当,但他强调"细读古人之书"却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同样的,时人未必都认同牧斋的观点,但他至少倡导了一种意识:读全书,重自得。这既促进了"学"之价值的彰显,对于改造其时的学风、文风也大有裨益。
三、学风之新貌
明末学人通过系统的诗学反思,迫切想要扭转"不读书",尤其是"不读古人之全书"的陋习,与此相呼应,时人积极倡导改善学术风气、调整治学方法,概而言之,以下三点颇值重视。
一为博与全。时人一反不读全书之陋习,在学术积累过程中注重博观泛览。如陈子龙,夏允彝称"其学自经、史、百家言无不窥;其才自骚、赋、诗歌、古文词以下,迨博士业,无不精造而横出"[30](P.1642),此语不无过誉之嫌,但卧子在求学过程中确曾多方取益,据其自撰年谱称:(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先君至慈爱,每夜分,则引予称述古今贤豪将相,以至游侠奇怪之事;并教以《春秋三传》、《庄》、《列》、《管》、《韩》、《战国》短长之书,意气差广矣。[30](P.918)又云:(万历四十七年己未)是岁,……始专治举子业,兼通《三礼》、《史》、《汉》诸书。秋,先君从京师归,益励以古学。[30](P.919)又有黄淳耀亦称:生平厌薄陈言,独好泛观古人之书,盖尝求义理于六艺,求事迹于二十一史,求万物之情状于骚赋诗歌,求载道之噐于汉唐宋数十家之文章。[31](P.67)
但有所警省的毕竟只是少数,陈子龙虽有多方取益的求学经历,但"今世无诵《史记》、《文选》者,有之惟陈卧子,盖其父学也"[32](P.274).文坛的整体形势仍呈恶化趋势,前引钱谦益等人语即是明证;加之现实形势日益危殆,在经世意识的推动之下,相关士人在自觉践行博学多闻原则的同时,试图集合同道,将"通经学古"营造为普遍的社会思潮,从根本上扭转颓败的局面。譬如张溥,其着述囊括经、史、子、集四部,个中除所谓的学术着述外,大都是整理编订的作品,如经部的合纂、史部的两种纪事本末,集部的自先秦至元的文选等等,为的是提供相关领域内具有典范性的作品,便于学人观摩、效仿,并藉由编辑活动中的全面、丰富旨趣向时人灌输博观、泛览的理念,由此可见张溥作为新风气推动者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如果说以前"博"只是一种自觉,如今则要推广为一种风气与方法。
受此风气的影响,文学领域内的编辑活动也有所改观。推行某种主张或理念的最普遍也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选本;同样的,选本也是反映风气转变的最明显的证据。查清华研究发现"明初期高棅的《唐诗品汇》虽然宗主盛唐,但立足于备一代之制作。进入前后七子时期,除少数几个选本略具一代规模外,大多都选某一段时期,又以初、盛唐为最,晚唐更是很少涉及",而自万历后期以来,随着"博观"意识的日益深入,选诗也具有了"求全备"的意图[33](P.304).一方面,中、晚唐诗歌选本大量出现,如朱之蕃编《中唐十二家诗》、《晚唐十二家诗》、李之桢编《唐诗十家集》、姜重生辑《唐中晚名家诗集》、刘云份编《中晚唐诗》、龚贤编《中晚唐诗纪》等,弥补了过往诗歌选本多以盛唐为主的不足。此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断代唐诗选集,如胡震亨编《唐音统签》,分为十集,收诗数万,将全唐三百年诗次为一编;又如范汭、茅元仪编《全唐诗》一千二百卷,试图将有唐一代的诗歌搜罗殆尽。
"求全备"的意识更多表现在通代诗歌选本的编选上。如钟惺、谭元春编《诗归》(包含《古诗归》与《唐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又如陆时雍编选《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收录自汉魏以迄晚唐之诗;个中翘楚自推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计五百零六卷,选诗范围上起古初,下讫于明,蔚为大观。
至于文章选本同样贯彻了这一"求全备"的意图,如梅鼎祚编纂有《八代文选》,共计三百余卷,四库馆臣云是书"上起古初,下穷八代,旁搜博采,旧合成编,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5](P.2652).又有陈仁锡先后编纂《古文奇赏》二十二卷、《续古文奇赏》三十四卷、《奇赏斋广文苑英华》二十六卷、《四续古文奇赏》五十三卷、《明文奇赏》四十卷,比较全面地收录了先秦至明代的文章。自然还要提及张溥的《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是书一百十八卷,四库馆臣虽批评这部书"编录亦往往无法,考证亦往往未明",却肯定其保存文献之功,云"然州分部居,以文隶人,以人隶代,使唐以前作者遗篇,一一略见其梗概"[5](P.2654).
二为博与通。时人积极强调博观泛览是文学研究与批评基本的原则,并认为只有在通盘考察的基础上获得的整体性认识才是合理并可靠的。
冯复京有感于"凡今之人,守琅琊之《卮言》,尊新宁之《品汇》,习北海之《诗纪》,信济南之《删选》,谓子美没而天下无诗"之论,于是用"一生目力",写成《说诗补遗》一书。具体的写作原则或方法即是"历观唐人诸集",兼及汉、魏、六朝之作。[13](P.3963)许学夷论及作诗之法,也称"学者闻见广博,则识见精深,苟能于《三百篇》而下一一参究,并取前人议论一一紬绎,则正变自分、高下自见矣"[34](P.313).所谓"一一参究"与"一一紬绎",强调的是对前代的文学遗产要有全盘的勘察和细致的辨析,从而获得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他在写作《诗源辩体》一书时就曾"《三百篇》而下,博访古今作者凡若干人,诗凡数千卷,搜阅探讨"[34](P.1),故而他在对前代文学的研究中,特别强调要有"全局"观,每每言及"全集",如:即李杜全集,瑕疵莫掩,况他人乎?于鳞似宗雅正,而实多谬戾,学者苟不睹诸家全集,不免终为所误耳。
二家之诗,前贤多未发明,其全集人未有竟读,怪癖者全篇既不可编入,而摘句又不容多,则人终不能知宋人之极变也。韩才智本胜欧,但以全集观,则韩太莽苍,欧入录较多而警觉稍逊,然不免步武退之。宋人七言律对着意变唐,然亦有自得之趣。惟介甫大多晚唐僻调,而恶句复多,又用事无虚句,可谓事障,以全集观,乃见。
故予论古人诗,即予所录有足证者,论国朝诗,非全集不足以为证也。国朝先辈取法初、盛,然视其全集,往往玷缺,多不足观。
从"全集"的角度看问题,最直接的益处在于我们可以获得对对象的全面认识,或是发现某些被我们忽略的现象,或是纠正某些偏颇的论断,从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这一切都只有"以全集观,乃见".但强调"全"或"博"根本的是为了对历来文学的发展获得全面的认识与深刻的感受,前文已然提及,七子诗学之弊更多的不是表现为"废学",而是忽略了理论表述所依托的深厚学养,因没有通盘的考量而缺乏深刻的认识,钱谦益斥七子为"俗学"时,曾有如此疑问:
弘治中学者,以司马、杜氏为宗,以不读唐后书相夸诩为能事。夫司马、杜氏之学,固有从来。不溯其所从来,而骄语司马、杜氏,唐以后岂遂无司马、杜氏哉?[12](P.993)依照钱谦益们的理解,历代文学处于先后相继的发展脉络中,有源(即六经)有流(即各代文学),有因有创,有经验也有教训,故而凡作诗者,第一要务即在于通读前代遗产,认识历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明晰其利弊得失,从而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奠定基础并明确方向。许学夷称其作《诗源辩体》"自谓有功于诗道者六",第一条就是"论《三百篇》以至晚唐,而先述其源流,序其正变",因为"诗自《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与言诗矣".
三为博与自得。博观固然能够获得对"文学"传统的深刻体认,但光有"博"的意识尚不够,许学夷特别强调了"识"的意义,其云:学者以识为主,造诣日深,则识见益广矣。今或有为古人所恐者,有为盛名所恐者,有为豪纵所恐者,有为诡诞所恐者,皆造诣不深,而识见不广故也。如初、盛唐诸公,已自妍媸不同,大历而后,益多庸劣,今例以古人之诗而不敢议,此为古人所恐也。如李献吉律诗,入选者诚足上配古人,其余卤莽多不足观,今但以献吉之诗而不敢议,此为盛名所恐也。至若才力豪纵者,顷刻千言,漫无纪律,资性诡诞者,怪险蹶起,而蹊径转纡,初学观之,震心眩目,俛首受屈,此为豪纵、诡诞所恐也。
苟造诣日深,识见益广,则精粗自分,好丑自别。[34](P.319)博观是为了强调有所发现,但这一发现必须建立在自我思考的基础上,若如"为古人所恐者"一般,依附于他人墙角之下,不懂得勤学多思,确立自己的一己之见,所谓的博观泛览也无法获得应有的价值。
对"自得"的强调,既是理论本身的内在需求,更多地则是针对当日的现实问题而发。因时人"不读书"或"不读全书",有识之士才有"博观"之提倡,但这种"博观"往往流于形式,缺少"一一究心"的细致涵养,渊博的知识成了炫耀的资本,取材的广阔更助长了剽窃习气,罗万藻云:戊辰以来,天下慕为经术深右之文,然而剽掇杜撰,其端百出,所谓伪经伪子,入于文字者日□。[35](P.422)艾南英论及作文之法时,特别提到了归有光,云:此老(震川)留心《史记》,摹神摹境,假道于欧,欧者,《史记》之嫡子,而此老则欧之高足也。
愿兄澄心静气,日取《史记》、《左传》反复读之,看古人所以为古人者何如,然后日取韩、欧两集,看两公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然后泛及于宋、余诸公,则不待比拟而皆合矣,然后又泛及于国初诸公,又泛及于今日荆川、遵严、震川数公,然后以较王、李,真若一入芝兰之室,虽非古清庙明堂,而芳洁自在;一若入粪厕屠肆,腥秽扑鼻。[29](P.212)不唯"博",更要在此过程中深入体味"古人所以为古人者何如"及"之所以摹古人者何如",对于为文之法有根本的领悟。
明末学风转型是多种因素推动下的产物,其影响亦遍及多个领域,就诗学而言,一方面,伴随学风转型,诗学势必要有所调整;另一方面,诗学领域内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了学风转型的进程,彼此影响,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J].文学遗产,2006(2)。
[2](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魏宏远。论王世贞明诗流变观[J].兰州学刊,2008(1)。
[7]李圣华。明清诗文新批评刍议[J].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
自明中期始,诗坛的主流是前后七子的齐气与公安、竟陵之楚风交互称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角逐之中。而在江南一带,仍然有许多文人在强势主流话语之外保持独立的吴蟎特色。明代中后期诗坛实际上是在三种不同地域诗学的相互抵抗、相互包...
引论古典诗学发展到清代,其内部已有从儒家经学话语和杂文学观念的束缚中逐渐松动的迹象,如阮元文言说对文学用韵比偶要求的提出。然而,古典诗学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异常复杂的文化生态,晚清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乾嘉时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到...
自刘勰《文心雕龙镕裁》提出士龙雅好清省的论断后,认为陆云诗学思想的核心是清省或曰清,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①.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虽然自然、清与清省等等,都是构成陆云诗学思想的基本范畴,但是却分属不同的逻辑层次.以自然为审美本体,以清为审...
一、诗学背景与研究背景有的学者将清代中期著名诗论家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归之为格调说,且强调格调说所承载的儒家诗教属性。实际上,将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归于格调说并不是很恰当。首先,沈德潜未以格调一词来标榜自己的诗学理论,没有像明代七子派那样称道他们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