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海上花列传》作为海派文学文化记忆的出发地, 以商业性上海叙事呈现上海记忆。在文化记忆视角下, 这种呈现就是海派文学文化记忆的唤醒和追忆。海派文学通过“上海叙事”构建文化记忆, 也促进了上海文化记忆传统的形成。《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建构上海记忆时, 其相互成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使它们互文记忆的意义昭然若揭。这不仅为确认海派文学的“身世”及《海上花列传》对海派文学的奠基性作用提供了另一种探寻的思路, 更重要的是, 为研究文学内部变化提供了一种记忆与文学模仿关系的分析范式。
关键词: 文化记忆视角; 《海上花列传》; 上海叙事; 海派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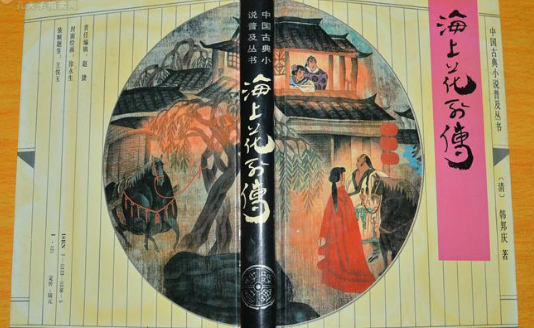
Abstract: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ultural memory for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restores the memory of Shanghai through commercial Shanghai narrative.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Shanghai has become the awakening and retrospec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memory in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Shanghai narrative in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establishes the cultural memory in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dition of Shanghai cultural memory.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Shanghai memory on the part of both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and other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they are mutually helpful, mutually conducive and complementary.It is completely bared there and the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of intertextual memory,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in identifying the origin of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and confirming the fundamental role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plays in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intertextuality provides a new paradigm-an analysis of memory and literary imitation to study the internal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Keyword: perspective from cultural memory;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 Shanghai narrative;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
一、引言
作为中国近代最为杰出的通俗小说之一, 学界对《海上花列传》的文学成就赞誉不少。如范伯群认为“《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1](P157);陈思和认为“《海上花列传》是海派文学的开山之作”[2](P259)以及“《海上花列传》是海派文学的另一传统的起点”[3](P4)等。具有一定成就的文学文本才有启发性作用, 才能发挥文本的记忆功能, 才能将该文本置于文化记忆视角下对其进行研究。《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通过对“上海”的记忆叙述将其文本纳入到对上海社会历史回忆的这个大文本里, 并以开创性的“上海叙事”模式存储近代上海社会文化信息, 从而实现其小说超越时间的记忆功能。叙事学家普林斯认为, “说时间性就是说叙事”, “在时间序列中发现有意义的图式”[4](P144)。韩邦庆通过对上海进行商业性叙事, 赋予近代上海空间以时间的意义, 这一叙述是创作者对上海这一记忆空间进行时间记忆的转换。以商业性的上海空间对近代转型时期的时间予以叙事记忆, 从而使文本成为记忆上海的文化文本。作者叙述的空间成为回忆上海的激活器, 通过对其文本的空间体验回忆了海派文学文本的过去, 文本对空间意义的呈现也成为了对时间记忆的存储。本文所谈及的上海叙事是语境叙事, 是对上海进行时间标识的叙事, 是赋予空间以时间意义的叙事, 是一种记忆形式。因此, 将《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置于文化记忆视角下研究很有必要。此外, 尽管学界对《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早有论及, 但目前对它们此种关系进行文化内部的分析仍有不足, 尤其是将它们的关系置于文化记忆视角下进行记忆与文学模仿的内部关系分析, 更是缺乏。不管是从小说对上海空间进行时间标识的文学成就来说, 还是从海派文学文本对“上海叙事”传统的形成所起的循环促进作用来说, 深入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研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基于这一状况, 本文以海派文化记忆为视角, 将“上海叙事”这一具有模仿色彩的叙事成规作为分析视点, 从《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特征出发, 对文本时间标识的叙述记忆进行分析总结。正如“文本的记忆就是它的互文性”[5](P215)所解释的那样, 本文试图探究叙述上海这一空间的互文文本是如何标识时间的, 并如何对海派文本的生成发挥其影响, 而海派文学又是如何回忆上海, 并在回忆上海中促进记忆上海文化传统的形成, 由此探讨《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之间的内部状态。这一研究不仅显示出它们之间互文记忆关系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 能为分析文学内部变化提供研究范式。
二、《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
文本叙事能为人类记忆提供讲述、提取、模仿等工作方式。《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就是作者对“上海”提取记忆的方式。创作于近代上海转型时期的《海上花列传》以何种方式提取记忆, 又以何种方式记忆上海?作者通过商业性叙事对近代上海进行记忆提取, 同时, 也以商业性叙事对近代上海进行时间标识。这种标识时间的商业性叙事是对近代上海社会面貌的再现, 任何个人记忆都是社会现象的产物, 作为个体记忆的小说文本《海上花列传》同样也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转型时期的近代上海, 由于海禁大开、商业社会的渐变, 商业性成了此时上海地标性的文化特征。而小说文本的商业性叙事对上海面貌的呈现具有转型社会的时间标识。历史是记忆的存储, 记忆是对历史的建构。社会历史的文化语境对叙述内容起着决定性作用。近代上海商业社会文化语境决定了作者的商业性叙事, 这种商业性叙事成规不仅以叙述商业文化的图景作为其记忆近代上海的记忆术, 还以作者商业行为的个体经验再现时代面貌。韩邦庆于1892年创办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 并由《申报》馆代售。将《海上花列传》连载在《海上奇书》上, 是作者对《海上花列传》进行的报刊连载小说文本的商业化操作。此种商业化运作行为也是作者与近代上海商业社会互动的产物。这一打上时代烙印的个体经验记忆充满了实证成分。“叙事成规决定着一个被描述的事件是否‘事实’”[6](P65), 文本的叙事成规决定着被打上时代烙印的商业性“事实”, 这些商业性叙事是作者建构上海的方式。这一建构方式既对近代上海进行了信息存储, 也对回忆上海起了媒介作用, 从而实现了对上海回忆空间进行时间标识的记忆转换。而这种时间标识的记忆意义是:如果说文本的商业性叙事标识的上海是过去的上海, 那么过去的上海不仅会影响现在的上海, 也会指导未来的上海, 尤其是在对上海的叙述姿态上, 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必定会发生着内在的联系。海派文学凭借与《海上花列传》这一内在联系, 在重构上海时必然回忆着上海的过去。正如拉赫曼所说:“文学和记忆之间的互文关系就是一种‘静态记忆’。”[5](P272)互文记忆是一种文本联结, 这种文本联结来源于文本之间的记忆技巧。《海上花列传》作为记忆的“静态”文本, 以商业性叙事技巧对近代上海进行商业文化记忆。文本商业性的叙事技巧是在社会框架下, 对近代上海商业文明集体记忆的分有, 这种个体记忆对上海社会集体记忆的分有是海派文学记忆的成规。《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不仅实现了对近代上海空间的文化记忆存储, 同时也唤醒了海派文学的上海回忆。
1.个体认同下的“鸦片”记忆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鸦片战争, 是西方列强非法兜售鸦片、强行打开中国国门的侵略战争。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下, 正统文化叙述的“鸦片”会借以抒发祸国殃民的哀怨或忧国忧民的悲愤, 《海上花列传》却将“鸦片”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趣味或物质文明的审美来叙述。在这个文本的个体记忆叙写中, 特别是在描摹近代上海人们日常生活时, 呈现了人们如何消费、享用鸦片的面貌。《海上花列传》全文文本共64回, 几乎每一回都会写到吃鸦片、抽大烟的日常情景。作者不仅将鸦片描绘成人们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的生活消费品, 还将其作为商业社交的形式予以呈现。如善卿与外甥赵朴斋相见时, 就“将水烟授与朴斋, 道:‘耐坐一歇, 等我干出点小事体, 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朴斋独自走着, 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7](P167)。善卿“授烟”会意朴斋耐心等待, 此时的水烟也如同今天的“烟”或“电视”给人礼遇, 供人娱乐消遣, 是一种礼貌性的招待。这种将鸦片作为日常消费品的去政治化写作, 再现了近代上海鸦片泛滥的社会情形。如善卿和朴斋相互“授烟”和“送烟”, 朴斋送水烟筒给善卿, 善卿又将水烟筒转送给小村, 并说一些让小村照应外甥朴斋的话, 鸦片不仅礼遇他人, 也成了人们传达情感的媒介。如果鸦片在近代上海没有如此流行泛滥, 那么鸦片就不可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催生成礼遇他人的“消费品”, 并成为衡量彼此之间情感的尺度。这一个体记忆下鸦片叙写的意义在于, 因为“历史学家学会了信任‘自己’最个人的、最私密的感受”[8](P52), 作者对近代上海流行的鸦片进行了忠于人们自我生活经验的描写, 所以, 这一忠于人们自我经验的个人化记忆也就越显得真实了。作者将忠于生活经验的“鸦片”存储成人们的“消费品”, 不仅促使人们对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历史记忆犹新, 更重要的是, 这一存储的记忆反映了近代上海商业社会的文化状况, 标识了近代上海商业文明发达的空间。
社会情境作为叙事记忆的基础对人们经验记忆的写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者以高超的叙事能力与不凡的叙事技巧将鸦片泛滥的近代上海“栖居”在《海上花列传》这部杰作里。作者对鸦片进行了遵从日常生活的私人化叙写, 是由近代上海商业社会情境所决定、以“群体”为单位的个体认同。正如哈布瓦赫认为的那样, 任何个人或群体单位的个体记忆都是社会框架内集体记忆的分有[9](P29)。小说文本对鸦片进行的商品化叙述是对近代上海商业文化记忆的存储。作者对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存储的鸦片记忆进行了呈现。如第二回《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创作者鲜明地将“鸦片大烟”的内容“内经验”到一种顺手拈来的自然书写中。如“左横安大床, 右一张烟榻, ……倒铺得花团锦簇”[7](P172), “王阿二索性挨过朴斋这边, 拿签子来烧烟。朴斋心里热的象炽炭一般”[7](P174)。作者对水烟的授、送、点、抽、拨等内容进行近乎自然的描摹记叙, 不仅再现鸦片充塞人们的日常生活, 还将鸦片参与人的“情欲”生发, 将吸烟描绘于人们生活习惯的养成中。作者对“吸烟”及其场所极尽翔实的描绘, 成了创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审美”。这种对“纯个人”当下历史状况的审美呈现, 被纳入到对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回忆的大文本里, 而这一个体认同的鸦片记忆对回忆过去的上海社会发挥着重要的记忆功能。尽管这种有悖于宏大历史的鸦片叙述, 或许已超出“鸦片”的自身范畴。正如《崇高的历史经验》所论述的那样:“对过去的经验并非它自鸣得意地符合了某个历史学家自己的记忆、期待和实际确信之事的那种经验, 而是出现在否定了我们对世界的一切直觉知识的地方。只有在这里, 我们才能与保持着其毫不妥协的、彻底的陌生感的过去相遇;这种陌生感也是过去的‘崇高性’……只有在这里, 我们才发现一种过去、一种文本, 它将挑战我们为理解世界而提出的一切范畴, 将过去转变为其本来所是的那个异己而奇妙的世界。”[8](P53)文本叙述的鸦片记忆不仅发挥了其“异己”“陌生化”等特殊力度的记忆效果, 丰富了上海的文化记忆, 更重要的是, 还使人们开始关注有悖于常理、异己、陌生的鸦片背后的原因。近代上海商业社会情境这一无意识的“政策性”影响, 促使创作者的书写遵从生活本身的鸦片记忆, 这一个体认同下的“鸦片”成了唤醒过去上海的激活器, 重新书写的“鸦片”记忆也成了近代上海商业文化的媒介。
2.个体认同下的商业文化记忆
鸦片战争后, 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通商口岸。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近代上海, 发达、繁荣与糜烂、畸形共生。《海上花列传》对于买办商人也进行了符合这一社会特征的身份记忆述写。作品描述了一个整天奔波、忙碌于矛盾调解之中的人物:洪善卿。作者对洪善卿出场的介绍, 要么是在嫖客和妓女矛盾的调解中, 要么是在奔赴解决矛盾纠纷的途中, 或赶赴置办用以解决矛盾的物资途中。作者就这样将洪善卿置身于传递信息、消除误会、宽解安慰的调解工作中。中国历史上的买办商人, 由于能获得外国殖民者和中国当权势力的信任与倚重, 成为传递双方信息、协调双方矛盾或利益的沟通者、联络人, 买办商人也利用自身联络人的身份牟取利益。小说所描绘的洪善卿恰如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买办商人”的形象, 对他的叙述不仅是作者对买办商人形象的临摹, 也是作者对近代上海日常生活人物形象的再现。这一记忆形象是创作者与当下社会情境结合的产物。记忆需要呈现或传播的方式, 创作者叙述的形象就是呈现或传播文化记忆的方式。这一形象回忆了社会历史情境, 近乎真实地再现了近代上海的商业文化。洪善卿对沈小红、王莲生、张惠贞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 对朱淑人与周双玉等人之间的矛盾进行解决, 并牟取自身的利益。这些协调工作的开展及其自身利益的获得, 都源于妓女和嫖客双方各自利益的需要, 洪善卿不仅成了协调矛盾或利益的沟通联络人, 期间, 也相应地被邀请参加各种“吃花酒”的聚会交际活动。在商业兴起的近代上海, 交际活动日渐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商业活动的重要内容。因为人们在聚会交往中能获得商业信息, 并为各自的经济利益而达成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洪善卿也在频繁的吃花酒聚会中, 构建自己的友好关系网络。这些活动的参与或进行, 都得益于他自己是沟通联络人这一特殊的身份, 同时, 洪善卿也从中获取了大量利益。文本描绘洪善卿的日常生活工作与历史上买办商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如出一辙, 洪善卿就如同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那些买办商人的影子。韩邦庆对这一人物日常生活的叙述, 是将买办商人的“类型化”特性进行了回忆, 是对买办商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模拟, 是将宏大历史内化成无意识的审美。文中对洪善卿日常生活经验的审美再现, 以及对其牟取自身利益的途径和本性的描述, 赋予了洪善卿这一人物形象以买办商人的想象。洪善卿是韩邦庆对买办商人的想象性记忆, 尤其是对其沟通联络人的身份记忆, 更是对近代上海商业社会集体文化记忆的分有。有历史的地方就有记忆, 作者对近代上海社会历史的想象性记忆显示了其不凡的叙事能力。
《海上花列传》的上海叙事不仅回忆商人的身份, 同时, 也回忆商人引领社会的精神文化。如第十四回《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小村道:‘要是牌勿好, 输起来, 就二三百洋钱也无啥希奇’。朴斋道:‘耐输仔阿拨俚哚?’……小村道:‘耐勿晓得。来里上海场花, 只要名气做得响末就好。耐看仔场面浪几个人, 好像阔天阔地, 其实搭倪也差不多, 不过名气响仔点’。”[7](P259)文本通过张小村的视觉描述, 对近代上海商人利用金钱造“势”的社会风俗进行了回忆, 这些社会风俗正是商人引领社会风尚的再现。文本就以展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回忆近代上海的社会精神风貌。大商人齐韵叟偶遇陈小云, 随口邀请他参加其家庭聚会。陈小云对大商人齐韵叟的邀请非常重视, 他非常兴奋地亲临“衣庄”拣取“新时花浅色衫褂”, 打听聚会是否要作对酒词等细节。可参加聚会时, 竟然找不到进齐府的门, 几经周转寻找, 总算问到了齐府的管事, 可是连管事也不知道主人邀请了陈小云。此种“慎之”与“淡之”的鲜明对比, 一方面极尽能事地渲染了大商人齐韵叟的怠慢和霸气;另一方面也反衬了商人引领社会风尚的精神风貌。陈小云渴望融入其中, 也属正常现象。“小云安心坐侯, 半日杳然, 但见仪门口一起出出进进, 络绎不绝, 都是些有职事的管事, 并非赴宴宾客。小云心疑太早, 懊悔不迭。”[7](P513)陈小云处处小心谨慎, 这与他的自我镜像相关, 而这种自我镜像认同, 又与近代上海社会精神风尚对商人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联。他周边的生活世界也印证了他对商人社会价值的认同想象。如陈小云有意在生活圈散布“被大商人邀请赴会之事”。“金巧珍也问道, ‘耐陆离去认得个齐大人?……耐搭俚做仔朋友末, 倪要到俚花园里白相相去。’”[7](P512)金巧珍对大商人齐韵叟巴望的心跃然于纸上。庄荔甫在与齐府的职事做生意时, 看见陈小云赴宴, 对此也表现出“不胜艳羡之至”。庄荔甫也渴望像“陈小云一样”能出入大商人的家。“秀林道:‘耐个财气到哉!’庄荔甫道:‘倒无啥!耐说财气, 陈小云故末财气到哉!’遂把小云赴席情形细述一遍。”[7](P514)言词之间, 他们都期许自己能进入大商人的交际圈, 并获得世俗社会认可的象征性身份。正如巴赫金所说:“语言是一个社会评价的大系统, 在这个大系统中, 言谈之间的碰撞、交流、对话和意义的价值交换, 会迸发出意义的火花……”[10](P17)陈小云、金巧珍、庄荔甫、陆秀林等人言谈举止的碰撞, 恰好对商人的价值认可做了中肯的评价。人们日常交往的言谈举止是“个体认同”下的社会文化。文本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取向的描写, 进而对商人引领社会的风尚进行了集体文化记忆的分有。
《海上花列传》以商业性上海叙事对近代上海进行了记忆存储, 同时, 也对上海的文化空间进行了时间的识别。从记忆上海的文化长河来说, 小说这一商业性叙事成了记忆上海的前文本。正如蕾娜特·拉赫曼所认为:“文学和记忆之间的互文关系就是一种‘静态记忆’, 作为静态记忆的互文性能够运用叙述性的方法来存储记忆。”[5](P272)“对具体文本的互文性的阐释看作是对记忆空间的阐释, 这一空间可在文本之间展开, 也可在具体文本的记忆空间展开。”[5](P215)《海上花列传》对上海商业文化的叙述性记忆储存, 是文学文本对上海的“静态记忆”。而“静态记忆”就是文学和记忆之间的互文关系, 对“静态记忆”的互文阐释可以在文本之间, 也可以在具体文本的空间中展开。对小说文本《海上花列传》进行记忆空间的阐释就是对其文本的互文阐释, 同时, 也能通过对上海这一记忆空间的建构, 呈现出小说文本与海派文学相互渗透的互文关系。
三、海派文学与上海叙事
用“海派”指称某一类文学, 始于20世纪30年代。“海派”一词出现是相对于“京派”而言, 意指出现在上海洋场带有商业消费文化色彩或表现思想异端特质的文学艺术。海派文学与《海上花列传》都对上海洋场文化进行空间文化的记忆认同, 对上海叙述的姿态呈现出一致性。此种文化认同姿态的一致性就是在同构上海空间文化时, 呈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空间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不仅为海派文学烙下了与《海上花列传》同一“出身”的印记, 也见证了《海上花列传》建构上海形象的开启性作用。鲁迅称:“‘京派’是官的帮闲, ‘海派’则是商的帮闲。”所谓京派与海派之争, 因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文化风格的差异, 导致了文化审美趣味不同。“海派”作为商人的帮闲, 对上海商业文化的认同与《海上花列传》对上海商业文化的认同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为此, 《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在文化记忆视野的选择上, 处于一种记忆的共生关系。海派文学置身在被《海上花列传》唤醒的记忆空间里, 《海上花列传》也置身在海派文学回忆的空间里。海派文学与《海上花列传》在对上海的叙述中进行回忆性的相互指涉。许道明、吴福辉、杨义等也对海派文学服务于上海地域文化的表达进行了不约而同的确认。他们认为, 海派文学是以特定地域文化为依托的历史文化现象, 是地域文化受欧美风雨的侵袭和与大一统文化相离析的历史产物;洋场文化受到包括工业文明及商业流通支配等因素的影响, 在追赶时尚和追求商品畅销的商业环境中实现价值, 大致是沪上文学与商业竞争结合的产物。尤其是沪上某些作家开始具备和传统“别样的眼目”后, 才萌芽出此种具有现代特质的海派文化现象。从以上研究学者对海派文化特征的共识可见, 海派文学与《海上花列传》都坚守上海地域文化的特征, 进而呈现记忆叙述原则的一致性, 它们具有了同样的记忆精神。海派文学与《海上花列传》在对上海空间的文化记忆视野下, 获得同样的身份认同也是显而易见的。海派文学单个文本所回忆的上海, 与《海上花列传》所记忆的上海, 都从上海的地域文化特征出发来进行重构。它们通过对上海叙述记忆成规的一致性发生文本联结关系, 从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中, 足见海派文学与《海上花列传》在文化内部关系上的互文记忆。
1.早期①海派文学的回忆
海派文学的上海叙事不仅包含如何定位文本的问题, 也包含如何促进上海叙事传统的问题。回忆总是依照记忆的方式来呈现。正如陶东风所说:“个体记忆内在地包含了集体维度和集体的内容。某种意识形态规范当然也在控制着个体的记忆书写, 但更深刻和内在的控制是集体性的叙述模式被内化到了个体的无意识层次, 在不经意间控制着个体记忆。”[11](P16)海派文学对上海的个体记忆叙事, 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上海”这一集体内容。上海地域文化作为个体叙述上海记忆的集体文化意识, 控制着个体的记忆书写。海派文学的上海叙事因循海禁大开以来的上海地域文化, 进行着上海文化想象。这种叙事记忆, 自然与《海上花列传》文本发生记忆互文关系。上海记忆的集体维度对个体文本的记忆控制更深刻和内在地表现在叙述模式上, 如张资平、叶灵风、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海派创作家, 都不同程度地呈现了上海地域文化特征, 显示了上海地域文化这一集体意识对其叙述模式的影响。他们在回忆上海的文化文本中, 呈现了其维护上海地域文化集体记忆的意图和目的。这一时期的海派文学以革新旧道德、反禁欲、迎合新市民“性”趣味为指向, 表现出与传统文化相离析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创作者们不断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洗礼, 不约而同地表达人欲不可遏止、性爱为人的权利等观念, 这些表达与其说是对性观念的阐释, 还不如说是维护上海社会文化现实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社会, 由于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导致新派读者市场的形成, 这样的读者市场对追逐利润的市民文学具有强烈的诱导性, 使得这一时期的海派小说家如张资平、叶灵风、穆时英、刘呐鸥等, 自然而然地滑向为满足市民消费文化的需要而进行相应创作的风气。这一时期上海社会的文化状况, 使得创作者以这样的个体经验分有上海社会的集体记忆。这种遵从上海社会发展变化的个体叙事, 继承了《海上花列传》服务于上海地域文化特征的叙事模式。自鸦片战争以来, 现代文明开启的上海, 俨然成了一块被现代商业文化浸染而冲击传统文化的试验地。早期的海派文学创作就在这样一块现代文明的“实验场”上, 以维护地域文化特征的叙事方式, 表达他们对上海本土社会文化的认同。正是海派文学对上海地域文化进行不断地回忆, 延续了上海文化的记忆叙写。由此也促进了上海叙事记忆传统的形成。如果说《海上花列传》叙述的上海是过去的上海, 而过去不仅影响现在也指导未来, 那么海派文学对上海的重构在对上海的叙事中, 与过去相遇, 同时指导着当下上海的记忆书写。《海上花列传》对上海的记忆不仅是海派文学记忆的基础, 还以其记忆成就提供了海派文学的回忆力量, 发挥了其记忆上海的奠基性作用。文本之间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成全的内部状态不仅呈现了其记忆互文关系, 也呈现了其关系的意义所在。
2.成熟时期海派文学的回忆
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文学,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予且、徐訏、张爱玲等。其中张爱玲的创作最能代表海派文学这一时期的记忆成就。张爱玲自言道:“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12](P266)这里所讲的“通俗小说”, 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海上花列传》, 张爱玲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对这部小说进行国语版翻译, 甚至临终前还在对其进行英译。她从13岁开始反复阅读该小说, 并在阅读欣赏之余, 提出颇有见地的研究主题。对起奠基性作用的文本进行注释和反思性阅读都是文本之间互文记忆形式[10](P102), 翻译、研究等行为正是张爱玲记忆这部小说的形式。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无法释怀的热爱, 足见它对张爱玲艺术趣味的影响, 这种影响成了张爱玲自觉创作模仿的艺术资源。张爱玲对上海的记忆叙写建立在她对上海的审美认识中, 她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 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 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 但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3](P20)在张爱玲的作品里, 她将此种上海文化记忆意识细致绵密地进行回忆叙写。如《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 呈现了他们在“生活磨练下”进行心理角斗的爱情传奇, 同时, 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传奇写照。《金锁记》呈现病态甚至疯狂的曹七巧, 更是近代上海长期以来“高压生活磨练”而成的文化果实。由于张爱玲以艺术创作的自觉模仿继承叙述上海的传统, 记忆上海的叙事模式成为她自带的叙事记忆。张爱玲以《海上花列传》这一小说文本为叙述上海的源起, 就在于她在上海的文化根子上进行其个体记忆书写。张爱玲以透视上海人的生命状态来触摸上海的历史文化底蕴, 这种对上海人进行生命体悟的记忆叙写, 不仅让读者对回忆上海具有深刻印象, 还显示了创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因此, 张爱玲的上海创作不仅是海派文学的成熟标志, 也成为了张爱玲创作顶峰的标志。她的文学成就呈现了海派文学与《海上花列传》相互促进、相互成全的互文记忆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海上花列传》以商业性叙事标识了近代上海, 再现了近代上海, 海派文学在其叙事模式的影响下, 纷纷对上海进行遵从地域文化特征的叙述。这种对上海进行记忆空间的循环叙事, 呈现了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小说文本《海上花列传》凭其记忆上海的开启性作用成为了记忆上海的起点, 海派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起点对上海进行叙述。因为“对于文化记忆来说, 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 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10](P46), 《海上花列传》以商业性上海叙事记忆标识的近代上海是作者对过去上海的形象建构, 那么海派文学基于过去上海之上的形象建构, 不仅是海派文学记忆的上海, 也是海派文学回忆的上海, 从而促其上海叙事传统的形成。海派文学作品通过重构自身文化传统来重构上海文化记忆, 同时, 也呈现了《海上花列传》对上海记忆模式的开启性效果。这一建构“上海形象”的记忆循环, 呈现出《海上花列传》与海派文学文本相互成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3) .
[2]陈思和.海藻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2 (1) .
[4]陈然兴.叙事与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5]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 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6]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韩子云.海上花列传[G]//吴组湘, 端木蕻良,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3卷.小说集一.上海:上海书店, 1991.
[8]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M].杨军, 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1.
[9]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 黄晓晨,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0]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1]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J].文艺研究, 2011 (6) .
[1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注释:
1 文本的早期是指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这一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