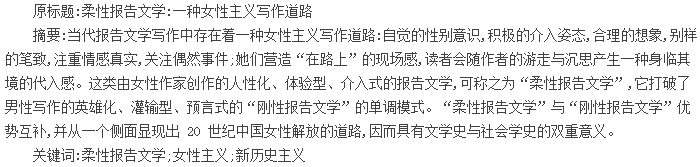
由性别角度检视 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史,就会发现:从梁启超那部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告文学诞生的《戊戌政变记》开始,到瞿秋白《饿乡纪程》、丘东平《第七连》、夏衍《包身工》、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等等,可以说直到 1950 年代,男性作家一直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他们往往站在进化论或唯物史观的立场上,自信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把握了人类发展规律,俨然是正义与真理的代言人和时代精神传声筒;他们创作的报告文学具有史诗性意图,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凸现精英启蒙、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等重大题材,因而这些作品总体上给人以宏大、崇高、威严的印象,同时也给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罩上了一层模式化的僵硬外壳。我们不妨将男性作家创作的这类报告文学称为“刚性报告文学”。
而由女性作家创作的报告文学却因为其“别样的笔致”而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多种禁忌,形成了迥异于男性作家的风格:自觉的性别意识,积极的介入姿态,合理的想象,注重情感真实,关注偶然事件;她们营造“在路上”的现场感,读者会随作者的游走与沉思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这类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人性化、体验型、介入式的报告文学,可称之为“柔性报告文学”,它打破了男性写作的英雄化、灌输型、预言式的“刚性报告文学”的单调模式。
大陆作家黄宗英和春桃、香港作家李碧华和台湾作家蔡惠萍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是“柔性报告文学”的典范,通过对她们的作品的分析,可以把握“柔性报告文学”特质及其文学史、社会学史意义。
从黄宗英到春桃:追求主观真实与写意抒情一般说来,报告文学要求内容、形式与目的的多重真实:内容上要实事求是,要有真凭实据;形式上要淡化作者主观倾向,将观点隐匿在他人的见证与口述之中,尽量减少作者对于事件的介入,而仅做客观公正的呈现;就写作目的而言,则要由表及里,发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某些规律甚至真理。但是,当黄宗英自1957年起在夏衍指导下开始报告文学写作时,这位“业余作者”的“越轨笔致”在无意间打开了报告文学写作的一扇窗:介入事件,书写体验,情感真实,写意抒情。
黄宗英的成名作当属《特别的姑娘》(1963)和《小丫扛大旗》(1964)。《特别的姑娘》描写北京知识青年、高中毕业生侯隽落户河北宝坻县,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故事。黄宗英在这篇作品里把自己与姑娘们相处时的感受以及与姑娘们的对话都写进了作品,这似乎是一种“业余写余”的表征,但这却无意中带来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变化。《小丫扛大旗》描写宝坻县小于庄铁姑娘队的张秀敏等人开荒种田的故事(张秀敏在当时是与邢燕子、侯隽一样享誉全国的铁姑娘)。
这类主流题材具有意识形态性,很容易“过时”:假如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 1960 年代,那么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种政治异化的产物,甚至是历史的倒退;而如果作家坚持“政治标准唯一”,那么其作品也就很容易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失势”。但是,由于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坚持“小题大做”,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开掘生活中的美和善,从“人的发现”角度反映女性解放的时代进步,并且注重情感体验和抒情写意,在结构上注重自身的情感逻辑,这就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前的性别意识和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可读性。比如在下面这一段里,黄宗英以速写笔法将小于庄勾勒成了一幅田园诗画:一个大清老早我来到小于庄。是初夏新雨后。村子就像才洗过脸的小闺女,又鲜活,又干净。
走村串庄的卖油郎把梆子敲得“倍儿”脆,左近又传来“鸡子儿换豆腐”“糠皮换大个儿红瓤煮白薯”的叫卖声。卖蛤子肉的也骑着带挎桶的自行车来了。小孩儿,点着一脸胭脂点儿,扎着冲天辫满街串。姑娘们、媳妇们、老奶奶们,都把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簪在鬓角边、发髻上、辫梢头压香。“嘚!哦—”,一阵驴叫、马嘶、牛吼,大牲畜出棚了。一个个武大憨粗的男劳力,扛上犁铧,拉起石磙,套着胶皮车集合了。媳妇把吃奶娃过手给婆婆,姑娘们兜里掖上本册子,扛起锄头铁锹。打头的是老队长,他嘴里叼的那根旱烟袋,像是神奇的“分水棒”。
茫茫麦浪被破开一条长长的白线,人们走向黑土的沃野。鞭声、吆喝声、笑语声四散开去……我怎么也想像不出,这里曾是满目凄凉的无人荒村。
恐怕罕有男性作家会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进行如此精致优美的写意抒情描写,更少有作者会全身心介入到事件中去。但正是因为黄宗英善于从女性体验入手书写闲情逸致,才使她的作品超越了时代局限。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比拟:黄宗英的写作风格让人想起孙犁,因为他们都在那个极左时代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标准,而进入了“美的创造”境界;也可以说,黄宗英因为善于捕捉大事件背后的优美人性而创作出了“诗化报告文学”,因此不妨称她为“报告文学界的茹志鹃”。
以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为标志,新时期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黄宗英也找到了她最为熟悉和喜爱的题材:为科技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画像。她的《星》旨在为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平反,《快乐的阿丹》为她的爱人、艺术家赵丹塑像,《越过太平间》写培育抗癌疫苗的科学家宋慕玲等,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她还尝试着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乃至音乐和电影的艺术手法灵活运用于报告文学之中,从而创作出了一系列诗化报告文学作品,其中《大雁情》《橘》和《小木屋》等堪称时代经典。
《大雁情》(1978)以“她……”“她?”“她”为小标题,书写有个性、有争议的西安植物园实习研究员秦官属的故事,外部矛盾集中,意志冲突强烈,具有较强的戏剧感。《橘》(1982)写中科院四川柑橘研究所所长曾勉的故事,他“孤傲疏狂。有点像三国时魏之阮籍,擅青白眼。爱其所爱,憎其所憎,毫无含蓄。”曾勉得罪过许多人,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的领导甚至说他“精神不正常”。黄宗英一方面为曾勉的科研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他不谙人情世故而着急,甚至将劝慰言辞形诸文字。整篇读下来,《橘》就像一篇优美的散文或一首叙事诗。在《小木屋》(1983)中,黄宗英将体验式写作再推进一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来描写西藏农牧学院徐凤翔老师带领学生建立“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站”的艰辛,其中“波密会议”一节采用拟人手法,让森林里的大狗熊召集喜鹊、阳鹊、地鼠、长尾叶猴、花大姐等开会,畅谈它们对这些科考人员的“观察”。别开生面地运用了童话笔调和合理想象,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
读黄宗英的报告文学,会感觉到她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而是事件的亲历者和体验者,她将自己融入报告对象的工作和生活,与他们共甘苦同忧乐,因而创作中也充满了主观情感。而“这种总能轻便地把自己化入报告文学对象及生活内容的表现方式”恰恰是她的报告文学常能引起读者共鸣的重要因素之一。
她不惮于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女性意识乃至母性和童心,这似乎有违报告文学的写作惯例和客观性原则,但是这种情感真实、内在真实却让读者产生了感同身受的现场感。另外,她笔下的人物不再是高大全式的“扁平”英雄,不再是完美无缺的“单面”圣人,而是一些既杰出又有着人性弱点的普通人,这样的人物更符合人性和生活真实,他们是立体的圆形人物,更具有可读性和启示性。可以说,黄宗英打破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诸多禁忌,使得报告文学的主题具有多义性,人物更具有鲜活性,文体更具有创新性。
实际上,报告文学既然属于“文学”,就必然具有主观色彩与合理想象。当一个作家在选择题材、选择见证人的时候,其主观性已隐含其中了。因此,要求报告文学“绝对客观”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她们从不隐瞒自己的主观情感,在写作时也并不强调作品的理性逻辑体系,而更看重情感真实,从而使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变得更具有知性、温情、诗意和抒情性。在黄宗英之后,陈祖芬等女性报告文学家延续了这种探索,越来越具自觉的性别意识,她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女性的解放和成长历程。到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年)等口述实录式的非虚构作品出版时,报告文学家已汇入到了“反思”和“寻根”文学大潮中,不仅女性意识更为自觉,文体意识也更为开放,女性报告文学家几乎成了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活力源泉。
可惜的是,这种在“新启蒙”理想烛照下的写作探索并未走得太远,1989 年以后尤其是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所谓“小时代”,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以私人的幸福感为中心,许多女性作者的写作重心开始向“小女人”转型,不再关注“大社会”。因此女性作者在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不过,经得起时间淘洗而留下来的,都是佼佼者,春桃就是其中一位。
春桃与其丈夫陈桂棣合作的《中国农民调查》堪称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杰作,它涉及重大题材,关注三农问题,注重细节真实,深挖一手资料,敢于真情流露,毫不掩饰地站在农民立场,是真正“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这部作品中,不乏如下这样饱含深情的片段: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邪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
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那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想象不到的悲壮……陈桂棣与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小岗村的故事》(华文出版社,2009 年)注定会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留下浓抹重彩的一笔:它见证了转型期中国农民的真实处境;它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中产阶级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它让我们看到当代知识者身上残留的一点良知。而我更想说的是:春桃的女性气质很好地中和了陈桂棣的“正义的火气”,使这几部充满血泪和力量的报告文学没有变成檄文,而是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革的建设性方略。—“柔性”一词,被春桃诠释为“柔韧”和“以柔克刚”。
李碧华与蔡惠萍:站在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立场上1990 年代以来,港台地区早已步入后现代状态。与大陆相比,港台地区女作家的报告文学走得更远,展现出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特质,也极大地拓宽了报告文学道路。李碧华和蔡惠萍的写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
李碧华是香港当红的畅销书作家,其《诱僧》《青蛇》《生死桥》《胭脂扣》《霸王别姬》《秦俑》《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川岛芳子》《饺子》等小说早已为大陆读者熟知。但很少人知道李碧华还是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杰出的报告文学家。她从 1999 年开始,参与到中国籍慰安妇事件的调查中,历时六年推出了《烟花三月》(花城出版社,2005 年),“记述李碧华厕身华籍慰安妇控诉日本暴行及兴讼求偿的行动中的一段奇遇”,作品讲述了如下事件:湖北女性袁竹林在抗战爆发时年仅 18 岁,却已两嫁;她被拐迫为慰安妇,饱受蹂躏;抗战结束后,她的“淫行劣迹”不能见容于同胞,却引起警察廖奎的同情,二人于 1948 年结合;大陆解放后,廖奎因为一个冤案而于 1953 年被发配北大荒;几年后,袁竹林北上寻夫,但那里同样物力维艰,袁只好于1961年与廖离婚回到武汉,二人从此音信断绝。
三十八年后,李碧华由于关注慰安妇事件,从袁竹林处了解到这段姻缘,打算帮助袁竹林完成最后再见廖奎一面的心愿;李碧华发动香港传媒,“从《明报月刊》至《天地图书》再到《壹周刊》都加入行动,引来众多回响”,又动用了网络搜索,甚至在一筹莫展之际,求友人用《易经》卜了一卦,最后在山东淄博找到了廖奎,并完成了这一寻找过程……传统的报告文学要求客观真实,隐蔽叙述者的态度与好恶。《烟花三月》却别开生面:“叙述中虽不乏被报导的对象,报导者李碧华的无所不在,才更耐人寻味。她不只写袁竹林与廖奎的乱世之恋,她其实也写了自己对这场乱世之恋的爱恋。”
甚至为了有现场感,李碧华为这次行程安排了摄影师全程跟拍实录。李碧华写的是重大主题,但是她有自己的方法和女性主义视角:主动介入事件,关注偶然事件,切入女性生命体验,加入合理想象。
李碧华将主人公袁竹林生活的武汉当作演示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一个舞台:武昌起义标举“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的口号,但中国却并未真正由此好起来;武汉随后经历了 1927 年“七一五”事件、1938年被日军攻陷、八年抗战、新中国成立、1955 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1980年代改革、1990 年代市场化等,这些事件统统被李碧华纳入叙事中,其微言大义在于:所谓“革命”和“解放”之类的宏大话语,其实并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幸福,相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经过兵荒马乱的百年,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问题仍是巨大的难题……读者会随着她的叙事语调而游走、沉思,她的“报道文学”给人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其中没有正义的火气、鲜明的主题和预设的指向,却给人更多的体悟与联想。
1990 年代以后的台湾报告文学则明显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果人们想找一个经典案例,那么可以选择 2007 年台湾“二二八”事件 60 周年暨台湾解严 20 周年之际出版的系列报告文学进行分析。
台湾 1987 年解严以后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学术研究或报告文学中,比较权威的有马起华编《二二八研究》(台北“中华民国”公共秩序研究会,1987 年)、陈俐甫编《禁忌 · 原罪 · 悲剧:新生代看二二八事件》(台北稻乡出版社,1990 年)和蓝博洲《沉尸 · 流亡 · 二二八》(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 年)等,这些作家和研究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二二八”事件进行定性:革命、民变、自治运动、城市暴动、阶级反抗、“具有近代意识并且武装化的社会反抗运动”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众声喧哗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反而使读者难以辨识史实与真伪。在此情形下,女记者蔡惠萍的报告文学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探幽发微,前提追问,发挖“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原因并给出了颠覆性答案。
引发“二二八”事件的当事人是林江迈,其女儿林明珠在 60 年后澄清说:“二二八根本不是从查缉私烟而起,更非‘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蔡惠萍采访到了如下的细节: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一如往昔的黄昏时刻,放了学的林明珠跑到天马茶房,“太平町”繁华的夜晚正要开始。当时虽是冬夜,但天还没全暗,林明珠照例捧着烟盒四处兜售,林江迈则是在离她十几公尺外。
这时,一个配枪的阿兵哥身影靠近了她,拿起烟盒里的烟,右手夹着点燃的烟,左手放进口袋准备掏钱,以国语问她“多少钱?”受日本教育只会讲日、台语的林明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没想到,一旁的地痞混混见状立刻在旁鼓噪、叫嚣“有人呷免钱的烟!”并且大声呼唤附近的林江迈,“阿桑,有人欺负你女儿喔!”
一群人立刻拥上,与阿兵哥拉扯,林明珠手上的烟跟着散落一地,就在语言不通及旁人起哄下,冲突愈演愈烈。这时阿兵哥掏枪想要吓退围堵他的人,一举起枪,尖锐的枪管刚好顶到了急着冲上前找女儿的林江迈的头顶,一注鲜血立即顺着她的脸流下,围观者情绪更加沸腾、激动。这时,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林明珠听到有人呼喊:“阿桑,你流血啦,还不快倒下!”“阿山仔,打人喔!”
事发后,林明珠立刻被送回龟山乡下躲藏,从此失学,受伤的林江迈则是被送进附近徐外科诊治。林江迈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就仓皇出院,当时她并不知道,全台湾已经陷入了遍地烽火、风声鹤唳之中,更没想到的是,她就是那个点燃引信的导火线。从二二八那天起,国府才开始查缉私烟。
二二八风暴渐次平息后,林江迈从耳语得知卖烟纠纷演变成一场空前灾难,但为了生计,仍继续卖烟,此时她也拿到政府发放的烟牌,林明珠也回到她的身边。
曾经影响台湾政坛的二二八事件,曾经那么高大的政治纪念碑,曾经被附加了众多象征意味的雕塑,在蔡惠萍笔下被还原了其“偶然性”面目,使之不再具有微言大义的价值。可以说蔡惠萍报告文学的新历史主义叙事已具有了后现代意味。新历史主义文学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辅以差异与断裂法则,展开对传统史学整体模式的冲击,打乱其目的演进程序,瓦解由大事和伟人拼合的宏伟叙事,以消除人们对历史起源及合法性的迷信,重现它们被人为掩饰的冷酷原貌”,力图回答“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
蔡惠萍等女性作者注重对细节的“知识考古”,努力还原现场而不做是非判断,更容易给读者以代入感;她重视偶然性、差异性而非必然性和同质性,从而给人一种“进错房间”的错愕感。
总而言之,只要将黄宗英、李碧华、蔡惠萍等女性作家创作的“柔性报告文学”与传统的“刚性报告文学”进行一下对比,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统的“刚性报告文学”往往以进化论、历史本质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为思想资源,具有宏大的史诗性架构,力图还原大事件,书写“真正的历史”,并揭示某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实际上,当报告文学与意识形态联姻的时候,往往主题先行,最容易沦为阐释政权合法性或政策合理性的宣传工具;传统报告文学作者努力放弃主观感受以凸显事件的真实性,以期达到“零度情感”的客观性,但时间和细节证明:这种“纯粹理性”叙事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而所谓“内容与形式的真实”不仅无法确保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反而形成了一种僵化模式,而模式化就意味着一种文体的死亡。
相比之下,女性作家创作的“柔性报告文学”不仅使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了悄然变化,也使报告文学总体上跟上了文学艺术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步伐,从而获得了新生力量:她们注重介入式的情感真实,以细节现实主义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的理性中心主义;她们营造出“在路上”的现场感,令读者随其游走沉思,从而远离了传统报告文学的填鸭式灌输;她们以知识考古的方式“小题大做”,轻松颠覆了传统报告文学的历史本质主义;她们关注偶然性事件并加以合理想象,从而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抒情性,弱化了议论性和结论性;她们强调女性意识和人道立场,从而超越了阶级和国族等时代主题的局限。总起来看,女性作家创作的“柔性报告文学”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引发了报告文学文体的巨大变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艺术的发展进步,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女性在当代中国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因而具有文学史与社会学史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国作家协会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编 . 报告文学第二集 · 小丫扛大旗 [C].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4.
[2] 宋玉书 .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女性写作特色 [J]. 辽宁大学学报 ( 哲社版 )2006,(2).
[3] 陈桂棣 . 春桃 : 中国农民调查 [M].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4] 王德威 .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 [C].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5] 杜继东 . 台湾“二 · 二八”事件研究综述 [J]. 近代史研究 .2004,(2).
[6] 蔡惠萍 . 林江迈之女 原爆人物谈 228 冲突——二二八事件后,林江迈转往台北市太原路摆摊卖烟 [N]. 联合报 ( 台北 ),2006-03-06.
[7] 赵一凡 . 什么是新历史主义 [J]. 读书 ,1991,(1).
[8] 海登 · 怀特 .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A]. 张京媛主编 .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C].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