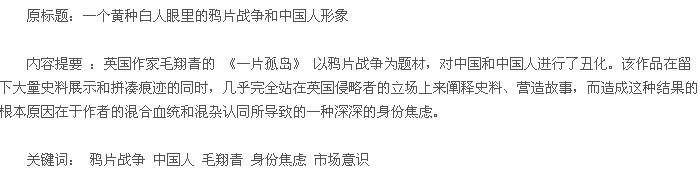
纵观中英混血儿、当代英语小说家毛翔青( Timothy Mo,1950 - ) 的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故事主人公无一不处在中西跨文化情境中,无一不在努力追问并建构新身份,却无一不为一种深深的存在焦虑所困扰。 《酸甜》( Sour Sweat,1982) 主人公丽丽·陈在二战后的英国谋生活,却因固守中国传统价值观而与英国社会格格不入。 《多余的勇气》 ( TheRedundancy of Courage,1991 ) 主人公华人阿道夫·吴身陷西方殖民势力撤退后东帝汶的内战泥淖,同样为其特殊的跨文化情境中特殊的种族身份所困惑。同样,在 《一片孤岛》 ( AnInsular Possession,1986) 中,作者以暧昧、错乱的身份定位进行了一种充满了偏见、错误和傲慢的中国书写,从两个来自美国的战争旅游者和一个种族身份不明的故事 “叙述者” 的暧昧视角讲述了一个扭曲的鸦片战争故事。有时候,毛翔青似乎要对中国人表示同情,对英国人进行谴责,但到头来屁股总是有意无意地坐在英国人一边,而对中国和中国人却是极尽丑化之能事。
一
《一片孤岛》与作者其他小说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故事讲述者不是中外混血儿,不是在西方社会被边缘化的中国人,也不是身陷极复杂的种族文化情景之中的海外华人,而是鸦片战争前后恰好居留中国的两个美国人———格登·蔡斯和瓦特·伊斯曼———和一个故事叙述者。在鸦片战争期间,这两个美国人在广州经商、办报,想以某种中立客观的态度来报道鸦片贸易、中英冲突和鸦片战争,最后却身不由己地卷入英国人针对中国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罪恶行动。稍稍浏览一下小说便不难发现,虽然战争通过两个美国人和故事叙述者等 “中立者”来呈现,但作者主要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来操纵这些故事讲述者,因而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而是带有明显的偏见。对一个几乎完全接受英国教育、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知之不多、远远说不上认同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而言,这种结果几乎是必然的。
读者首先可能注意到的一个情形,就是故事里中国人的集体失声。可以说,中国人几乎处于完全缺席的状态,即便出场也只能充当一种被打量、被评判、被怜悯的对象,完全不像是中英冲突和战争的当事方之一。不仅如此,作者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敌视比比皆是,这就更使他竭力营造的中立客观立场大打折扣。故事中最重要的一个中国人竟是可鄙可悲的仆人,便很好地说明了这点。阿强是爱尔兰画家欧罗克身兼数职的男仆,除了为主人清洗画笔、做厨师和总管家务外,还做为其拉皮条客的生意。他地位低下,在主人面前总是一幅谗媚相,总是咧着嘴傻笑,总是用一种极卑微的语气说话,对其总是唯唯诺诺、点头哈腰,随时听从使唤。除了会说几句蹩脚英语,以及总是咧着嘴傻笑以外,阿强几乎不再说话,因而不仅在小说主题传达方面无足轻重,从故事叙述的角度看也微不足道。
当然,小说中还陆续出现了其他一些中国人,但他们大多为暴民或士兵。他们或正在拼命逃跑,或正被刺杀或枪杀,或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倒毙。即便把这也算作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的出场,这种出场也总是仅在蔡斯、伊斯曼和叙述者面前一闪而过,因而更像是一种非人非生命的背景设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蔡斯和伊斯曼纯粹只将其所见所闻告诉读者,使其根本无从知晓中国人的姓名、声音和外貌特征等。他们形象昏暗模糊,没讲出任何有意义的只言片语,故而只是一群无形无语的中国人,一群无主体性可言的中国人。
不仅主要人物没有一人是中国人,作者对出场极为有限的中国人也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讲一讲其如何懦弱、可怜和可笑,舍不得花一丁点笔墨描述其外貌、言语和心理活动。这固然与作者叙事技巧粗糙嫩拙有关,但其几近纯粹的西方立场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他身上理应具有的中国文化特质既为乌有,中国人统统成为被远距离打量的似有似无、似在非在的对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这么做? 只能用混合血统和混杂文化背景所导致的错乱认同来解释。
尽管身上有一半中国血统,甚至在香港度过童年,但毛翔青终究自认是西方人。有证据表明,他试图撇清与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公开声明自己是西方人而非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他表示自己 “是英国人”,①“不了解也不喜欢中国文化”,②甚至 “蔑视中国文化”。
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企图划清与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之界线的做法解释了为什么《一片孤岛》一方面看似同情中国,一方面却给人以这种印象: 中国人是肉,英国人是刀,英军队伍中的印度人是俎,而美国人蔡斯和伊斯曼、叙述者等只是一些逍遥看客甚或战争旅游者,在优雅闲适中偶尔显一显慈悲之心。作为有一半中国血统、十岁后才从香港移居英国的人,作者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多少应有所了解甚或认同,可他为什么总是让战争中重要的一方即中国人处于主体缺失的状态? 这种几乎将中国人完全排除在外、纯粹采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讲述鸦片战争故事的做法,除了迎合部分西方人的口味,究竟有多么可信?
二
在中国人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让谁担当叙述代言人来讲述一个中国不仅挨打而且活该挨打、同时又具有说服力的故事,是毛翔青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也许在他或任何像他那样的西方人看来,让中国人担任故事叙述者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人不可能没有民族本位思想,而像萨伊德模仿 “东方主义者” 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任何民族都 “期望他们能够在欣赏并且不加批判地忠实于本民族与传统的同时,贬低其他的民族和传统,并与之斗争”。
④让一个英国人担当这个任务也不现实,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人是参战的一方,很难做到客观,也是因为英国人有一种难以消弭的文化优越感。这大约就是作者为什么让蔡斯和伊斯曼这两个年轻且不乏正义感和公正性的美国人担纲,充当貌似公正、客观、甚至人道的旁观者。
除了蔡斯和伊期曼,毛翔青还煞费苦心安排了一个貌似中立客观的故事叙述者。跟蔡斯和伊斯曼一样,叙述者也看似超然。但与两个美国人不同的是,叙述者是一个姓名不清、身份不明的旁观者,作者压根儿就没有交待其文化背景和国籍。他这么做,在取得客观可信的效果方面得分了吗? 未必。叙述者固然像蔡斯和伊斯曼那样也是旁观者,甚至给人一种竭力要做到中立、客观的印象,但最终说来,他不可能不是毛翔青的一个叙事替身,不可能不用西方人的眼光来打量中国人以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因为大体上并不具备中文读写能力的毛翔青从一开始就完全是用英国方面留下来的鸦片战争史料来写作 《一片孤岛》 的。他想当然地以为,只要用了叙述者、蔡斯、伊斯曼这些既非中国人亦非英国人的视角,就能成功地营造一种客观、中立的叙述效果。在他看来,他的造物在各方面都如出一辙,都摆脱了种族、文化和利益的羁绊,从冲突双方的获胜或者失败中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因而最有资格站在客观立场上讲话。作者显然相信,让两个美国人和一个种族文化身份不明的叙述者讲鸦片战争的故事,比直接使用一个英国白人的视角更能说服读者。
为了让苦心经营的战争故事显得客观,作者还让他所青睐的替身蔡斯和伊斯曼用语言、绘画和摄影之手段 “忠实” 地记录鸦片战争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在商行工作,四处游玩以外,两人还各自发展自己的爱好:
蔡斯为了解中国文化,拜葡萄牙牧师利比罗为师学习中文; 伊斯曼则拜欧罗克为师学习绘画。两人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每一个机会提高中文和绘画水平。不管到哪里游玩,包括到战场游览,伊斯曼和老师欧罗克都会安静地画上一会儿,用绘画将所见的景象记录下来。后来伊斯曼又学会了照相,这在作者看来,是一种比绘画更先进、更有效、更忠实的记录事件的手段,更能让视觉冲击成为永恒的一瞬。
为了使故事听起来客观、公正、可信,作者还采用了另一种手法: 办报。在第五章,叙述者介绍 《广州时务报》 的办法是大段摘取原文展示给读者,不附加任何评论。然而从报道内容来看,这份报纸显然是亲英国的,甚至可以说就是英国政府在广州的喉舌。也不难发现,两个主人公与叙述者立场不尽相同,与实施战争行动的英国人更是不同。二人俨然以鸦片贸 易 和 鸦 片 战 争 的 反 对 者 出 现,常 常 因《广州时务报》频频歪曲事实而感到气愤。随着商行业务的扩大,他们发现其他美国商人也卷入鸦片贸易,于是决定跟他们断绝关系。为了有效地反对鸦片贸易,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 《伶仃洋与河蜂简报》以与 《广州时务报》抗衡。在 《简报》 第一期第二版,他们揭露英国商人的虚伪面孔,说他们乘坐满载鸦片的帆船沿珠江直上,把 《圣经》 连同毒品一起分发给中国人,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但如何解释两个标榜反对鸦片贸易的美国人却干起了助纣为虐的勾当? 蔡斯 在一次战斗中竟然充当英军将领沛德的随身翻译。他全然未能意识到,这种行为与其一贯标榜的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多么明显的矛盾。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发生在 1841 年5 月 24 日的一起事件。 那天, 充当英军翻译的蔡斯译好英军起草的一份 《告中国人书》,大意是英军当日将举行一系列庆典活动以庆祝英国女王的生日,届时将会鸣炮,将准时在中午时分开始,请中国民众不要恐慌,因为礼炮里面没有弹丸,只有炸药。乍一看,读者一定会认为英军多么细心周到、善解人意。可发射礼炮后两个小时,英军竟在中国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大肆轰炸整座城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蔡斯当天就写信给英军司令,对英军这种杀戮行径表示抗议。然而,以中立、正义的旁观者相标榜的他,怎么可能以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来改变中国人被屠戮的事件进程! 他至少可以警告英国人,将不再为其充当翻译,并将此情形公诸报端。但他为什么没这么做? 所以,他的抗议只是一种徒劳无益甚至小骂大帮忙的姿态。也不妨作如是观: 正由于作者身份认同的错乱,蔡斯的抗议声不可能不是细弱的,因而是没有意义的。
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看似同情中国人的两个美国人跟英国侵略者并没有本质区别,蔡斯这个貌似客观的观战者与作者本人之间也没有根本的距离。这就解释了毛翔青为什么不放过任何一个丑化中国人、美化英国人 ( 尽管也抽象地否定鸦片战争) 的机会。同样,这在很大 程 度 上 也 解 释 了 为 何 两 个 美 国 人 乘“复仇女神号”参与屠杀中国人的作战时,甲板上竟一片喧嚷闹腾,欢呼雀跃的英国人似乎不是在作战,而是在过一个盛大而浪漫的狂欢节。此时此刻,以反战自居的伊斯曼竟激动万分,忙个不停地东奔西走,寻找精彩美丽的景致,用训练有素的画笔记录下来。
三
《一片孤岛》 对中国人的有意、系统的丑化随处可见,而这种丑化又无不被裹挟在两个战争旅游者对中国人的暧昧的同情中。故事开始时,伊斯曼与其绘画老师欧罗克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伊斯曼明确表示反对鸦片贸易,声称东印度公司的 “自由贸易者” 把面包从中国人手中偷走,反过来却卖给他们毒药。在另外一次交谈中,天真的蔡斯问美国同行瑞德利: “我们竟然强迫中国人跟我们做生意,而这不是他们愿意的,这么做对吗?”
⑤这时另一个资深美国商人科里根以一种傲慢的理论教训其年轻同行: “当然是对的,蔡斯。贸易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文明的先锋……我们有义务通过贸易让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让它不仅和其他所有的人,而且和我们的上帝真正进行自由顺畅的交流。贸易会给半文明的中国人带来文明,而且很自然,基督教的真谛也会紧随其后。我坚信我们的努力是神圣的。”
⑥科里根的口吻未必不可解读为作者对鸦片战争 “合法性”的讥讽性反思,但这里传达出来的信息无论怎么看也是模棱两可的。科里根的傲慢言论在西方人中博得满堂喝彩,却未受到任何人———包括蔡斯、伊斯曼和叙述者在内———的质疑。这表明,作者虽然并非不知道鸦片贸易的非正义性,却又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英国人用鸦片和武力传播 “文明”的霸道逻辑。
之后不久,蔡斯和瑞德利一起外出游玩。
他们来到一座红色庙宇前,发现在对面小山上完全可以俯瞰整座城市。像当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沿途观察到中国人在军事上有诸多明显的弱点一样,瑞德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防卫的缺陷: “负责保卫这座城市的中国政府官员太缺乏军事科学方面的知识了; ”⑦“在那些小山顶上,架一门炮就可以控制整座城市,就能从容地 轰 倒 指 挥 官 想 要 轰 击 的 任 何 公 共 建筑。”⑧对此,蔡斯表示认同,但他在根本没有检讨自己实际上已经参与了侵略战争的情况下,却有点不合时宜地指出,中国人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大型灌溉工程、大运河和长城都说明这一点,所以他们并非真正的软弱者; 中国的衰弱是中国政府领导才能低下以及官员的贪污腐败造成的。最后蔡斯得出这一结论: “一旦被唤醒,中国人一定会成为很多人的强大对手。”
⑨这里,读者分明听见两个相互矛盾的声音: 一个说中国人落后愚昧、软弱可欺,另一个却说中国人是一个勤劳而富于智慧的民族,有着惊人的潜力。
不难想见,两个相互矛盾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毛翔青的内心深处,就是说作者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文明的伟大和中国人的优点。
尽管如此,反映作者复杂身份的各种声音虽然贯穿作品始终,但代表其西方立场的声音总是最强,总是占据上风。从其欧亚混血儿出身以及既不愿认同自己身上的中国元素、又不被英国主流社会所接纳的情形来看,毛翔青对其身份的体认是复杂的、矛盾的,而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又源自其混合血统和混杂文化身份所带来的漂泊感、无归属感和失落感,正如一论者所言: “流亡使一个知识分子处于文化交际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表现为与祖国政治和家乡传统的断裂,异国文化的扞格以及作者自身的疏离感。”
⑩但如果说流亡使许多漂泊在外的中国人或华人加强了其中国认同和寻根意识,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流亡者的毛翔青身上,混合血统和跨文化的身份背景所带来的影响完全相反。他不仅宣称自己 “是英国人”,而且宣布他不了解也不喜欢中国文化,甚至 “蔑视中国文化”。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猴王》 中,在 “正宗” 英国人面前,中葡混血儿华莱士( 在较小的程度上,另一个重要的混合血统者形象即中印混血儿玛贝尔·威普也是如此)总是处于一种无根失语的状态,而在东方人面前他又无不流露出西方人的优越感,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在 《酸甜》和 《多余的勇气》中,毛翔青总是把海外华人塑造成一些可鄙、可笑、可悲的形象。
如上文所说,故事里的中国人总是西方人从远处观察打量的对象,本来就很少出场; 在少有的出场情景中,他们不是兼营皮条生意的仆人,便是无形无声、什么也不是的群氓。无论以何种形象出现,中国人都给故事的叙述者、两个主人公、其他西方人,当然也就给读者留下一种软弱无能的印象。但中国人的缺陷还不只是软弱无能。中国人不仅个个是伪君子,而且人人说谎成性。自认同情中国人的蔡斯和伊斯曼在 《简报》中竟然写道: “公正地说,许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习惯性的骗子和伪君子。他们会恬不知耻地撒谎,说最无耻的谎言,而且往往没有显而易见的原因,甚至频繁得不仅仅是为了占便宜。”
一个民族既然如此虚伪,如此习惯于撒谎,遭受西方人入侵,利益被损害,尊严被践踏,岂不活该?
故事中西方人眼里的中国不但软弱、胆小、虚伪,而且意志薄弱,缺乏爱国心。在第37 章,两个主人公随英国军舰 “复仇女神号 ”船长爱略特参与英军作战。军舰停泊时,一些水手弄来五六个被捆缚的中国士兵。爱略特命令蔡斯审问他们获取情报,然后将其释放。中国士兵获悉审问结束后英国人将释放他们,不会被拷打或被淹死,于是纷纷主动提供情报。
稍后蔡斯在给伊斯曼的信中甚至写道: “我和爱略特船长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相信: 这里人民可以成功地摆脱统治者。爱国心根本不是一种可以认真考虑的力量,根本不存在于他们心中。我们不是亲眼看见中国农民自愿帮助我们清理沟渠,为我们提供准确有用的情报吗? 难道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为停泊在香港海港的轮船提供物资吗?”
事实上,在认定中国人意志薄弱、缺乏爱国心方面,蔡斯毫无顾忌地宣称,他与英国人的看法是 “相同的”。然而,作为牛津大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毛翔青难道不知道,所谓 “中国” 是一个文明,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 ( 美国学者白鲁恂持这种看法) ,而根本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尽管极少数吃着 “皇粮” 的官员和曾经为官或者向往为官的儒生、文士、乡绅很可能会效忠 “国朝”,甚至表现出某种堪称现代 “爱国主义” 的情怀,普通百姓几乎不可能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既然如此,把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标准强加在他们身上,岂不犯了时代错误?
四
还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仁人蔡斯对自己充当英国军队的向导和翻译之事没有深刻的反省。很明显,这一角色与他所标榜的大慈大悲的中国同情者形象是完全矛盾的。但这个人物的内心矛盾与其实际上的矛盾行为并非没有逻辑联系,完全应有一种更为充实和更自圆其说的交待。但作者终究没有———通过蔡斯本人也好,通过叙述者也好———为其自相矛盾的行为作出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当然,蔡斯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充当英军翻译是为虎作伥,是直接参与对中国人的杀戮或伤害,但除了一点不痛不痒的检讨 ( 例如他说, “我想我是一个受人雇佣的杀手; ”再如他自问: “我帮助爱略特船长是不是完全错了?”) 便没有更进一步反省了。为什么如此? 这要到作者源自混合血统和混杂身份认同的心理矛盾中去找原因。
正是这种身份认同上的矛盾使他笔下的蔡斯一方面说 “我几乎不知道是不是该为中国人的胜利 ( 指中国军队一次局部、暂时的胜利)感到高兴; 他们站在正义的一边”,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污蔑中国人 “是习惯性的骗子和伪君子”,会 “恬不知耻地撒谎,说最无耻的谎言”。
毛翔青写作手法的粗糙嫩拙也无疑加深了故事和人物形象前后矛盾的印象。这一点除了能够从蔡斯这一大慈大悲的中国同情者形象与他助纣为虐充当英军翻译之间的明显矛盾看出,从故事结尾处也不难看出。此时香港已沦为英国殖民地。两个主人公读到港英政府报纸《香港卫报》 ( 前身为 《广州时务报》) 上的一篇报导,得知好友梅雷迪斯被当作强盗首领遭到逮捕。于是,二人积极组织营救,蔡斯为此还亲自写信给驻港英国法官陈述理由,但当局不顾二人曾为英国军队做出诸多贡献,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于是,二人心灰意冷地彷徨于江边,决定停办 《伶仃洋与河蜂简报》。故事至此嘎然而止。读者看不到他们帮助好友与故事的整体进展有何因果联系,看不出帮助好友不果与停办 《简报》 之间有何逻辑联系,更不明白此事与二人的反战立场有何内在关联。正如整部作品的立场非常暧昧那样,故事的结尾也莫明其妙。
阅读一篇文字尤其是阅读一篇讲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字时,读者应当开放性地面对两种可能性: 写进文字的东西和被作者有意无意排除在外的东西。
作为牛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生,毛翔青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应当能够熟练使用英国方面留下来的有关鸦片战争的材料,应该对英国当年侵略中国的真相 ( 当然是英国人眼中的真相) 有较深的了解。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具有较强的汉语阅读能力,更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汉语好到能熟练阅读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方面留下来的大量鸦片战争史料。对此,他似乎没有任何内疚感。可以肯定的是,他非常清楚其所讲鸦片战争的故事不是什么 “正史”,所以不必追寻事实真相,不必忠于历史。更重要的是,毛翔青深谙 “消费者是上帝”这一商业时代的至道。要赢得西方读者的青睐,必须投其所好,将其愿意看、喜欢看的写进作品,而将其不喜欢看、不愿意看的坚决排除在外。这就是为什么 《一片孤岛》 在留下展览史料 ( 英国方面保存下来的史料) 、拼凑史料的痕迹的同时,给人一种几乎完全从西方立场来利用史料、营造故事、歪曲真相的印象。这也是为什么两个主要人物和叙述者虽然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但因作者几近全然英国的教育背景、错乱的身份认同和过分敏锐的市场意识,都表现出明显的偏见。
另一方面,作者虽然公开宣称不喜欢、不了解甚至蔑视中国人,但两位主人公和故事叙述者在小说中却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其中虽有不少的偏见,却也不乏符合事实的叙述。作者甚至时不时地对中华民族表示一种未必不真诚的同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显然源于作者的混合血统和混杂认同及所导致的身份焦虑。
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作家与其母体文化是疏离的,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居住地的文化; 对两种文化而言,他们都处在边缘位置。毛翔青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不仅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跨文化小说家,更是一个有着混合血统却抱定西方立场不放的作家,简言之,一个黄种白人作家。正因这一缘故,他对其特殊身份的体认充满了矛盾、困惑和错乱。这不可能不影响 《一片孤岛》 中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和叙述者的叙述视角。
《一片孤岛》对中国人的深深偏见使人怀疑,有一半中国血统、十岁以后才从香港移居英国的毛翔青究竟知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过郑成功、林则徐、卫青、霍去病、班超、辛弃疾、岳飞、史可法一类民族英雄,或者说虽然也多少知道,却故意隐瞒信息,以迎合西方读者的庸俗口味。不过话说回来,抹黑、丑化和嘲笑自己所属的种族和文化,不也是一件赢得笑声、赚取眼球的法宝? 随着中国崛起,日渐强大,全世界华人无不欢欣鼓舞。但愿身体里有一半中国血统、灵魂却为此骚动不安的毛翔青能够安静下来,淡定一点,不再像从前那么焦虑和烦燥,把身上的中国血统当作 “他者”看待,总 是 与 之 过 不 去,总 是 想 与 之 划 清界线。
注释:
①②③转引自 Elaine Yee Lin Ho,Timothy Mo,17,25,150,150 页。
④爱德华·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前言 4 页,91 页。
⑤⑥⑦⑧⑨Timothy Mo,An Insular Possession( Toronto: Collins Paperbacks,1998 ) ,p. 23,p. 23, p.47,p. 47,p. 47,p. 521,p. 520,pp. 520 - 521, pp.520 - 521,p. 446,p. 446.宋国诚: 《后殖民文学: 从边缘到中心》,台北擎松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前言Ⅻ页。玛贝尔·威普是 《猴王》 中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