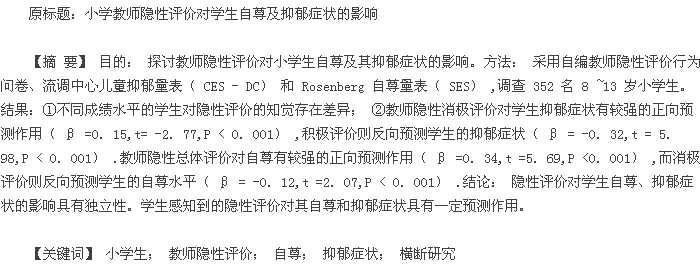
Ranjini 等人利用多组潜在成长跨域模型( Mul-tigroup latent growth cross - domain models) 的研究[1]显示,6 ~8 年级学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能够预测他们的自尊和抑郁。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感知到的教师支持可能具有更加不同的意义。
根据 Erikson 的理论[2],小学生处于“勤奋感 vs自卑感”的特殊成长阶段,能否获得“我是努力勤奋的”这一评价对其成长极其重要。而教师无疑是该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在日常校园生活中,除了成绩,教师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学生的关心、欣赏或漠视、冷淡等情感性行为,在孩子眼里可能也会具有评价意义。这是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对教师偏于情感上的依恋,孩子对成人的情感表达已具有足够的敏感性[3].同时小学生思维仍然处于具体运算阶段[4],他们难以区分喜欢与评价,容易将“老师喜欢我”与“我是好孩子( 成功的孩子) ”等同。“隐性行为”较于教师给学生的学业评分、品行评语、荣誉及奖励等而言,其评价的属性更具有隐蔽性、广泛性和情境性。然而教师往往没有察觉到这些行为对学生产生的评价作用,一般情况也很少去留意。例如,郑维廉等运用 IAT 方法揭示,小学教师中普遍存在对成绩差的学生和农民工子女的消极隐性评价[5-6].
而目前关于教育中“隐性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隐性知识、隐性课程、教师期望等,对教师“隐性评价”却涉及甚少[7].隐性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一种类型,其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决不亚于“显性”评价[8].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多以描述为主,缺少量化探讨。
本研究根据自编的小学生感知到的教师隐性评价行为问卷[9],对教师的这些行为进行量化分析,以了解孩子的学习成绩、教师隐性评价行为及其与自尊水平和抑郁症状间的关系,帮助教师意识到隐性评价对小学生心理的影响,促进教师思考并改进自己的包括言语、表情、肢体动作在内的各种会影响学生的行为,为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取江西萍乡城北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从三、四年级各 7 个班中随机抽取 2 个班,五、六年级各 8 个班中随机抽取 2 个班,发放问卷 400 份,有效问卷352 份,男生159 人,女生193 人,年龄范围8 ~13 岁,均龄( 10 ± 1. 1) 岁。语文成绩为优、良、差的人数为 218、109 和 25 人; 数学为优、良、差的人数为192、125 和 35 人( 因该校已取消分数制的成绩,以优、良、及格和不及格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本次数据是学生期中考试成绩,及格和不及格学生人数少,从研究角度,将该两类人数合并,分为优、良、差3 类) .
1. 2 方法
1. 2. 1 自编教师隐性评价行为问卷 据教师评价行为的理论基础和已有研究[10-11]、编者在中小学校的实习经历及对小学生的访谈情况,结合一线教师的意见,初步形成 85 个项目。经初测、重测和再测删去难度与区分度不当、可能有较高社会赞许性的项目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Kaisor 标准化最大斜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KMO 等于0. 931( > 0. 50) ,球型 Bartlett 检验值为 6377. 28( P< 0. 000) ,其中删除最大载荷 < 0. 4、有多重负荷且负荷值较接近的项目,终提取 2 个因子,命名为积极评价和消极评价。项目因子负荷在 0. 59 ~0. 75 间,解释率为48. 2%.整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0. 90,积极、消极评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91、0. 67.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0. 34 ~0. 73 间。问卷校标效度为 0. 83( 选用赵希斌[12]编制的《中小学生知觉的教师评价行为问卷》为校标) .采用 Amos 17. 0 对问卷结构进行验证,其拟合指数为 χ2= 362. 07、χ2/df = 2. 14,GFI = 0. 90、AGFI = 0. 88、IFI = 0. 92、TLI= 0. 91、CFI = 0. 92、RMSEA = 0. 057.说明该问卷的信效度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每年吸引着大量的务工人员来沪打工。大量农民工进入上海后,其子女也伴随在身边。相对于留守儿童来讲,农民工子女虽然被父母带在身边,但是其生活和学习环境缺乏稳定性,生活比较复杂,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健康问题[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