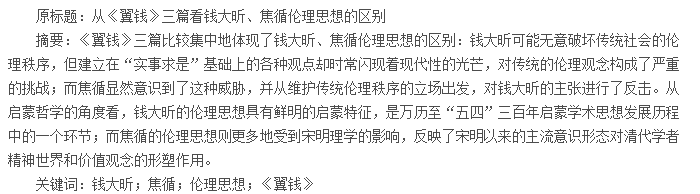
钱大昕(1728-1804)和焦循(1763-1820)均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关于钱、焦二人的学术交往,学界已有所讨论;但对于两人在思想方面的分歧与差异,则还较少有人关注①。事实上,焦循在钱大昕逝世后曾撰写《翼钱》上中下三篇(载《雕菰集》卷七),对钱大昕关于夫妻伦理中的“七出”、父子伦理中的“显亲”以及君臣伦理中的“弑君”等问题的主张进行了反驳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翼钱》三篇集中地体现了钱大昕和焦循在对待传统伦理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和观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意义和价值。因此,本文拟通过对《翼钱》这一典型文献的梳理和分析,进一步揭示钱大昕、焦循这两位乾嘉时期的“通儒”在伦理思想方面的区别,从而深化人们对钱大昕、焦循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一、《翼钱·上》:对妇女贞节观的挑战与坚守
《翼钱·上》表面上记录的是钱大昕、焦循对夫妻婚姻关系中“七出”问题的不同观点,而其实质则反映了钱、焦二人对传统社会妇女贞节观的不同认识和态度。
所谓“七出”,也称“七去”或“七弃”.根据《大戴礼记》的记载,是指当妻子犯有七种过失时,丈夫可以行使“休妻”的权力,单方面终止婚姻关系。“七出”之礼就其最初的设计目的而言是为古代宗法制度服务的,是为了维护夫权和族权而对女性行为的单方面的束缚和制约,因此在实质上与宋明以来日益强化的要求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一样,都是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关系在婚姻观念和制度中的表现。不过由于“七出”之礼主“分”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主“合”,因此在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钱大昕正是在利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通过对“七出”之礼的“还原”与阐释,含蓄地表达了他对传统贞节观念的不满。
在回答“妇人之义,从一而终,而礼有七出之文,毋乃启人以失节乎”这一问题时,钱大昕首先对父子兄弟关系与夫妻关系的不同性质进行了区分:“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①在他看来,父子兄弟关系是先天的血缘关系,所谓“以天合者”,因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法摆脱和改变;而夫妻关系则是后天的婚姻关系,所谓“以人合者”,因此“可制以去就之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②,并没有什么必须“从一而终”的坚实理由。
在此基础上,钱大昕指出,盲目遵从夫妻关系只能“合”而不能“分”的教条往往会对家庭成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一方面,如果妻子不能守妇道,例如出现“牝鸡司晨”之事,就会伤害“骨肉之恩”,从而使“孝弟衰于妻子”,甚至于导致“破家绝嗣”;另一方面,虽然妻子本身可能并没有过错,但“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③,妇女在夫家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因此钱大昕认为,当夫妻关系确实无法维持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义合则留,不合则去”.因为“使其过在妇与,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过不在妇与,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钱大昕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并明确提出了妇女“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的大胆主张,他说:“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
焦循明确反对钱大昕“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的主张,认为“先生之言激矣”,并引经据典,对钱大昕的观点一一进行了驳斥。其论说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认为夫妻关系虽然是后天的婚姻关系,但却是先天的父子兄弟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焦循说:“伏羲之前,夫妇之道不定。夫妇不定,则有母而无父。同父而后有兄弟,兄弟不可以母序也。故父子、兄弟虽天属,而其本则端自夫妇之道定。”⑤因此如果“夫妇不定”,则父子兄弟关系也不具有稳定性。他进一步指出,按照《易·序卦传》的排列,“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则夫妻关系在传统社会伦理关系系统中居于基础和根本的地位,这种关系一旦动摇,就会直接威胁到整个封建伦理秩序的稳定。基于这一理由,焦循强调:“夫妇之别关乎忠孝如是,苟夫可以去妻,妻可以去夫,则夫妇之道仍不定。天下之为夫妇者,稍一不合,纷纷如置弈棋,非其道也。”
2.指出钱大昕对“七出”之礼的理解和阐释不符合“先王”的“原意”.他说:“七出者,以其妇之可出也。若过不在妇而出之,先王无是法矣。”⑦上文已经指出,“七出”之礼其实是对妇女行为的单方面的束缚和制约,是以维护夫权和族权为目的的,因此并没有多少保护妇女权益的内容。钱大昕试图通过还原“七出”之礼的“原意”,利用经典的权威来阐发自己关于夫妻伦理关系的新思想,以旧瓶装新酒,就难免会出现过度诠释的问题。焦循正是看到了钱大昕肯定妇女权益的观点与“七出”之礼的内容和设计目的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通过对钱大昕藉以立论的“七出”之礼的“还原”,同样利用经典的权威消解了钱大昕主张的正当性。
3.对钱大昕“义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的可操作性提出了质疑。他说:“其出也,仍返之母家乎?抑嫁之乡里乎?其嫁也,夫家嫁之乎?听妇人自适人乎?或有司主之乎?抑私出之乎?嫁之乡里而夫又不良,乃一嫁再嫁之不已乎?”①可以看出,焦循刻意回避了不良婚姻关系对妇女的伤害,而是设想出一种在当时看来十分荒谬的图景---“嫁之乡里而夫又不良,乃一嫁再嫁之不已”,以此来说明钱大昕赞同受不公正对待的妇女“去而更嫁”的主张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困难。
由上可以看出,钱大昕和焦循在关于夫妻伦理关系问题的思考和论说中,立场是很不一样的。钱大昕在论述夫妻关系问题时虽然还有歧视妇女的一面,但他对古代“七出”之礼的“还原”,其着眼点已不再是对妇女义务的片面强调,而在于为现实的婚姻关系的“分”即夫妻离异问题寻找历史根据。在这个意义上,他弱化了“七出”之礼本身具有的压迫女性的男权主义色彩,而强调了这一古礼在终结不良婚姻关系方面的积极的制度性功能。同时,他在夫妻伦理关系的探讨中,能够正视现实生活中不良婚姻关系对家庭和妇女的伤害,并且比较关注作为弱势一方的女性的权利问题。他主张夫妻关系有去就之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遭受欺凌迫害等不公正待遇时,有终止现有婚姻关系、重新追求人生幸福的权利。考虑到钱大昕对夫妻关系的思考是在宋明以来贞节观念空前强化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理学家片面强调“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的消解和反抗。
而焦循则是妇女贞节观的坚定维护者。他认为夫妻关系是所有伦理关系的基础,因此必须具有稳定性,否则会动摇整个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婚姻关系及妇女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而只是片面地强调女性只有“从一而终”才能使“夫妇之道定”,而“夫妇之道定”对于维系整个封建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比较而言,钱大昕在讨论夫妻伦理问题时更注重从实际出发,而且似乎具有了一种朦胧的“以人为本”的意识,体现出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重视;而焦循则更多的是“以理为本”,强调秩序和结构的稳定。这可以说是钱大昕与焦循伦理思想的第一个重要区别。
二、《翼钱·中》:对盲目“显亲”现象的批判与回应
《翼钱·中》记录的是钱大昕和焦循对现实生活中“显亲”现象的不同看法,其实质则体现了两位学者对于传统社会中“孝”观念的不同理解。
“显亲”是传统孝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见于《孝经》卷首《开宗明义章》对孔子论孝的引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②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录其父司马谈的言论时也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③可见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将“显亲”看作是人子尽孝道的最高阶段,是“孝之大者”;而所谓“显亲”,指的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钱大昕对这种通过自己立身扬名来“显亲”从而尽孝道的思想非常认同,他说:“古圣之言孝也,曰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夫扬名者一己之事,而其父母之贤,亦因有贤子而益显,此孝所以居六行之首也。”
然而在乾嘉时期,社会上却流行着另外一种“显亲”的风气:人子在为过世的父母写行述时,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如何,而对亲人的生平学行作过高的评价,并自认为自己是在“显亲”,是在尽孝道。钱大昕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予见近人家传行述,日繁一日,学必程朱,文必韩柳,诗必李杜,书必钟王。究之,皆妄说也。夫过情之声闻,君子耻之。子孙而以无实之名加诸先人,是耻其亲也。欺人而人不信,欺亲而亲不安。以是为孝,何孝之有?”他指出,古代圣贤所说的“显亲”,其重点在于要求人们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立身行道”,而不是从事这种歪曲事实的“饰亲之美”的行为。他说:“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扬名者,扬己之名也。”⑤并进一步强调:“显亲之道在乎立身。亲果有善,何待子孙言之?子孙言之,徒使后人疑之,恶在其能显亲也?亲之名,听诸公论;而己之名,可以自勉。”①在钱大昕看来,“显亲”行孝的关键在于“立身”,在于通过不懈的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同时也为父母带来荣誉;至于父母本人的品行名声,人们自然会根据他们各自的行为作出公正的评价,由不得人子瞎编乱造,上下其手。
焦循的观点则不同。他对钱大昕着力阐发而且在《孝经》中有明文记载的“立身显亲”的主张不置可否,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子是否应当以及怎样“程朱韩柳李杜其亲”的问题上面。
首先,焦循认为对时人“程朱韩柳李杜其亲”的做法应当具体分析。他说:“人子不能实述其亲之善,顾程、朱之,韩、柳之,李、杜之,诚妄也;然人子之妄,不在程、朱、韩、柳、李、杜其亲,而在不能知其亲之善而缕述之,而泛程、朱、韩、柳、李、杜其亲也。”他进一步指出:“夫为人子,而程、朱、韩、柳、李、杜其亲,犹为人臣而尧、舜其君也。尧、舜其君,不可为不忠,程、朱、韩、柳、李、杜其亲,不可为不孝。惟徒以虚名,而遗其实事,乃为欺其亲。”②在焦循看来,给逝去的父母冠以“程朱韩柳李杜”等溢美之辞是人子尽孝道的表现,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要“知其亲之善而缕述之”,要有具体真实的“善行”来与“美名”相对应。
其次,焦循指出“称扬先祖之美”是子孙应尽的孝道和义务。他引用《祭统》的话说:“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惟贤者能之。”又说:“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③他认为钱大昕“亲果有善,何待子孙言之”的主张是《祭统》所谓“知而弗传,不仁也”的表现,并进一步指出子孙有详述先人之善行的责任和义务:“隐微之节,外人不知之,人子心乎其亲则知之,故有外人不能知,必俟人子述之者。抑即外人言之,或不详,亦必人子细言之。”④再次,针对钱大昕“亲之名听诸公论”的观点,焦循以钱大昕自己的记述为证进行了反驳。他说:“先生固自述其先大父、先考矣,且述其亡妻王恭人矣。妻有善,尚曰岂有贤如吾妻而无后者,而乃禁人之贤其祖父乎?先生贤其妻,即缕述妻之事;贤其先大父、先考,即缕述其先大父、先考之事。……何先生之大父、之考、之亡妻王恭人,不畏人疑,不听诸公论也?”⑤综上,可知钱大昕与焦循关于“显亲尽孝”问题的关注焦点似乎并不一致。钱大昕并不反对记录和表彰过世亲人的“善行”,这从他自己为亲人所作的行述、碑、铭等文章中可以得到验证;他所批评的是时人“以无实之名加诸先人”,即不顾实际情况如何而给予亲人过高的评价,从而出现“名实不副”的现象。
焦循则强调“称扬先祖之美”是子孙应尽的孝道和义务,并主张在“称美而不称恶”的原则下,去发掘亲人为外人所不知的“隐微之节”,以使其名实相副,避免“徒以虚名而遗其实事”.但他所理解的“名实相副”,其实指的是有“善行”与“美名”相对应。对于亲人的“善行”是否配得上“美名”,即是否会出现评价过高的情况,焦循则认为“尧舜其君不可为不忠,程朱韩柳李杜其亲不可为不孝”.而这一点正是钱大昕着力批评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焦循和钱大昕虽然都强调对亲人的记述要“名实相副”,但各自的理解却并不相同,与焦循相比,钱大昕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似乎更为彻底。
进一步来看,正因为钱大昕在思考“显亲尽孝”问题时坚持的是“事实优先”的原则,因此在涉及对亲人的评价时,他采取的是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钱大昕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因此其“名声”,即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所以他主张“亲之名听诸公论,而己之名可以自勉”,将“显亲尽孝”的主要途径转向成就自己的德行与功业,通过“立身”来实践孝道。他的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先秦儒家“孝”观念的一种创造性的解释,要求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实现对亲人之孝,因而与晚明以来逐渐强化的“贵我”的价值新观念具有隐然的联系。而焦循则是传统“孝”观念的维护和践行者。他虽然也有尊重事实的一面,但他对事实的尊重实际上是不彻底的。
他对子孙“扬亲尽孝”义务的强调,对“称美而不称恶”原则的坚持,以及对过高评价亲人学行现象的宽容,都说明他在思考“显亲尽孝”问题时,坚持的是“价值优先”的原则。这可以说是钱大昕与焦循伦理思想的第二个重要区别。
三、《翼钱·下》:对君主地位之神圣性的消解与维护
《翼钱·下》主要讨论的是史学家关于“篡弑”现象的“书法”问题,其要害在于对封建君主地位之神圣性的消解与维护。
“篡弑”问题是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早在西汉初期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是“篡弑”还是“受命”的时候,汉武帝就凭借政治权力对其加以干涉和禁止。从此之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①。不过从这次争论也可以看出,早期儒家学者并不讳言“篡弑”问题。他们虽然肯定“君尊臣卑”的上下之别是人伦之“大义”所在,但并没有将这种伦理规范绝对化,所以才会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从道不从君”等政治伦理主张。秦汉之后,随着君主专制权力的不断加强,君臣关系逐渐异化为对臣子单方面义务的强调;特别是在君权空前膨胀的康雍乾时期,任何抗议君主专制的行为都被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遭到残酷镇压和打击,而很少有人反思君主自身的责任和过错。
钱大昕对“篡弑”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根据《潜研堂文集·答问四》的记载,有弟子曾就孟子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将谓当时之乱贼惧乎?
则赵盾、崔杼之伦,史臣固已直笔书之,不待《春秋》也;将谓后代之乱贼惧乎?则《春秋》以后,乱贼仍不绝于史册,吾未见其能惧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②这一提问虽然针对的是《春秋》一书的性质和功能,但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传统社会君臣政治伦理关系中最敏感的“篡弑”问题。钱大昕对这一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解答,其大意包括以下几点:
1.他认为《春秋》一书阐发的是“王道”,因此其适用对象主要是君主和帝王,其目的在于为“后王”立“法”.他说:“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为后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春秋》之法行而乱臣贼子无所容其身,故曰惧也。”③按照钱大昕的理解,孟子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不是因为《春秋》中有某些经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一字褒贬”的“笔法”,而是因为《春秋》一书中有圣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王道”,因此是后世帝王治理天下的“教科书”.只要后世帝王遵循《春秋》的指示,以“王道”治天下,那么在一个政治昌明、贤人当位的时代,“乱臣贼子”不但没有“犯上作乱”的可乘之机,而且连容身之所也不会有。这才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真正原因。
2.那么《春秋》中有哪些“王道”呢?钱大昕指出《春秋》所记录的“篡弑之事”,其实都蕴含了“为有国家者戒”的“王道”.他说:“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渐,圣人随事为之杜其渐。”④例如“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邱”一条,说的是“大夫不得专兵柄之义也”;“崔氏奔卫”一条,“此卿不得世之义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一条,目的是要说明“母弟虽亲,不可使逾其分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是要“明君之昆弟不可以爱憎为予夺也”;等等⑤。总之,就“篡弑”一事而言,圣人在记载这些历史事实的同时已经提示了防范和应对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属于“王道”的一部分,应当成为后世帝王和君主遵循的原则。
3.对于后世那些不遵守“王道”而遇弑的君主,钱大昕直斥为“无道之君”.他说:“左氏《传》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各得其所,又何乱臣贼子之有!”⑥在钱大昕看来,“有道之君”是不会被“乱臣贼子”行篡弑之事的,反过来说,遇弑的君主自然就是“无道之君”;行篡弑之事的“乱臣贼子”固然需要加以谴责,但遇弑的“无道之君”似乎也不值得同情。
4.最后,钱大昕强调:“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义见诸行事故尔,故惟孟子能知《春秋》。”①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孔子成《春秋》”而后世之“乱臣贼子”不惧、“犯上作乱”之事不绝于史的尴尬局面,原因就在于后世帝王没有按照《春秋》所记载的圣人关于治理天下的“王道”行事---这实际上是认为对于“弑君”现象的发生,君主本人也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
而这一点正是焦循所难以接受的。在《翼钱·下》篇,他对钱大昕的上述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驳斥。仔细考察其论说内容,似乎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从立论的基础来看,焦循认为《春秋》一书的性质和功能是使天下后世“明大义所在”,即明白“君尊臣卑”、“君上臣下”的道理。他说:“人之性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自有《春秋》,而天下后世无不明大义所在。”②在他看来,懂得这种君臣“大义”是“人之性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标准之一。
2.从这一认识出发,焦循实际上否定了钱大昕对《春秋》一书性质的认定,即将其视为关乎“天子之事”,是圣人“述王道以为后王法”的著作。因此他不同意钱大昕的“防微杜渐”说,其理由是“孟子自谓‘乱臣贼子惧',不谓君父惧也”③。
3.对于钱大昕藉以立论的《左传》义例(即“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焦循的态度和万斯大一样,认为是动摇封建纲常根本、助人“犯上作乱”的“邪说”.他引万斯大语云:“甚矣,其说之颇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所谓’暴行‘,即弑父弑君是也;所谓’邪说‘,即乱臣贼子与其侪类,将不利于君,必饰君之恶,张己之功,造作语言,诬惑众庶是也。有邪说以济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己可告无罪然者。……于弑君而谓’君无道‘,是《春秋》非讨乱贼,而反为之先导矣。邪说之惑人,亦至此乎!”④因此他再三强调《春秋》之教在于“示人以惧”,而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不论其君父之无道,而臣子之恶,无可饰免”⑤。
4.至于“孔子成《春秋》”而后世之“乱臣贼子”不惧、“犯上作乱”之事不绝于史的问题,焦循认为在“君臣大义”面前,“乱臣贼子”并非不惧,“其怒也,即其惧也”.可是如果“乱臣贼子”心知恐惧,那为什么历史上还会有那么多“犯上作乱”的事情发生呢?焦循实际上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是强调正是因为有了《春秋》,天下后世才知道君臣大义之所在,才会有“乱臣贼子之恶无所容”的社会共识。在发生篡弑之事的时候,才会不断地出现“举义师以讨贼”的“正义力量”,而那些“乱臣贼子”虽然没有“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但也不至于心安理得,“晏然于心不一动”.而这些正是《春秋》教化的结果。
总的来看,钱大昕与焦循的分歧首先体现在对《春秋》一书的目的和性质的不同理解上面。钱大昕认为《春秋》的撰写目的是“述王道以为后王法”,因此其性质是供后世统治者学习和遵循的关于正确治理天下的教科书;而焦循则强调《春秋》一书的目的是使天下后世“明大义所在”,即懂得君尊臣卑的道理,因此其性质是明确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教化之书。正是基于这种不同的理解,二人对“篡弑”问题的态度也大不一样。钱大昕认为篡弑之事的发生,固然是臣子“犯上作乱”的结果,但也与君主不守“王道”、不遵循《春秋》关于治理天下的原则规范有关。因此他赞同《左传》揭示的《春秋》义例,认为行篡弑之事的“乱臣贼子”固然需要加以谴责,但遇弑的“无道之君”似乎也要承担责任。焦循则强调“人之性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认为封建等级秩序、君主的权威不容挑战,不论君主是否守“王道”,行篡弑之事的臣子都属于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因此他对《左传》“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的书写义例深恶痛绝,认为是动摇封建纲常根本的“邪说”.可以看出,钱大昕关于“篡弑”问题的论说仍然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还有一种借助经典来弱化或消解君主地位之神圣性的倾向,而他对“无道之君”的贬斥,也似乎隐含着一种要求君臣各尽其职的平等意识。而焦循则将君尊臣卑的等级观念上升到“人禽之别”的高度,片面强调臣子单方面的义务,极力维护君主地位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这可以说是钱大昕与焦循伦理思想的第三个重要区别。
四、评价与小结
通过以上对《翼钱》三篇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看到钱大昕与焦循都不是“为考据而考据”的学者,他们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且都试图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还原”和阐释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但在大致相同的宗旨(即明体致用)下,两人的伦理思想中却不乏相互冲突甚至对立的观点和主张。
这种冲突和对立,表面上看只是对各种伦理异化现象①的不同见解,而其实质,则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向现代伦理思想转型过程中新旧两种伦理价值观念的激烈交锋。
我们知道,钱大昕、焦循所处的清代乾嘉时期,既是满清政权极力强化专制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十分严酷、各种伦理异化现象大量出现的时期,同时也是晚明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市民文化又一次获得大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在不可遏制地产生和生长起来的时期。这一矛盾反映在思想领域,一方面是一部分学者对满清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增强,成了宋明以来日益强化和僵化的传统礼教思想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继承了晚明以来的启蒙思想传统,在批判各种伦理异化现象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早期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阐发自己的新思想、新观念。《翼钱》三篇中焦循和钱大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体现。
具体而言,钱大昕对“伦理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对早期儒家经典思想的“还原”,其实都是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的。例如他在夫妇关系的探讨中对贞节观念的反思和对女性权利的重视,在君臣关系的探讨中对君主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实际上都隐含着一种朦胧的平等精神;而他在父子关系的讨论中主张通过“立身显亲”的方式来实践孝道,以及反对各种歪曲事实的“饰亲之美”的行为,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晚明以来不断强化的“求真”、“贵我”的现代价值观念在乾嘉时期的曲折反映。而这些都是与传统礼教思想格格不入的新内容。因此,从启蒙哲学的角度看,钱大昕的伦理思想实质上继承的是晚明以来新的思想文化传统,并与其在治学中秉守的“实事求是”精神实现了内在的统一,从而成为万历至“五四”三百年启蒙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环节。他可能无意于挑战整个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但他所阐发的各种主张和观点却时常闪现着现代性的光芒,并对传统的伦理秩序构成了威胁。而焦循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威胁,因此他从维护传统伦理秩序的立场出发,对钱大昕的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而对钱大昕着力批评的各种伦理异化现象,则采取了一种回避和宽容的态度。他的伦理思想属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宋明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学者之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塑造和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