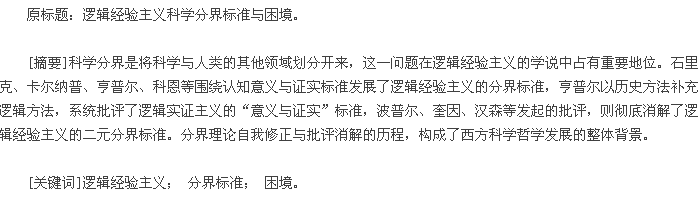
逻辑经验主义是 20 世纪西方科学哲学兴起的第一个成熟理论派别,它的最初形态是 20 世纪20 年代在维也纳大学发展壮大的维也纳学派,布鲁姆伯格( A. E. Blumberg) 与费格尔( Herbert Fei-gl) 最早用逻辑实证主义一词指代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主张,但该学派理论的随后发展逐渐向经验主义靠拢,在 40 年代最终汇入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与它的早期形态逻辑实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同义语,都被称为标准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自洛克、休谟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传统,针对当时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与新康德主义,鲜明地提出“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1]
的基本信条。他们认为,命题是否有意义,在于能否用逻辑分析与经验证实确定其真假,经验的意义标准与证实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只有科学陈述才有意义,这一意义标准就是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的分界线。
一、分界标准的自我发展。
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完全接受维特根斯坦有关意义标准的观点,指出“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对此较为详细的解释是,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具有真理性,只需要看它是否不依赖经验事实,而仅凭逻辑语法就可以判断其真假,如当时的分析科学、数理逻辑等,其结论的证据早已包含在前提之中; 而判断一个命题是否是经验可证实的,必须通过观察、证实得出结论。
经验可证实的命题,即石里克的“经验真理”,是包含实际知识的命题,是一种表达生活的、科学事实的命题,属于康德所谓的“后天综合判断”,判断其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必须与事实相符合。
在石里克的证实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关于“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的区分。考察“逻辑证实”与“经验证实”可以看出两者虽都有证实之意,但区别非常明显。就判断一个命题或句子的意义而言,只存在逻辑证实与否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存在与否,其划分界限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哲学家所担负的任务,因为哲学本来的使命就是寻找论断或问题的意义,并把这些意义搞清楚。
至于判定一个命题或句子是否是“真”的问题不是哲学家要关心的,应该留给科学家去解决。到这里,留给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判定一个命题的真假了,石里克说: “在日常生活和一切科学中,每一个陈述的真( 或) 假全都是这样确定的,即由观察和直接经验证实了一定的事实,根据这一事实便能断定该陈述的真假。”[2]
紧接着他解释到: “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有意义的问题都能指出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因为很明显,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指明问题的意义是一致的。”[2]
石里克把可证实性原则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一原则并未因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逻辑经验主义而消亡,事实上,卡尔纳普在后期转向逻辑经验主义后,对可证实性原则做了诸多批评与调整,但这一原则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动摇。
卡尔纳普是逻辑经验主义的又一旗手人物,20 世纪中期,他接受石里克邀请参加到维也纳小组的每周四定期讨论中,在维也纳学派前期,他追随石里克认为证实原则与意义标准是统一的,基本赞同石里克的可证实性原则,但随着该学派论争的活跃,建立在现象主义基础上的可证实性原则遇到了种种挑战,这就迫使卡尔纳普修改了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更加宽泛的分界标准。
就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而言,存在着证实的不可靠性问题,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传统的经验总结归纳出的命题难以解释科学发现的新事物。此外,许多事物的属性也是无限的,要把他们全面证实是不现实的。所以,经验的间接证实是不可靠的,甚至在直接经验中也有幻觉、错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主观性、私人性,每个人由于受主观因素或种种客观因素影响,只能感受自己的感觉,无法感受别人的感觉,相互之间不能“相通”或“交流”.针对可证实性原则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卡尔纳普决定把意义标准与证实原则分开,对科学命题的逻辑分析仅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句法分析,而不需要了解命题的实际内容。卡尔纳普说: “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3]
因为逻辑问题与对象问题的明确区分,哲学只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句法,而不用对科学命题的形式进行逻辑分析并对其内容进行意义证实,故此,对象问题只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哲学不直接介入对象问题。另一方面,卡尔纳普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可检验性”与“可确证性”这两个概念,对一个句子的检验与对它的确证是不相同的,如一个全称命题,我们知道可以对它进行一系列的检验,即这一命题是可检验的,如果我们知道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证据能够验证该命题为真,这一命题就是可确证的。
按照卡尔纳普的这一区分,逻辑实证主义者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继承下来的可证实性原则就放宽了许多。应该说,卡尔纳普在此持有的是一种温和物理主义还原论的立场,生物学、心理学等定性描述的科学也被纳入统一科学的范畴。亨普尔曾是柏林小组的核心成员,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躲避纳粹政权迫害而移居美国。
随后,他发表《经验主义意义标准上的问题和变化》( 1950 年) 一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和意义标准做了进一步的批评与分析,亨普尔的批评工具之一是现代数理逻辑。他指出,认识的意义标准应该满足一个虽然不充分但是却必要的条件,即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判断某个句子无意义,那任何包含这个句子的复合句也将无意义。亨普尔说: “单独一个句子通常并没有经验蕴涵,在科学理论中,单独一个句子照例不能推出任何观察句。”[4]
因此,坚持经验主义的标准,会使许多无意义的句子变成有意义,从而破坏了这里的必要条件。可证实性面临着既不能排除一些无意义的复合句,又无法证实一些公认的有意义的句子的困难。为解决这一困难,亨普尔强调,不能以单个命题而应以命题系统来作为认识意义的单位,在一个理论系统中要排除直观上无意义的句子是困难的,因为科学理论若要深刻地反映自然界的普遍定律,就必须突破一切都要获得直接观察这一框框。亨普尔对划界理论的重大贡献是放宽了认知意义标准,他指出,认知意义并非是绝对的“有一无二”分,而是可以有程度之分,正如思辨哲学关于宇宙、生物或历史的理论系统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意义,但仍不足以与现代科学理论相提并论,因此也就不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亨普尔的观点是逻辑经验主义发展中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他称之为“分析的经验主义”,这是一种在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与新崛起的实用主义之间折衷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摒弃逻辑经验主义理论传承,正像他说的: “经验主义的意义判据的一般意向基本上是合理的; 尽管用法上往往过分简单化,它的批判的应用整个说来还是有启发作用的,也是有益的。”[4]
科恩( Jonathan Cohen) 是逻辑经验主义后期较有影响的代表,他提出了一种非帕斯卡的归纳概率逻辑,科恩称其为“培根型”归纳概率逻辑,这一归纳逻辑运用于医学和法学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个科学家的两种目的中,即一种是他接受或坚持某一假说,当且仅当它是真的或似真的; 另一种是他接受或坚持某一假说不仅当且仅当它是真的或似真的,而且他也知道证明相信它是真的或似真的证据,科恩认为只有后一种目的才能归之于科学。在科学中,仅认为目的是接受或坚持真的或似真的命题是不够的,人们的目的必须是由于正确的理由接受或坚持它们。
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分界标准的主要问题是证实问题与意义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维护和修正,构成逻辑经验主义的完整理论进路,这是它进步的一面。但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提出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经验主义理论显然并不现实,否证论和历史学派分别沿着证实与意义问题发展开来,从而孕育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几乎所有的主要命题。逻辑经验主义在修正自身不足的同时埋伏着最终衰落直至终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