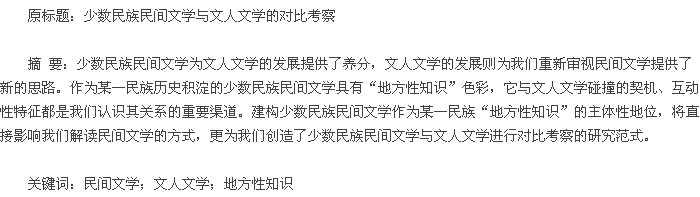
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绝非是随心所欲的,他们不仅无法选择自己创造本民族历史的时代境遇,也无法超越特定的条件限制,只能是延续着前人所创造既有成果,去努力创造真正属于本民族文化的新气象。通常意义上,不同民族创造的民间文学作品是文人文学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 《国风》,楚地巫歌之于 《九歌》, 《蔡中郎》 的故事之于 《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 《西游记》。[1]
因此,我们研究“文人文学” (或曰“雅文学”)绝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它是孕育、灌溉和滋养文人文学的精神之源。
一、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中国是诗的国度, 《诗经》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详细地记录了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它是在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最终被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因此,我们理解 《诗经》 必须回到孕育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诗》 是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特殊时代的历史记忆和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的集体记忆。其中最为当代学者所重视的十五《国风》 的地域特征尤为突出,它展现了特定时空架构中人们理解社会的方式,即某种形式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形成方式和思维模式不同于现代科学创造知识,它是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根据日常生活所积累的经验总结的不具备体系结构的知识。一方面,它有别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创造的结构性强、逻辑严密的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更多针对农业生产、生理健康、食品安全和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活动的物质性基础。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由于它是从人类学研究中拓展、延伸出来的,我们仍需要将其置放于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进行讨论。在文化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我们不应将人的行为、人的情感或者物质性空间的事物作为重点,而是要将人们认识事物的概念以及构建这一切的原则作为关注的焦点。
任何形式的理论在其诞生之后被译介到其他文化体系中,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就“地方性知识”的内涵而言,我国学者指出这一学术概念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一,它与西方社会建筑在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演基础上的知识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二,它的基本构成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知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模式下的传统知识;其三,“地方性知识”往往为特定地域、特定空间的掌握者所享有,是无法与特定对象、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语境脱离关系的存在。人类学家在试图了解某一族群的历史记忆,乃至于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时,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与这一文化所孕育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作品的持有者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由于早期形态的文学作品并不具备完整的体系、鲜明的形象和突出的主题,他们属于笼罩在历史迷雾中“口耳相传”的精神遗存,通常将其称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他们应该被纳入到“地方性知识”的范畴中进行考量,又由于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所处的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广泛分布在贵州的苗族为例,他们曾经拥有本民族的文字,却由于逃避战争和民族迁徙的需要,将原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抹去、焚烧。最终,当仅存的掌握苗族文字的族人逝去后,苗族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因此,属于苗族的历史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的:其一是在苗族群众中传唱的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既涵盖了苗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涉及到他们从社会经验中所总结的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实验科学和理性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表现为“前经验主义”的历史累加。但我们可以在苗族古歌中寻找历史的痕迹,这是苗族的“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渊薮。
我们不仅可以在民间文学中发现民族历史迁徙的痕迹,更能直接感受苗民族在历史发展早期的生命体验。如果说 《苗族史诗》 中记载的“溯河西迁”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支系苗族的历史记录,我们还能在苗族古歌中看到更具代表性、更具广泛意义的历史记忆。以 《洪水滔天歌》 为例,它分为“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两部分,围绕着姜央和雷公展开叙述,当二人的争执最终引发滔天洪水之际使得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天上哗哗下,地下无路淌,洪水满地流,水小浪滚浪,日日往上升,夜夜朝天涨。姜央老公公,相两和相芒同坐葫芦里,随水起,水淹过屋顶……淹没千条岭,沉没万条冲、淹没万年杉,沉没万年松,淹没千支奶,沉没万支公,寨边朋友绝,楼门伴侣空,只有姜央公坐在葫芦里……拉着大棕索,向着天上划,心想到天上,捉住老雷公,同他把账算。
古歌的内容是苗族先民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却又充满着卓越的想象力---人可以坐在葫芦中。
如此的描写使得我们对于苗族先民所经历的一切不再陌生、不再遥远,瞬间拉近了读者和苗族先民的心灵距离。但古歌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它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劳动方式、文化形态以及思维观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是苗族先民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劳动生活的某种形式的折射。
人们可以通过苗族古歌的描写与现代生活进行对比,进而使今人洞悉出古人和今人的差异。同时,苗族先民在 《洪水滔天歌》 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以及他们应对艰难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策略,已经随着苗族的集体记忆不断沉淀,成为凝聚起民族认同感的文化资源。同样的故事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传说都有反映,苗族在历史上极有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了苗族古歌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发展的痕迹。
上述两则古歌分别记录了特定苗族支系的发展历史、以及苗族先民的关于上古洪水的集体记忆。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苗族先民是将本民族早期的生活经验、历史遗存和情感表达都内化在一首首的古歌中,使得苗族古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层面的情感宣泄,而是具有广泛意义层面的诗性言说。
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碰撞的契机
作为“地方性知识”构成要素之一的民间文学必须要面对“现代化”的考验,它不仅要成为记录、反映和描写某一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神载体,也应该成为支撑古老民族面对现实的拯救。同样以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例,它是维系苗族社会繁衍、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只能是被现代文明所制造的鸿沟所阻隔,无法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能否参与到当下的文学建设中来,往往需要一定的历史性机遇。
我们无意于辨析两种形态的知识究竟哪一种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更有现实意义,或者说对于我们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是否能够提供参考性意义。事实上,西方学者很早就针对非地方性知识的逻辑构成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精细化,能够将研究对象拆分为若干构成元素。但却很容易陷入到以拆分为拆分的思维模式中,最终遗忘了将某些构成元素重新拼装起来。他们的反思开始于20世纪中叶,根本目的在于弥合传统文明形态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试图实现二者之间“无缝隙”的对接。
正是受到这一价值诉求的启发,现代人开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性知识”---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延续至今的民间文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社会剧变对于形成我们今日的多民族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着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方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
学界习惯将中国的少数民族按其所在国家疆域位置划分为不同的民族群落,因之,世居东北地区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便被称为东北少数民族,成为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并称的民族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