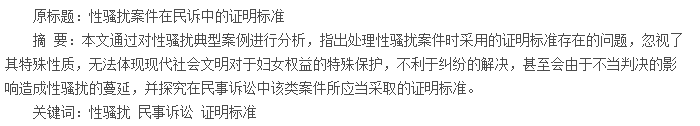
一、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现状
(一)对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理解
在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是否是同义概念问题上,各国法学家对于证明标准的具体概念存在争议,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认为:"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卸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中、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事实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 我国学者江伟也曾说到"证明标准指的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它像一只晴雨表,昭示着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能否解除".
两位大家从证明责任的角度来理解证明标准问题,既表明了二者并非同义概念的观点,同时又明确地表达了二者的关系。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针对我国民诉中的证明标准,大部分学者认可追求客观真实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认为民诉法中规定的"原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这一启动二审的标准就是认定事实的错误,故认为追求案件事实清楚就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特点各异,刑诉中,根据具体案件的性质会有相应的司法机关专门进行立案侦查,即第三方取证;民诉中,则是由当事人进行举证,证明相应的案件事实,其同刑诉的区别就在于无法保证证据中立无倾向性。因此,法官根据这些证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同客观真实之间是很难直接画上等号的。旨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一样去追求完全的客观真实可行吗?随着新型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如下文要论述的性骚扰案件的出现,可以明确民事纠纷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而证明标准仍旧是一元化的,不能够完全适应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需要。
二、对我国性骚扰第一案败诉的思考
(一)我国性骚扰第一案
2001 年 7 月,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国有企业女职员童某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起诉,指证受到总经理的性骚扰。童某在起诉状中称,该总经理早在 7 年前就以调岗为由,不顾其抗拒在办公室内做出骚扰行为,之后更是在不同场合对她进行骚扰,甚至提出去酒店开房间。由于她严词拒绝,总经理便通过无故克扣福利奖金等手段进行报复。童某忍无可忍选择了起诉。审理之后,该法院认为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性骚扰事实存在,遂驳回原告的起诉。
其同事提出曾经在总经理办公室门外听到里面的厮打声以及原告抗拒的喊声,但法院对此份证人证言的结论是由于证人没有进门,不能认定总经理办公室里的人就是被告。法院判决后,童某没有上诉,这起闹得沸沸扬扬性骚扰案就此划上了句号。
(二)对我国性骚扰第一案败诉的思考西安市莲湖区法院追求客观真实,要求原告的证据能够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客观存在。在探讨这一证明标准合理与否之前,先要明确几个问题。
第一,性骚扰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对女性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侵犯,很多情况下心理伤害比身体伤害更为严重,此前提下,法院要求原告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性骚扰事实的客观存在,证明心理上承受的伤害和程度,真的合理吗?
第二,性骚扰是一种突发性行为,很多都是在某种场合、环境下突然发生,在受到侵犯的紧急状态下,受侵犯的女性是否有能力或者有精力、时间去思考如何收集证据呢?
第三,我国是一个传统国家,我国的女性心理同欧美等国家的女性是不一样的,面对性骚扰问题,很多女性难以启齿,能忍则忍是一种普遍心理。这种国情和心理状态是处理性骚扰案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或者说是法官进行自由心证的前提。
原告方同事的证人证言被法院否认了,理由是证人没有进入案发现场也就是总经理办公室内,因此不能够证明总经理办公室的人就是被告,也就不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这一事实的存在。作为一个公司的高层人员,总经理的办公室并非普通职员随意进出和逗留地方。如果当时法院考虑到了上述三个问题,可能结论会有所不同。
没有人能够再现案发时的场景,所有的证明只能实现法律上的真实,以力求达到客观真实的最高目标。在性骚扰这种特殊侵权案件中,被性骚扰的女性往往急需法律予以保护,才能改变弱者地位,因此法官要追求实质上的公正。将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该类案件的证明标准,不仅不能够真正通过司法手段来解决性骚扰纠纷,而且会牺牲追求公平正义的司法的公信力,给社会大众的行为造成误导,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赖,损害司法者的形象。
三、性骚扰案件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探究
从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和我国学者江伟对证明标准概念的理解上可以明确,获取证据的可能性和能力是其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同时放到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中和性骚扰案件中来看,被侵权人在后一种案件中的地位明显要弱势的多,这正是上文分析的几点问题的展现。
(一)性骚扰案件与民事诉讼中一般侵权案件的比较
尽管无法对侵权行为提前预知是一般侵权案件和性骚扰案件的共同点,但是在证明侵权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时,性骚扰案件的难度要普遍更大。举个例子,在是否实施了侵权行为这一证明要件上,由于一般的侵权案件中的侵权行为通常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的,或者有目击者或者有外伤等证据,而性骚扰案件中的侵权行为往往在私密、隐蔽环境下进行,而且是一个侵权者针对一个被侵权者,通常不会留有外伤等明显证据,因此,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明难度要更大。
尽管有此种特殊性和难度,但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将性骚扰案件归入特殊侵权案件中,其证明难度不亚于特殊侵权案件,却不能适用特殊侵权案件中的证明方式进行证明。所以性骚扰案件中就进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无法律依据的,也不能依靠高科技设备来鉴定是否存在性骚扰行为。即使是测谎技术也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的,而且不能够因为侵权人拒绝测谎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定。
(二)降低性骚扰案件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理由
通过将一般侵权案件和性骚扰案件进行对比,可以了解到在证据获取的可能性上,性骚扰案件是较小的,在当事人获取证据的能力上也是较低的。而且证据获取的方式,甚至证据本身就是违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如侵犯他人的权利而获得的唯一证据就要被排除等,这与性骚扰案件通常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是有关的。因此,性骚扰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应该同其他的民事诉讼的案件一样,需要适当的降低。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之采取较高的证明标准,是为了尽可能减小错误判决导致的不利益,刑事诉讼中采取较高的证明标准就基于此原因。刑事案件中,一个人的损失不会成为另一个的收益,刑罚大多是有其净成本的,而非转移,所以对施以刑罚应该更加谨慎。但是在民事诉讼中,惩罚本身没有成本,它只是一种简单的转移。由于民事诉讼主要涉及的是财产权利义务的分配,即使出错也可以获得实质、完整的补救。所以,民事诉讼没有必要采取和刑事诉讼一样的证明标准,而性骚扰案件就更有必要降低证明标准。
在我国首例性骚扰案件中,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再坚持上诉,但是判决的影响却是不会就此结束的。
(三)由案例总结出的降低性骚扰案件证明标准的具体方法
由于很多案例中的性骚扰行为都是出现在工作场所内,针对这一类性骚扰案件,可以规定一些缓解被侵害人证明困难的措施,如要求不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事实解明的义务 ,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雇主责任承担的证明方面,也明确规定雇主承担其证明已经遵循《两性工作平等法》所规定的各种防治性骚扰的规定,且对该事实的发生已经尽力防止仍然不能避免时,才能免除雇主责任。 我国首例性骚扰案件中,要求被告承担案件事实的解明义务对被告而言是轻松的,即让该总经理解明证人证言中提供的办公室内的人是否是其本人,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原告的举证困难且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
再者,发生在工作过程或场合里的性骚扰,没有严重伤情的情况下,原告能够提供的证据往往是证人证言,也就是同事们,这时就要考虑到证人如实作证问题。某些情况下,如被告是领导者或者其上司等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相关人等时,证人能否作证、能否如实作证、其证言的真实性就值得考虑。如果因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问题而导致法院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很容易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这类性骚扰案件中,法院要考虑到证明妨碍的情况的存在,通过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在从其它证据获得的心证基础上综合考虑妨碍的方式、可归责的程度以及被妨碍证据的重要程度,最后依据自由裁量来对事实作出认定,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能够降低性骚扰案件的证明标准。
降低性骚扰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并不会失了公正的天平,反而更能维持平衡。维护女性权益,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