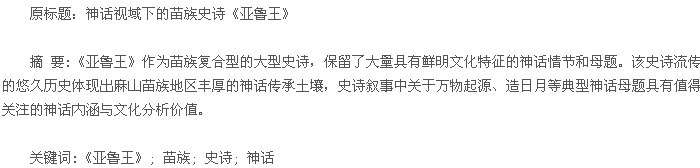
本文以《亚鲁王》为分析文本,重点探讨其颇具特色的神话叙事及神话意蕴。该史诗作为目前仍广泛流传在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活态口传史诗,是一部叙述苗族祖先创世、迁徙、英雄争战、生产生活经验等多种内容的复合型史诗,也保留了带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大量神话情节和母题。在神话视域下全面审视这部长达10 819行的史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观察少数民族口传文化传统。
一、《亚鲁王》的长期流传彰显了苗族地区丰厚的神话生存土壤
从演唱语境、演唱者、接受对象和创作目的方面看,《亚鲁王》体现良好的神话演述环境和浓厚的民间信仰文化氛围。该史诗主要由“东郎”( 歌师) 在葬礼上口头演述,其主要目的就是在苗族葬礼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通过规定性史诗演唱仪式系统讲述苗族先人特别是文化英雄祖先亚鲁王的家谱、身世以及争霸称雄的不凡经历,指引亡灵一步步回溯到先祖起源的地方,起到安抚亡灵和教诲后人的效果。这种情况与彝族、纳西族、普米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葬礼上演唱的“指路经”或祖先“创世史”异曲同工。因为讲述者面对的主要对象是死者或称“死者亡灵”,《亚鲁王》的口头演唱体现的是苗族先民规范化了的文化传统,不在于娱人,而是为了“娱鬼”、“娱神”,无论是歌师在初丧前夜为死者开路时所演唱的“亚鲁王的根源”、“亚鲁王的历史”、“亚鲁王的谱系分支”,还是葬礼中配合其他具体仪式或巫术演唱的相对独立的一些仪式歌,都不能不涉及必要的神话情节与神话母题。这也从某一个侧面反映出神话的传统文化功能以及神话与民族信仰、民族宗教的密切关系。《亚鲁王》通过神话元素与人生重大仪式的有机结合,旨在达成族群内部所有个体的情感互动与文化共识,在维系群体秩序和各层级关系方面发挥着其他文化样式难以取代的作用。
从《亚鲁王》的汉译本看,它也像其他大型史诗一样,在演唱中是有一定的程式。值得注意的是,《亚鲁王》中常常反复应用一些神话元素的相同或相似的句式,形成若干章节固定的口头程式。
如《亚鲁王》中许多章节都有这样的唱词: “羊天,成群的羊过江而来,大群羊逐浪跟随而到。鸡天,成群的鸡过江而来,大群鸡逐浪尾随而到。狗天,成群的狗渡江而来,大群狗浮水尾随而到。猪天,成群的猪渡江而来,大群猪浮水跟随而到……”下面是“牛天”、“马天”、“猴天”,“虎天”、“龙天”、“蛇天”、“兔天”、“鼠天”,用 12 个属相把时间定格为 12 个日子里,与动物名称相对应的日子,该类动物就会渡江而来,这意味着现实中该类动物的来源。这些相同的情节由 24 行组成,计264 字,粗略统计,这些排列整齐而带有神话色彩的相同段落在许多章节中都会反复出现,如在第一章第十一节《日夜迁徙,越过平坦的坝子》中出现 16 次; 第一章第十二节《捣毁家园,走入贫瘠的山地》中出现 4 次; 第一章第十三节《血战哈榕泽莱》中出现 1 次; 第一章第十四节《亚鲁王迫战哈榕泽邦》中出现 1 次; 第一章第十五节《千里大逃亡》中出现 3 次; 第一章第十六节《闯入凶险的高山峡谷中》中出现 5 次; 第二章第一节《逃亡中的艰难重建》中出现 1 次。这种现象从文本本身看,虽然在咏唱内容上属于大篇幅的重复,甚至因为在某些语境中并不产生新的或实际的意义而显得冗长啰唆,但作为丧葬环境中的神圣唱词并无可厚非。相反,这些会产生有益于演唱者与手中双方的演述功能,对于演唱者而言,相同情节与句式的多次重复,加强了史诗诵唱的韵律,有利于缓解演唱者记忆的负担与内容变化方面的压力,对引导史诗的其他内容起到提示与铺垫作用,也便于师徒口耳传承; 对听众而言( 包括死者) ,这些相同的句式和诗句营造了一种特定的意象和氛围,能理解史诗中的事件和人物起到相应的暗示,口述固定的诗句表面看似乎在专注于生肖与动物出现的关系,解释了祖先迁徙中十二属相的当日出现了相应的动物,今天看来这种现象本身荒诞不经,但是若从神话的维度考虑,正是有了这些眉目清晰的超现实逻辑,才能把内容宏大的史诗中的复杂事件交代得井井有条,使演述内容更加符合人类对自然界的文化认知而不是一般科学关注的客观逻辑。
二、《亚鲁王》的神圣叙事得益于一系列具有鲜明特征的神话意象
《亚鲁王》的神话叙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将文化英雄个体的塑造置身于世界产生、万物起源等神话叙事的大背景中。这些神话背景一方面强调了英雄的业绩与祖先的神性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也符合大型民族史诗的文化认知需求。至于许多民族历史的大型史诗往往把带有神话色彩的世界和万物产生放在作品的前部,作为主体叙事或现实性叙事基础和文化铺垫,体现出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于创世史诗比较丰富的南方民族而言,无论是解释祖先的迁徙,还是追溯英雄的业绩,往往离不开天地产生万物起源这个文化背景。如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叙述,远古的时候格兹天神造天地时,从天上放下金果变成五个儿子造天,又让银果变成四个姑娘来造地,天地造好以后,格兹天神又让五个儿子捉来世上凶猛的老虎,用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鼻作天鼻,虎耳做天耳,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肚做大海等等,设定了一个万物有源的叙事基础。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在解释族体迁徙之前,也首先将世界和万物起源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史诗中叙述远古时候天地混沌,先有三样天地日月影子,三生九,九生出真假虚实。真与实相配变出日,虚与假相合变出月。神鸡出现后,神鸡生的白蛋孵出了神与人。天神九兄弟开了天,地神七姐妹辟了地。然后就是人类的产生、祖先的迁徙以及祖先创业中的奋斗历程和英雄业绩。诸如此类,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程式,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受众的心理期待和接受习惯,有利于他们思考“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应该到哪里去”的一系列世界观问题。史诗中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正是史诗自身的价值所在。
若将《亚鲁王》与分布在我国贵州、云南、湖南等地普遍流传的以创世为内容的苗族“古歌”相比,神话叙事特征方面共性与个性都非常明显。
如流传于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古歌”中神话内容非常丰富,古歌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开天辟地以及滔天洪水后人类再生,再到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等无所不包,借助于大量的神话使古歌充满神圣色彩,并且苗族古歌古词神话大多在鼓社祭、婚丧活动、亲友聚会和节日等场合演唱,演唱者多为中老年人、巫师、歌手,其中的神话作为古老苗族长期文化积淀和心灵记忆,至今这些古歌古词神话元素仍在民间民俗或说唱艺术中找到影子。
针对目前搜集整理出版的《亚鲁王》而言,虽然文本中展现的宇宙诞生、人类起源、开天辟地、制造日月等没有苗族“古歌”细致多样,但在整个叙事中并没有忽视这类母题的作用,特别是史诗的开篇部分,特意交代神性祖先的创造世界万物的种种情形,不仅体现出人类信仰文化与人类早期文化创作模塑的共性,也反映出作为以塑造英雄为主体的《亚鲁王》,同样将英雄的出生、成长与创业等情节放置在神性世界的大背景中。
同时,《亚鲁王》对文化祖先根谱的叙述和对祖先神性的塑造具有明显的个性。该史诗在代代口传中解释世界和万物产生时已经融入了极为丰富的地方性苗族文化,而在祖先根谱的表述中也把祖先与神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神话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开篇中所说的在远古的岁月中“哈珈生哈泽,哈泽生哈翟,哈翟生迦甾”,到生出的第 8 代祖先火布冷则是宇宙的统领和主宰。前 8 代全是女性始祖,带有明显的母系氏族遗迹,而从第 9 代“火布碟”开始变为男性为主线男女祖先混杂的情况,《亚鲁王》中叙述的苗族祖谱中的先祖有 30 位之多,与汉族神话中三皇五帝的谱系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母女联名制或父子联名制相比,各代祖先的辈次演化反映出更为复杂的神话背景,这些祖先既是神与人的结合体,也是各苗族支系分支演变的写照,他们不但繁衍了人类,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和万物,这对强化祖先崇拜和稳固族体团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这部作品之所以在演唱中具有令人震撼的神圣性,因为作品中不单单描绘出庞大谱系中的英雄祖先的艰难发展史,更重要的是将神话作为不可或缺的元素渗透在祖先的显赫业绩中,这不仅在形式上拉长了史诗的历史跨度,而且毋庸置疑地增添了作品本身的神圣性。
三、《亚鲁王》中典型神话母题具有丰富内涵与文化意义
《亚鲁王》在叙述世界万物起源和祖先的非凡业绩时,使用了大量的神话母题。这些母题大多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母题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大多数典型母题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或地域特点。以《亚鲁王》中造日月神话母题为例,探讨一下该类母题的独特神话意蕴与文化意义。
关注日月的产生,在各民族创世神话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母题,为便于比较,下面利用《各民族常见造日月神话母题统计表》、《苗族神话( 史诗) 关于日月产生的神话母题一览表》两个表格,用直观的形式供大家参照。值得一提的是,《亚鲁王》中关于亚鲁王第二次造日月的情节与其他大多数民族口头传统中的造日月情形具有明显的不同,具有不可忽视的神话内涵和意义。亚鲁王第二次造日月的情节安排在第二章第二节《造日月,射日月》中,如果说前面亚鲁王的成长与争雄带有更多的现实色彩,那么为什么在其后又出现造日月这样的神话叙事呢? 表层意思而言,正如该史诗注释中所言,亚鲁战败迁徙南下,进入南方之后,亚鲁重演祖业,再一次造日月、射日月。从史诗内容与结构看,其直接原因是亚鲁王意外地射落了祖先原来制造的日月,第二章第一节尾有这样两句诗行: “只怪我挥舞七百竿梭镖射尽了太阳,只怨我射出七十支响箭射落了月亮。”甚至还特意交代亚鲁王射落日月后,导致了“亚鲁王疆域黑尽三年白天,日后亚鲁王领地黑了三年夜晚”、“不能开荒坡,没法种荒地”。所以他不得不派人再次去造日月,日月造的太多,造成灾难,还要派人再次去射日月。亚鲁王祖先造日月和亚鲁本人造日月,史诗中唱诵的情节有相似之处。但这不单单是两个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将这些神话元素镶嵌在英雄创业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同样表现出亚鲁是具有神性祖先所具备的神性和素质,并且人类现在的生活环境直接与亚鲁的创造相关,这不仅增强了叙事的现实感,而且还进一步凸显了英雄祖先的神圣与业绩,这一方面说明英雄有改天换日之功,另一方面也是塑造英雄崇拜的有效方式。
此外,诸多神话母题的关联性也是《亚鲁王》一个有意味的问题。第 9 代祖先火布碟作为男性始祖出生后,创造了 12 太阳和 12 月亮,这 12 太阳和 12 月亮分别照着 12 个集市,这些集市按照十二动物属相的规律分布在宇宙中不同的地方,这其中既有人类活动规律的展现,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时间历法与生产生活关系的积极关注。《亚鲁王》史诗中这类看似荒诞不经的造日月母题虽然在其他民族神话中非常普遍,但这些母题与其他地区苗族、彝族、哈尼族中广泛流传的十月历不同,不是简单的对历法现象的解释,其中蕴含着父系社会产生后该地区苗族各氏族或支系间的简单原始性交易。特别是 12 对日月运转与12 个属相的对应,则反映了《亚鲁王》对时间与空间关系的探索与认知,是人类由蒙昧到文明历程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苗族英雄史诗: 亚鲁王( 汉苗对照) [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