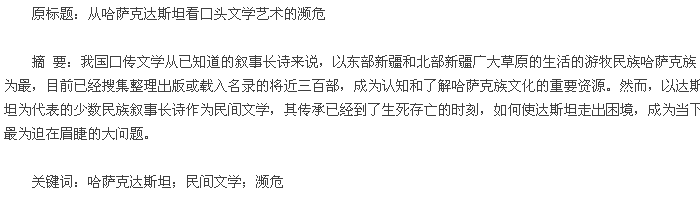
游牧民族的文化和其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作为其中杰出代表的口头文学可以视作其文化符号。几千年以来,游牧民族在寻找祖先记忆和自身历史以及描述自己生产生活时,无不以口头文学作为最直接的载体。随着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游牧文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在动态中的创造活动中看到了静态中的另一个文化样式,即以文本系统作为载体的农耕文化。20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工业文化的不断侵蚀中,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和发酵、散发着巨大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游牧与农耕文化传统都面临着新的选择:是主动融入工业文化还是被动接受工业文化的洗礼?如何才能保持文化传统不被变异和消灭,而一直以来坚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该何去何从?
一、达斯坦的起源及其历时性和共时性
达斯坦究竟起源于何时是一个永远值得津津乐道的话题。从游牧文化的属性观察,草原民族善歌舞的 DNA 贯穿于今,他们始终保持着吟咏的天性,把祖先的信史宗教、习俗、生命观、世界观全都包容到了叙事长诗里,附加其中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成为长诗里的片羽和火花。
对于北方草原民族各个族群来说,达斯坦成为他们血脉中的一种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承形式,在时间和草原的马蹄中,不断琢磨精细,最终发展成为以诗体语言和散文结合的文体,虽然在形式上不一定配曲,但大多合辙押韵。尤其在故事情节上复杂跌宕,一首达斯坦吟唱下来,短的几千行,长的上万行。从目前已知道的叙事长诗来说,首推哈萨克族为最多,目前在哈萨克族中已知已经搜集整理出版或载入名录的就将近三百部,成为认知和了解哈萨克族文化的重要资源;其次当属蒙古族,已经收集和发现的有一百八十多部;再次当属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各约有一百来部;塔吉克族、锡伯族也有少量的叙事长诗得以保存。这充分说明一个历史事实,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中,有着以游牧文明共性的这些族群都有着叙事长诗的流传和保存,这在文化属性上,堪称是一种“共有记忆”. 对于民间文学和民俗来说,共时性和历史性(或者说稳定性和流变性)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始终相伴相随,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共时性通常相对稳固表现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也就是注重经度,而历史性注重纬度,二者共同组成了经纬时空。在历史的长河里,“时移则俗易”,流变性绝对存在于整个过程之中,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尤其当受到外界强劲的外力作用时,就会出现强弱上的变化,而不会绝对不变。
以“黑萨”为例,“黑萨”类叙事长诗是浩如烟海的民间长诗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然学术界对于“黑萨”类长诗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争论颇多,这也说明在哈萨克和柯尔克孜中黑萨的重要性。实事求是地说“,黑萨”类长诗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数量众多;二是情节复杂;三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神话和传说、传奇色彩;四是不可避免地在伊斯兰教传入后受到其深刻的影响。从目前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学者认为“黑萨”类长诗是采用了外来的故事情节,采用或借鉴外来神话、传说和故事达到创作的目的,从内容上判断,更多采用了本民族的生活场景,从而形成哈萨克族长诗的语境,发展成为哈萨克长诗中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表达方式。从收集和整理的目录观察,这类长诗已然在哈萨克族中成为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如:《霍尔赫特阿塔书》(由 12 部长诗组成)、《克里米亚的 40 个巴图尔》《鹏鹉的 40 个故事》《4 个宰相》和《巴克提亚尔的 40 个故事》以及《先知传》(由 70 多个长诗、传奇、故事、传说、诗歌和文章等组成)等。这些作品都是由系列叙事长诗组成的。有些学者将这类长诗称为“连环长诗”.幸运的是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即敏锐关注到哈萨克达斯坦的收集整理,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以录音为主,在开始着手采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的同时,两条腿走路,把当时还没有列入计划的达斯坦抢录了一百多部。今天看来,这绝对是一个先见之明。在 2004 年,文化部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哈萨克达斯坦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 2009 年,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完成了对 200 部达斯坦的整理和汉译。根据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新疆已经查寻到的少数民族长诗近八百部,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存的哈萨克族达斯坦文学作品就有二百多部。就其数量,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法相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授予立陶宛“长诗之国”的称号,其实,和中国新疆相比那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立陶宛所有的长诗不过三百来部。虽然,我们不一定去计较“长诗之国”的名誉,但这至少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文化艺术有时候一定要注意对自己本民族的宣传。
二、达斯坦:突厥语系里的历史叙述
在阿尔泰语系里的突厥语族中,叙事长诗被称为“达斯坦”.在新疆,有维吾尔达斯坦、哈萨克达斯坦及柯尔克孜达斯坦。在柯尔克孜语里称它“坎吉波斯”,蒙古族叙事长诗被称为“土吾勒”.其代表是从公元 9 世纪把家乡从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迁到塔里木盆地定居的回鹘人为代表,也就是维吾尔族祖先开始,其叙事长诗作为文化传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是叙事长诗中伟大的杰作,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另外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用木卡姆为载体,巧妙融合了“叙事长诗”,成为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在民间自觉地保持了下来。以哈萨克族为例,《迦萨甘创世》《神与灵魂》等古老的创世神话,保存了萨满教的遗迹,反映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内容、风格均与南方诸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迥然不同。《哈萨克名称的传说》《冬不拉的传说》等,有着浓郁的草原游牧民族的风采和特色。
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极为丰富,它是哈萨克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族群的集体记忆。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从内容上可分为英雄长诗、爱情长诗、历史长诗或是英雄达斯坦、爱情达斯坦、历史达斯坦等几类。其中,以英雄长诗中形成时间为最早,可信的当推属 10 至 11 世纪的《阿勒帕米斯》、11 至 12 世纪的《阔布兰德》、14 至 15 世纪的《英雄塔尔根》。这些长诗起初无不是为了赞颂为保卫部族安全而与敌人英勇奋战的英雄,这也是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的共同特点。特别是 17 至18 世纪,在族群意识的不断觉醒中诞生了一批新的英雄长诗,如《夏班巴依》《哈邦拜》《加尼别克》《布甘拜》《阿尔卡勒克》等,至此,英雄长诗或者说是英雄达斯坦已经非常成熟,在哈萨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在爱情达斯坦中,《阔孜库勒帕什与巴彦苏鲁》是哈萨克族最古老的一部,这部三万行的长诗最初可能形成于公元 9 至 10 世纪,在历代众多阿肯(歌手)的不断琢磨和锤炼中,成为哈萨克的一部艺术珍品。被哈萨克族群公认的其他脍炙人口的爱情长诗还有《吉别克姑娘》《艾曼与巧勒潘》《萨里哈与萨曼》等。历史长诗以叙述部落历史、谱系为主要内容,如《阿布莱》等,都成为哈萨克人的宝贵艺术珍品。
尽管至今对叙事长诗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哈萨克人相信,哈萨克族民间达斯坦是共时性和历时性发展的结果,与哈萨克民族的生活、历史同时产生和发展的,是在不断总结和提炼哈萨克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谚语和故事等民间文学丰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成熟起来的,是哈萨克人的“文化符号”.从已获知的调查结果看,哈萨克族达斯坦约有三百多部,从内容上划分,哈萨克族达斯坦可分为英雄史诗、爱情长诗、历史长诗和黑萨这四种。在这里面,最着名、影响最为广泛的是英雄史诗 《阿里帕米斯》《豁布兰德》;爱情长诗是《吉别克姑娘》《豁孜阔尔佩席与色彦苏鲁》等。达斯坦是哈萨克人认为可信的历史文化,包括了哈萨克历史、文化、习俗和信仰。游牧文化的传统是口口相传,因此即便没有文字,或者不甚重视文本传承,但是口传历史无不是通过以达斯坦为传播路径把哈萨克传统的文化记录下来传给后人。对于游牧文化传统来说,在看待自身的史诗传统及其文本的形成问题时,特别要重视和注意的是,口头史诗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部作品”,而是一个流动的、有生命的经过时空不断琢磨和打造“史诗演述传统”,更不能以农耕文化的传统和眼光去判断。这方面具有客观和历史的眼光学者当属哈佛大学古典学者格雷戈里·纳吉,他的代表作《荷马诸问题》通过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推演,论证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何样、何时、何地等问题,并回答了为什么上述两个伟大史诗最终以书面文本形态被保存并流传两千多年的缘由。这个缘由揭示了荷马文本背后潜藏着的相当漫长的口头创编和传播过程,以及最终是在公元前 550年史诗文本才趋于定型和成熟。格雷戈里·纳吉因此提出了“演进模型”的结论,这也深刻揭示了荷马文本的形成历程。
通过这个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意识到,荷马史诗的文本定型问题其实完全可以视作一个过程,而不是当做一个事件。
从文本的经典属性阅读来看,只有当口述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以文本进入书面写定之际,文本定型就称之为了经典,这也就成为一个事件。这种有趣而艰难的过程如果移植到达斯坦来看的话,其“过程”与“事件”完全一致,所以如果用这种变迁来理解和探究达斯坦的演述传统和文本定型问题的话,也就会真正站到游牧文化的视角去实践和开启更有益的学术实践。
有了上述视角和实践,在看待哈萨克族达斯坦的流传方式上,就会发现其重要的传承者是草原上的阿肯。阿肯由民间诗人、歌手组成,其功能一是传承和传播达斯坦以及相1达斯坦;三是其中的优秀的阿肯,擅长于达斯坦的,被称为“达斯坦奇”.这是因为达斯坦情节复杂,篇幅很长的,一部达斯坦往往要唱上一天一夜。他们在表演时,达斯坦中属于散文部分的用说白叙述,而韵文部分一般配有较固定的曲调,用冬不拉伴奏,自弹自唱。目前,居住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0 岁的哈孜木能唱其中的 104 部,是目前民间吟唱达斯坦数量最多的人,因此,他被人誉为“哈萨克族达斯坦的活唱片”和“活化石”.
三、口头文学的濒危和拯救
就目前的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口传文学存续状况看,口头文学已经面临着巨大危险:即口传文学的严重濒危。首先是传承人的状况不容乐观。除了居素甫·玛玛依(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国家级传承人,已经于2014 年 6 月不幸去世)、加朱乃(《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国家级传承人)、哈孜木(哈萨克《达斯坦》国家级传承人)外,国家级传承人再无他人。当前哈萨克族的达斯坦还比较有造诣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新疆沙湾县的 61 岁的自治区级传承人朱买·可尼瓦别克,他能掌握几十部达斯坦;第二个是伊犁州尼勒克县哈拉托别乡萨依博依村已经 70 岁的哈萨克族牧民吐尔逊艾力,他可以演唱三十多部《黑萨》。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通过二十年的努力,在全疆所收集整理到的《黑萨》有二百多部。其次,由于人亡艺绝带来了文化生态危机。许多当年在新疆大草原远近闻名的“达斯坦奇”都不断离我们远去,这种文化生态的变迁也昭示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一样,最濒危的都是民间文学。究其原因,不能否认当代群体审美的心灵转移,尤其是城市化和现代化所引领的现代文明体系正以绝对优势的话语权消解着以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几乎所有符号。第三,现代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使传承链条面临断裂。目前牧区的年轻一代基本都到城市打工,牧区基本是妇孺老幼,传承无对象。第四,年轻人的审美改变。多少年轻人更喜欢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化兴趣不大,这个巨大的改变其实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面对这些问题,福海县在解决危机上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福海县在对待达斯坦的危机上想了很多办法,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鼓励国家级传承人哈孜木办班,建立传习所,由县里寻找徒弟,找了几个对民间文学有兴趣的年轻人和中小学生,请哈孜木来人授课;二是打造“达斯坦乡”;把哈孜木老人生活的阔克阿尕什乡命名为“达斯坦乡”,与旅游结合;三是抓紧录像录音,与新疆音像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哈孜木版的达斯坦音像资料。这些措施无疑在某种意义上对挽救达斯坦做了很多贡献。
通过对全国和全疆的考察发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和布克赛尔县的“教育传承”不失为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即传统文化进校园。上述两个地方把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当作乡土教材进入了课堂,每周请自治区级传承人去授课,目前已经培养了四十多个学生做传承人。另外,把《江格尔》制成动漫,激发了学生热爱传承《江格尔》的兴趣,扩大了传承路径和内容。还有一个做法非常值得推广,与高校合作,共同研究。和布克赛尔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师范大学积极合作,打造传承基地和设立《江格尔》研究基地,为弘扬和传承《江格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看,保护与拯救民间文学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无论如何,民间文学是目前人类对于早期世界和历史以及自身来历的认知和记忆。类似达斯坦这样的口头文学是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的文化符号,在当今社会和世界如何陪伴人类,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无疑都是重要而艰难的事情,我们深深期待,这种口传文学能引起全人类的关注而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 哈萨克民间达斯坦[M].哈衣夏,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2]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哈萨克族达斯坦与达斯坦说唱艺人---以福海县阔克阿尕什乡为例[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0,(3)。
赫哲族作为我国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富饶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交汇而成的三江平原,以及蜿蜒曲折的完达山余脉,孕育了赫哲族渔猎生产生活的历史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