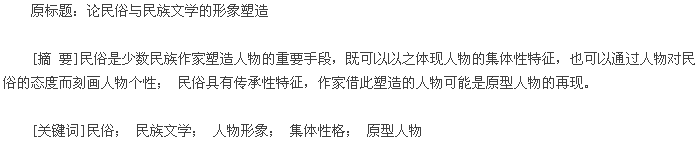
民俗,按钟敬文先生的定义,“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民俗与人须臾不可分割,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交织着民俗。民俗具有集体性特征,只有一个群体都承认和遵循的行为或心理定势才能成为民俗。民俗常常成为集体精神的表象,是民族性格以及民族信仰的外在体现。
文本世界根源于生活世界。民俗既然必然存在于生活世界,也就必然存在于文本世界。但文学的文本世界需要通过形象、故事等呈现意义,作为文本整体之一的民俗就在不同程度上承载了意义。因此,文本世界的民俗实际上是双重载体,既与生活世界的群体特征相关,也与文本世界的意义相关。民俗通常不能直接呈现意义,它需要与文本的其它因素相结合,通过某些因素进行转化,而人物形象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人物形象往往寄寓着作者的思考,讨论民俗与人物形象的关系,既能够通晓在人物形象的形成机制中民俗的功能,也能够揭示出民族特征在文本中的转化途径。
一 民俗与人物形象的集体特征
集体性格指某一个集体或群体中,人们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性格。如美国着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对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比较: 新墨西哥的普韦部落人是日神型的,现实主义者,重视仪式,轻视财产,讲求中庸之道,生活有分寸和节制; 新几内亚东部多布人郁郁寡欢、过分正经又极重情欲,为嫉妒、猜疑和愤懑所吞噬; 而美洲西北海岸的克瓦基特人却是酒神型的,并且妄自尊大,非常自负,喜欢自夸和嘲笑、羞辱别人。[2]
一般来讲,处于某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会分享该群体的传统以及群体性格。民俗因为具有较为显着的地域性和集体性,自然而然会限定同时也是凸显人物的集体性格。
藏族作家梅卓的长篇小说《月亮营地》,首章便是对藏族祭祀山神仪式的描写。在藏族人心中,几乎每一座山都有神灵,每一座山都有关于神灵的神话传说,神灵主宰着人们的生活。因此,藏族人对山非常崇敬,视山为“圣洁之地”.藏区的山也多,并且雄伟,如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横断山等等,而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神山之王”岗仁波钦、“擎天柱”南迦巴瓦更是受到了特别的瞻仰。西藏有着名的四大山神: 东方的雅拉香波、南方的库拉卡日、西方的诺吉康娃桑布、北方的念青唐古拉。还有四大念神、世界形成之九大念神、十三念神、地神、十二丹玛女神、四药叉女神、四医女神等等。[3]
藏族人对山神的崇拜不仅仅体现在心中的景仰上,而且还有相关的民俗,比如到山上祭祀、朝圣、祈祷、煨桑、转经、磕头、转山等等,神山的许多山洞都有信徒在里面修行。特别是转山,这根源于宗教信仰的仪俗是许多藏族人重要的修行方式,转山的次数越多,被认为功德积累越多。因此,居住在神山附近的藏族人,转山几乎是每日必行的功课。除了神山崇拜,藏族人还有圣湖崇拜、江河崇拜等等。
因此,《月亮营地》中祭山仪式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是藏族人对山和自然的敬畏。同时,祭山仪式的高潮是口剑穿刺,在这个环节中,藏族男儿会争先恐后涌向法师。这是考验个人能力和技巧的竞争,也就展现出了藏族男儿勇猛和豪壮的集体性格。
依据这两种集体性格,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物及其行动: 对神山、圣湖以及江河等等的敬畏和崇拜,必然会催生出群体的自豪感和集体感,以及对群体生活环境的保护。这正是月亮部落逐渐团结起来抵抗外来侵犯的深层基础,也因为藏族男儿勇猛豪壮的性格特征,使得他们绝不会将生活环境、神灵庇佑之地拱手让出,他们一定会挺起胸膛,骑上骏马和侵犯者决一死战。由此,人物得以理解,故事得以把握,作品雄放之气跃然纸上。
民俗除了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之外,它还可以超出某个具体的民族,而体现某个群体的性格特征。如锡伯族作家觉罗康林的长篇小说《喀纳斯湖咒》,小说展演了新疆图瓦人的古老信仰,他们关于老爹石的历史传说,萨满的通灵、预知和仪式,试图传达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民族与民族平等尊重的主题。在小说中,通过萨满的驱邪仪式,巴勒江的母亲---萨满后人各自的性格特征得以体现。因为巴勒江的母亲是萨满后人,萨满的集体特征在她身上有体现。萨满,出自古通古斯语,“意思是激动、不安和疯狂者”[4].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归纳过巫师的特性,通常成为巫师的人主要是: 神经紧张、躁动不安的人或者弱智者,具有粗野的姿态、尖锐的嗓音、雄辩或诗人般的天赋的人,身体不健全以及患有疾病者,女人以及铁匠、牧羊人、挖墓者等等。[5]
在《喀纳斯湖咒》中,巴勒江母亲也表现得古怪、不安、紧张,行为不可理解,这是萨满的集体性格赋予她的特征。
二 民俗与人物的个体特征
除了集体性格,人物性格还包括个体性格。不同的人物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不同的性格特征可以通过外貌、对话、行动和心理等方式得以体现。
民俗虽然是一个整体,但细致来看,民俗的参与者却具有不同的身份。另外,在文学作品中,作家还可以依据不同人物对民俗的不同看法和体会传达出人物的个体性格特征。因此,民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个体性格的形成和展现。
在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最后的土司》中,讲诉了土司覃尧、外乡人李安和哑巴伍娘三人的情感纠葛。小说中的摆手活动、梯玛活动等民俗形式首先说明了覃尧、梯玛、伍娘、李安等人的区域性,前三人在土家地区土生土长,而李安则是外来人。通常来说,同一区域、同一部族的人民会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共同的思维和精神特征。这为解释土家人和外乡人李安的冲突提供了途径,也为理解文本的深层结构和意蕴打下了基础。
不过,对于小说文体来说,人物形象的有血有肉是重要的,这也成为衡量一篇小说艺术手法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覃尧是土家山寨的土司,土民敬仰的王。从人物性格来说,覃尧是一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他既守卫土家传统又打破传统,他认识到了初夜权的不合理,却又通过初夜权占有了伍娘; 他两次救了李安,却又数次举枪要杀掉李安; 他果断却又优柔寡断; 他既宽容却又妒忌; 他希望保护伍娘却又深深地伤害了伍娘……特别初夜时,站在伍娘卧室门外,覃尧心里的辗转纠结,其矛盾性格显露无遗。深思之,这种矛盾的心态又清晰地展现了覃尧的伦理选择: 对家园、根脉、土家文化传统的热爱和坚守,对爱的不顾一切,对别人的宽厚和容忍。
如果说覃尧是性格最复杂的一个,那伍娘便是小说中最单纯也最美丽的人物。她热情奔放,在舍巴日的摆手舞中像火一样燃起全部土家山民的激情; 她纯洁虔诚,将自己的身体真诚无邪地献给神;她执着忠贞,对外乡人李安的爱始终不渝; 她隐忍顽强,毫无怨言地包容了李安非人的虐待。然而,在覃尧和李安的斗争中,她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不但失去了爱情,受到了虐待,连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因此,她只有选择在舍巴日尽情的舞蹈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伍娘,生命的结束既是一种悲苦,同时又是对神灵的又一次献身,这次是把整个的生命献出。通过这样的献敬,伍娘在祈求什么?
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明说,而是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揣摩。这让读者在感叹伍娘命运之时,又多了沉思,从而让小说显得韵致无穷。
李安则是一个有心机、凶狠、有仇必报的人。
为了从师傅那里学到手艺,他忍受欺压,曲意逢迎,待到学成手艺,又施以报复,气死师傅; 为杀死覃尧,不惜去当兵偷枪,然后再返回土家地区; 也是为报复覃尧,含恨等了整整半年有余,以孩子相逼迫,可谓处心积虑; 为了泄愤,屡次殴打、折磨伍娘。除了开始对伍娘短暂的喜欢,李安满脑子中就只有“仇恨”二字。另外,梯玛覃老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身为巫师和医师,他救活了李安,在土司和李安的斗争中,他多次暗示土司杀死李安;同时,他第一个发现了伍娘的孕情,这时他也预知了悲剧的后果。他希望下药让伍娘流产,来维护土司、李安、伍娘三人暂时的和谐。重点在于,四个人物形象的形成机制中,民俗起核心作用。覃尧的矛盾性格是在初夜习俗之中呈现出来的; 伍娘的热情和悲苦是在摆手舞中体现,而虔诚和纯洁又在初夜之俗中表露; 梯玛本身就是土家民俗的一部分,是土家传统的维护者; 李安虽然不是土家人,但他的狠毒和心机却是因为初夜习俗被激发出来。由此可见,民俗是不同人物形成不同性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