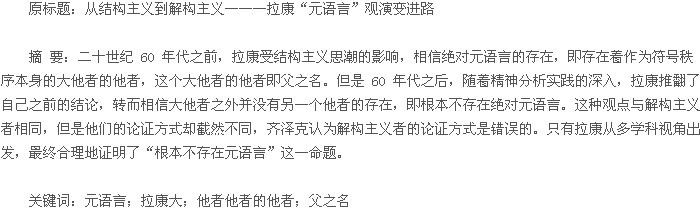
对元语言的研究始于现代逻辑学,1933 年波兰逻辑学家塔斯基为了解决“说谎者悖论”问题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之分。“对象语言是用来谈论外界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语言,……是第一层次的语言;元语言是用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是比对象语言高一个层次的语言”。
但是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在某种场合下被称作是元语言的一句话,在另一种场合下亦有可能成为对象语言。在塔斯基之后,学者们对元语言的研究热情不断高涨,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元语言作为描写手段,任何符号文本(包括宗教、礼仪、民俗等)都无法被人所理解,也不可能形成逻辑学、语言学、甚至是哲学等学科,可以说“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
因此“元语言”问题被提出后不久就很快突破了逻辑学界,成为语言学、哲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热点。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康受到当时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综合精神分析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理论,对元语言的存在进行了论证。但是随着拉康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的深入,他在 60 年代时突然一改之前的言论,提出了“不存在元语言”这样惊人的论断。他的这种观点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不谋而合,这种观点的转变可以看作是拉康作为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标志性事件。那么拉康是怎样得出这种结论的呢?元语言真的如拉康所说是不存在的吗?
一、语言与拉康三大界域的观念
拉康将元语言定义为“大他者的他者”,所谓不存在元语言,即不存在大他者的他者,那么大他者与语言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若要对其进行深入地了解,我们则需要回顾一下拉康有关人类生存的三大界域的观念。1953 年拉康发表了《精神分析学中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一文,提出了人类生存的三大界域的观念:
实在界、符号界和想象界。想象界与拉康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密不可分,婴儿在 6 至 18 个月期间一般都会经历一种镜像阶段的变化,他无意间看到了自己在镜中的形象,一开始他认为那是另一个躯体,然后会发现那只是一个镜像,最后他终于发现那个镜像就是他自己。婴儿看到了镜中的形象会随着自己的动作而相应动作,这误使他认为自己已经能够自如地控制镜像了。正是这种误认性的想象功能造就了以自我为代表的想象秩序,所以拉康称其为“想象界”。
拉康认为儿童在镜像阶段结束之后,就进入了俄狄浦斯情结阶段。他认为可以将俄狄浦斯情结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段时期,母子间亲密无间,孩子想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从而达到与母亲同化为一体的目的;在第二段时期,父亲插入到母子之间的关系当中,他作为“法”的代表为母亲的欲望以及孩子颁布禁令,他挫败了孩子成为母亲欲望对象的企图,并自己取而代之;在第三段时期,孩子告别母亲,认同于父之名所代表的法和禁令,即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孩子由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文化状态,他才真正完成了主体的建构,俄狄浦斯情结也随之结束了。父之名及其所代表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秩序共同形成了一个他者的维度,拉康称之为大他者。对我们来说,我们向之认同的文化习俗、道德规范、甚至是理想、意识形态等概念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它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是一个个漂浮的能指,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语境中被缝合到不同的所指之上,形成不同的意义。所以拉康说:“这个能指的集合体的定义就是它们构成了我所说的‘大他者’”。
由于拉康认为“语言是由一系列能指构成的”,所以大他者不是具体的某人或某物,而是符号秩序本身,在拉康看来,只有进入到符号秩序、即象征界才意味着主体的真正形成。
人类生存的另一大界域是实在界,拉康认为实在界并不是指外部的客观现实世界,实在与现实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是指主观现实界,该现实界抵抗着任何符号化和辩证化,因此它是外在于意指过程的、思维无法逾越的领域。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假定实在界的存在,因为“实在界是这样一种实体,它必定是在事后构建起来的,这样我们才能对符号结构的扭曲作出解释”。
比如对“父之名”的形成去寻求其最初的历史原型是毫无意义的,但若要解释人类是如何进入到符号界的,假定“父之名”的真实存在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实在界是符号化过程的出发点、根本和基础”。而且实在界也并非无迹可寻,由于实在界总是会时不时地回归,(如在梦中反复出现的创伤性事故等),“以原始的无序和无知来骚扰主体”,使其产生各种幻觉以及个性分裂的妄想。正是为了抵制实在界的入侵,拉康才设想出了大他者的他者存在,以保证主体不变成精神病患者。
二、元语言与“大他者的他者”
在有关元语言的问题上,拉康的观点并非前后一致,60 年代之前,拉康认为元语言是存在的。在1955-1956 年期间进行的第三期研讨班中,拉康说:“语言整体就意味着元语言的存在”。
在 1957-1958 年期间进行的第五期研讨班中,拉康进一步解释说:“分析经验向我们表明,在谈到他者时,作为背景的他者(即大他者的他者)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大他者的他者,语言就无法表达自身”。
这意味着作为能指场所的大他者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他者,在拉康看来,这个超验的他者就是那个代表法和禁令的父之名,正常人的话语由于受到父之名的组织调节,因此阻止了真实界对主体的入侵;而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缺乏父之名(即元语言、大他者的他者)的调节,作为能指场所的他者就会与实在界混为一谈,由此在患者头脑中产生幻象,所以他们就无法组织起连贯的话语。
对于元语言的存在,拉康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类是唯一会假装欺骗的动物,而这种假装欺骗的行为必须预设出一个“非欺骗性成分”来保证它的成立。正如他经常引用的弗洛伊德讲述的一个有关犹太人的笑话所示:“为什么你对我说你要去克拉科夫,着使我以为你是要去朗伯格,而你实际上是去了克拉科夫?”
这则笑话的要义在于二者已对“你说去哪实际上就不去哪”达成了共识,将其设定为“非欺骗性成分”。也就是说,作为能指场所的他者具有欺骗性,而对于作为语言之存在的人来说,他必然需要一个“非欺骗性成分”来保证其日常现实客体的真实性。但是,不同文化和研究领域内的人会选择不同的东西来执行这种不欺骗的功能。例如,亚里士多德传统下的自然科学就将未经加工的自然界看作是“非欺骗性成分”;而在人文学科,拉康深受列维 - 斯特劳斯的影响,认为“乱伦禁忌”是将自然与文化区分开来的基本法则,因此是保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下去的“非欺骗性成分”,而实际上乱伦禁忌就源于父之名的调节作用,所以拉康认为大他者之外的那个超验的他者、即元语言就是父之名。
拉康在 50 年代对于元语言存在的肯定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当时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50 年代的法国正是结构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结构主义将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从作为个体主体存在的人转向了超越个体主体而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结构和体系。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是由许多成分按照一定规则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成分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整体的结构体现的是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这些关系与结构就可以理解所涉及的领域的各种现象;与成分相比,整体处于主导地位。结构主义者们对结构的寻求使得拉康相信在大他者(即语言符号秩序)之外存在着一个能统筹它的超验他者,即元语言。
三、不存在元语言
但是到了 1960 年,在一篇名为《主体的倾覆和在弗洛伊德无意识中的欲望的辩证法》的文章中,拉康明确地表示不再将父之名当作是大他者的外在保证者(即非欺骗性成分),他说“:让我们从他人作为能指的场所这样一个概念开始。所有权威的言谈只是其言说本身为其保证。倘若要去另一个能指中寻找保证,那是徒劳的;能指是不可能出现在其场所之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可以说出来的元语言。用一种格言式的方式说就是:没有他人的他人。出场来取代它的立法者(就是那个声言要制定法律的人)是个冒充者”。
在拉康看来,虽然父之名依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其他能指的能指,但它已不再是先验的、外在于大他者的成分了。没有父之名包围的符号界就是一个直接向实在界开放的结构,父之名只是像“软木塞”一样堵住了符号界藉以向实在界敞开的裂缝,“虽然这裂缝被堵住了,但裂缝仍然存在”,并未被缝合上。按上文拉康所说,主体与实在界的接触会导致精神疾病,因此为了避免疯狂,我们要尽量逃避实在界。而实际上要逃避实在界的唯一方式就是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元语言,但是拉康通过多年的精神分析实践发现,实在界是无法逃避的。因为即使在正常人的身上,我们也能找到些许幻觉、幻象或是症状这些实在界所遗留下的痕迹,我们总是会时不时地与实在界偶遇。无法逃避的实在界说明了元语言的不可能性。
上面提到,拉康对元语言的追求在于为人类语言寻求一种“非欺骗性成分”,而实际上精神分析的实践表明,对“非欺骗性成分”的追求全部以失败告终,因为正如拉康援引弗洛伊德的那个笑话所示,人们可以轻易地通过背叛原则来骗过对手。对此现象拉康说非欺骗性成分,即真实的话语“在从一定的言语中析出许诺的素材时就使言语显得在说谎,因为许诺承担起未来,而正如人们所说,未来不属于任何人;而且还多义,因为许诺在构成其变迁的异化中一直超越了它所涉及的人。但是,真实的言语在质问什么是真实的话语的意义时会发现意义总是提及到意义,没有什么事可以用符号以外的东西来指示;由此总是使真实的话语显得必定会出错”。
非欺骗性成分的不可能性使得元语言的存在也变得不再可能了。
对于拉康的“不存在元语言”的观点,齐泽克提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进行审视。元语言是针对对象语言而提出来的,因此所谓的“不存在元语言”就意味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象语言:即不存在无对象的语言。对此齐泽克说“:即使当语言明显地陷入了自我指涉运动之网时,即使当它明显地只谈论自己时,也存在着对这一运动所作的客观的、非意指性‘指涉’”。
“不存在元语言”的观点使拉康超越了结构主义思想,开始向解构结构主义过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拉康是法国结构、解构主义思潮中一位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继他之后,解构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普遍采纳了“不存在元语言”的观点,只不过他们的论证方式不同而已。
四、解构主义者与拉康元语言观的比较研究
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来自文本内统一、固定的结构,而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文本是一种差异化的网状结构,这个结构没有固定的中心,没有最终的所指,它有的只是能指以及符号间开放式的差异性运动。任何语句都不可能精确地言说它想言说的事物,阐明的过程总是要颠覆语言的,所以在参考文献解构主义这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元语言。但是,与结构主义的论证不同,拉康认为不存在无对象的语言,而解构主义者的论证要点在于说明了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对象语言。因为在解构主义者们在其自我阐释性的语言游戏中“没有过多地提及对象,通常的情形是,人们指出‘现实’是如何已经通过语言的中介而被构造出来,并以此把对象剔除出去。……‘根本不存在元语言’事实上被用来意谓它的对立面: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对象语言”。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清楚地说明“现实”的存在,任何所谓的客观陈述都包含着某种“自我距离”,所以,语言总是如德里达所说,其意义在空间中存在着差异,在时间中又地向后延宕,它没有中心、没有尽头,在延宕中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意义。
对于解构主义者们的论述,拉康的忠实门徒齐泽克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解构主义者们对于文本的无尽的阐释往往会产生黑格尔意义上的“恶劣无穷大”的效果,这种“恶劣无穷大”并不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解构主义者忽略了这样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们总是站在安全的立场上说话,而这一立场通常不受离散化的文本进程的影响,所以解构主义者们在对文本进行多重性地阐释时,经常会发生偏差。在齐泽克看来,他们的种种努力不过是在“掩饰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事实:在解构主义所言说的根部,存在着一个明显经过界定的立场,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以某种纯粹而简单的元语言,清晰说明这一明显经过界定的立场。”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元语言”是解构主义者们的普遍命题,但实际上,解构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地证明这一命题。只有拉康,他首次提出了“根本不存在元语言”的观念,并以其独特的视角证明了这一命题。
结论
元语言问题是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的热点话题,结构主义时期的拉康利用人类学和精神分析理论证明了元语言的存在。但是,到了 60 年代,随着精神分析经验的不断深入,拉康推翻了自己之前的理论,认为“根本不存在元语言”。这一观点与解构主义者们的观点一致,但是其论证方式却大相径庭,齐泽克甚至认为解构主义者们根本就没有证明这一命题。对于这一命题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里所谓的元语言指的是绝对元语言,即能解释所有其他语言的语言;无论是拉康还是解构主义者,他们都没有否定解释某一对象语言的相对元语言的存在。因此严格地说,他们的最终结论是:根本不存在绝对元语言!实际上,拉康的论证进一步证实了分析哲学家们的观察。罗素在为维特根斯坦所著的《逻辑哲学论》写的导言中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结构,存在着处理这一语言结构的语言,针对这一新的语言又有一种新的结构,而且语言的这种系列是可能没有止境的。这意味着对象语言与元语言之间的阶层是无限的,所以绝对的、终极的元语言是可能不存在的。但是塔斯基和罗素都没有说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之间阶层的这种无限性的结果如何,他们并未能有效论证绝对元语言的存在与否。只有拉康另辟蹊径,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多维视角出发,最终证明了“根本不存在元语言”这一命题。
参考文献
[1] 丁晓金.现代西方哲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 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拉康. 拉康选集[M].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
[4] 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5] 陆杨,张艳. 拉康与弗洛伊德:无意识结构的语言分析[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