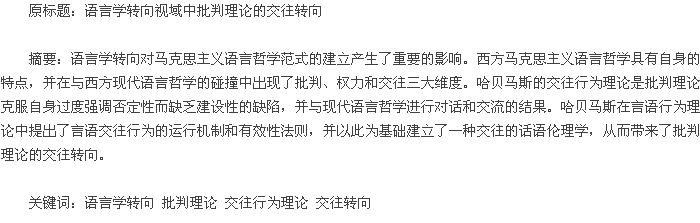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学术界之所以对语言问题如此关注,原因在于“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①。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是哲学界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甚至带来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革命。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论述,并以 此 为 基 础 形 成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语 言 哲 学 的 特 有范式。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语言学转向主要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两条路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正如本维尼斯特所言:“语言学的新方法对其他学科来说有着范例甚至模式的价值;目前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学科日益繁多;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精神开展人文科学研究渐成潮流”②。而英美分析哲学则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语形、语义和用法的分析来研究人类的意义和精神世界。语形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是语言学(阿佩尔称指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重心由语形学向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依次转移也正是分析哲学的三个发展阶段③。哈贝马斯从事理论活动之时语言哲学正在经历语用学转向,语用学代替语形学和语义学成为语言哲学的主流形态。哈贝马斯深受语用学转向的影响,并将其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通过对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吸收、批判和改造,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普遍语用学的理论构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进而将其拓展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正如马丁·莫里斯所言:“哈贝马斯在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更普遍的语言学转向中进行了一种语用学转向。他通过言语行为的语用学理论走向语言研究,并把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许多核心问题转化成语言的使用问题。”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通过与现代语言哲学的对话为批判理论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其弟子霍耐特把这种范式转换称为“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①。
一、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维度
哈贝马斯将20世纪的学院哲学区分为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大思潮。尽管这四者之间差别很大,但都是通过对语言的关注使哲学研究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差别仅仅在于语言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思考和研究语言的角度不同而已。前三者都把语言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则是劳动、生产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其语言哲学思想包含在对诸多社会问题的论述之中。正如保罗·利科所言:“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哲学不一定要作为一门研究一种实体性的、自成一体的、决定着各类现象的现实的特殊学科而存在。
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语言只有与或多或少决定其基本特性的其他非语言现象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够被正确理解。”②因此,马尔 库什把前三者的理论方法称为 “语 言 范式”,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称为“生产范式”,并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对话的可能性③。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思想非常分散,涉及的理论家也比较多,每个理论家的语言哲学思想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讨论不同的问题,但是正如雅各布森所言,每一个流派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其思想都具有一个“主导”的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也必然存在共性。戴维·福加克斯指出:“一种模式既要以语言为中心,同时又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概念来说明语言在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④因此,要同其他语言哲学区分开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范畴和研究路径。自称为“老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学者让-雅克·勒塞克尔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有时候仅仅只是一些碎片,但是它也构成了一个传统。为了重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语言学文本,就需要阐明一个框架,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轮廓勾勒出来。”通过对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到德勒兹和加塔利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分析,勒塞克尔用六个论题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即一个主命题“语言是一种实践形式”;四个支撑命题,即语言分别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物质现象和政治现象;一个总结性命题“语言是通过质询而得到的主观化场所”⑤。
这几个命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主要特点,从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与分析哲学传统、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以及结构主义传统之间的显着差异。马克思主义不像分析哲学那样谈论语言的语义结构,也不像现象学和解释学那样讨论语言与存在及意义的关系问题,又不像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那样仅仅将共时性的语言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包括文学和艺术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现象,并且与社会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将索绪尔式的侧重于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的语言学称为“内部语言学”,那么,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称为“外部语言学”.尽管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具有明确的共性,但这些共性并不能掩盖不同理论家的语言哲学之间的重大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和斯大林主要关注语言的社会本质问题,认为语言作为交往工具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因此他们对语言的讨论就自然集中于语言的起源、语言的阶级性、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等问题。与此不同,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交流和碰撞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理论维度,即批判维度、权力维度和交往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也把语言批判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其中最早论及语言问题的应属本雅明。本雅明在写于1916年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一文中从神学角度对语言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把对语言的讨论与对现代性危机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本雅明看来,上帝用语言创造了人类和万物,并给予人类对万物命名的权力。同时,巴别塔计划直接导致了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此,语言既是人类起源的标志,也是人类堕落的诱因。也就是说,人是由上帝用语言创造的,而人类的堕落首先起源于语言的堕落。在此体现了本雅明的现代性批判中的神学色彩,因此沃尔法思将其 概 括 为 “一 个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的 ‘创 世 纪’”是 颇 有 见地的①。
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且直到70年代才得以面世的《论哲学家的语言》一文中,阿多诺指出:“今天所有的哲学批判都可能成为语言批判”,因为历史和真理等问题都与语言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就蕴含在语言之中,所以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不可能脱离语言而单独进行。当今的哲学家面对的是一种破碎的语言,因此,与语言的物质性的灭亡相伴随,蕴含于语言中的历史和真理等也会与语言自身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语言的意义性,要求哲学语言具有可理 解 性,也 就 是 社 会 的 可 交 流 性,是 唯 心 主 义 的。
……今天,哲学语言所预想的可交流性在其所有方面都被发现是欺骗性的”,而“所有欺骗性的本体论都是通过语言批判的方式被揭示出来的”②。虽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哲学都可以还原为语言批判,但是语言批判成为哲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却是毋庸置疑的。
马尔库塞更是把语言批判作为他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尔库塞认为:“语言的荣枯兴亡在政治行为的荣枯兴亡中有其对应物。”③一个单向度的压抑性社会中的语言是一种“全面管理的语言”,在语言的不同使用中渗透和体现着权力关系,其中句法、语法和词汇都变成了道德的、政治的行为,语言也成为控制和压抑的工具。人们在讲自己的语言的时候,也在讲他们的主人、赞助人和广告商的语言。语言的功能化有助于从言语的结构和活动方面来击败非顺从要素,从而有利于单向度的社会控制。尽管这种语言也存在着对立面,比如大众语言就是带着尖刻而轻慢的幽默来攻击官方和半官方话语的,普通人也在其俚语中表明反对现存权力的意图,但这并非语言的主流状态。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包含着意识形态,因此,除了那些用于指称日常生活中的客体和器具,指称可见的特征、根本的需要和希求之类东西的术语之外,语言使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为阶级统治和控制服务的。马尔库塞认为,罗兰·巴特所说的极权主义的封闭语言助长了一种看法,即“现存政权的语言是代表真理的语言”④。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的语言观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极权主义的、仪式化的封闭的语言。这种话语的极权主义的仪式化往往在冒充辩证语言的地方出现,比如斯大林主义的语言。可见,按照马尔库塞的理解,资产阶级的统治语言是一种话语的极权主义,是封闭的、操控性的、单向度的,不允许对立面的存在。基于此,马尔库塞对分析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关注语言中的权力和政治因素,因此他的话语分析必然沦落为一种语言游戏。
葛兰西把语言作为统治阶级建立文化霸权的重要方面,从而开启了语言的权力维度。葛兰西区分了内在语法和规范语法⑤。所谓内在语法就是内涵于语言结构自身之中人们借以说话但却并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语法,而规范语法则是人们总结提炼出来用于指导学习的语法规则。在葛兰西看来,规范语法的形成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逻辑选择,而是内在语法相互竞争的结果,是政治选择的必然。因此,这种规范语法就是强加于人的,语言问题就不是纯粹的文学或修辞学问题,而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因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统治者总是通过对语言习得的控制,来达到控制被统治者的目的。由此可见,语言背后也存在着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 或 政 治 无 意 识,语 言 习 得 也 就 成 为 实 现 霸 权 的工具。
布迪厄发展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人们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包含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当交流所涉及的行动者在相关资本的分配中占据着不对称的位置时,情况就更是如此”⑥。语言本身就是权力场域的一部分,语言关系最终还是一种符号权力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就以一种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福柯进而认为包括语言在内的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都与权力密不可分。因此,格罗斯认为:“话语模式必然是使用它的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编码。”⑦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交往维度方面,巴赫金提出了语言的对话性,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只有通过平等对话才能够达到交流的目的⑧。哈贝马斯则借用日常语言学派的言语行为理论建立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并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这一转向具有自身的演进逻辑,其内因在于批判理论克服自身缺陷的需要,而外因则在于语言学转向的影响。
二、批判理论交往转向的演进逻辑
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它过度强调否定性和批判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特点也为其发展带来了危机。哈贝马斯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相同的经验视野出发来把握文化现代性,同样充满了强烈的善感性,使用的同样也是狭隘的视角---从而使得他们对交往理性的足迹和现存形式视而不见。”①正是这种视而不见使他们的批判理论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现实发生变化之后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而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在矛盾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及时调整,致使批判理论在7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因此,对批判理论及其立场和方法进行适时调整,从而将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就成为批判理论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其继承者所面临的主要工作,而语言学转向为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福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深入剖析发现了社会文化和历史背后所隐藏的微观权力的运作逻辑和社会斗争的潜在方式,而哈贝马斯提倡在平等的主体之间通过言语交往而达成共识来消解或缓和社会权力的运作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建构一种理想化的和平世界。换言之,福柯采用了行动理论的“斗争”范式,而哈贝马斯则采用了行动理论的“相互理解”的交往范式②,其中语言交往取代了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并用语用学对社会批判方法进行改造,由此使批判理论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理论形态。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交往理论始于洪堡。洪堡语言学中所包含的对主体自我关涉的反思以及对主体间的相互活动的认识,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哈贝马斯所直接批判的则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不同于洪堡语言学所包含的主体间性的因子,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则在反思主体性,把主体消解在了语言的语法结构之中。
索绪尔关注语言的静态结构,而不是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言语,因此,从结构语言学中自然不可能发展出交往理论。相反,语用学转向为走出结构主义的藩篱开辟了道路。如哈贝马斯所言:“是语用学转向促成了主体哲学的决定性变革。
语用学转向认为阐释世界的语言优先于生成世界的主体性---阐释世界的语言是一切理解、社会合作以及自我调节的学习过程的媒介。这样就使得长期以来宗教语言一直在言说的那些必需的基本概念第一次得到了解放。”③传统的主体性哲学把研究人类主体的精神、情感和意志作为对象,而语用学带来了主体性哲学的巨大变革,因为语用学认为语言是人类用以理解、表达和阐释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得以自我学习,乃至形成人际交往的媒介。结构主义语言学忽视了主体性的存在,行为主体的语言能力和交往意愿等被排除在了语言学研究之外。这是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将研究重心置于语言的共时结构造成的。因此,要超越结构主义语言学就要改变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把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言语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此,哈贝马斯试图建立一种普遍语用学,从而为“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提供理论基础④。哈贝马斯把他的普遍语用学构想进一步拓展为交往行为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批判理论。
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学术界之所以对语言问题如此关注,原因在于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①。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是哲学界的一场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