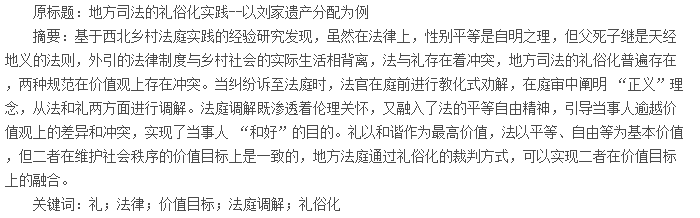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中国基层社会的状况与费孝通在半个多世纪前所描述的已大不相同,但许多乡村地区仍然保留着礼治社会的特征。中国现代法制建设是由外而内(法律移植)、由上而下(官方推动)进行的,因此还承担着匡正风俗的功能,礼受到否定和批判。经过数十年的普法运动,国家法律在生活中已广泛发挥影响,但从秦始皇开始,中国有数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1](PP.8-48),礼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日常生活。
法与礼有深刻的价值观上的冲突。因外来的法律在短期内很难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中国社会存在着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普遍分离[2],即便法律已发挥影响,冲突也是避免不了的。在乡村社会中,法与礼的冲突尤其明显,表现在司法领域,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地方司法的礼俗化普遍存在。在地方司法中,礼仍然以两种方式扮演着规范角色,一方面,礼以“情理”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影响司法审判,另一方面,礼以习惯规则(如父死子继)的方式进入司法程序。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虽然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之中,但原有的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地留存在广大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因为现行法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中国原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3](P57)。
如何认识地方司法礼俗化的实践价值,学界还没有共识。关于法与礼的冲突问题,已有的研究几乎都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结构中宏观地论述二者的关系,往往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例如,朱苏力认为,现代性法律制度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又禁止那些与熟人社会性质相符但与现代法治相悖的实践,这使村庄秩序处于极其艰难的地位[4](PP.23-37)。范愉研究转型时期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后指出,中国法制改革的速度过快,尤其是诉讼程序和司法改革的过快,导致了法律和社会之间差距越发加大,由于国家对习惯采取一种强势和无视的态度,习惯的作用已经显着降低且缺乏正当性[5](PP.28-29)。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研究材料主要来源于文献,如法院的判决书等,缺少乡村社会的实际经验;二是这种视角遮蔽了法与礼的冲突和地方法庭实践的真实情况,无法形成对地方司法礼俗化的实践价值的认识。例如,在法与礼相冲突的具体场合如何?
法官是如何运用法律条文的?依据何种规范做出判决?礼如何影响法庭的行为?地方司法的礼俗化对现代法治建设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调查方法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通过深入调查西北乡村一个遗产分配纠纷,在法庭这个具体场景中展示了法与礼的冲突以及地方法庭的裁判过程,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在甘肃省H县刘村,村民刘今明的遗嘱引发了一场冲突。刘今明生于1940年,1974年刘今明的妻子病逝,夫妻二人育有1子(刘东)3女4个未成年孩子。同年,H县王村妇女李燕的丈夫遭遇车祸身亡,夫妻二人育有1子王斌1女王慧2个未成年的孩子。
1975年,刘今明和李燕重新组建家庭,并生育1女。因违法计划生育政策,刘今明被H县D镇医院开除。
1980年初,夫妻二人在D镇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每年约有3万元左右的纯收入。刘今明长期住在诊所,一年中回家几次,李燕承担了所有的农活并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7个孩子。王慧于1995年大学毕业后成为该省L市的一名法官,王斌初中毕业后辍学。
2007年刘今明公开一封遗嘱,内容为:存在D镇信用社的全部30万人民币给儿子刘东,诊所里的全部药材药品给刘东,在D镇信用社给李燕开一个户头,存入1000元现金。
二、遗嘱遗产分配引发的争议
此遗产分配所引发的争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产争夺,其核心是法与礼的价值冲突。个案中的刘家是一个再婚家庭,家产纠纷主要在王斌和王慧这对亲兄妹之间展开,他们的母亲李燕站在王斌一边。这场“争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财产争夺,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展现的是人物不同的社会化历程、不同的家庭地位,以及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同时,不同家庭成员的意见也随着事件的发展过程逐渐明晰起来,或者说家庭成员的意见分歧是推动事件进程的动力。
父死子继在礼的观念中是天经地义的法则,女性既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也被排除在继承关系之外。滋贺秀三在论述中国家庭的继承现象时说,中国人的继承问题,继承的对象是人,继承的是人格,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后继人,代替他继续生存,老而奉养,死后祭祀,因此,中国私法上的继承首先所继承的是人格,其次是象征人格连续关系的祭祀,人格连续的实际效果就是财产转移到儿子手中[6](P97)。女性被排除在继承之外,这也是宗族观念的必然逻辑。滋贺秀三分析认为,社会性的宗属关系决定财产继承权,女性在自然意义上属于父宗,在社会性宗属关系上则属于夫宗,且结婚以后其人格被丈夫吸收[6](PP.15-16,P109),这样一来,在社会规范上,女性必然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也被排除在对父亲和丈夫财产的继承关系之外。瞿同祖的研究也表明,在传统宗族观念中,“姑虽属于本宗,但嫁后属于异宗”,古代的法律根本否认妻有私产,也否认妻有继承夫财的权利[7](P2,P114)。个案中的李燕对自己的身份极其认同,即使她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有“权利”得到遗嘱中涉及财产的大部分时,也没有“非分之想”,认为女人嫁人就是为了“穿衣吃饭”,自己没有能力挣钱,丈夫的财产没有自己的份。
宗族关系所产生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规范,就是异姓不养。异宗则异类是宗族观念的基本信仰,所以继父绝不是父亲,继子也不是继父的继承人[6](PP.476-478),这是宗族观念的必然逻辑。现行《婚姻法》和《继承法》没有规定继父母对未成年继子女具有抚养义务,从立法精神上看,也确实贯彻了“异姓不养”的原则,继父母抚养继子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义务。不过,法律规定一旦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抚养关系,就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一般规定,即产生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而不考虑他们之间是否有抚养、赡养的真实意思。《婚姻法》和《继承法》的规定实际上将形成抚养关系作为形成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当抚养关系形成后,继子女就有权利继承继父母的财产,也有义务赡养继父母。王斌和王慧自幼生活在刘家,李燕和刘今明共同抚养了双方的子女,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属于法律上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关系的情形,王斌和王慧依法对刘今明的遗产有继承权,在遗嘱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主张法定继承情形下的继承权。不过遗嘱公开后,异宗之子王斌不仅不依“法”否定遗嘱,反而极力维护遗嘱的合法性。王斌自幼辍学,未曾离开过村庄的经历,能够给他的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家庭和村庄这种最基本的初级群体是一个人的自我观念发展的摇篮,初级群体里人们密切的交往和合作为个人的社会性奠定了基础,使个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认同。
从法律的角度看,该遗嘱无效,应当进行法定继承,这是王慧坚持为“权利”而斗争的依据。王慧1991年考入L市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法学院,1995年大学毕业后进入L市中级人民法院担任民事审判工作。虽然幼年也生活在刘村,但在大学里接受的法学训练以及法官的职业生涯使得王慧与王斌在对待遗嘱上产生了分歧。王慧没有主张自己的遗产继承权,不过与哥哥王斌不同,她依据法律否认遗嘱的合法性并极力争取李燕的财产权。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因为刘今明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而导致遗嘱无效,那么就应当进行法定继承,首先对30万元进行平均分割,然后对刘今明的15万元进行法定继承。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下,李燕能得到15万元里面的大部分财产。王慧的意见就主要在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面,在她看来,李燕和刘今明的人格是平等的,他们对家庭财产的贡献也是平等的,虽然李燕干的是农活,没有人给她付工资,但不能否认干农活的价值。
为“权利”而斗争的思维遵从的是法律形式主义逻辑。现行《婚姻法》和《继承法》以普遍原则为前提,以保护权利为目的,采取的是形式主义的法律逻辑。孟德斯鸠称法官是叙述法律的嘴巴,韦伯“自动售货机”[8](P354)的隐喻,都揭示了法律形式主义的特征。法律形式主义坚信法律制度是一个封闭的逻辑自足的概念体系,它的最基本要素为机械的演绎推理和一个封闭的规则体系。[9](P11)
在法律适用上,法律形式主义主张由专门受过训练的专业群体从逻辑、语言等角度严格适用法律,不需要道德、习惯等的支持,也无需考虑案件的具体社会背景;只关注法律的形式和结构,不管它的道德内容和社会内容;只考察法律制度,不考虑法律外因素。按照韦伯的描述,就是借助于法律的逻辑体系,任何具体案件的判决都可以从抽象的法律前提推导出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被解释和运用的,法官也是被这样要求的。
接受过现代法学训练、在课堂里学习了西方法律的王慧,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知识体系,很难对地方的礼俗产生同情理解。韦伯论述法律形式主义思维时指出,大学里“学问式”的训练,使法律规范具备了理性、系统的性格,极少有具体的内容,法律人的思维便大幅度地从利害关系人的日常需求中解放出来,法律的适用,只是纯粹逻辑的贯彻[10](PP.182-189)。接受过学院式法学训练的王慧,以西方法的先入之见来评价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自然就会产生冲突。
三、起诉与调解
随着遗嘱人刘今明死亡,王慧与王斌的冲突升级,王慧将继承人刘东起诉至D镇法庭,要求法庭依法判决遗嘱无效,保护李燕的财产权。
基层法官依然遵循息讼的宗旨,试图将纷争消灭在诉前。中级法院的法官到乡镇法庭来告状,让D镇法庭庭长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他仍然坚持了自己对诉讼的看法:
在咱们这个地方,起诉到法庭的主要是离婚案子和邻里纠纷,这些事情不能只从法律角度考虑,完全按法律办反而不好。首先要尊重当地的乡土人情,还要有心理战术,在程序和实体上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解决矛盾还不能伤了感情。一场官司十年仇,你已经是公家的人了,这件事还是要妥善处理,要考虑到你家人的处境。不过我也是法官,不能劝人家不要打官司,你可以把起诉状放在这儿,先找村长书记调解一下,如果一个月内调解好了,你就来撤诉,如果一个月内不见你撤诉,我就给被告发个传票。
因王慧坚持要为“权利”而斗争,庭长在等待了一个月之余后,给被告刘东发了传票。这位庭长庭前的做法实际上是教化式的调解。
D镇法庭的这位庭长,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长期生活在D镇,其庭前的言行显示出其角色是年老有德的长者而不是法官。作为乡村精英,庭长自动承担起了教化和维护社区秩序的功能,此庭前调解明显属于“教化性调解”[11]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庭前调解。如果从司法技巧的角度来看,庭长的做法也是一种息讼的策略,颇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意味。
基层法官是地方社区的一员,法庭行为受地方礼俗约束,体现出“入乡随俗”的特点。基层法官对地方礼俗有极高的认同度,他们处理社区纠纷常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情理调解,法律只能发挥参考作用。
D镇法庭的审判没有遵循法律程序,庭长直接用一种不同于正式法律概念体系的知识和智慧对案件进行调解: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确实有夫妻共同财产的说法,遗嘱人首先要把夫妻财产分开。不过国家这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完全按照国家法律办也不太合适。国务院总理来咱们村子里了,他是大家的总理,可谁跟国务院总理熟悉?都不熟悉。这就跟对照具体法条来解决咱们的问题是一个效果,所以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所以这个遗嘱,我看就不管它有没有效力,这只是个形式,我们以公平为宗旨,达成一个你们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因为原告是庭长的“上级”,庭长用村民对总理的熟悉程度来隐喻村民与法律的关系,巧妙地利用他在基层司法实践中获得的智慧化解了面对“上级”的尴尬。
当庭长说完上述话时,原告表示不接受调解,庭长则继续顽强地调解。庭长通过向当事人阐明“公平”的涵义,再次将双方当事人引入调解机制中,从中可见地方法官最关心的不是权利的保护,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纠纷,法官也为帮助双方达成和解做了认真的工作。
咱们是国家贫困县,村民都过得很苦,他们的女人也跟着苦,不是每个村民都像刘今明那样能挣钱,这是个特例。如果刘今明与其他男人一样穷,你(李燕)的生活就会比你实际过的辛苦很多;因为有了刘今明,你过得比一般女人好很多,这确实很有福气。
庭长的上述话,可以说是对“正义即应得”的一种具体阐释。“应得”不仅意味着权利义务的对等,也意味着权利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规定。父死子继、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等,在刘村当地是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性别平等原则已经得到贯彻,妇女的家庭劳动是有价值的,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但相比较而言,父死子继、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是中国人长期形成且稳定维持下来的生活方式,是生存理性的体现。法律在乡村社会并没有被适用的经济和道德基础,村民极其不熟悉法律的理念和价值观。地方法官虽然也学习法律,但他是乡村社区的一员,不可能违背社区的正义观做出判决。
经过法庭努力调解,原告自愿放弃诉讼请求。
走出法庭之后,被告主动给了原告3万元,纠纷彻底平息,双方当事人和好胜当初。
D镇法庭的裁判方式与传统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处理是传统中国人处理纠纷的基本准则和理念[12](PP.123-126),尽管从明清到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但法庭调解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社会长期延续了下来。面对纠纷,法官将事实的判断和对社会秩序的考虑放在首位,而不是从普遍规则出发来保护权利,即法官首先考虑的是具体事实的性质,之后才确定解决纠纷的方式和规范,与西方社会的裁判方式完全不同。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之间联系密切,确有必要将和谐的人际关系放在首位考虑,尽可能以不分胜负的方式解决争端,避免人们之间产生积怨。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结论是:法与礼的价值相冲突,但二者的价值目标相一致,这也是地方法庭所追求的。
“礼之用,和为贵”,礼以和谐作为最高价值,体现在纠纷解决机制上,礼治的要求是通过调解实现双方当事人“和”的价值,并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秩序等是法最基本的价值,在纠纷解决机制上,法律制度通过界分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平等、自由等价值,并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由此可见,法与礼的价值有冲突,但二者的价值目标一致,法庭调解可以选择适用礼规范或者法律规范,实现法与礼在价值目标上的融合。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D镇法庭调解既渗透着伦理关怀,又融入了法律的平等自由精神;既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又引导当事人彰显人性中的真、善、美,促使当事人逾越价值观上的差异和冲突,最终实现了和谐的秩序,其法律思维方式是一种实用的道德主义[13](PP.1-36)。
地方司法的礼俗化现象有深远的价值基础作为支撑。滋贺秀三认为,在传统中国,情、理、法互通互融,法律使情理实定化并赋予其强制力,情理与法律的关系,就像大海与冰山的关系。礼顺人情,且主要体现在国法当中。法律条文在适用时往往要通过情理加以解释或者变通。因此,礼与法律、情理是互相亲和的,三者协同运作,并构成了法律条文的真正来源。与此相适用,裁判的公正性主要在于当事人的承认,而不在于有明确稳定的裁判规则。在裁判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通过交涉谈判,在“情理”范围内终结案件是最理想的结果[14](PP.39-40,PP.83-87)。黄宗智研究清代的司法实践之后,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他说,在有关小农生活的领域,法律的立场显示了始终如一的道德姿态,父母官的隐喻包含在《大清律例》等法律之中,法律和民间习俗都体现了“父子家庭秩序与生存伦理”[15](P69)。由于国法、天理、人情互通,传统中国人知礼则知法,无需在乡村社会之外学习国法,只要按礼俗行事,行为就是适宜的。
在几千年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法不外乎人情”的法观念和礼俗化的裁判方式在乡村社会一直保留了下来。
地方法庭借助现代的形式正义实现传统的实质正义。全国地方法庭是国家法律普及到乡村社会所必须的形式工具,也属于法律形式主义的一部分———借助统一的场所、统一的仪式、专业的方法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适用的普遍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乡村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是传统的,在地方法官的观念中,最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是立足于当地、当时的一般价值观,作出合乎情理的解决。
韦伯早就指出,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原本都是非形式理性的[10](P232),没有普遍的原则和严密的逻辑,法律判断首先考虑伦理或政治的要求。作为现代社会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维护法律的形式,履行一定的仪式,地方法官正是借助现代的形式正义实现了传统的实质正义。
法律的形式化代表了法律制度发展的方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也不掩饰并不能通过中央集权的代理人安排好每一种法律制度,相反,不仅给地方法规而且给传统习惯留下相当可观的调整地方利益的余地。”[16](P153)基层法官把法和礼相结合,也是一种积极的维护社会秩序的途径。这里也许存在两个问题:礼是不是习惯?礼进入司法的合法性前提是什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滋贺秀三研究发现,在中国,没有与情理不同而单独存在的习惯法,情理就是习惯的价值判断标准[17](P14),礼多数与理重合,且限于身份法的领域[14](PP.40-65)。再通过观察司法实践,可以判断,礼作为一种习惯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就习惯进入司法的途径而言,“民事问题,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习惯,无习惯依法理”是一种常识,我国《物权法》、《合同法》中都有规定。不过“无法律从习惯”模式强调习惯只在法律模糊、法律有漏洞时补充适用,对于习惯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习惯与法律冲突时该如何处理,国内少有研究。我们认为,在习惯与法律冲突时,如果适用法律会使社区秩序和社区共识遭到破坏,从而使判决不具有可接受性,那么,习惯就应当替代法律而得到适用。总而言之,法律以外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也会形成社会秩序[18],地方法庭为习惯和法律的实际运作提供了一个可以进行互相竞争和渗透的场域[19],其裁判方式是从另一个方向上构筑社会秩序的人类文明现象。
村落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前, 在社会改革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一方面是社会的整体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村落文化遗产面临着悄无声息的消亡。...
村落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当前, 在社会改革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 一方面是社会的整体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村落文化遗产面临着悄无声息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