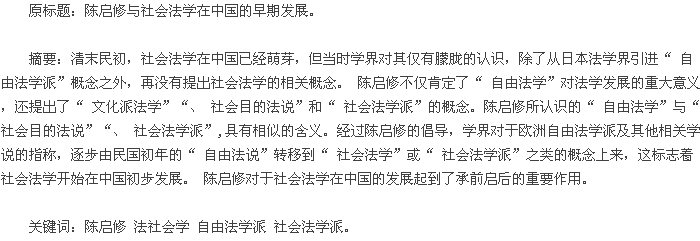
陈启修( 1886-1960),又名陈豹隐,字惺农,四川中江人。 学界所认识的陈启修,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更是作为“ 第一位翻译《 资本论》的中国学者”而扬名全国。 实际上,陈启修还是一位法学家。 对于社会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他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目前学界对陈启修的法学思想尚无研究,笔者不揣简陋,愿略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一、学术背景:留学日本与任教北大。
陈启修所学,并非专在经济学,对法律学和政治学亦有不少涉猎。 1907 年,陈启修赴日留学,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1913 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 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期间,他主修经济学,并对财政学有不少研究,曾在 1914 年翻译了小林丑三郎所着《 财政学提要》 . 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的最大贡献确实在经济学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法学学科体系是模仿大陆法系而来。 在大陆法系国家“, 对 Droit 这个字义的解释, 因为受到哲学派的影响,不是专指法律, 他们于法律的意义之外, 包含有理想的公正意义在内,其意义非常广泛,因为法律和政治、经济和关系非常密切,遂不免放在一起研究了”[1]48. 受此影响,日本大学的法科通常包含法律、政治和经济三门,这三门“ 不免放在一起研究”. 具体而言,三门之中的任何一门同样会开设其他两门的课程。 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是日本最好的法科,也是受大陆法系影响最深的法科之一。 陈启修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期间不仅学到了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受到过良好的法学和政治学教育,这一点当无疑义。由此可知,陈氏对社会法学相关知识的了解,来自于日本学界。
陈启修学有所用,得益于北京大学法科改革的契机。 1917 年,蔡元培入主北大,试图对大学教育进行全盘改革。 蔡元培主张大学的宗旨是“ 研究高深学问”, 对此前法科欠缺学术性和过于追名逐利,颇多批评[2]. 他先主张将法科划出,并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从而组建新的法科大学,北京大学则专办文理两科。 后因各方关系复杂而作罢,蔡氏转而探寻北大法科的学术化之路。 裁减旧有官僚式教员,延聘海内外法学精英,是其推进法科学术化的重要举措之一。民国初年,从欧美学成归来的法学精英为数甚少,留学日本学习法政的人数虽以千计,但能入东京帝国大学等名校者亦不为多。该年底,陈启修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返回北京。他这种出类拔萃的人才,正是蔡元培寻求的对象。于是,陈启修受蔡元培之邀进入北京大学法科任法本科教授,并被选为政治门研究所主任[3]76.
在蔡元培和法科诸教授的推动下,北大法科的学术化进程非常快,课程设置、教学风气也焕然一新。 1918 年 7 月,北京大学各研究所共同议决的《 研究所总章》中,就规定全校各研究所合作共办一种月刊,作为“ 发表及讨论各门研究之结果之机关”[4]. 蔡元培视《 北京大学月刊》为北大师生“ 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5]. 该刊对所载文章的学术性要求很高“, 以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着作”,绝不以无谓之文字填充篇幅[6]. 可见,《 北京大学月刊》 在其创办之初,就被视为北京大学的“ 学报”,颇有“ 研究高深学问”之意。《 北京大学月刊》 将文、理、法、工诸学科知识融为一刊,每期刊文并不多,基本上只发表北京大学教授和极个别优秀毕业生的学术论文。 以 1919 年 1 月的创刊号为例,仅刊文 14 篇,法科文章共有三篇,其中两篇的作者是陈启修。《 北京大学月刊》存续到1922 年,被北京大学新兴的四种季刊替代。 在其存续期间,陈启修共在该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十余篇, 是在该刊上发表论文最多的教授之一。 陈启修在北大及北大法科的学术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二、初识社会法学“: 自由法学”与“ 文化派法学”.
陈启修最早阐释对社会法学的理解,是在 1919 年。 该年 2 月,陈氏在《 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 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一文,阐述了他的法学发展观。
陈氏的法学发展观,带有一种进化论的兴味。他认为,一切学术的发达都要经过“ 事功”“、 事理”、“ 道义”和“ 人生价值”四个发展时期,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学无一例外。 根据这种学术发展的“ 四时期”理论,他对法律学的发展做了一种进化论式的解释。法律学发达的第一时期,将法律作为一种方便之术。“ 专重习惯,不尚成文,尊崇经验,蔑视道理”,法律仅有“ 维持事实之功”而无“ 创造事实之力”.
法律学的第一时期,只可称为“ 法律术”.法律学发达的第二时期,其特点是将习惯法变为成文法“, 法律术”变为“ 法律学”,法律与事实“ 相倚为重”,“ 法律维持事实,事实亦巩固法律”,法律的解释,最注重严格的论理( 逻辑)。法律学的第二时期,可称为形式法学时代。法律学发达的第三时期,则重在救第二期法律学的流弊。 因形式法学时代过于注重严格的论理,视成文法为万能法律,最终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第三时期的法律主张“ 成文法的自由解释”,注重“ 法律的实质”. 这一时期的法学,可称为自由法学时代[7].
自由法学学说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于法德等国,常被视为社会法学派的一个重要支派。 20 世纪初期, 自由法学说传到日本,而留日法政学生又将其传到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学界便出现了自由法学说。 先后介绍自由法学说的有:1913 年,上海《 法政杂志》
刊载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石坂音四郎发表在日本 《 法学协会杂志》的法学论文《 何谓法律学》的中译本[8];1913 年,上海《 独立周报》刊载了日本学者中田薰的《 法兰西自由法说》之中译本[9];1915 年,上海《 法政杂志》再刊石坂音四郎发表于日本《 法律新闻》的《 最新十五年间民法学说之变迁》的中译本[10]. 此间,陈启修正在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习,对石坂氏的学说以及日本法学界的动向不可能没有了解。 由此可知,陈启修关于自由法学说的理解,当来自日本法学界。
不过,陈启修并不认为自由法学说就完美无暇。 自由法学说的确能矫正形式法学的弊病,能够“ 发挥其维持共同生活之本质”,但是该学说“ 尚未注意人生之价值,谋共同幸福之增长也”. 他认为,“ 文化派法学”还要比自由法学说更高一筹。 文化派法学“, 谓法律当以人生价值为批判之基础,以人类文化之增进为归宿者也”.陈氏认为“, 人生活动之基础在社会,社会之根本在个人,而现今之个人又皆处于国家主权之下”.“ 人类文化”是一个高于“ 个人”“、 社会”和“ 国家”的概念。 故而“, 专重人权”“, 不足以言最近之法律”“; 偏重社会”,也不合于“ 近代思潮之干流”;“ 国家本位”和“ 国权万能”的思想,也是“ 偏倚之见解”. 所谓文化法学派,是“ 以人生价值为基础”,“ 既重社会之利益,复谋人格之发展,亦图国家正义之申张”“, 以个人人格、社会利益及国家正义为本位者也”[7]. 言下之意,文化法学派能够兼顾个人、社会和国家三者的利益。
从对“ 文化法学派”的解释中,不难发现陈启修对柯勒的“ 法与文明理论”的推崇。柯勒接受了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认为法对人类文明生活的进化中具有重大作用。法一方面维护已有的文明价值;另一方面促进新文明价值的实现。 每种文明必然有相应的法律准则,法或法律准则始终与文明有关。 法的内容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时一地的,会随着文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刺激人们从事创造性劳动,企图制定消灭它们的法律是愚蠢的。 但社会结合也是必不可少的,因而法律应谋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调和。 由于他主张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法律,主张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所以常被视为社会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1]97.
早在 1908 年,马德润就对柯勒的思想观点做过简要介绍,不过仅限于“ 法学之等于文明现象”的程度[12]. 陈启修对柯勒“ 法与文明理论”的理解, 要更深刻一些。 基于对法律学的以上理解, 陈启修认为,1917 年那些号称护法者的法学思想“ 斤斤于护法之形式,而置护法之实质于脑后”,不过处于“ 形式法学时代”的水平[7].
清末民初,学界对法学派的认识往往不出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推理法学派和比较法学派。即使偶有学者注意到“ 根据社会学因考法律之原理”的学派[13]和“ 自由法学派”,学界也未引起足够重视。陈启修则认为自由法学说要比“ 形式法学”的“ 进化”
程度更高。陈氏理解的“ 形式法学”具有“ 过于注重严格的论理”并视成文法为“ 万能法律”的特点,实指分析法学派。 这是中国法学界较早对自由法学之地位做出的肯定判断。 陈启修还进一步认为,法学将来还会从自由法学进至“ 文化派法学”.
三、阐释学说“: 自由法学派”与“ 社会法学派”.
1920 年,陈启修对社会法学的理解进一步加深。 该年 1 月,陈启修在讨论法律性质和法律变迁的问题时, 再次谈到了对社会法学的认识。 陈氏认为,法律不过是“ 社会生活之集合的意思力”,是为了达到“ 共同生活之目的”和维护“ 公共利益”而强行的“ 规则”. 其作用有二:一是“ 谋社会生活主体之法律上之平等”,二是谋“ 社会生活之安固”. 一方面,法律既然是社会生活的规则,社会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法律的内容也必须随之变迁。 如果社会生活已变而“ 犹墨守成法,不知变通”,就陷入“ 形式法学派”的通弊。 另一方面,法律固然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其变化当以“ 民意”为标准,而“ 民意”往往时时刻刻变迁不定。 法律必须具有安定性,不可以“ 今日一变,明日又一变”,否则便“ 踏于极端社会法学派之弊矣”[14].
结合陈启修在 1919 年提出的关于法律学“ 四时期”的理论,可知此处所理解的“ 社会法学派”,与“ 自由法学派”的含义有许多相同之处,甚至从“ 自由法学派”当中来。 同年 7 月,陈启修在《 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 何谓法》,在对法律性质的探讨中再次论及各派学说的特点。从中可知,陈氏对社会法学的认识已经趋于明晰。按照陈氏的理解,关于法之本质的学说,主要有六种“: 神意或天命说”“, 自然法说”“, 正义法说”“, 国民精神法说或国民确信法说”“, 命令法说”,“ 社会目的法说”[16]. 此处将“ 社会目的法说”与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观点相并列。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这在中国法学界尚属首次。
陈启修认为,社会目的法说发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纠正“ 命令法说”的“ 法律万能主义”观点,救“ 法律专制之流弊”;二是“ 受实验主义的哲学之影响”;三是“ 劳动阶级之自觉”[16]. 陈氏理解的社会目的法说,主张如下:此说谓法为手段而非目的;故所贵乎法者不在其形式,而在其内容及作用。 法者,社会共同生活之规则也,故尤当重其社会的作用及目的。 社会者随时随地,发达进步者也。 故法之内容,当然随社会为转移,而不必有绝对之真理。 故法可以人类之智的努力,随时随地创造变更废止之。此说之根本主张如是,故对于法之研究法,则取社会学的方法,而非难所谓法律学的方法,即注释的方法,对于法之适用,取不取论理的解释,而重自由的解释[16].
陈启修认为,根据注重方面的不同,社会目的法说可分为三派。 一是“ 心理学的”,主张心理力为社会现象之真因,法的真正基础在于法律意识。 二是“ 社会连带的”,主张法的基础在于社会的连带关系。 社会生活需要“ 协力”和“ 分工”,含有一种连带的性质,所以必须有一种规则来加以维系。 三是“ 实际的理想主义的”. 该派认为,如果专重“ 事实”,则“ 法将永无进步”,如果专重“ 理想”,法又不能有实效,所以既要有法的理想,又要“ 根据于社会之事实”[16]. 可以发现,陈氏所说的“ 社会目的法说”实际上至少已经涵盖了沃尔德等人的心理法学、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以及施塔姆勒关于法的理想的观点。 而这些观点,通常都被认为是西方法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陈启修也认为,社会目的法说的具体主张有不少过激之处。 一是过于重视法的内容。 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而不同于其他社会规则,在于法有一定的形式和强制力。 如果专重社会学的方法而轻视法律学的方法,则“ 不可谓当”. 二是过于重视自由解释“, 有失却法之安定性之虞,殊与社会上发生法律以求安固之原理相背”.
这也是陈启修所说的“ 极端社会法学派”的缺陷。陈启修称赞社会目的法学“ 注重法之目的及作用,实为法学史上最大之发见”. 其学说一出“, 法学大势,为之一变”“, 其先社会而后个人之根本观念,可谓得理之正”. 社会目的法说出现之后,关于法之本质的舆论,虽然尚有纷歧“, 然法以社会利益为目的,则已成各说共通之概念”[16].
依陈启修之意,社会目的法学大有异军突起,与分析法学、历史法学等固有法学派平起平坐,甚至取而代之的势头。 这是中国学界较早认为该学说是法学发展之趋势的论说。 清末民初,社会法学在中国已经萌芽,但当时的学界对社会法学知识仅有朦胧的认识。 除了从日本法学界引进“ 自由法学派”的概念之外,学界再没有提出社会法学的相关概念。而陈启修不仅肯定了“ 自由法学”对法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还提出了“ 文化派法学”、“ 社会目的法说”和“ 社会法学派”的概念。 在陈启修的观念中,除了“ 文化派法学”是法学未来“ 进化”的方向而外“, 自由法学”与“ 社会目的法说”“、 社会法学派”,其实具有相似的含义。 此后,中国学界对于欧洲自由法学派及其他相关学说的指称,逐步由民国初年的“ 自由法说”转移到“ 社会法学”或“ 社会法学派”之类的概念上来。这是社会法学在中国初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事实上,在陈启修之后,紧接着就有李炘、吴经熊、陈霆锐、张志让等一批杰出的法学者对社会法学派做了更为详细的阐释,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启修对于社会法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晓楼。法律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蔡元培。大学校长蔡孑民就职之演说[J].东方杂志,1917,14(4)。
[3]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17.
[4]北京大学。研究所总章[N].北京大学日刊,1918- 07- 16.
[5]蔡元培。月刊缘起[J].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6]北京大学。编辑略例[J].北京大学月刊,1919,1(1)。
[7]陈启修。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J].北京大学月刊,1919,1(2)。
[8]石坂音四郎。何谓法律学[J].达人译。法政杂志,1912,2(11)。
[9]中田薰。法兰西自由法说[J].逐微译。独立周报,1913(26)。
[10]石坂音四郎。最新十五年间民法学说之变迁[J].铸夫译。法政杂志,1915,5(5)。
[11]徐步衡,余振龙。法学流派与法学家[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
[12]可烈亚。法学哲学与世界法学史[J].马德润译。法政介闻,1908(2)。
[13]户水宽人。法律学纲领[J].译书汇编,1902,2(1)。
[14]陈启修。法律与民意及政治[J].评论之评论,1920,1(1)。
[15]上杉慎吉。非自由法说[J].天顽译。法政杂志,1913,2(10)。
[16]陈启修。何谓法[J].北京大学月刊,19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