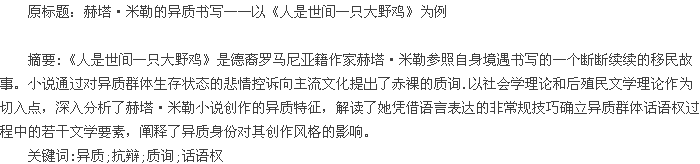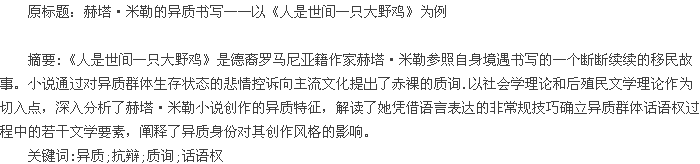
2009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德裔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ller )的作品《人是世间一只大野鸡》(Der Mensch ist ein grober Fasan auf der welt)创作于 1986 年。 与其他早期作品相较,《人》在生动地展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才华的同时更加突出地展现了对流亡主题的反抗特写。 由于译介的关系,这部作品被我国读者接受较晚,然而部分国内学者仍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关注,先后考察了作品中的文化杂糅现象、文学乡土性、政治话语权、隐晦虚构及诗意表达等方面的文学特征,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这位非主流作家的认识,但就小说中所表达出来的“异质”抗辩内涵及影响方面的研究尚少涉及,本文重点挖掘了赫塔米勒小说创作的这一特点,深入探讨她通过移民事件前后经过的描述为自己以及所有受到齐奥赛斯库时期罗马尼亚政府排斥的社会群体提出的抗辩,并在此基础上以《人是世间一只大野鸡》的片段分析为例阐述作者的异质身份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
一、异质身份的揭示
“异质(hétérogène)”一词常用于生物学领域,指那些本质与周围事物完全不同的物质。 20 世纪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从社会学角度将其特征定义为“他们是‘不能同质化的’。同质的事物可以构成秩序,构成生产活动,而异质的东西将被‘排泄’。反过来,同质世界只有不断吸收和转换异质世界,使其‘同质化’,才能维系同质世界的存在。”
(1991:99-100) 巴塔耶的这段描述反映了社会对异质存在的两种态度:一是排泄,二是同化。 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 即异质之所以被称为异质正是因为它的不可同化性, 所以它是不可能被同化的,所谓“同化”只是理论性地存在,实际上异质只有一种出路就是被彻底地排泄掉, 以保证同质社会的正常运行。
《人是世间一只大野鸡》恰恰集中体现了这一异质被排泄的过程。 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 但是从头至尾都没有片言支语交待为什么要移民, 只是说温迪施一家焦急地等待着当局同意他们去国外的许可, 越来越多的罗马尼亚邻居离开了村庄,而他们还在漫长的等待中,后来女儿阿玛丽决定用肉体换取当局的公章, 直到故事结束始终也没有告知是否获准离境。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Michael Blau)曾指出 “异质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 而禁止与某个群体成员进行互相交往的歧视行为将导致阶层群体的流动,”(1989:78) 我们注意到《人》创作于赫塔米勒迁居德国的前一年,主人公温迪施和女儿一心想移居海外的念头很可能正是赫塔米勒真实思想斗争的再现, 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可融合性,打算主动疏离,但是处境不允许她逃走,逼迫她自我同化,去做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她对此感到无助,却又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好有意不谈及这个问题,然而她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一个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徳裔作家来说,特殊的身份和成长压力造就了她精神上双重的无所寄托。作为一个罗马尼亚人,她因曾是纳粹的子女而受到歧视和监视,失去了内心的平静和人格的平等。作为一个德国人,她又受到东欧语言和文化的熏陶,她虽然会讲德语, 但是她的表达显然在有意无意地对抗着繁复阴郁的母语,民族、祖国和家乡在她的信念里缺失了确定的涵义,代之以具体、简单、迅捷地直抒胸臆, 生活在她的笔下是一连串反抗的思考和行动,也许互不链接,但却是异常的真实,涵盖了一切“隐而未言” 的东西。 (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 2010: 55)正如罗宾·科翰(Robin Cohen)所言:“对个体创伤事件的记忆有助于离散者通过想象积极构建真实存在的家乡的真实样貌。 由于这种理想化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处境的根源归结为一种充满敌意的且被主动行为实施的迫害的结果”(Global Diasporas,1997:125-126),米勒的异质状态是在不平等的社会压力下被动形成的,她所谓的“隐而未言”即是她被社会异质化后的自我抗争与辩白, 对移民避而不谈不是因为不热爱自己置身的国家、 也不是因为理由的本身不可言说, 而是痛失主体身份后的一种无可奈何,她用“沉默与迫害教会我写作”(Herta Miller’sLife and Writing, 2010: 57 )来控诉异质身份对她的影响。
二、异质群体话语权的确立
苏迪·米萨(Sudesh Mishra)揭示了被异质化的群体在意识领域的普遍特征,她指出“离散者通常较为深入地关注那些使其陷入离散境地的集体意识,他们往往沉浸在家乡与寄居地的选择性踌躇之中,将意识深处的记忆以表格形式罗列总结, 或通过诸如绘画、音乐、电子创作等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生产表达形式验证暗藏在其意识深处的主张, 这使他们更深程度地陷入了社会组成与文化生产的纠结之中。 ”(Locating Diasporas,1996:108-128)作为异质化个体, 米勒体会到如何被同质世界排斥的痛苦,她被自己熟悉的社会隔离,在焦虑中寻找自身的价值, 试图明确建立所属群体的话语权。
1973 年米勒曾就读于罗马尼亚着名的蒂米什瓦拉大学,大学所在地靠近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文化和教育都比较发达,许多居民都会讲三种语言: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丰富的语言环境为米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养料。 她甚至能够像讲德语那样自如地运用罗马尼亚语, 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份得天独厚的无价之宝。 她本人也曾坦诚地认为在罗马尼亚学习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的成长经历对她的写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 米勒经历了大量的文学体验和尝试并从中提炼出清晰明确的个人创作理念,即“艺术是反抗的特写”。 (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2010: 96)为了实现这个宗旨,她从形式到内容都做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在叙事技巧上,她采取了超越文字的方法,通过精妙的细节、混沌的时间、虚构的惊愕以及旁白的宣泄混杂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奇异的和声, 并恣意地放纵它们在心灵的伤口上弹奏平凡而压抑的神经, 指使它们到生活的场景中拿捏病态思想的延伸,她的文字与其说是写作的工具,不如说是意识的抽象裸现, 每一个主题之下的小小篇章都像是一幅充满奇思妙想的立体画, 尽管它的格调总显得忧郁低沉, 但却在光线和角度的协助下不断地暴露出灵魂对现实的种种质疑和讥讽。
比如“针”和“大丽花”两段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件:细木工的母亲死了,她的棺材就停靠在儿子起居室的一角,此时,细木工并没有表现出对母亲的追思和悼念,而是在和妻子纵情嬉闹。时空错乱间又回到母亲去世前, 她正提刀砍去院子尽头一株盛开的大丽花,在她看来这花早该完蛋了,可它没有脱落,于是她用刀子帮它结束残局, 然后她用刀子在地上挖了个洞,把花埋了起来。接下来她又去井里提回一个冰镇的甜瓜,用尖刀挖出红色的瓜肉,大口地咀嚼吞咽着,红色的汁水淌了一身,她还在边吃边抱怨着夏天太热,只有这瓜能让她凉下来。 葬礼结束后,儿子对邻居说甜瓜纯粹是个借口,大丽花才是她的灾难,而女邻居则强调大丽花是一张脸。(133)在这段时空混乱的叙事里, 精巧的细节描写将母亲与儿子之间难以磨合的种种矛盾暗自隐藏起来, 文字的表面看上去好似精神病人的絮语, 代表作者眼中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 内容不衔接,逻辑不通顺使语言的传统表达功能几近丧失,一片狼藉的符号中仅存若干可以用来连接表象的蛛丝马迹,将读者引领到作者想集中展现的心理现实。 棺材里的母亲无法接受儿子对她的疏离,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了挂在椅子腿上一根牵着灰色线的针尖晃来晃去;她的遗像惨淡地露出垂死的微笑;还有她砍掉的大丽花以及血红的甜瓜瓤和流淌在手臂间鲜红的汁液。 (141)这些普通的不能再平常的细节描写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立于文字之上表达了超乎文字的意义:生命在无奈间的抗拒总有它独特的表达形式,无论多么超乎常理,它总是存在着的,而只要它是存在的,就应该受到世人的理解和关照。
维亚·米萨(Vijay Mishra)认为“离散者希望通过护照确认其市民身份,然而,身体样貌的区别又将其排除在单一种族政治认定标准之外,所以他们确定身份的愿望遁入对‘第三时空’的想象之中。 所有的期望都驻足其中,时空脱离了现实的一般意义的存在形式变得虚无散碎。 ”(The Diasporic Imaginary,1996:189-237)。 《人》中时间的混沌使小说呈现出令人无法忍受的迷茫的局面,主人公温迪施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在毫无生机的境地里怀着一个虚妄的希望打发日子,时间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记录的准确性,年份和日子被随便地拆解,两年也只有两百二十一天,意义在数字间消失,等待变成了无休无止的煎熬。 混沌的时间不再是虚拟的概念单位而是一种内心风景的参照物,它让我们看到了“每天早晨,当温迪施形单影只地骑车穿过街道奔向磨坊的时候。他都数那个日子。他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前数年分。 当自行车驶过第一颗白杨树,径直驶向那同一片洼地时,他数日子。 而到了晚上,当温迪施锁上磨坊门的时候, 他把年份和日子再数一遍”“温迪施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数到两年,在白杨树前面那片洼地里数到两百二十一天”。 (97)米勒非常敏感地抓住了时间这个叙事要素,象摆弄魔方那样把它翻转叠挪到希望放置的空间,以配合整个立体图形的需要。 人的思想与时间形成了一对抗力,互不让步、永不妥协地僵持着又彼此塑造着。 仿佛两个相近质量的天体在抗衡,两种意志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关注和表现。
虚构是小说创作的常规艺术手段,但在米勒的笔下,它用来编织叙事的功能消失了,代之以惊愕。“黑斑”一开始是写实的场景“橱柜是一个白色的正方形,床是白色的边框,那之间是墙上的黑斑”, “挂钟在壁炉旁留下一个长长的白色斑痕。 时间就挂在壁炉旁边。时间到头了……时间没有指针。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221)但是随着时空和光线的变化,这块黑斑被异化了“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时间拥挤着从白色的斑痕里溜走,顺着墙壁掉落。那黑色的斑痕就是其他房间里的地板……地板将颜色冲到房间的墙边,其他房间里的时间涌进来,黑色的斑痕一起游动……它们在靠近,在触碰。它们沿着自己那瘦长的裂痕落下,他们变得沉重,而大地将破碎……温迪施张开嘴。 他觉得它在脸上长大, 那个黑色的斑痕。 ”(225)米勒借助光线的变化将时间虚构成鬼魅般的阴影,时而攀爬在墙壁上,时而流动在角落里,时而恶兽般吞噬周围的一切,时而狞笑在人的脸上。
随着米勒笔触的延伸,惊愕不断地侵扰着人的感官,最终汇聚成古典悲剧落幕时那种无以偿付的凄凉和极具警示力的庄严。 温迪施脸上的黑斑其实是长在心里的, 一种空洞的未来耗尽生命分分秒秒的隐忧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意志最容易被吞噬,米勒认识到这个危险, 于是她结文字为鞭绳不断地抽打着日渐麻木的神经, 使他们在惊愕间保持清醒的抗拒。
在被异质的世界里有些痛苦是直接而鲜明的,但更多的是不便讲明的, 米勒使用旁白对此加以宣泄。 皮革匠的儿子因为参加罢工被送进大山里的集中营,他去看儿子,回来对温迪施说他在一家玻璃工厂工作, 谈话间他似乎一度忘记自己撒的谎又提到了那个集中营,甚至某个政治犯出了车祸被撞死,最后他又讲到墓地, 讲到了儿子让他带给母亲的那个小盒子, 可是这盒子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就是找不到。 这段叙述里皮革匠的妻子一面倾听丈夫和温迪施谈话,一面担当着旁白者,为丈夫的谎言遮掩“山区应该很不错,就是太远了,我们没法去,鲁迪也回不来”,然而,儿子的死作为一种伤痛是很难掩饰的,尽管不便明示,但她还是找到了宣泄的对象“这鸡蛋太老了,打出来的蛋液有点儿苦”。 当丈夫起身试图出示儿子带回的“礼物”,她极力配合道“我们会找到它的”,(276) 事实上, 那个礼物是儿子空空的骨灰盒, 怎么能够示人呢。 掩饰构成了旁白者讲话的动机,小小的尊严在掩饰中似乎得到了保护,实际上却袒露出更深层次的痛苦。
三、异质情感的非常规表达
威廉·萨弗兰(William Safran)认为“通常侨居在国外的少数群体只是部分地被寄居地所接受,而祖先的家园作为心中的神话才是他们能够最终获得满意的安全感的归宿。 种族意识和孤独感并行存在于他们的观念和社会联系中”(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1991:83-99)对于米勒而言,既不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信仰的支撑,又不被寄居地的法律认可,危机感和孤独感成为了她潜意识里最想摆脱的现实。 于是她选择了机械地拼贴来书写人与环境的永久性疏离。 “温迪施朝马路望去,草地在路的尽头冲进了村子。有一个人在尽头处走着。那人行走在草丛里像一条黑色的线,突进的草地将他托起在大地上。”(155)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景物被完全倒置了,人失去了能动性,受到了环境的摆布,无力挣扎,被迫沦为陪衬物。 原有的自然和谐的或者说是合乎常理的主次关系在这里变得生淡冷漠,完全一副被强大的外力硬拉进来才不得已凑在一起的样子, 路、草地、 村庄和人之间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排斥与抗拒仿佛永恒之力在诸多因素间僵持着。
如上文所言,异质者一旦意识到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必然会积极主动地参与重新建构自我的努力之中,通过对特殊处境下灵魂扭曲度的凝视,剥离虚假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展现鲜活生命的诗意存在,从而确立自我的崭新价值,但是由于要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发出的呼喊注定是无法等到回应的。 米勒采用意境的比较、转换和抽取来表达这种绝望的思想和浓厚的情绪。
《洼地》一节关于二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周围的环境描写展示了生死之间一种独特的抗拒关系。 “纪念碑四周是一片灌木丛,是玫瑰花丛。 盛开的小白花蜷缩着,像纸一样,压得身边的青草好像透不过气来。
树丛发出簌簌声。 黎明时分,天快要大亮了。 ”(102)米勒选取了色彩意象的转换将现实的压抑与想象中的浪漫作对比,抽取使二者产生永久隔阂的矛盾,并最终将其推入混沌的时间接受煅打和研磨。 压抑、烦躁的情绪在这种氛围里凝结发酵成沉默的反抗,伤感的格调背着历史的十字架呻吟前行,愤懑令其迷失在渺茫的未来之中。
米勒曾说 “人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甚至会把实实在在的物体拟人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就会特别注意周围的每一样事物。 他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了, 而这些事物也定义了人本身。 ”于是许许多多眼前可见的事物被零零散散地搭配在一起,构成了异质群体的一种独特的意义表达。
在米勒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带着孤独感动的陌生性才能产生意外的错位效果, 人们的感官只有在受到物质世界的剥夺之后才有可能彻底脱离传统印象的束缚,产生新的理解和反射印象。 题目“人是世间一只大野鸡”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米勒以极其意外的修辞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鲜明的对立起来, 十分醒目地宣告了她所要谴责的尴尬现实, 即原本归属于社会的人迫于某种压力不得已变成了一只鸡,人的社会属性被自然属性所置换,并最终沦为异质。 人的灵性、禀赋、尊严和自豪感在这里遭到了嘲弄,社会作为迫害人的罪魁祸首受到了超然淡定的谴责。
瑞典文学院将米勒的风格描述为 “诗歌的凝练与散文的率真”。 (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2010: 201)然而 ,米勒创作的文学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她的文字常常令读者在顷刻间获得感官的顿悟,抽象的时间与具象的事物彼此链接,互换形体,彼此交融, 坦诚地描绘着人既无未来可追寻亦无现在可立身的双重的无所寄托之痛。 异质抗辩作为赫塔米勒小说艺术的独特表达带我们走进了异质群体真实生活体验的最深处, 聆听他们面对压迫时抑郁的喘息和每一声质疑的心跳。 她写作中凝练出的生活的影子将每一根神经所承受的负担彻底地释放, 任由他们在微弱的颤动中传递对主流文化的赤裸质询和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悲情控诉, 为更深刻地理解异质文化提供了更鲜活更丰富的视阈。
参考文献:
[1] 赫塔·米勒.人是世间一只大野鸡[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 胡蔚.政治·语言·家园 ———赫塔·米勒的文学观[J].探索与争鸣, 2010(01).
[3] 李银波,苏晖.2009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9(05).
[4] 李丽琴.赫塔·米勒作品的时代隐喻[J].当代文坛, 2010(04).
[5]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 2004(02).
[6] 张霁.异质与边缘的表达 ———论赫特·米勒创作的跨文化视野[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01).
[7] Georges Bataille, Trans. Robert Hurley. The Accursed Share: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umeⅢ, Sovereignty [M].New York:Seminar Press,1991:99-100.
[8] Herta Miller. Pheasant Human[M].London:HarperCollinsPublishers Ltd,2010: 97, 102, 133, 141, 155, 221, 225, 276.
[9] Nicholas Mudish. Herta Miller’s Life and Writing[M].London:Wordsworth Classic Ltd, 2010: 55, 57, 96, 201.
[10] 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J].11, 1991, 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