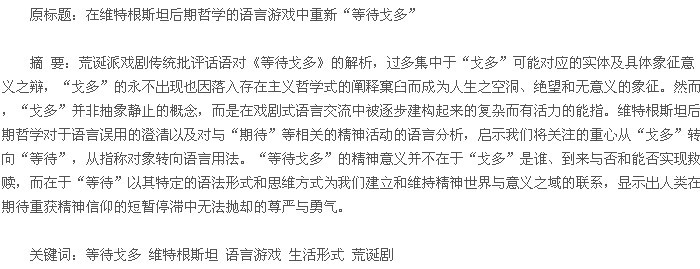
一
自 1961 年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在其代表性专着《荒诞派戏剧》中为这一先锋戏剧正式命名,并以敏锐而深刻的剖析为其奠定权威性批评话语以来,荒诞派戏剧的主流评论一直未离开他着重探讨的二战之后精神信仰幻灭的主题以及他所构建的存在主义阐释模式。作为荒诞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正是马丁·艾斯林用来开启这一阐释传统的经典举证和叙述起点。在《荒诞派戏剧》一书引论的开头,艾斯林描述了《等待戈多》这部将当时“老练的巴黎、伦敦和纽约的观众弄得糊里糊涂的东西”,怎样被圣昆廷监狱的 1400 多名囚犯观众并不困难、毫无勉强地接受、理解、掌握,甚至深刻体味的。一些囚犯认为,戈多可能指社会,或指局外人 ,在艾斯林看来,这都证明了这批特殊观众对于这部在当时最具先锋色彩的戏剧的出色理解和阐释。艾斯林接着还引用了监狱老师的一段评论:“他们能理解等待意味着什么……,而且他们知道即使戈多最终来了,他也只会使人失望”。在他看来,这一评论同作者所代表的崭新世界观及戏剧理念基本符合,至少比当代那些权威评论家和老于世故、先入为主的观众们对这类戏剧的盲目指责和蔑视要高明得多。
《等待戈多》无论是在观念还是形式上都被艾斯林视为那一群值得重视、肯定和研究的荒诞派戏剧的范例。爱斯特拉冈(简称戈戈)和弗拉基米尔(简称狄狄)是两个衣裳褴褛、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他们每天结伴在一棵树下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但从未见过戈多,对戈多的情况一无所知,也并不清楚戈多究竟能带给他们什么,甚至连等待的地点和时间是否正确都无法确定。在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中,他们重复着琐碎无聊的对话和行为,甚至用上吊自杀来打发时间。而一个替从未出现的戈多传话的小男孩在两幕即将结尾处各出现一次,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了,但明天准来。
在当时较为开放和敏锐的评论看来,《等待戈多》“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不可能性,即:一出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戏剧,却将观众们牢牢地吸附在座位上”。而后来随着荒诞剧的精神理念逐渐为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和领悟,以及荒诞剧理论、研究话语和阐释惯性的普泛化,怎么也等不来的那个“戈多”,或被解释为上帝和神,或被认为是人类早已遗失的精神信仰,或被看成心理学上自我、本我与超我的关系,或者直接等于剧中的“波卓”、幸运儿,甚至是孩子。但不管戈多到底是谁,是什么,他在剧中出现的“不可能性”,或是不确定性,是艾斯林及其他主流评论者们用以剖析剧中“等待”以及“等待”行为所构成的人生境遇和哲学意义的唯一准则。
并且,这一准则是具体还是抽象,是平凡还是神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出现还是永不现身,都无可争议地决定着“等待”行为及其代表的“天堂的远离、人性的萎缩”之精神世界的空虚、幻灭、失落、孤独、荒谬、走投无路和混乱无序。在这样一种持续 50 多年的论调中,“戈多”这个词在剧中的意义被越来越紧地吸附于其理当对应的那个“实物”之上,而戈多作为实体之永无回应,作为信仰对象之不可捉摸,作为精神源泉之子虚乌有,也必然使得作为戏剧语言现象和语法表现的那个“戈多”的意义落入空泛。“等待戈多”的行为无异于一种自知毫无价值但又被迫停滞于此的愚蠢可悲之举,它从在剧中诞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极度悲观绝望的黑雾中徘徊。
但是,当我们评论这部戏剧中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当我们说本应到来的“戈多”迟迟未到,或者可能永不现身的时候,当我们暗示“戈多”的到来也只是失落和绝望的时候,我们到底意指什么?在这部戏剧所能给我们提供的全部隐喻中,到底该发生的是什么?戈多又是谁?他的长相应该如何,他的到来应该为世界带来什么,他给狄狄和戈戈应带来何种影响?为他们指出一条怎样的救赎之路?当我们不断地将这一切悲观绝望、荒谬失落叠加于“戈多”这个意象时,我们借此作为意义判断的基础是什么?
在剧中,包括在荒诞剧命名之前的阅读视野中,没有任何预设的理念可以暗示或引导我们猜测“戈多”到底是谁,或应该是什么。剧中主人公在一个几乎没有标记的时间和地点,因为一句没有根源的“我们在等待戈多”而将“戈多”置入“等待”所确立的语法位置和精神境遇里。对于我们一无所知、毫无概念之物,我们如何可能对它的到来与否进行判断?我们又如何更进一步评判它与我们的精神联系?如果“等待戈多”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那个戈多实体的出现与否,以及是否有可能实施某种拯救,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等待一个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有可能从来不曾存在的东西,并且由此还给这种等待以是否符合理想的判定呢?
二
正是在对荒诞剧传统评论模式问题的上述反思中,正是在涉及“词”与其指涉之“物”,以及由此引申的“词”的意义表达本质的谬误上,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部分核心理论可为上述语言悖论提供最为契合的深刻启示。
艾斯林的《荒诞派戏剧》以一群囚犯意外地解读出“戈多”的意义如何随着实体的虚幻而落入空洞来导入,而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代表作《哲学研究》却正是以反驳奥古斯丁建立在类似观念上的“指物解释(Hinweisende Erklarung)”和“指物识字法”(Hinweisen des Lehren der Worter)如何误释词与物之真正关系,以及如何误导词的意义呈现为起点。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提及儿童如何学习单个词语,继而学会语言:“当他们(我的长辈)称呼某个对象时,他们同时转向它。我注意到这点并且领会到这个对象就是用他们想要指向它时所发出的声音来称呼的。”奥古斯丁认为我们就是如此这般来学会和理解出现于不同句子中特定位置上的语词究竟是指称什么事物的。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番论述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和模式,即:“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就是这些名称的组合。……每一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但这一对语言意义的总结在维氏看来显然是极大的谬误和混乱。
维特根斯坦认为在词与物之间建立一种静止的联系,这在学习语言的初始练习中是有用的,但是这“指称”活动本身绝不是语言习得的全部内容,也绝非语言意义的根源之所在。维特根斯坦用不胜枚举的日常语言实例和引导式的分析对此进行彻底的澄清和正名。比如,维特根斯坦假设存在“诺统之剑”这个说法,于是事实便是:不管这把剑是完好无损,还是被毁成碎片,“诺统之剑”这个词在其所生成的语言游戏中仍有意义 ;“摩西”这个词的意义有着“整整一系列的支柱”,不但“摩西”可以指向不同事物,连“摩西不存在”这句话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哲学研究》第 8、15、40—42 小节中有过相关的命题假设。第 8 小节中维特根斯坦以 A、B 两人从事递送工具活动为例:他们给所有工具标上名称,这样 B 即使在完全不知道每个工具的名称的情况下,仍可通过 A 的指令中的对应符号来完成这一工作。在 40—42 节中,维特根斯坦继续分析这一语言活动,他假定名称为“N”的工具坏了,而 A 不知道这一情况,仍然对 B示意和“N”相关的指令,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名称或者说记号还有没有意义呢?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也可以设想一种约定:如果 A 给 B的记号是属于已破碎的工具的,那么 B 就必须摇摇头以作为回答。——这样,即使在该工具不复存在时,命令‘N’在这个语言游戏中也可以说仍被给予了一个位置,记号‘N’甚至在它的承担者不再存在时仍有意义。”
维特根斯坦还假定说,即使是一个从来找不到对应物的语言符号“X”,仍然可能在此意义上于语言游戏中得到运用并获得其意义 。这种实现性内在地包含了一个前提——人们对于其在语言中的位置比对它的定义概念和相关解释要先一步清晰,或者能够先一步地给予可能性猜想。
除了把词的意义归于其对应实体之上这个谬误,奥古斯丁式的指称归意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还继而引起了另一类谬误性推导,即:在对应实体缺席的情况下,语言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能够唤起人们心中关于它的图像。对此维特根斯坦用大量表颜色的词来说明其中的漏洞。维特根斯坦认为,假定表颜色的词的意义是它们在人们心中能唤起对于相应颜色样本的记忆,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对于这个词的意义把握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记忆是否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完全符合我们当时看到的物体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又凭什么去断定我们对某种颜色的记忆是否正确,是否没有任何偏差呢?
“假定你在某一天感到这颜色比前一天见到它时更鲜艳些;你是不是有可能说‘我一定搞错了,这颜色当然同昨天的完全一样’?这就表明,我们并不总是依靠记忆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并把它当作最高上诉法庭的裁决。”
此外,这种“图像论”解释还有另一致命缺陷,就是心中的图像如果是词的全部意义所在,那么它必然要具有一种普遍的认识意义,是对所有可能的图像的集合和总概,那么如果对于心中一片树叶的相应图画,这片叶子应该集合了全部树叶的共同点,那它该是何种颜色、形状呢?而“红”这个词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看到它和说起它时心中浮现出一个样本性的、标准的红颜色或红的事物,而在于我们懂得它是一种颜色的描述和分类,懂得将它在正确的语法位置上来使用 。
当我们将这种词与物的对应释义方式推及一些表达抽象意义的词时,一副更为荒谬和怪异的“精神图画”和“精神世界”的构图便出现在眼前。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由此论及语言与人的“精神活动”的关系实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疼痛”、“私人语言”以及人的各种心理活动表述的分析。
对于“等待”、“期待”和“希望”等类型的主观愿望词,我们通常认为其意义与核心价值就在于它们所指代的,或者我们脑中所想象的那样一个事物、场景、画面或结果,但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一种最大的思维混乱和语言误区。首先,一个期待或愿望并不在于它们在语言中指向的那个事物的实际满足,而它们自身的意义也不在于被填满,“期待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对某种东西的期待”。比如,当人们说:“我期待一声枪响”,随后可能真的会有一声枪响,或者根本没有枪响,但是否这种不确定性或失望会取消这个句子的意义,取消“期待”的意义呢?如果真的听到了一声枪响,那么我们又如何判定这声枪响在时间长度上,在声音大小上,以及清晰度上等等,全部符合先前的具体“期待” ?其次,正是在以上问题上,“期待”、“等待”和“愿望”完全可能表述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完全不清楚的事物。例如当我表述“我希望他今天会来”时,无论他是否现身,这并不会影响语法中所包含的愿望与期待。而当我说“我不希望他今天来”的时候,具体语境上所启动的意义显然和“他来”这个事实更加没有关系 。再次,我们还可以由此认识到与“期待”、“希望”等在语言结构上形似的一些表达的语法意义。下列说法并不在实质上属于“期待”和“愿望”的语法意义:“我正反复思索着明天离开的决定”,这类似于对一种精神状态的描述;“我今天听说他要来,我整天一直等着他”,这更像是对一天活动的报告;在一场争吵的最后“我”说:“好吧,那么我明天就离开”,这里是实施了一个决定。在和“期待”、“希望”极为近似的各种表达中,它们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愿望的对应实体和结果,而在于它们在具体的语言使用层面上是如何于设定语境中发挥作用的。正如这个例子:他不在时,我可以寻找他、期待他或等候他,但是他不在时,我却不能吊死他 。
在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中采撷的鲜活例子及其分析之中,我们就能看到将类似“期待”和“希望”等精神活动的意义归结于一些外在实体的说法是如何之谬误。心灵内容所处理的对象其实不必以独立于心灵表现(和语言表现)的方式存在,我们的心灵内容所处理的对象并不是任何在生活中必须找到实体形式存在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语言、语法结构建立起来的联系和生活事实。
三
如果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意义实质问题的以上澄清和阐明可以为荒诞剧陌异语言现象打开一扇通向无限“意义”的归返之门,如果我们能将灰暗颓丧的眼光从“戈多”身上收回,而转向其他的语言使用和意义生成方式,我们是否可以期待为那些被传统阐释掩盖的意义找到更为合理的位置呢?
在传统阐释中,“戈多”是那个无望的希望,是永不兑现的精神承诺,是走投无路时的空洞期待,可我们却大大忽略了来自文本的一个事实:它是被有意地在语言游戏中建构起来的。“戈多”最为荒诞的“不确定性”并非他是否到来的问题,而是这个语言概念是否需要存在,如何存在的问题。两位主人公的对白在多处显现出这种极富建构意味的游戏性。比如,他们谈论与戈多的上一次谈话及戈多的私人情况:爱斯特拉冈一开始是以漫不经心的无知者出现的,他向弗拉季米尔提出很多关于戈多的疑问,如戈多交待了什么、要求他们做什么以及怎样回应等,但随着对话的发展,爱斯特拉冈却明显开始表现出一种和对话者一起建构的欲望和行动:
弗拉季米尔:说他瞧着办。
爱斯特拉冈:说他不能事先答应。
弗拉季米尔:说他得考虑一下。
爱斯特拉冈:在他家中安静的环境里。
弗拉季米尔:跟他家里的人商量一下。
爱斯特拉冈:他的朋友们。
弗拉季米尔:他的代理人们。
爱斯特拉冈:他的通讯员们。
弗拉季米尔:他的书。”
在这段对话中,爱斯特拉冈从最初对“戈多”
记忆模糊、对谈话内容几无所知,到开始对这些情况自问自答,以及弗拉季米尔对这一自问自答的跟随与推进,无不表明:与其说他们是在共同回忆,不如说是在带着商议和希冀的口吻共同设想着一个可以为他们带来惊喜与抚慰的“戈多”,以及他们与他的基本关系。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无论是与一个人,还是与某一事物,也许是愿望的起点。
剧中两人对于“系住”一词的语言游戏尤其富有上述意义:
“弗拉季米尔:你说“系住”是什么意思?
爱斯特拉冈:拴住。
弗拉季米尔:拴在谁身上?被谁拴住?
爱斯特拉冈:拴在你等的那个人身上。
弗拉季米尔:戈多?拴在戈多身上?多妙的主意!一点不错。(略停)在这会儿。
在此,“系住”与“拴住”微妙地暗示了被“等待”
瞬间建立起来的语言场所和精神联系。虽然“戈多”的意义尚未明晰、有待填充,但“等待”已在语言游戏中为它留出一席之位,并且它的功能也将随着下面语言游戏的运转和深入而获得更多信息,并得以显现。在与前后两次突然出现的“孩子”关于“戈多”的对话中,这种以精神之愿景来建构的痕迹也很明显,并且这里还暗示了另一种与精神信仰有关的复杂心理。在第一次与“孩子”的对白中,“孩子”并不真正像在通告和描述所有关于“戈多”的情况和意愿,而弗拉基米尔则更像是于犹豫不决中引导“孩子”和他一起想象和建构那个可能对他的境遇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或事物。而这一点在他们的第二次谈话,尤其是“孩子”对于弗拉基米尔的回应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些回应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试探性的肯定、否定、鼓励与合作:
“弗拉季米尔:这是你头一次来?
孩子:是的,先生(沉默)弗拉季米尔:你给戈多先生捎了个信来。
孩子:是的,先生。
弗拉季米尔:他今天晚上不来啦。
孩子:不错,先生。
弗拉季米尔:可是他明天会来。
孩子:是的,先生。
弗拉季米尔:决不失约。
孩子:是的,先生。”
弗拉季米尔通过语言来无限接近一个更为具体的“戈多”的语言存在,远远超过了那个充当使者的孩子的直接描述。两位主人公和孩子的两次会面,隐含着主人公在将一个精神建构中的“戈多”以何种方式具体呈现的问题上的忧虑不安和模糊不清,这在孩子询问弗拉季米尔如何回复“戈多”的细节上体现得更为清晰。弗拉季米尔在此体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度和倾向:“跟他说……(他犹豫一下)……跟他说你看见了我,跟他说……(他犹豫一下)……说你看见了我。”
对于传统阐释中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来说,“戈多”本应是唯一的、最后的精神救赎和希望之路,但是弗拉季米尔在此的回答却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切、脆弱、期盼和渴求,相反,他表现的是一种对于“戈多”的难以解释的复杂情绪——一种融合了犹豫和焦虑的沉思,一种临场的畏惧和退却,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冷静和审慎。“戈多”被语法带入了精神领域和“生活形式”之中,但是“戈多”在“等待”的语言游戏中和什么实体来对应,在什么生活经验中实现,却是被反复思考和斟酌的,是在用语言交流所建构的场域中不断地被猜测、犹疑和否定的。突然与两位主人公相遇的波卓和幸运儿就是在这样的语言游戏中和“戈多”建立起联系和矛盾的。波卓及幸运儿给两位主人公带来了可疑的猜测和兴奋的希冀,他们带着复杂的心情和模糊的自我认同来与这两个不速之客周旋,同时他们自己也在语言建构中寻找他们相关的位置,但最终他们还是自己否定了这个可能的希望。爱斯特拉冈提出他早就知道波卓是戈多,然而这一认定马上被弗拉季米尔否认了,随后前者也陷入了迷惘之中 。
这里与剧中所提供的境况相悖的是,弗拉季米尔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戈多,虽然有“孩子”对于戈多的描述,但这一外形描述也没有给我们提供生活经验中的足够信息,但弗拉季米尔却断定波卓不可能是他们所期待的“戈多”,或者说,他们决定,波卓和幸运儿无法成为“戈多”。在这个意义上,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即使在迷失与无助中,也并未如传统评论所言——将精神世界的救赎绳索系于一个空泛的希望意象之上。他们其实一直于寻求意义的语言游戏中,决定和选择他们自己的“戈多”。
对于整部剧作及其主人公而言,“戈多”最重要的意义便是:它是通过“等待”这种语言方式和主人公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等待”是主人公在一个失去了大部分语言意义的世界里寻找到自己的语法位置的关键。此剧开头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颇具试验性的语言部分失效的世界:位置的难以确定,时间失去意义,主人公“生活形式”的截断等。在失去了具体“生活形式”的世界,人类的语言游戏面临着一种来自无意义的威胁。两位主人公之间看似漫无目的、喋喋不休的对话一直在不断地给语言建立有意义的背景,但是直到“等待”的语法出现,才使得境况大为改观。因为有了“等待”,今天和明天的区别变得有了参考;一棵树和一条路的存在因为服务于“等待”地点的确认而在语言中变得有意义;主人公关于生存价值的讨论、甚至是绝望而悲观的叹息,也在语言中找到了有意义的联系。他们与波卓和幸运儿的交流是从关于“等待戈多”的询问开始的,在无限的“等待”中,他们才得以不断地和“孩子”进行有意义的语言交流。“等待戈多”并不是一种被迫无奈的选择,它的意义也不在于现实中叫做戈多的人到来与否,而在于它是人类用类似“我期待”这样的语法形式在这个符号性语言渐失意义的世界里仍然有力地抓住意义之绳的勇气之举。它的意义因而并不归属于那与“戈多”所对应的实体之上,而是在于我们成功地运用有关主体意向的语言来独特地处理世界这一活动仍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它并没有因为语言家族某些部分的失语受损而失去力量。正如剧中弗拉季米尔所说:
“……可是问题不在这里。咱们在这儿做些什么,问题是在这里。而我们也十分荣幸,居然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是的,在这场大混乱里,只有一样东西是清楚的。咱们在等待戈多的到来——”。
借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着名论断,我们可以说:“戈多”的全部意义,就是它在这场不断确立着新规则的语言游戏中的使用,以及它所呈现的全部方式,“戈多是谁并不重要,他于语言中存在,……词语使他具有了生命”。在“等待”与“期待”的语法形式中,对象与意义其实已清晰可鉴,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我们能看到一种期待的表述,那就等于看到了所期待的是什么,“难道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方法,在别的意义上看到它吗?”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建立在语言使用之上的意义发现方式启示我们:心灵内容是经由其语言表达式的使用来处理对象和事实的,也就是说,是经由其语言表达式的语法来做到这点的。由于相关的语法规则是在语言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一个心灵内容之处理一个对象和事实或事态的方式是在特定语言游戏的语法解释中得到说明的,而不是在语法之外的某“物”之上。无论是期待、愿望、想象还是意指,心灵内容与其对象只在语言中发生接触,一切都可在语言中获得澄清,一切也会经由语言的使用来确保意义。
狄狄和戈戈也许会继续使用“等待戈多”的语法形式来与意义世界保持一致,并在这过程中不断丰富关于戈多的语法规则,但他们也可能会考虑换一种语法形式来尝试。比如,在该剧结尾,他们犹豫着要不要离开,或者说他们是在考虑要不要冒险去尝试其他的语法形式。但不论他们,或者说我们,会选择安稳,或尝试冒险,只要精神世界保持在不断运转着的语言游戏中,“等待”、“期待”和“希望”这样的语法方式和思维联系本身,就会使我们的脚跟始终紧贴着意义的地面。“等待”正是意味着相信所有的失效、空虚、孤独、荒谬、无路可走和举目无助都是暂时的,虽然它算不上重获精神信仰的积极之举,但却应被看作人类精神无法完全自我抛却的尊严和无尽的努力。它的意义在剧本的这两句对白中已然澄明:
“弗拉季米尔:你们要是在无人相助的地方摔倒了,那怎么办呢?
波卓:我们就等着,一直等到能够爬起来为止。随后我们重新上路。走!”
雷蒙德卡佛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文坛上最受关注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卡佛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俄国着名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有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性,他曾被誉为美国的契诃夫.虽然与契诃夫相比,卡佛作品体现出他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难以规避的局限性,但其在沿着契诃夫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