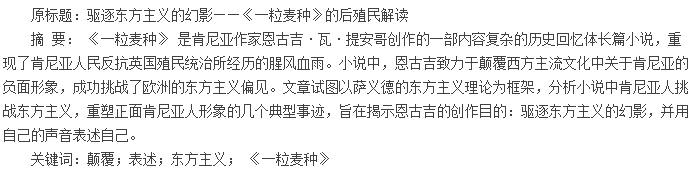
一、引言
恩古吉·瓦·提安哥 (1938- ) 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独立意识和本土文化保护意识的肯尼亚作家,并被冠以“继阿契贝后影响力最大的非洲黑人作家”的称号。他的作品明确地表明了作者恢复本民族人民自我表述权的决心,为肯尼亚文学的发展和肯尼亚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做出重要贡献。他的“长篇三部曲”: 《别哭,孩子》、 《大河两岸》 和 《一粒麦种》 广受读者和批评家的赞赏。 《一粒麦种》 是其第三部小说,也是其代表作。故事以肯尼亚独立前夕为写作背景,作者采用倒叙、插叙和直叙等多层次叙事方式,把自 1952 年“茅茅运动”到 1963 年民族独立十年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一经出版,影响非凡,并被评为“二十世纪非洲一百种最佳图书之一”。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国外研究比较丰富,一些学者从象征手法入手解读小说的后殖民主义。如杰克逊指出恩古吉在小说中反复提到狗,狗象征着恐惧、对立,小说中寇义纳和卡冉加与狗的冲突映射了土著居民与殖民者的关系。一些学者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如瑞迪特海娄指出恩古吉在《一粒麦种》 中塑造了一批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女性,她们与肯尼亚男性一同反抗英国殖民者,为肯尼亚独立运动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朱黎从心理分析角度,运用人格三段论来分析主人公穆苟成为叛徒的根源。韩雪、邵石能运用法侬的民族主义理论,分析小说主要人物卡冉加、基孔由、穆苟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民族主义的内在局限性。王雅君运用霍米·巴巴的矛盾心理和模仿行为理论对小说进行解读。徐静则结合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分析不同个体在探求身份定位时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和心理活动。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来分析 《一粒麦种》。“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的……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
因此,萨义德所指的东方并不是实际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而是一种人为建构的东方,或者说是西方话语语境中的东方。东方主义者眼中的“东方”是野蛮的、落后的、软弱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文明的、勇敢的。肯尼亚人民也被强加上种种负面的、消极的形象,英国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观实现了对肯尼亚长达七十多年的殖民统治。西方用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东方,就好像隔着一层迷糊的幻影,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作为一名具有民族自豪感的作家,恩古吉旗帜鲜明地与东方主义偏见作斗争,描绘出一个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肯尼亚人,维护了本民族的文化和本族人民的形象。本文将从英国人对肯尼亚人的诬赖及对其文明的否定,塑造肯尼亚阳刚男性和坚毅女性两个方面,分析恩古吉在 《一粒麦种》 中驱逐东方主义幻影所做出的努力。
二、驳斥英国人对肯尼亚人及其文明的偏见
英国人对肯尼亚人的看法往往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而对他们持有一种单方面的、格式化的认识。肯尼亚人就是野蛮、落后、无知的,白人则是光明、进步和理性的。东方主义成为了他们实行统治最有效也是最经济的工具,这种二元对立的论调毫不费力地帮助他们在殖民地建立等级秩序,维护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使其能名正言顺地对肯尼亚人实行管理和整治。为了维持他们高人一等的姿态,英国殖民者刻意丑化和扭曲肯尼亚人的形象,有时甚至睁眼说瞎话,凭空捏造。恩古吉在 《一粒麦种》 中对此有极富讽刺意味的描写。如文中写到德琳博士的那条凶残的狗突然发疯似得追向卡冉加,把他逼到墙角,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卡冉加捡起一块石头,举到空中。狗正要扑向这个可怜的黑人时,琳德博士冲狗喊了一声,狗才停止攻击卡冉加。琳德博士不但没有一丝歉意,还恶狠狠地指着卡冉加,用鄙视的语气指责他没有一点爱心和羞耻心,朝她的狗扔石头。卡冉加说自己没有扔石头,却又遭来劈头盖脸的辱骂“你们这种人就会撒谎。说着,她朝围观的其他黑人看去”。围观的黑人看得清楚,读者也一清二楚,卡冉加并没有撒谎,琳德博士的诬赖纯属东方主义色彩的幻想。作为英国的知识分子,她从英国的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肯尼亚人就是残忍的撒谎者,这种思维定势在她心里扎了根。她的强词夺理、恶意中伤正好验证了艾伯特·史怀哲的那句话“在与非洲人斗争的过程中,每一个白人都不断地陷于道德崩溃的边缘”。
这种指责是毫不讲理的,当然也不攻自破,反而暴露了琳德博士蛮横霸道的一面。恩古吉极具讽刺意味地描述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目的就是要毫不客气地驱逐东方主义的幻影,还原事实的真相。欧洲的东方主义观念在小说的体现还表现在对东方文明的否定上。赵一凡说过:“西方文明是通过压迫东方,描述东方,将自己同东方分割对立,得以从中获取力量,确立身份的主体自信与支配权。”萨义德也曾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的内容。”
在英国殖民者看来,肯尼亚传统之所以不可思议,令人无法接受,是因为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在非洲流传了数千年的传统习俗。他们一味谴责其令人厌恶的陋习,却没有考虑到产生这些习俗的文化背景。在马西嘎学校(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穆钮老师讲到了妇女的割礼术,认为那是一种异教徒的礼仪。“作为基督徒,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礼仪。”
此言一出,随即遭到基希卡的反驳:“这只是白人的说法。 《圣经》 里并没有提到妇女的割礼术。”
穆钮洋洋得意,想也没想,就命令学生打开 《哥林多前书》。刚读了几行,他便意识到自己错了。 《圣经》 中不但没有提到妇女的割礼,而且也没有明确谴责这一行为。面对穆钮老师对肯尼亚传统文化简单粗暴的否定,基希卡不再无动于衷,而是自豪地反驳。恩古吉再次借基希卡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为自己所属的非洲文明进行有力的辩护和重申,又一次驱逐了东方主义的幻影,令西方白人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无地自容。正如王岳川所言:“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的总体经验,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却通过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
恩古吉驳斥了西方对东方的歪曲与偏见,表明了西方曲解东方的意图的落空。白人企图用文化侵略的方式为非洲人洗脑,割断他们的文化传承,使他们成为驯服的属民,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三、塑造肯尼亚的阳刚男性和坚毅女性
东方主义者眼中的“东方人”是非常软弱,甚至是女性化的,东方女性则是心甘情愿的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恩古吉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小说中塑造了英勇无畏的基西卡,睿智慈祥的瓦瑞,拘留营里宁死不屈的非洲黑人,坚忍不拔的女性等积极正面的肯尼亚人形象。
基希卡从小受瓦瑞关于被殖民者如何团结起来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鼓舞着,并树立了带领肯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远大理想。被白人教会学校开除后,他自学斯瓦希里语和英语,证明了他过人的智商和才气。后来,他成为了茅茅运动的领导人。“茅茅组织是吉库尤族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为了肯尼亚人民的独立而不懈奋斗。”
他,振臂一挥,一呼百应,重创玛溪警署———“白人高地”的心脏;他,英勇无畏,只身一人,刺杀专区员罗宾逊———残暴的殖民者代表。没多久,基希卡就在基内聂森林的尽头被活捉了,不管是严刑拷打还是威逼利诱,他都拒绝开口,最后被吊死在一颗树上。他为肯尼亚的独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正如小说中所说“尽管基希卡的死给组织带来了重创,茅茅运动仍然在继续,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基希卡的壮举给肯尼亚的人民带来了光明,赐予人们以信念,让他们感受到了黑人的力量,找到了自我的身份。
这也是恩古吉在给小说命名为“一粒麦种”的用意: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入土里死了,它仍然是一粒麦子,若是死了就会出很多籽粒来。就像每一束麦穗的生命都带着死去的那颗麦子的生命一样,每个肯尼亚人民的生命也联系着基希卡的生命。
基希卡受到人民永远的爱戴,但还有成千上万被关押在拘留营里的黑人,他们的壮举同样令人可歌可泣。“被拘留的人常常不分昼夜地唱着一些反抗歌曲,公然嘲笑白人。他们中有些人横遭毒打……但是他们都死守誓言,决不泄漏半点有关茅茅组织的信息……他们忍受着白人的侮辱,因为他们始终坚信,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赢得胜利的鲜花”。汤普森被调到瑞拉拘留营后,便开始实施他在管理非洲黑人方面所依据的一套理论,他告诉拘留营里的黑人,只要坦白招供,就可以回家和妻子儿女团聚。“但在瑞拉,他却遭遇到了一群大不相同的人,他们甚至连张口说话都不愿意,只是直愣愣地看着他”。不仅如此,所有的囚犯团结一致,都坐下来开始绝食抗议,这些绝食抗议的囚犯被包围起来,关进牢房,日夜受到毒打,结果是十一个人被活活打死。瑞拉惨案引起国际轰动,彰显了肯尼亚人民的英雄气概,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基希卡和关押在拘留营里的黑人形象颠覆了白人主流文化刻意渲染的肯尼亚人怯懦被动,唯唯诺诺的女性化形象。
恩古吉不仅描述了血气方刚、不屈不挠的肯尼亚男性,还塑造了一批坚忍不拔、自力更生、目光长远的肯尼亚女性,她们为肯尼亚独立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小说中,恩古吉重点描写了以恩姬丽、万伽俐、梦碧为代表的女性。恩姬丽虽然个子矮小,但内心却很强大,抱负也很远大。
在作者笔下,她是这样一位女性:“她鄙视女人软弱,鄙视她们动不动就掉眼泪。每次基内聂森林发生打斗,她肯定会参战,甚至和男人动手。男人称她为野猫,因为很少有人可以强迫她听命”。此外,她对基希卡矢志不渝的爱情也着实令人感动。基希卡走进森林参加茅茅运动后,她也随即冲入森林与基希卡并肩作战。基希卡牺牲后没多久,她也在一场战斗中阵亡了。
另外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是基孔由的母亲———万伽俐。她遭遇了不幸的婚姻,并被丈夫无情地抛弃。要知道,在那个男权至上,女性地位极其低微的社会里,被丈夫休掉的女人又带着个孩子想要生存下去是艰难的。万伽俐经历了难以想象的不幸,但她并没有被不幸击垮,而是坚强地忍受了所有的痛苦,肩负起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带着年幼的孩子来泰北开始新的生活。她亲手盖房,下地种田,独自一人把孩子拉扯大,并送基孔由到学校学习技能。在“紧急状态”时,白人殖民者打着“维护和平,维护安全”的旗号,把村民都赶到规模更小,分布更密集的村落里,为此,他们强行烧毁村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万伽俐的房子也难逃不幸。殖民者烧毁的不仅仅是她的劳动成果,更烧毁了她与儿子、媳妇朝夕相处的美好记忆。善解人意的梦碧想带着婆婆离开这残忍的一幕,“可她却推开了我的手,轻轻地摇了摇头,双眼继续盯着那愈烧愈烈的火苗……撕心裂肺的痛……我听见婆婆倒抽一口气,但她的视线始终没从眼前的场景挪开过……。殖民者卑鄙的行径令人发指,但万伽俐直面不幸表现出来的坚韧令人赞叹之余,更给予人心一种顽强不息的力量,希望之火永不磨灭。
梦碧,一位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女子,“只见她手持火把,熊熊燃烧的火焰驱散了眼前那片黑暗”。她就是希望和光明的化身。基孔由被抓之后,她不得不系上腰带,干起男人的活。她用挣来的钱买面粉,解决了一家五口人的温饱。她选择包容丈夫的疏远,淡忘卡冉加的伤害,甚至原谅那个出卖自己哥哥的叛徒,这不是软弱,而是因为她有一颗包容一切、善解人意的心。她长远的目光让她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渴望和平,渴望真正的幸福。“真得要为报基希卡之仇而杀死卡冉加吗?血已经流得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在这片土地上增加更多的罪恶?”,恩古吉借梦碧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认为肯尼亚历经劫数后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不应该在沉迷于过去而再次陷入混乱恐惧之中,而应该把目光投到现在及未来的建设中。民族独立的真正意义乃是民族意识的更新与民族团结的再出发。
这些光辉的女性形象照亮了那段黑暗的历史,颠覆了白人主流文化中肯尼亚女性没有主见,依附顺从的形象,展现了肯尼亚女性坚毅顽强,外柔内刚,秀外慧中,不屈不挠的优良品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恩古吉在 《一粒麦种》 中有力地控诉了宗主国对非洲文化的否定和贬损,颠覆了西方主流文化中关于肯尼亚的负面形象,成功挑战了白人东方主义偏见,从而进一步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驱逐东方主义的幻影,并用自己的声音表述自己。正如王岳川所表述的:“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恩古吉承担起自己作为肯尼亚作家的责任,对西方文化霸权提出挑战,借此小说挑战并重新协商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去争取自我表述权。萨义德对东方学表示明显的批判和拒绝态度。同时,他也强调面对世界上的文化霸权,要去消解霸权本身,而不是用一个话语霸权去替代或抗衡另一个话语霸权,更不是要“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共生,建构东西放平等对话的新型关系。恩古吉并非要把白人文化和黑人文化对立起来,而是展现了肯尼亚人民也具备世界上其他民族拥有的特质,如坚忍不拔、承担责任、勤劳勇敢、热爱祖国等美德,提倡黑白文化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对话,而不是按固定的思维模式去定格或以一方的标准去衡量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