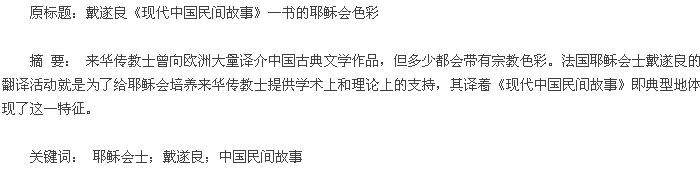
一、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作品向法国的译介与传播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将其置于当时不少译介者所处的宗教话语体系中观察。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往往打着符象派(figurisme)的烙印,并体现了耶稣会宗教活动的需要。其中戴遂良的文学翻译尤其值得注意,他的翻译行为即是对中国文学作品美学特征的否认,其翻译作品集《现代中国民间故事》(Folk-lore ChinoisModerne)的编纂、翻译和命名值得探究。
二、戴遂良的耶稣会士身份
在中国文学早期的海外传播中曾起过关键性作用的耶稣会士认为,任何民族的人都有资质和权力听到上帝的声音,并接受上帝的恩泽。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耶稣会士乐于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耶稣会创立者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曾叮嘱信徒要懂得“从他者的门进去,将他者带出来(entrer par la portede l’autre afin de le faire sortir par la sienne)”(Standaert,2002 :126)。 他者自然是指尚未归依者(infideles)。不少耶稣会士通过对中国典籍的研究来佐证上述资质之存在,或者干脆研究起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基督因素或情结,其中着名的就有戴遂良。
戴 遂良(Wieger,1922 :3) 在《 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Histoire des CroyancesReligieuses et des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Chine)一书的初版前言中将研究动机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是应巴黎天主教学院之约撰写这个读本的。来华三十年,我为上帝开疆拓土,孜孜研述;本书即集三十年来探究之心得也。谨呈之于天主教学院,忝列鸿庠,或能对宗教与科学有所芹献(J’ai écrit ces Le ons,à la demande de l’Institut catholique de Paris.Je les lui offre, comme un modeste apport à sesgrands travaux pour le religion et pour la science.
Elles représentent trente années de recherches etd’études, en vue de la propagation du royaume deDieu.)。”戴遂良(Wieger,1909 :4)认为,中华民族的意识中有先天的基督情怀(Cependantles manifestations de la conscience naturellementchrétienne ne font pas défaut.)。先他三百年来华的另一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传教受挫后,花十几年功夫学习中文,并研读中文典籍。利玛窦学习中国文化是一种宗教行为,他力图从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找到儒教同基督教间的契会之处(Bouvet de Cresse,1826 :193)。他认为,中国人所信奉的天地即基督教的上帝,中国人的祀仅仅是为了对祖先表达缅怀之情和孝敬之意而已,不属于偶像崇拜 ;所谓的祠堂只是简单的厅堂,宰牲只是为了烘托节日气氛,主持宰牲的人只是屠夫而已(ibid. :193-194)。有些学者将这种来华耶稣会士入乡随俗的现象称作中国化(sinisationdes jésuites)(Li,2002 :32)。作为耶稣会士的戴遂良秉承的是自利玛窦以来的耶稣会精神和传教手段,其文学翻译活动应该亦属于这一宗教范畴。
三、《现代中国民间故事》的命名由来
戴遂良的《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于 1909年在河北献县出版,共收入 222 篇中国志怪类文章。文章分别来自《聊斋志异》、《西游记》、《红楼梦》、《剪灯新话》等作品。全书共计 422页,正文采用竖排版式,每页左侧印有中文原文,右侧是法语译文。《现代中国民间故事》所录文章之间的排序颇为肆意,看不出作者刻意安排的痕迹。与戴遂良同时代的学者、“汉藏语系”这一术语的创立者普茨路斯基(Jean Przyluski,1909 :172)当时就 评论说 :“如果故事间的排列不是任意为之而是经过系统的处理就好了(On aurait souhaité queles contes, au lieu d’être rassemblés au hasard,fussent groupés systématiquement. )。”其实戴氏完全可以为故事间的排列定一个标准(如原文的成书时间、原文的体裁等),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细节,他这种不拘小节的特点也常常为同行所诟病(Chavannes,1914 :288-289)。
我们可将戴氏这种不拘小节视为一种取效 行 为(perlocutionary act)(Austin,1962 :109)。戴氏似乎担心译文读者会为故事所吸引,以至于不能到岸舍筏,因而故意抹杀了原故事的文学性。普茨路斯基(Przyluski,1909 :172)认为,戴遂良的译文采取了自由意译的方式,“甚至更像是译者自己对原文的诠释”。
他译介这些作品的目的相当明确,无非是让来华的耶稣会士了解中国文化,并通过比较来确认中国和上帝之间的因缘。因此,在他看来形式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危险的。他始终坚持宣称那些被后人称作文学的文本只是“大杂烩式的民间故事”(folklore hybride)(Wieger,1922 :613)。
folklore 一词出现较晚, 英国作家通斯(Williams John Thoms) 于 1846 年 8 月 在 当时的文学杂志《书府》(Athen um)上撰文呼吁“记载昔时的礼俗、规仪、迷信、民谣以及谚言”,“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 PopularAntiquities( 民间古事) 或 Popular Literature(民间文学)。但是这些所谓的文学倒更类乎Lore(口传故事),用 Folk-lore—the Lore of thePeople(民间的口传故事)这个撒克逊组合词来代称更为恰当”(Simpson & Roud,2000 :143)。当时 folklore 一词刚刚(1885 年)进入法语,在法语中基本上也被赋予了通斯创词时的含义(Ambs,1994),主要指称口头的、民间的故事。与戴遂良同时代的葛郎热(DesGranges,1922 :46)称 folklore 为“庞大的口传传统”(vaste tradition orale)。法国重要的民俗家、几乎与戴遂良同时代的盖奈普(A. VanGennep,1912 :5) 认为 :“folklore 原则上只涉及民间生活。从文学意义看,它只收集集体的、佚名的作品,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学史关注的则是作者姓氏翔实且具浓郁个人风格的作品(Le folklore, par définition, ne s’occupeque de la vie populaire. En matière littéraire, ilrecueille la production collective et anonyme[tandis que] l’histoire littéraire au sens courantdu mot ne s’intéress[e] qu’aux uvres signéeset individualisées.)。”在这个问题上,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66 :162-163)在《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一文中对 19 世纪以来法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也曾作过类似总结,并认为不可全盘否定社会、历史及传统的文学性。
即使按照传统的文学批评理念,戴遂良翻译并收入《现代中国民间故事》的这些作品也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文学,都是“作者姓氏翔实且具浓郁个人风格的作品”。或许学界对某些作品到底出自谁人之笔仍有争议,但这些作品的个人风格(individual expression)突出(Lévy,2000 :142),已不同于它们所依据的大杂烩式的集体结晶(composite authorship)(ibid. :137)。这些作品归入 folklore 之列倒不是因为他对文学之定义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而是因为他想通过文学作品来印证中国人的宗教特色。他甚至在后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中大胆指出中国大众的信仰便是这些民间故事的观点:“从平民中随便找一个自称佛教徒的人,问他几个关于佛教的根本问题,我敢说他一个也回答不上来,道教徒也是如此。但这些大杂烩式的民间故事竟是各地蕞尔小民耳熟能详且笃信不疑的。正是这些故事在底层民众中营造了恐怖的迷信氛围。”(Wieger,1922 :613)在戴氏眼里,中国人的信仰是感性的,宗教教条为民间故事所取代。
《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几乎全盘收录了《现代中国民间故事》。而《现代中国民间故事》收录之中国文学在戴遂良看来委实等同于街谈巷议,此处又是一证。
这 种对他 者 世 界 的 任意 揣测(ex suanatura ceteros fingere)(Cicero,1815 :83) 和理论虚构(fiction)大多源自人们对自身文化中某些层面的忽略或一知半解。从辞源上看,“虚构”一词自拉丁语 fingere(捏造)的过去分词形式 fictus。而捏造的前提则是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材料。戴遂良对中西文化材料的甄选行为却因囿于他所处的话语体系而失实。假若戴遂良跳出他所处的话语体系,就会发现法国大众的信仰何尝不是依赖一些感性材料作支撑呢?在一部分人替大多数人读书的年代,以读书和着述为职业的僧侣每每利用感性的图像和雕塑来宣讲宗教故事(Sartre,1948 :92)。
如果将宗教的教义视作符号的所指(signifié),那些宗教坟典如《圣经》或《金刚经》则是符号的能指(signifiant)。《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中的中国文学作品无疑是难以摆脱相关宗教坟典影响的,但这些作品的写作和建构并非完全以再现坟典故事及坟典内涵为初衷,其所指不是这些本身以教义为能指的坟典。换言之,这些中国文学作品不是符号的符号(signe dusigne)或能指的能指(signifiant du signifiant),其野心是作为独立的符号存在,它们与天主教教堂彩绘玻璃这种纯粹以另一符号(如《圣经》故事)为所指的符号 不同。
戴氏认为,文学在客观上有教化民众的功能,这一点不无道理,且与周作人的观点吻合。周作人(1995 :5)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不是老庄的道家)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所谓的道教不是老庄的道家,则一定是民间的道教迷信和道家故事了。文学家周作人和传教士戴遂良在这方面都无视了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所谓作品的意向(intentiooperis)。
四、是诠释文本还是使用文本
巴尔(Mieke Bal,1977:4-10;1997 :5-9,144)将叙事分为三个阶段:本文、故事和素材(texte,récit,histoire)。本文是最终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成品,素材是一些“逻辑上相关联的事件(événements logiquement reliés entreeux)”(Bal,1977 :4),故事则是作者对素材进行初步整合的结果(不管是口头的还是笔头的或者别种形式的)。整合范围包括调整事件发生的次序(正叙、倒叙),压缩或扩张事件时间的跨度,赋予行为者鲜明的类别特征和个体化特征,将其转换为人物角色,赋予事件地点鲜明的类别特征和个体化特征,将其转换为故事空间,在素材的事件、地点及行为者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赋予新的、象征的或指事的关系,自然整合范围还包括视角的调整(ibid. :7-8)。本文的形成还需要在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语言的或元语言的加工润色,此为叙事的最后阶段。
戴遂良所理解的 folklore充其量只能算作故事这个层次。据上文对 folklore 的定义,尽管他将《西游记》等作品看作 folklore,但不能否认这些作品最后是以文字形式呈现,因此属于真正的文学而非 folklore。按照戴遂良(Wieger,1922 :753)的估算,那个时代中国能读懂这些书籍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多一些。
因此,代表中国人思想的不是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所依据的素材。这才是他要向其他耶稣会士传达的信息。可以说戴遂良看重的是故事更下一级的素材。只是口语中民间相传的素材在处理上不如书面故事那么方便罢了。
这一点通过《现代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二书的互文性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中所讲述的民间故事多集中于该书的第七十讲,戴遂良未注明出处,但其实这些故事大多来自《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他得知这些故事的途径也只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戴遂良(ibid. :731)将小说和戏剧看作是“固化的和传播民间迷信”的手段,认为这两种文学形式对大众有着深刻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识字率低,大多数中国人无法直接阅读文学文本这个因素,我们在客观上或许可以认可戴遂良的这个观点。那时的文学文本只起到中转站的作用,少数有阅读能力的人将通过阅读获知的故事再讲述给邻里亲朋,邻里亲朋之间再将这些故事口耳相传。而戏剧因其直观的表现形式更是起到非常大的传播作用。这是从本文还原至口传故事的逆向过程。
戴遂良力图通过文学作品证明中国文化中的基督教义成分,这一出发点决定了他在处理中国文学文本时的一些倾向。在《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中,戴遂良难以按捺其作为耶稣会士的冲动,时而插入自己的评价,有时还将中国的某些信仰与基督的教义进行比较,或寻找共同点和差异,目的是方便传教士读者对中国信仰的理解和日后的传教工作。
在《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中提及基督性及对中西信仰差异作出说明的地方有 25 处之多。在《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中也处处插入自己的诠释和读后感,在译文最后还不忘加注说明,这更意味着戴遂良所构建的文本是封闭的。一个封闭的文本有专门的用途,有固定的使用方法,有固定的读者群(Eco,1984:8)。
而文本的开放性是文学文本乃至一件艺术品的重要价值所在。一个开放的文本可以由读者进行多种解读,期待着一个有可能对其意向进行各种体验的合格读者(model reader)。
但这种解读应该限于文本意向范围(intentiooperis)。文本的意向实际就是“文本的内在连 贯 性 ”(internal textual coherence)(Eco,1994 :59)。 如果文学文本意向的一个方面是作为文学文本存在,我们便不能把这个文本当成广告词或宣传书解读,甚至不应有意识地去审视文本的性质。文学文本的合格读者应沉浸于故事(如果作品形式是小说)中不能自拔,而不应去揣摩作者为何要采取某种写作方式。
超出文本意向的解读在艾柯看来是对文本的使用而已。例如,在读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时,假若读者推测欧几里德有喜好晦涩黑暗事物的癖好,这个读者就已经超出了遵循文本意向进行解读的范围,他是在使用《几何原本》这个文本(ibid. :57)。戴遂良对《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中一系列名着节选的限定性说明(这些说明在该书前言中分门别类地列出)、所加的批注、法中对照的排版方式以及关于阅读注意事项的标识等都是属于文本外部的行为,都破坏了原着的文学性,应归入使用文学文本的范畴。这同时也是一种呼吁读者使用而不是解读文本的举动。
五、《现代中国民间故事》的翻译策略
戴遂良使用文本的行为还体现于他的具体翻译活动。对《现代中国民间故事》译文的处理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来华耶稣会士快速了解中国文化的需要。这具体表现为删改中国文学里不符合基督教理性的词汇及叙事方式。
从基督教教义出发,他极不认同的是中国文学里的志怪成分。因为志怪并非欧洲的传统体裁,难以阅读。法国的志怪体裁诞生于18 世纪末,第一部法国志怪文学作品是卡皂特(JacquesCazotte)1772 年创作的《 魔恋 》(Le DiableAmoureux),后来该体裁受到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和超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视。由于托多霍夫的发掘,志怪文学才又在大学课堂上得到一些关注。据格尔玛齐(Salma Guermazi)的研究,志怪文学之边缘化是由其所涉主题超出人们的理性思维习惯而致,而且它在客观上对上帝赋予的人之本位构成质疑(Guermazi,2007:1)。 这种文学在叙事上也相对幼稚。在《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中戴遂良(Wieger,1922 :405) 写道 :“ 道家文学怪异至极。 从不需证据,从不质疑,从不感到诧异。我们只发现每个术士都有一套灵验的把戏。”志怪文学的特点是介乎现实和超自然之间的悬疑(Todorov,1970)。这种超自然悬疑所营造的氛围是对读者感性的强势侵袭,令读者处于无暇推理的境地。自幼接受笛卡尔式教育的法国人难以适应这种文学,于来华耶稣会士而言这更有困难,因为志怪文学违背了基督教的推理习惯。但理解这些素材又同时是来华传教不可或缺的一步,戴遂良相信去掉这些推理上的障碍就可直触中国人同样充满基督特性的内心世界。鉴于此,他选择让译本尽可能直接地反应中国人思想中具有基督情结的部分。这一点在其《净土宗》一书书末可见一斑。
一言以蔽之,为了让来华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更容易接受耶稣会的命题,即中国人有被授上帝恩泽的资质,戴遂良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调整处处以强化中国文化的基督因素为目的,中国文化中一切有悖于基督教的因素都为戴氏所弱化。戴氏的译介策略体现于三个方面:
故事情节、叙事方式和词汇语义。具体做法是删减原文情节、添句添词、改词、更改标点、语义义素的择弃和拆解分散。
在故事情节上,戴遂良采取节译手段,主要删除了不符合基督教推理的情节片段。例如,他只将《牡丹灯记》的前面一部分译介给耶稣会士读者,却删除了乔生、符丽卿和纸人金莲后来被押赴九幽之狱的结局以及魏法师因泄露铁冠道人之行踪而患失语症的故事(瞿佑、林芑、尹春年,1564 :26-27),大概也是因为他认为其缺乏质疑精神和缜密的推理过程。魏法师仅仅因为泄露铁冠道人的秘密就患上失语症在耶稣会看来是缺乏逻辑关系和理论依据的。这更是因为戴遂良未能从根本上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形而上学的体系。
在涉及志怪文学时,叙事方式自然又同故事情节密不可分。由于自身所处的话语体系,更是出于传教的需求,戴遂良除了诉诸肢解原文本,大段删掉无用部分这样粗线条的手段外,在翻译保留的部分文本时,他主要通过篇章和字词处理,在译文中实现叙事上和语义上的归化。《牡丹灯记》开篇乔生与符丽卿相遇本身就是异常荒谬和违反耶稣会士推理习惯的。
至正庚子年,即1360 年,一个国色天香的妙龄女子(符丽卿)在深夜轻易跟随一个陌路书生回家,并与之“低回就枕,甚相欢爱”,是非常不符合常理的事。在戴遂良看来,来华传教士未必能够适应这一情节安排,在翻译时作了一些添词添句处理。他将“女忽回顾而微哂曰”一句译成 La jeune fille remarquace manège. Tournant la tête et souriant au jeunehomme, elle lui dit. 第一句是戴遂良添加的句子,中文意思是“这位芳龄女子发现了乔生的把戏”。有了识破乔生伎俩这样的铺垫,下文的进展就显得顺理成章一些,译者就可以安排女子利用乔生想占便宜的心理施展各种有利于女子自己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铺垫,故事便会不符合一个阴谋的发展顺序,正如戴遂良自己所说,作品原文作者“从不质疑,从不感到诧异”。如果采取完全忠实原文的翻译,来华的耶稣会士恐怕无法进行顺畅的阅读,疑窦丛生会阻碍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内涵。
原文中以“‘……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尸柩及生,殡于西门之外”(同上:30)一句将怪异性推向高潮。而在译文中,译者在叙事成分“遂以尸柩及生,殡于西门之外”前给故事人物魏道士额外增加了一句独白 Quoi qu’il ensoit, ce vampire ne restera pas plus longtemps ici.如此明确地指出问题所在,提早打断了志怪小说所维系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特质(incertitude)。
况且vampire为西方所熟知,不会增加额外的来自异域的怪异因素(这也是下文将提及的语义上的弱化策略)。戴遂良经过深思熟虑,让vampire 一词出自于故事人物之口,故意让读者相信故事的虚构性和杜撰性,以此表示他作为耶稣会士对该词指称(référence)的客观真实性持保留态度。又如“女无难意,即呼丫鬟曰:‘金莲,可挑灯同往也。’”译为 Sans répondre,la jeune fille rappela la bonne qui marchait devant.‘Revenez, Kinn-lien, lui dit-elle; éclairez-nous.’译者选择 sans répondr(e没有回答)译“无难意”是为了让情节显得不那么突兀,让读者不会觉得女子无来由地过分主动。戴遂良还在译文中用替换标点符号的方式弥补原文意义上和叙事上的缺陷或不连贯。
例如,在翻译《牡丹灯记》中“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这句话时,他在法语译文的末尾以省略号替代句号,形成叙事上的留白,在不中断叙事的前提下将女子到底还说了什么或向乔生暗示了什么留给读者去想象。经过读者自己补充这个过渡后,下文乔生“趋前揖之”邀女子回家的更大胆举动才不显得突兀。省略号发挥了一种复调(polyohony)作用。通过标点的更改隐约可以看到戴遂良想改善志怪文学叙事唐突的缺陷,让《牡丹灯记》这份素材更符合省时有效地培养年轻耶稣会士的需要。一个词往往具有多个义素,对其中某个义素的选择和对其他义项的舍弃体现着译者的某种归化主张。这种翻译策略旨在弱化中国文化中的非基督色彩,或强化其中的基督色彩。
戴遂良将“鬼”这个文化负载词译成 morts(死人)。这个词的中文意思与基督教义不符。而morts 一词却是最中性的,丝毫没有违背基督教义的语义成分。鬼在中国是个复杂的文化概念,戴遂良在《中国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中说关于鬼的问题是个重大问题。他通过《诗经何人斯》中的一些诗句推测鬼是无形的,而且需要后人的祭奠才能安息(Wieger,1922 :55-56)。而前文中的“骷髅”在法语中的最佳对应是 tête de mort,即便仅仅从呼应前文的必要性考虑,于戴遂良而言这一选择也是妥当的。对于其他文化负载词,如“妖气”和“妖道”,戴遂良不侧重于“妖”字,而是分别译作 effluvesde malheur( 不幸之气息 ) 和 méchant tao ste(凶恶道人),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又如,“不意作怪如是”译为 Est-il possible que cettepersonne se conduise ainsi“.怪”这一义素完全消失。该句话在原文中是感叹语气,在译文中则为感叹和质疑的语气,可见译者在处处弱化“怪”这一义素的语义。而且原文的人称是省略隐藏的,在译文中则为 cette personne(此人),鬼怪因素又一次弱化。
戴遂良甚至将“鬼”的义素束分散开来,将某些义素散布在原文中本未出现“鬼”字的地方。例如,他将“忧怖之色可掬”译为N’osantpas passer la nuit chez lui, de peur d’être visitépar le spectre.spectre 在法语亦有鬼的意思,只是在语义上更偏重于幻象这一义素。戴遂良选用 spectre 一词是为突出鬼幻觉不实的一面,以弱化中国传统中的非基督性质。女鬼符丽卿在乔生看来“韶颜稚齿”,而在邻翁看来则是“粉妆骷髅”,也正暗合鬼之幻象性。spectre一词还将全文所有的视觉成分归纳进来。篇末的“云阴之昼,月黑之宵,往往见生与女携手同行,一丫鬟挑双头壮丹灯前导,遇之者辄得重疾,寒热交作”(瞿佑、林芑、尹春年,1564 :30)也属 spectre 范畴。
这一系列翻译策略的采用有助于拉近中西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和清除来华耶稣会士在认识中国时所遇到的概念性障碍,增强他们的信念,这也是耶稣会所鼓励的。但无论如何,戴遂良对中国神祗、鬼怪和妖魔这些范畴又是表示理解和尊重的,《现代中国民间故事》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涉及这些范畴,如河神、女鬼、城隍、社公等。因为这是理解传统中国无法规避的思维模式。在实在无法回避时,戴遂良在译文前写有一系列导论 , 在导论里他尽量用基督教甚至是新教的一些名号来翻译中国的神祗鬼魅。例如,他将关帝译作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Etre suprême。
而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Etre suprême在天主教里又是对教皇的称呼。在谈及阎王时,他所使用的术语所包含的义素则更能体现天主教色彩,如 me,réincarnés,bilan desexistences précédentes 以及 communion。 而这每一篇导论又约束和解释着后面的译文。
六、结语
通过对《现代中国民间故事》的分析,并结合我们对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观察,发现法国研究中国文学者大致可分为两类,儒莲(Stanislas Julien)和雷威安(AndréLevy)等人属第一类,是对中国文学深怀挚爱者;另一类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出发点则是超出文学范畴的,包括伏尔泰(Voltaire)和于连(Fran ois Jullien)。伏尔泰创作《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是为了用他者的言行理论来印证自己的哲学观点。而于连则是福柯(Michel Foucault)另类空间(hétérotopie)理论的实践者,他企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与西方思维对立而未受西方思维侵扰的他者性(altérité)。他们关于中国文学的探索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文学于他们是工具。戴遂良则是因来华传教士的培养需要而译介中国文学。第二类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有时为达到目的甚至不惜改造中国文学这个工具,上述戴遂良的翻译便是最好的例证。
参考文献:
[1] Ambs, P.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 aise[M]. Paris: CNRS, 1994.
[2]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3] Bal, M. Narratologie Les Instances du Récit[M]. Paris: Klincksieck, 1977.
[4] Bal, M.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5] Bouvet de Cresse, A. J. Précis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Jésuites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eur Ordre[M]. Paris: Librairied’Aimé Payen, 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