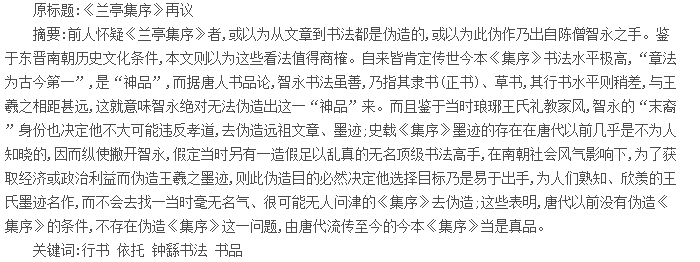
近五十年前,关于《兰亭集序》(以下简称《兰亭集序》)真伪的论辩[1],曾轰动一时。郭沫若先生坚持认为《兰亭集序》无论文章或书法,都不出自王羲之手笔,而“乐于肯定”全是他“末裔”僧人智永所“依托”[2]。这一看法,立即遭到“驳议”。谁是谁非,众说纷纭。只因不久十年动乱开始,论辩方才不了了之。
我于书法完全是门外汉,只因一个偶然原因而得以拜读了《兰亭论辩》有关文章,勾起了兴趣,经过查找一些古代书法史资料,竟然也形成了一点肤浅看法。兹不揣谫陋,提供出来,请方家哂正。
一
我是站在“驳议”诸先生一边的,不同意郭说。但诸先生的方法主要是针锋相对,就事论事[3],我则从另一角度着眼,予以配合 :即结合东晋南朝历史文化条件,认为《兰亭集序》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当时不会有人伪作《兰亭集序》,智永更不可能,而且他也没有这个水平。
我这样说,有两个前提:(一)肯定《兰亭集序》的书法水平极高,这是唐宋以来的定论。如宋苏轼诗“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4],“遗迹”(指各《兰亭集序》临摹本)犹“龙腾”,真迹自必更高明。元赵孟 则说 :“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禊帖》(按即《兰亭集序》)为最善。”[5]明董其昌也说 :“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6]
正如郭文所肯定:自来“《兰亭序》被认为法帖第一”,“《兰亭序》是佳书,是行书的楷模。这是不能否认的”[7]。
(二)《兰亭集序》墨迹名气并非从来就很大,在书法界家喻户晓,应该说唐代以前它几乎是不为人知的。
据我国古代第一部汇辑并选录唐代以前书法资料的总集—《法书要录》记载[8],凡唐以前人论述书法并涉及作品者,从没有提到过《兰亭集序》之名。特别是如书法高手梁武帝与陶弘景讨论书法[9],一再讲到王羲之,评论“逸少(墨)迹”。可他们只提《乐毅论》、《太师箴》、《劝进》、《洛神赋》;陶弘景甚至说“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东方朔像赞》、《洛神》”;他还细论“《乐毅论》书乃极劲利,而非甚用意,!!
《太师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10]。全都一字不提《兰亭集序》,更谈不上评价了[11]。充分证明《兰亭集序》在唐以前书法界并不为人知晓。这是本文的另一个前提(按郭文也主张梁武帝等未见《兰亭集序》墨迹,但由此所推出的《兰亭集序》文章、墨迹“乃梁以后人依托”说[12],矛盾却是不少的,见下)。(图一至图五)二。
如果承认以上两个前提,依据郭文“依托”《兰亭 集 序 》 的 时代 又在 南朝梁以后,那么问题便来了。首先便是当时谁有如此高超的书法水平能“依托”出《兰亭集序》来?须知郭文所说“依托”,便是伪造。从文章内容看,郭文只同意清末李文田说,承认出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的《临河序》是原文,凡传世《兰亭集序》与之不同的文字,全属伪造。所谓“(传世)《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之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其中“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是“增添”的,亦即伪造的[13]。从书法看,郭文也沿李文田说,认为“文章都是依托的,墨迹不用说也是假的了”[14]。可是,如果这些说法可信,文章先不说,首先一个问题便是:当时谁能伪造出《兰亭集序》墨迹,使唐太宗为之痴醉,用以陪葬昭陵?又使一千多年中诸顶级大书法家皆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查书法史资料,梁陈之时找不出这样一位书法高手[15]。
郭文所“乐于肯定”的智永,同样不够格,而且他的王羲之“末裔”身份决定他也不可能“依托”《兰亭集序》。
(一)的确,智永书法水平相当高[16],当被认为具有“依托”的基本条件。郭文具体讲到智永“铁门限”和“退笔冢”的“故事”[17],大概也是为了陪衬这一点。可是智永书法水平是否高到足以“依托”出传颂千古之《兰亭集序》的程度呢?恐怕未必。因为如按唐人《书断》中的评价,智永书法虽是“妙品”,但离王羲之的“神品”还差一个档次。更重要的是,即就这“妙品”言,智永擅长的也只是“隶书”、“章草”、“草书(即今草)”[18],他的“行书”则归入更下一个档次“能品”之中,这与王羲之“行书”归入“神品”[19],相差该有多远!何况这只是张怀瓘《书断》中的标准,如按同时代李嗣真的标准,智永书法仅为“中中品”,前有“中上品”、“上下品”、“上中品”、“上上品”,而王羲之则更在再高一等的“逸品”中[20],差距就更大了。李嗣真还说智永书法“精熟过人,惜无奇态”[21]。试问:这一书法水平,说他“依托”出传颂千古,“奇态”迭出的《兰亭集序》墨迹,能让人相信吗?不仅如此,从另一角度说,既然如郭文所说《兰亭集序》本来并无墨迹,如要“依托”,自然哪一种书体都可以,则作为智永说,为使人们信为真迹,最保险的自是使用自己所擅长的书体(如草书),为什么却撇开这一书体不用,而选择了并不太擅长的“行书”来“依托”?这样书法质量很可能会降低,从而增加了被揭发伪造的危险性,如果“依托”者是智永,他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呢?
(二)智永既为王羲之“末裔”,则他“依托”远祖《兰亭集序》之事,也不能不让人费解:
1. 是为了抬高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吗?则当时王羲之书法已被视为“上之上”品“,贵越群品,古今莫二”[22],“依托”《兰亭集序》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有何必要!何况“依托”之事如被揭发,很不光彩。智永究竟所为何来?
2. 如果确如郭文所说,《临河序》就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全文,则智永为何不一字一字照原文书写,却要“删改、移易、扩大”,“增添!!一百六十七字”?而据郭文,永和九年修禊,凡参加者所赋之诗“全都留存下来了”,则作为修禊概述的《临河序》,即使墨迹欠缺,文章内容在当时自同样必留存[23],所以刘孝标《世说》注能随手拈来(纵使此《临河序》原来流传不广,经刘孝标这一注,也应为梁陈两代人所知晓)。如果这样,智永伪造其墨迹时又大量“增添”文字内容等等,岂非画蛇添足,难道不怕“依托”之事立即被人识破?
3. 智永作为王羲之“末裔”,“依托”《兰亭集序》比他人还多了两条罪名:擅改远祖文章,伪造远祖墨迹,有违琅琊王氏的礼教家风与孝道[24]。特别是如果改变的是一般内容也就罢了,现在如郭文所说,修禊时王羲之毫无悲观心情,他性格“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这就是说,认为通过“依托”,智永把他的远祖涂抹得完全成了另一个人[25],在那个重视礼教和孝道的家族和时代,他为什么要这么涂抹,这种可能性大吗[26]?
由此可见,智永不但不具备“依托”《兰亭集序》的书法水平,而且琅琊王氏“末裔”的身份,也排斥了他“依托”《兰亭集序》的可能。
为了证实《兰亭集序》不伪,下面再作两点补充。
其一,由于郭文在论述智永“依托”之事的同时,作为背景,还曾说梁以后“依托临摹的风气”“盛极一时”,其中包括伪造王羲之的作品[27],那么从理论上说,有没有可能《兰亭集序》墨迹虽非智永“依托”,却由当时一位尚无名气,未为人所知,作品又极少的顶级书法高手(所以梁以后各书论、书品论都不及其人)所伪造的呢?为了考证更严谨一些,试对这一假定作一探讨。
如果存在这一顶级书法高手,则只能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他虽然尚无名气,却自信书法水平极高,将来墨迹必定传颂天下后世,如果这样,则他为什么要以书写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不直接书写自己极少的文章、作品,以扬名千古呢?可见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这一顶级书法高手并不自知书法水平拔尖,在如郭文所说临摹风气“盛极一时”风气下,伪造王羲之墨迹虽有可能,可其目的不外乎两种:或是为了卖一个好价钱,属于经济利益,或是为了谄媚皇帝、贵族,讨取好感,当是政治利益[28]。而这又都难以解释以下问题 :
1. 他为何不挑选当时公认的王羲之已有墨迹的某些名作如《乐毅论》等临摹[29],而要去找一个一直无人提及,并且从未见墨迹的《兰亭集序》,无所依傍地模仿王羲之行书笔迹书写?首先临摹要比仿写更容易让人信以为真,而难度甚大、破绽自多的仿写则容易079OURNALJFOANIONALTUSEUMFOHINAC招人怀疑 ;其次挑选公认已有墨迹的名作,也比找默默无闻,是否留有墨迹尚不可知者容易出手(经济),或讨取当权者欢心(政治)。这个高手既要伪造名作,为什么在这两点上正好全都相反呢?
2. 当然,也可能这一高手排除公认名作,单挑不为人知的《兰亭集序》,意在爆冷,要以新发现墨迹为由,出奇制胜。可是如果这样,因《临河序》如郭文所说已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全文,则他为何不完全照原文书写,却要去增添删改等,画蛇添足,使伪作轻易便被人识破(与前述智永情况同),经济或政治利益全都泡了汤?
3. 不仅如此,纵使当时《兰亭集序》文字全与今本同,郭文之说有误,这一顶级书法高手并未增添、删改等,而是照原文书写,以伪造《兰亭集序》墨迹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梁陈之时书法崇尚隶(正)书、草书,而行书虽流行,却一直不被看好,难登大雅之堂。
这一高手作伪既旨在取得经济或政治利益,利用《兰亭集序》一文爆冷也就可以了,因为毕竟它还是王羲之作品。至于伪造墨迹,由于当时从无《兰亭集序》墨迹乃行书一说,他为什么不迎合风气(如用草书),以求尽快出售或让对方满意,而要用行书书写,去冒遭到冷遇的风险呢?既用行书书写,自然便是不存在这一书法高手伪造《兰亭集序》墨迹之反证[30]。
其二,在《兰亭集序》真伪论辩中,支持郭文者,还多有一个共同的论点,这就是主张在书学发展史上真书(正书)即楷书(包括略有变化的行书)始于齐梁或隋唐[31],力图釜底抽薪,从根底上揭示用行书书写的《兰亭集序》既称出于东晋,则必为伪作。可是此说显然与传统史料相矛盾。早在西晋,卫恒已说“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刘宋王愔也说钟繇已“善行押书(即行书)”;刘宋羊欣又说“行狎(押)书”是钟繇书法的“三体”之一 ;南齐王僧虔同[32]。再如《晋书·王岷传》,王岷出身琅琊王氏,乃王羲之堂侄,他也“善行书”。特别是他还曾专写《行书状》,盛赞行书水平胡昭“壮杰”,钟繇“精密”[33]。以上这类史料,并不难找,主张楷书、行书始于齐梁或隋唐的先生应该熟悉,可是他们全都似乎视而不见,径直自说自话。试问,像这样论述显然不周密的新见,它们能有说服力吗[34]?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早在东晋之时行书已经流行,并非始于齐梁或隋唐 ;而在两个前提条件的决定下,《兰亭集序》既不可能由智永“依托”,梁以后其他书法高手也不会去伪造。
结论是,《兰亭集序》文章、书法当出自王羲之手笔(图六至图十一)。
三
那么为什么《兰亭集序》在唐以前又不为人所知呢?我以为情况当是这样的。
(一)《兰亭集序》墨迹一直存于王家,但因所用书体为行书,而行书在东晋南朝虽已颇为流行,却还远不如隶书(正书)、草书受到重视。其证如下:
1.《宋虞和论书表》综论当时流行书体,涉及“草体”、“真正”、“草法”、“正草”、“或草或正”、“草正”、“章草”、“飞白”等十余处,均不及“行”;只在一处提到“孝武(宋孝武帝)撰子敬(王献之)学书戏习,十卷为帙,传云戏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35]。
就是说只在讲到“学书戏习”时方才带上“行”,正反映对它的不重视。
2. 我国古代最早定出“书品”九等(从上上至下下)的《梁庾肩吾书品论》,其序言总论只讲“草正”、“隶书”、“正书”、“草书”、“草隶”等,而一字不及“行书”;在九品分论中提到“草书”、“真草”、“草正”、“隶草”等,同样不言“行书”[36]。
3.《梁庾元威论书》一上来便说写好“正书”、“草书”,“章表笺书,于斯足矣”。下面细分各种具体书体,也只在讲到一种“九体书”时提及其一为“行押书(行书)”,可是接着便说“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仍然把它概括于真书、草书之中[37]。
4. 现存梁武帝、陶弘景论书法之九封信,无一字言及“行书”,即使讲到“逸少好迹”,涉及书体,也只举“飞白”、“正书”[38];两人讨论、欣赏,多次提到的《乐毅论》是正书,一再赞许的王羲之《黄庭(经)》、《(东方朔)像赞》,也是“正书”[39]。
5. 固然,《书断上》曾说 :“(宋)王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繇)善行押书是也。’”[40]粗粗地看,连顶级书法大师钟繇都靠行书“著名”,则当时行书地位岂能不重?其实不然,“多以行书著名”,并非“只”以行书著名,如联系其他史料,就可看出,它只能理解为当时行书已流行,工此书体著名者甚多,但并不意味它已被看重。其有力证明正是钟繇之例。据宋羊欣语:“钟书有三体 :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41]。所谓“铭石之书”,自指汉隶。用汉隶铭石,历代受到重视,不仅《隶释》、《隶续》载有大量实例;郭文所引东晋王兴之等五种墓志后说“基本上还是隶书(汉隶)的体段,和北朝的碑刻一致”[42],是又一新证。而所谓“最妙者也”,乃指钟繇的这一书体在“三体”中书写水平最高[43],同时它也有力说明钟繇首先并不是以行书著名,行书只是钟繇所擅长的次要书体,不能把钟繇“善行押书”视为行书受重视之证。这一点从行押书“相闻者也”这句话便可明白。按“相闻者也”,指的是互通信息,此处则指行押书写书信互通信息[44],当包括朋友聚会所撰彼此欢乐感慨之文如《兰亭集序》等。它写得比较随便。郑诵先先生便曾说 :“凡篆、隶、真、草各有一定规则,惟独行书,却没有一套规定的办法”,并引《书断上》“行书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而行”以证之[45]。正因如此,很长一个时期,行书不受重视,强证便是《梁庾肩吾书品论》定出上上品三人,专门论述钟繇、王羲之、张芝的书法时,竟一字不及三人之行书。在单论钟繇时也只说他“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46]。许昌、邺下均钟繇追随曹操父子之地。“碑”自指“铭石之书”,“牍”限于魏都“邺下”,自指官府公牍,用的当是三体中“传秘书”等的“章程书”,证明定钟繇上上品,是与“行押书”无干的。可见钟繇所善“行押书”,在书法界当时地位尚低。如果以为前引王愔语反映魏晋南朝行书极受重视,则庾肩吾岂能有此重大疏漏!按庾肩吾本人书法,唐人《书断中》将它归入“能品”《;墨薮》卷一又归入九品之“下中”(第八品),且说指“隶、行、草”[47];近人《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三章高度评价说 :“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庾肩吾的《书品》,是一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著作”[48]。庾肩吾既善书法,又善行书,《书品》又是全面评论之作,如果行书当时受重视,钟繇又确只以行书“著名”,他在《书品》中是绝不会一言不及的[49](图十二至图十七)。
(二)由于行书不受重视,所以《兰亭集序》的流传出现了以下情况。参见《唐何延之〈兰亭记〉》(以下简称何《记》)[50]:
1.《兰亭集序》墨迹似并未外传,当一直保存于王家,未为世人所知,自然也不存在流入梁宫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梁武帝、陶弘景论“逸少迹”均不及《兰亭集序》的原因,而绝不是因为它当时尚未为智永“依托”。
2.《兰亭集序》墨迹虽保存于王家,但因是行书,时代使然,并不很受重视。据何《记》“此书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如果王家知《兰亭集序》墨迹传颂千古的价值,怎不传归嫡长系,而留给旁支[51]?
3. 智永也不很重视《兰亭集序》墨迹,所以死后“遗书”将它传给他姓(袁姓)弟子辩才,而王家竟也无人计较。
(三)因智永“学书以羲之为师法”[52],自然会临摹手头王羲之真迹包括《兰亭集序》。他行书水平相对说较差(见前),临摹《兰亭集序》的可能性极大[53],但可以肯定,这类本子智永必定注明乃临摹本,并非真迹 ;所以这类本子传出,唐太宗见到后虽十分欣赏,仍知当另外寻找真迹[54],最后方得之于辩才处。在唐太宗的推崇下,逐渐形成摹拓、转摹《兰亭集序》墨迹之风 ;唐代全国南北统一,文化日益发展,《兰亭集序》所用行书又具有“趋便适时”的特点[55],再加上行书本身的艺术之美,如《书断上》所赞“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剑光芒,云虹照烂”[56],作为基础、前提,于是行书地位便随之得到提高[57](当然,唐太宗书写《晋祠铭》用行书,当也起着推动作用)。
总之,《兰亭集序》确为王羲之作品。其所以在东晋南朝未为人知,唐朝以后方名声大振,成为“天下第一行书”,是有一个曲折演变过程的。它绝非出于任何人包括智永的“依托”。
顺便一说,对于法帖中《兰亭集序》以至整个“二王手笔”均为“伪作”的怀疑,早在1936 年章太炎已发表《论碑版法帖》一文,予以驳斥,以为其说“似是实非”。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最后想说的是,《兰亭集序》墨迹从默默无闻到终于脱颖而出,名满天下,首先自然是它行书水平高超,后代无人能及;其次则是在行书符合文化潮流,逐步流行之时,它因为得到唐太宗这一特殊人物的赏识而声誉腾飞。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体现的,否则也可能《兰亭集序》便在悄无声息中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