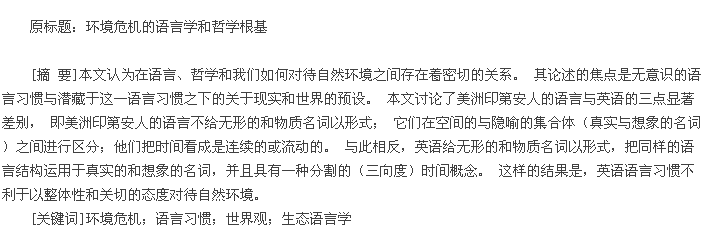
一、引言
提纳民族(Dene nation)注意到,尽管他们能够与像麦肯齐河(Mackenize)这样的北极圈河流和谐相处两万八千多年,但这些新来者(欧洲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已经使这些河流污染了。
在接下来这篇文章中,我提出在语言、哲学(或称世界观)与我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当一个人讨论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他可以区分出现实的两个向度: 客观现实和认知现实。 客观现实是指自然环境———空气,水,海洋,山,气候等等。认知现实是指人类的知觉和创造。认知的创造可以修改客观的现实,从搭建一个棚屋到竖起一个摩天大楼,从使用畜动力到建造核电站。 认知现实与语言密切相关,因为对客观现实的改造是被语言促进的。语言具有激发意象和复杂观念的力量。 观念起初是模糊的,慢慢地变得确定并变成结晶化的现实本身。 例如,当飞翔的渴望被适当地表现出来并开始起作用之后,它可能采取萨满教僧的飞翔形式,甚至带来飞机的发明。 语言因此被说成是人类大多数认知活动的源头。
将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与英语相对比,学者们已经指出美洲印第安人语言的三个突出特征:(1)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在真实的与想象的名词之间进行区分;(2) 他们不给无形的名词和物质名词以形式;(3)他们把时间看成连续的。 相反,英语把同样的语言结构用于真实的和想象的名词,不断地试图给无形的名词和物质名词以形式, 并且具有一种分割的(三向度)时间概念。
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英语语言的模型促进了离析的而不是整体性的知觉资源的倾向。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对现实进行分割的倾向。 举例来说,海森堡(Heisen-berg) 呼 吁科学中的观念的改变———他认为这种观念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观念开始,已经带我们走向迷途,———他敦促科学家们放弃物理理论中根本性的基本粒子理论。
一种对环境的整体感知要求我们对思想和言语中无意识地分割现实的习惯变得具有意识。这样一种感知的变化或许也促使一种我们语言习惯的变化。只要我们还把家中的水与河流或海洋中的工业废水区别想象,要避免水污染就会是困难的。
二、语言与世界观
种族语言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已经指出,我们的语言习惯, 亦即我们安排和解释客观现实的方式,对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一个共同体的语言习惯影响我们的知觉和经验,使我们预先偏向于选择某种特定的解释和行为方式。 “现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建立在一种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 语言习惯不仅仅包括一种语言,它还包括所有与这种言语类型相似的或由这种言语类型所暗示出来的价值。 例如,时间的客观化及其意味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一种世界观,正表明了语言塑造性的影响。 大规模的语法分类,诸如名词的用法、复数和时态等,都对我们对现实的知觉施加影响。例如,数量的分类(单数对复数)对一种广阔的既涉及人类世界也涉及自然的经验秩序进行解释,它表明了经验是怎样被综合和被分割的(如果它被分割了,什么样的经验被称作“一”和“多”)。
根据美国文献学者的研究,美国所有土著居民的语言,从北冰洋到好望角,就他们所考察到的来看,都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
学者们注意到,在不同的言语形式的基底存在着一种基本统一和惊人的一致性:(1)对物质名词个体化和对无形事物具体化并进行测量的倾向比较弱;(2)在真实的和想象的名词之间进行区分;(3)动词时态的差异不发达,时间被视作连续的而不是三向度的现实。
就物质名词的个体化而言,就是在物质名词和个体名词之间进行区分。个体名词用确定的轮廓表示物体,如一棵树,一根棍子,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物质名词表示一种没有边界的同质的连续体,例如,水,牛奶和酒。 在英语中,物质名词通过语言手段被个体化了,例如,一杯水,一扎酒,一杯咖啡或者一瓶啤酒。英语时常要求言语者以一种把指涉物分成无形式的和有形式的二项式来指涉物理事物。
与此相反,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显示物质名词的不确定性。它们既没有被以形体类型———如一条肥皂的方式个体化,也没有被以容器名称———如一杯牛奶的方式个体化。 定冠词“the”的使用,再一次说明了把物体从物质名词中分裂出来的习惯。英语中的复数和基数词有两种使用方法:用于描述真实事物的复数和想象事物的复数。 更确切地说,用于描述可感知的、 空间化的集合体以及隐喻性的集合体。
英语不仅测量树、车、男人、女人,而且测量快乐、满意、偏见等等。结果是,人们倾向于把经验客观化和对经验进行测量。例如,在家庭社会学中,男人和女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虐待”在儿童虐待、配偶虐待、身体虐待、情感虐待之下被分类。族群关系的社会学拥有测量社会距离的刻度。 尽管 10 个男人或者 10 棵树能被客观地感知, 但对社会距离进行客观感知却是困难的,因为,把社会距离放在一个测量的刻度上通常会歪曲社会距离的经验。
客观性在对时间的经验中也是成问题的。在英语(和所有的欧洲语言)中,时间都被客观化了。 然而,在经验的意义上,5 天是没法被客观计数的。 一个人只能经验一天,其他四天是通过记忆或想象在脑海中被唤起的。 由于时间的客观性,技术世界观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时间和循环的意识包含某种即时的和主观的东西,一种“变得越来越晚”的感觉。
结果是,有关时间的种种概念失去了与那种“感觉早些或晚些”的主观经验的联系,被客观化为可计数的量,而且这些概念往往被看做由单位构成的长度, 而这些单位又可以被划分为肉眼可见的英寸。
在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中,不同的术语被用于空间的或隐喻性的集合体。 在英语中,“年”、“世纪”和“十年”都是名词,他们被复数化或计数化,好像他们是可见可触的客体。 在这种方式中,对真实时间的主观经验已经丧失了,因为当我们使用这些词语时,那种“越来越早或越来越晚”的意识不能被暗示出来。在英语中,时间仅是一种阶段。这类的时间知觉类似于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旅行: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我们很快将会进入一个后技术的时代;我们穿越了中世纪。 正是这种时间的客观性导致把时间知觉为三种时态的系统。 与之相反,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将时间看做是由两种时态构成的系统,即较早的和较晚的。 这种对时间的理解更接近于人们所经历的时间持续性的主观感受。这种时间概念或许更接近于那种把人类意识作为经验实体的观念。 如果我们检验人类的意识,我们会发现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只有一个包含着复杂性的统一体———意识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同时存在的。
作为结论,由于英语一贯地把物质名词个体化或具体化(并因此把它们分裂),把空间或隐喻的集合体(包括真实的想象的名词)计量化,并把时间理解为三种时态的框架;它因此促进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存在被知觉为破碎的而不是整体相关或相对性地相关的。这样一种世界观使言语者预先倾向于对世界作出某种预期。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它通过把技术呈现为自动化的和不可避免的行进而加剧了一种无助的感觉。作为一种被均匀刻画的、无限卷尺的时间意象,激发了一种对不可避免性的幻景(vision),造成一种对于技术进步的盲目信仰,以对抗我们无助的感觉,抑制我们预见环境压力和改变我们的习惯以减轻这种压力的能力。
三、物质名词的个体化及其对环境的压力
现代技术世界观没有充分考虑这样的观念: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那些对我们来说看起来重要的差异都是表面上的。生物学告知我们,高级的灵长类动物和昆虫、小鸟、红杉树、病毒等等,都是蛋白质和核酸共同作用的表现形式。 所有的生命都是由细胞和细胞产品组成的,新的细胞只有在预先存在的细胞发生裂变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所有细胞在化学成分和新陈代谢活动方面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
然而,这种洞见在公众层面上的传播,被那种一开始就以清楚的生物学分类术语思考有机生命的倾向抑制了。 与此不同,这种抑制没有在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发生, 如提纳族(theDene),欧及布威族(the Ojibway),克里族(the Cree)部落。 对这些部落来说,人类与其他有机体的生命形式是一体的。 他们都是自然的体现,为了确保他自身和他的部落不受伤害,他们都必须被尊重和敬畏。
在因纽特人(Netsilik Inuits),欧及布威族人,克里族人,和西北海岸其他部落的世界观中存在的一个共识是:海豹,北美驯鹿,熊,鲑鱼,青鱼,都拥有强大的要求被尊敬的灵魂。人与动物处在一个彼此互惠的关系之中。 这些动物如果被虔诚地对待,就是有益的;如果不被虔诚地对待,它们就会带来灾难。 在狩猎中,这种因果关系被解释成拟人性的(personal)而不是生物学的或机械的。 如果猎人对动物表现出适当的敬意,动物就会把“它们自己送给猎人去杀”。这种因果关系的概念,也被应用于非生命的存在。 在纳瓦霍人(Navaho)的语言中,一个人不能让一个球去转,他或她只是把球预先存在的转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与这种因果关系的视野相一致,彻罗基族印第安人(Cherokee Indians),把亲属关系的术语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一切事物———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在宇宙中都有它的位置。新月被称作祖父———他提供庇护使人免于疾病和事故;太阳,一个女性,被设想为月亮的姐姐;河流被给予特别的崇敬———往河里扔垃圾被设想为会使他们发怒。 在普罗布洛(Pueblo)族中,太阳是父亲和首要的养料提供者;地球则是母亲;小鸟、动物、昆虫在必要时都会提供帮助,水、土地和庄稼都被称呼为人类和家庭成员。
这些把神人同形论归属于有生命和无生命世界的做法,被那些受一种科学世界观影响的人解释为迷信。然而,由于这种信仰,印第安人传统上怀着敬畏和关切对待有生命和无生命世界,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从不任意地损害自然环境,并且这种信仰系统是与海森堡的呼吁相兼容的。海森堡呼吁我们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分裂的、把人类置于支配地位的方式感知宇宙。
给有机生命划分等级并把人类置于金字塔顶端的倾向,类似于把杯子从水中分离出来。 人类站立在有机生命之外,假定他们可以对整个有机体世界施加权威。“自然能被支配”变成当代技术社会的指导原则。人类征服自然的现代观念正携带着这种习惯的全部暴力。 在过去,只要宗教世界观还保持着关键的调控性力量,人类作为支配力量的观念就会被一个更广阔的伦理框架所抑制。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世界观的发展, 宗教规约已经被扔到了一边,人类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已经对环境施加了肆意的影响。
在社会的水平上,个体化和区分实体的习惯表现在企业、国家和公众这三个范畴上。 企业是独立的私人实体,他对他的股东而不是对公众负责。国家被设想为作为企业和公众之间的调节机构起作用。 然而,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存在着权力的区分和差别。 国家通过三个步骤“调控”企业:首先是对受环境污染侵害的公众的诉求假装不知情;进而是承诺执行减排;很久之后是力图将安装预防污染设施的成本最小化。
三种不同的实体概念创造出一个有趣的场景:制造污染的企业拒绝减少倾倒他们的污染物,如果施以压力,他们就会以倒闭和减少工作需求相威胁。 面对这种威胁,国家官方往往倾向于让步。 相应的一个结果是,直接受害者遭受毒害,公众(他们是受害者的一部分)必须为他们自身的康复纳税,企业(污染方)实际上从毒害公众中获利。 通过这种方式,对社会的分裂性感知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在这里,每个人都受到影响但没有任何人负责。对社会成员进行个体化和分类的倾向忽视了一种事实,即环境的恶化也会影响到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因为他们同样也是公众的一部分。
企业在广告的帮助下,持续地在一个商品和服务快速变化的语境中分解和重释人的需要。
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社会化是高度结构化和稳定的。社会化进程规定了阐释个人需求的合理标准是什么,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是什么。人类的需要是被整体性而不是被个别性地知觉的。 例如,社区生活(家庭和修道院的生活)应该是满足人类的所有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秩序,可预期性,环境的可靠性)、爱、情感、归属感、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一个技术社会,不断扩张的经济目标和各种各样的商品供应要求需要的分裂。因为,人类需要的每一部分被分解成日益增多的越来越小的组成元素,对一个人来说,去简化需要或者在没有夸大的商品消费的情况下去想象满足需要是困难的。 蕾丝(Leiss)曾举例说明人们如何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客体,而每一部分都有它自己的需要。头发、面部、眼睛、手和脚,都需要使用化妆品去获得正面的自我规定性。
这种确认自我的途径是对环境的破坏,因为这些化妆品都创造了一些无用之物(污染物)。 与此同时,也不存在高商品消费就一定确保正面的个人身份的事情。
四、对无形事物的计算与对需要的分割
对空间化和隐喻性集合体使用同样术语的语言习惯与碎片化的需要紧密相关。计算(测量)的语言习惯不仅用于男人、女人、树、椅子,而且用于无形的事物,例如,用于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就使得人们容易把信仰寄托在对物质进步,亦即对消费品不断增长的可用性上,从而使之更喜欢选择一次性商品。 经济事务在日常生活中的优势,对生产效率的全神贯注,以及通过购买商品来获取个人需要的最大满足,都与对计算和测量的着迷紧密相关。 根据同样的逻辑,一座建筑要比一片小树林重要。 一座建筑能用美元和税收进行估价;相反,一片小树林(作为一片小树林)不能被估价或征税,除非它被简单地视作木材。 与此相似,计算由于引进高科技或中程技术节省的数百万或数亿的美元,要比深入探查由于引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而导致的失业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容易得多。 以量化的方式来看,每个个体的幸福被视作是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同一的。而社会的福利则被以消费品的不间断增长和生产与消费水平的持久上升来测量。当这些方面的水平上升时,人民相应地就会受到工业污染的伤害,而受害者也应当以数字形式来证明受害程度。
由于被数字所吸引,社会不断地为其持续增长的生产能力寻找借口,然而,如此的产品和消费仍然不能总是带来个人的满足。量化无形物的习惯为个人的所有努力确定了方向:为了获取个人满足而面向商品消费。 因为商品消费能够被量化,当代社会实践鼓励个人把商品消费置于日常关切的中心。与此同时,每当消费达到一个新水平,广告会促使人们对这种已达到的消费水平产生不满足感。
对于发展个人身份和寻求自我实现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例如,内省沉思,宗教仪式和工作环境中的创造性的自我表现的机会。 然而,这些选择不容易被量化。 虽然如此,我们现在拥有的大量的、可用的、来自前工业社会的信息表明,那些表达崇敬的仪式和典礼既间接地保护了环境,也提供了个人身份和自我实现。 在美国的奥加拉(Ogiala)印第安人中间,自我出现在自愿与自然世界发生关联之中。 在那里,“孩子被教授静坐和观看”。 在因纽特人(Inuits)中间,自我感出现在自愿忍受苦难和遭遇道德危险之中,出现在发现自己与宇宙相关联之中。
这种自我发展的途径,也发展了知觉、敏感和机警。
五、两时态与三时态框架
以三时态框架—过去、现在和将来看待时间的习惯,忽视了人们将时间作为一种流动性体验的主观意识。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既可以置身于将来也可以置身于过去。 站在“永恒现在”的有利位置上,决定能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做出,并且今天做出的决定可能成为将来的范型。 对时间以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计量的习惯,鼓励了把这些时间范畴视作分离的空间配置的态度。技术社会的思维方式是倾向于线性化的。 如果 A 导致了 B,那么达到了B 之后,A 就被抛弃了;如果 B 可以导致 C,那么达到 C 之后,B 就可以被抛弃了。 这种习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又使过去与现在和将来不相干。
任何有关重新考虑我们今天的浪费的生活方式的建议都会唤起一种退回到黑暗时代的意象。过去被视作险恶的、野蛮的和短缺的,而今天由于技术的帮助则被认为是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的。 事实上,对当今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多少自由和选择,但这一事实很轻易地被忽视了。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相信技术进步,将来就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和浪费的生活方式在二战之后被生活在高科技时代的人们广泛接受。 在二战之前,节俭、储蓄、仔细维护和重新利用个人物品的习惯,以及家庭制作食物和衣服的活动都是非常活跃的。 在二战之后,节约的习惯变为浪费的习惯: 物品的快速翻转,一次性物品的使用,与相应的资源枯竭和费弃物的累积,对市场刺激的持续关注,批量生产的食物和衣服对家庭制作的食物和衣服的替代。
每当我提醒我的本科学生早些年代的节俭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总是回应说:“你不可能让时光倒转。 ”这种反应与其说建立在经验的现实之上,不如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之上。从经验上来看,我们每 24 小时就让时光倒转一次。
六、结论
综上所述,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讨论了语言习惯、哲学假设以及技术型社会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这三方的关系问题。 我坚持认为,对物质名词的分割,对想象和无形名词的量化,以过去、现在和将来方式对时间的知觉,都是导致我们不能从整体上感知自然环境的因素。 让人担忧的是,这些语言习惯已经被其他文化所接受, 因为技术语言———英语,变成了世界语言。 随着英语的迅速散播,对其他文化来说,继续信奉不同的面向自然的价值观或许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这一灾难,既要求非专业人士,也要求科学界的思维和语言习惯的改变。这种改变类似于一个数学教授曾建议我所做的———一个人一旦开始学习数学,他就必须开始数学地思考。 为了关爱地接近自然环境,我们必须开始整体性地思考。 与把人类从生物圈中分离出来、保持我们不断进展的账务报表、 维持我们对幸福的量化测算不同,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对待自然环境的更具综合性的经验视野。 自然环境的质量必须被提高(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没被有毒物质改变的食物),自然(湖和河里有鱼,北极圈有北美驯鹿,热带雨林被很好地保存),美丽(吸引人的感觉)。这样的改变并非易事,它们也不能被立即实现。 30 年来发展起来的习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然而,仍然值得强调的是,如果有一些改变将要发生,它必须在感知的层面上并在语言的层面上被改变,因为这种感知就反映在语言中.
摘要本文研究基于对致谢类言语交际过程的经验阐释,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如何用语言的形式满足各交际参与者的需求。致谢类言语交际的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致谢者选择特定的话语形式实现表达感谢的过程。致谢类言语交际的核心是致谢者如何选择话语形式...
【摘要】:网络流行语不单是一种语言现象,更反映了社会事实和个体情感的深层结构。随着屌丝、高帅富、白富美等新兴词汇的蹿红,身体化的网络流行语现象开始凸显。该现象是指网络通行语言单位的要素构成或深层隐喻在语言法则和社会意义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