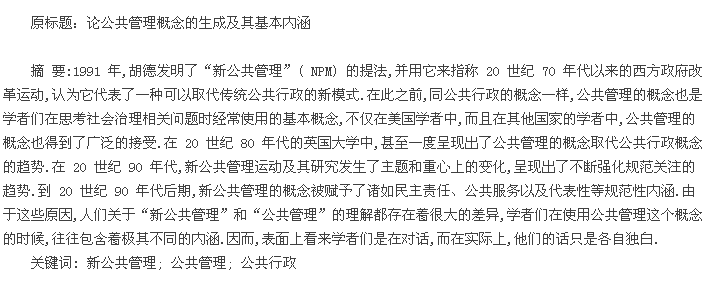
概念是一个学科的基本标志,对于公共管理学而言,“公共管理”这个概念是怎样生成的,是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人们必须了解的内容.因为,这关系到对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基本内容的理解.我们知道,公共行政的概念是起源于英国的,但是,只要人们提起公共行政这门学科,首先就会想到美国,事实上,正是在美国的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建构起了这门学科.相反的情况是,公共管理的概念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界得以流行,而且,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美国的一些公共政策学院的推动下,这一概念再度成为学者们乐于使用的概念.但是,公共管理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与公共行政相并列的概念,则得力于一场发轫于所谓威斯敏斯特国家,即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学术运动来看,在美国,“新公共行政”一词早在新公共行政运动之前便已成为学者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提法,而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早于“新公共管理”这一提法.今天,人们往往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起源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而新公共管理的提法则是1991 年第1 期的英国《公共行政》杂志发表了胡德的文章而正式进入学者们的视野的.当然,在此之前,与美国一样,公共管理的概念也已经在英国公共行政学界中流行开来,不同的是,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更多地受到了撒切尔改革的影响[1]7,1因而与诞生在政策学院或管理学院中的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有着内涵上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看到了撒切尔改革与传统公共行政实践决裂的决心,英国学者才在公共管理一词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并最终让这一新的公共管理概念取代了传统公共行政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从而成为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关键词.
一、“新公共管理”以前的英国公共管理研究
正如凯特尔( Donald F. Kettl) 所说,“从 1970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一场引人注目的革命席卷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管理改革,以求从公共部门中挤压出额外的效率---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更多产品和服务.威斯敏斯特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尤其是新西兰---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激进的改革者,并被广泛地视为样板.从韩国到巴西,从葡萄牙到瑞典,政府部门改革已经改变了公共管理”[2].显然,在这段话中,凯特尔所说的公共管理指的是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不过,与之同时也发生改变的是关于社会治理活动的学术研究,其中,在这场改革运动中,英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就首先出现了逐渐用公共管理的概念替换公共行政概念的学术发展轨迹.
我们知道,英国学者对公共行政的理解是与美国学者大不相同的,如果说美国学者对“政治---行政”二分原则总是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恋,那么,在议会主权的政治体制下,英国学者则从来也没有真正接受把政治与行政进行严格区分的观点.在英国,“公共行政是建立在对一个议会制政府的政治模型和一个关于国家结构及其运行的专业化的官僚模型的接受之上的”[3].相应地,“传统上,作为一个学科,英国公共行政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附属物,其实践也由一代又一代的政客与行政官员所主导,他们对于行政的政治背景以及服务于诸政治和行政价值之结合体的各种结构拥有一种共识”[3].当然,由于实践的演进,也由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影响,英国学术界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解也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把公共行政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学术子系统来看,则一直是英国学者的基本共识.
然而,从 1970 年代后期直到整个 1980 年代,这些共识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认为它们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则是失败的.取而代之的是对市场灵活而具有回应性的组织以及分权的强调.在公共部门研究的辞典中,”管理“一词开始取代”行政“的位置”[3].这种变化给英国的公共行政研究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于公共行政研究来说,撒切尔主义的到来预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年代.历届政府已经缩减了公共部门的规模,并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置于向那些处于贫困之中的人们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之上.这些压力促使公共行政研究者将这一学科的重心与方向从政治与伦理考虑调整到一个更加强调管理的取向上来.大量研究经费被输送到关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和效率的研究之中.教学也被推向了这一方向.尤其是本科以下的 BTEC( Business&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 项目,要求其公共行政课程拥有一种实质性的”技术“内容.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公共管理研究生课程被创造了出来,其中的某些课程包含了此前的公共行政课程内容.”[4]可见,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在 1970 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特别是当学术追求与改革实践相呼应时,公共管理的概念也就被刻上了撒切尔主义的印迹.
格雷与詹金斯( Andrew Gray and Bill Jenkins)看到,“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发展的结果包括: 将公共行政研究重新定义、分离和安置为公共管理,在这一领域中引入许多新的角色,以及重构相关的文献.
公共管理研究越来越多地不再被安排在大学中传统的政治科学部门,而是安排在商学院( 比如伦敦、阿斯顿与瓦利克大学) ,专门的研究机构( 比如地方政府研究所、高级城市研究学院) ,试图连接理论、实践与咨询世界的各种专业机构( 公共管理基金会与公共财政基金会) ,甚至各种颇具争议的”智库'( 亚当·斯密研究中心、欧洲政策论坛、经济事务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这些机构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但它们通常共享着一种不同于那些支持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研究的机构( 如前皇家公共行政学院) 所拥有的方法和视角”在这些机构的努力下,“公共行政似乎被描述为一个与一个过时的部门联系在一起的相当乏味的领域”.“许多人倾向于将这一领域视为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内容,而主要是面向有效执行的描述性的和条文性的分析……公共管理则被描述为一个紧跟时代步伐,切合像英国这样的美好新生意( brave new business)之需要的全新的动态主题.它是这样一种课程,可以在一个通过私有化而变得充满活力也更加苗条的公共部门中提供工作.它的支持者将它看成对于一个更高效社会的一种令人兴奋的现代回应”.如此强烈的对比之下,结果显然是不难预料的,那就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很快地就把公共管理视为对自身进行重构的方向.结果,“这一学科已经变得更加“实用”,更加职业化,而不是维护其传统的边界.特别是,在 PCFC( 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 机构中,“公共行政”这一老名称正在迅速地消失”[5].
不过,在钱德勒( J. A. Chandler) 看来,虽然公共管理的概念已经非常流行,而所谓的公共管理研究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相反,“朝向以公共部门管理为名的学位的运动可能更多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门名称中包含了管理一词的课程将比以公共行政为名的课程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许多理工学院和大学院系在没有对课程内容做出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将公共管理加到了公共行政之上,仅仅反映出了一种关于学生偏好的时代风气.
在全英学术奖项理事会上,一个由公共行政教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调查发现,让许多代表都看到,从行政到管理的更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课程,并且提供了许多可信的证据证明,如果对这一学科进行重新命名,则学生数量将会有更大规模的增加”[3].钱德勒认为,这样的更名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欺骗,但这种欺骗行为又正好迎合了公共管理支持者们关于市场决定一切的信条.因而,在短期内,它得到了一种变相的合理化,但从长期来看,它必将破坏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基础.“这种不道德的欺骗从长远来看将是一种自杀式的策略.
如果公共行政学者对他们的学科感到如此绝望,以至于不得不窃取另一个名称来描述它,则这一学科缺乏信心的状况就变得恶化,它离消失也就更近了一步”[5].也就是说,尽管公共管理的概念日益流行,但关于公共管理的实质性研究则处于一种极为贫乏的状态,所谓公共管理研究,其实只是对公共行政学的一种扭曲与剪裁.钱德勒的不满,正是对公共管理研究的这一现实状况的表达.
既然公共管理研究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对公共行政的一些主题的扭曲,那么,对公共管理研究产生怀疑甚至否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事实就是如此,钱德勒明确地反对公共管理研究: “将狭隘的公共管理研究---事实上就是被剥夺了政治、社会与道德内容的公共行政学---与公共行政研究相比,认为前者是有趣的而后者是乏味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一种缺乏政治或道德内容的关于管理技术的研究应当被看成是乏味且不真实的.相反,公共行政则是一个有趣得多且更有挑战性的主题,它要求不仅研究好的管理实践,而且分析其在一个广泛的社会与道德背景下的可行性.如果关于一个学科领域的一种更为广泛的分析解释比一种更狭隘的实际分析更加可取的话,则公共行政应当在研究的深度、刺激性和有趣性上获得轻而易举的胜利.”[5]在钱德勒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与美国不同的情况.在美国,由于公共管理研究存在着 B 途径与 P 途径两种不同的途径,因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包含着对公共行政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而且,这种对公共行政概念的不同理解实现了公共管理概念建构上的相互牵扯,起到一种制衡和“中和”的作用,以至于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倾向不会显得过于激进.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在英国由于缺乏 B 途径和 P 途径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从而在管理主义的方向上前进得更加坚决,公共管理这个概念显得更加偏激,成为完全反公共行政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试图维护公共行政研究传统的钱德勒表达了他的激烈反对意见.
不过,在滚滚涌动的市场大潮面前,钱德勒对于公共行政研究所持的乐观态度注定是悲剧性的.1990年,《公共行政》杂志增设了一个“公共管理”专栏[6],公共管理研究完全攻陷了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阵地.1991 年,该杂志发表了克里斯托夫·胡德的著名论文《一种普适性的公共管理?》,论文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正式命名为“新公共管理”( NPM) ,并通过对这一模式要素的经典性归纳而对 70 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浪潮作出了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也将英国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推向了整个世界.
二、何谓“新公共管理”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里根革命”在时间上要晚于撒切尔的“私有化”,但即使在“里根革命”之前,市场化与分权等主题也并不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专利”,相反,无论是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还是在尼克松的“新联邦主义”中,分权都是行政改革的一种基本取向,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7],“市场化”事实上已经发展到了催生出“再私有化”[8]、“第三部门”[9]等概念的地步.但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这一类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内容已经极度泛化了的公共行政的内容,而没有与公共管理的概念建立起独特而稳定的联系.所以,在美国,公共管理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由政策学院加以使用的专门术语.在英国,公共行政概念包含着浓烈的政治属性,致使那些具有明显“去政治化”色彩的主题与公共行政的概念相冲突,公共行政概念不得不被归入到公共管理的概念之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的不同特征.我们从钱德勒的叙述中又可以发现,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在含义上也存在着不确定性,既有人试图将其与撒切尔主义的政府改革相联系,也有人只是把它看成公共行政学中的技术方面.因而,学者们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是比较随意的.1991 年,胡德发表了《一种普适性的公共管理?》,明确地使用了“新公共管理”的提法来指称以撒切尔改革为代表的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为此后英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公共管理研究开辟出了一种不同于美国的途径.
胡德指出,“新公共管理”( NPM) 的兴起是过去 15 年里公共行政中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潮流之一.尽管本期杂志中其他论文所报告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英国的经验,但 NPM 绝不只是英国独有的一种发展.NPM 的兴起与其他四股行政“元潮流”有关,它们是: ( 1) 减缓或逆转政府增长---在公开的公共支出与人员上---的努力; ( 2) 从核心政府机构转向私有化与准私有化,并重新强调前者在服务提供上的“辅助性”; ( 3) 自动化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 ( 4) 一种更加国际化议程的发展,除了公共行政中单个国家专业主义的旧传统以外,日益聚焦于公共管理、政策设计、决策风格与政府间合作的一般问题”[10].更准确地说,“NPM 的起源可以被解释为两种不同理念的联姻.一方是“新制度经济学”.它建立在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二战后公共选择、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婚姻”中的另一方是公共部门中一系列企业类型的“管理主义”浪潮的最新发展,它所继承的是国际科学管理运动的传统”.胡德看到,尽管都可以被归入 NPM 的范畴之中,但在不同国家中,NPM 的侧重点则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在“威斯敏斯特模型”传统之内,“婚姻”双方的相对优势也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例如,在新西兰的独特环境下,公共选择、交易成本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综合明显处于优势地位,造就了一场具有不同寻常的一致性理论驱动的NPM 运动.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企业类型的管理主义则更加突出,造就了一种更加实用主义而在理论上不那么优雅的 NPM 或“新泰勒主义””[7].
不过,如果抛开上述这些差异的话,那么,不同国家的 NPM 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共性的,胡德也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概括出了构成“新公共管理”的七大要素: “( 1) 转向更加分散化的公共组织,并成为提供公共部门产品的独立运营单位( 每个都是独立的,具有事实如果不是法律上的独立组织身份,在资源决策上进行更大程度的分权,并处于一场朝向单行预算、任务陈述、业务计划与管理自主的运动之中) .与这一公司化的运营方式相对的则是通过一个单一集中单元中的“半匿名”组织提供所有公共服务的进步主义公共行政( PPA) 方式,这种方式拥有详细的适用于全机构的规则、关键操作领域中的共同服务供给,以及对工资谈判和人员配备水平的事无巨细的中央控制.( 2) 转向公共部门组织之间以及公共部门组织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更强竞争.与朝向一种更具竞争性的方式的目标相对的,是将准终身制的“指定”职能指派给公共部门组织的 PPA方式,也就是被无限期分配给特定“特权”生产者的圈养市场.( 3) 在公共部门内更大程度地借鉴广泛采纳自私人部门中的管理实践,而不是像 PPA 一样,使用所谓专属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 4) 更加强调资源使用上的有序性和节约性,并积极寻找更加低廉成本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替代方式,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制度连续性、机构维持与政策发展上.( 5) 更多强调“抓手管理”( hands - on management)( 即高级管理者通过行使裁量权来对公共组织施以更积极的控制) 而不是传统 PPA 的“放手管理”( hands - off management) ,后者所涉及的是在公共部门组织高层的相对匿名的官僚,旨在防止被任人唯亲与打击报复的人事管理规则严格地包围起来.( 6) 强调根据所要提供服务的范围、层次与内容来为公共部门组织制定更为详细和可以衡量( 或至少可以检验) 的绩效标准,而不是相信公共部门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 7) 尝试依据预先设定的产出标准( 尤其根据以报酬为基础的在职绩效而不是教育等级) 而以一种更加“自动平衡的”方式来控制公共组织.”
显然,无论是相对于美国的公共行政概念,还是相对于英国传统上的公共行政概念,以上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新的要素.因而,胡德把包含这七大要素的 NPM 看成是主要形成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传统公共行政 PPA 的一种替代模式.胡德认为,“对于进步主义公共行政( PPA) 而言,民主责任取决于对注定与之相伴的腐败、浪费与低能的限制……进步主义公共行政的责任范式强调两条基本的管理原则.其一是从连贯性、道德观、工作方法、组织设计、人、奖励以及职业结构等各个方面保持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显著区别……其二是通过一个旨在防止任人唯亲与腐败的复杂的程序性规则结构来缓冲政治与管理裁量权的行使,并在政客与特定公共服务“信托”的稳定监护人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而作为 PPA 的替代模式,“NPM 包含了一种关于公共责任的不同理解,拥有不同类型的信任与不信任,因此也拥有一种不同的追责方式.NPM 奠基于对PPA 两大基本原则的颠覆,即缩小或消除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差异,并将所强调的重点从过程责任转向一种以结果为依据的更强的责任要素.审计是这一新的责任观念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它反映了对市场与私人企业方法( 不再被等同于有组织犯罪)的高度信任,特别反映了对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 现在被视为预算最大化的官僚而不是伪苦行僧)的不信任.因此,后者的活动应当受到审计技术更严厉的核算与评估.NPM 的理念通过经济理性主义的语言而得到了表达,并得到了高级公共职位中新一代的“经济官僚”( econocrats) 与“审计官僚”( accountocrats) 的推动”.在这里,胡德从责任的角度阐述了 NPM 与他所理解的作为传统公共行政代表的 PPA 的基本差异,并提出了用 NPM 替代PPA 的主张.
作为《公共行政》杂志的编辑,罗兹( R. A. W.Rhodes) 在这期杂志的介绍文字中呼应了胡德关于新公共管理的提法: “1980 年代见证了一种坚决的努力,要在英国政府的所有层级上贯彻经济、效率与效能的'3E“标准.作为一场既不局限于”3E“也不局限于英国的运动,”新公共管理“包含以下核心原理: 一种对于管理而不是政策的关注,强调绩效评估与效率; 将公共官僚机构分散化为以使用者付费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机构; 使用准市场与合同外包以促进竞争; 成本削减; 建立起一种强调产出目标、短期合同、金钱激励以及自主管理的管理方式.由此,新公共管理的概念正式进入了英国主流公共行政学界,成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以“私有化”、“市场化”为取向的政府改革运动的共同旗帜.
同时,“新公共管理”这一名称也迅速地传向了大洋彼岸,其标志就是,奥斯本与盖布勒出版了《再造政府》一书,从十个方面详细阐述了“企业家政府”的基本内容.尽管这本书并没有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提法,但由于它的主张与胡德、罗兹等人对新公共管理的概括高度一致,所以,这本畅销书很快就被人们与同样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提法联系到了一起,“掌舵,而不是划桨”也被“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支持者们奉为座右铭.此后,新公共管理的概念在学术文献中的出现频率逐年上升,根据 BIDS( Batu Infor-mation Data Systems) 的数据,“”新公共管理“一词没有出现在整个 1980 年代学术论文的标题、关键词或者摘要之中,它首次出现在 1993 年.数据显示出了”新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关键词的稳定增长: 1993: 2; 1994: 5; 1995: 12; 1996: 16; 1997: 22;1998: 30”[13].“到了 1990 年代末,”新公共管理'一词在学术、政府和组织讨论中得到了国际层面上的广泛使用”[13].至此,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同时也成了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
三、公共管理概念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多元建构应当看到,在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的提法之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主要是把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来对待的,而在胡德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的提法之后,“公共管理”一词则被赋予了一种形成于进步主义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方案的意义.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模式,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公共管理概念都被赋予了强烈的反公共行政取向: 作为研究主题,它力求把自己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区别开来; 作为实践模式,它则试图颠覆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无论是否在公共管理一词前加上“新”的定语,它都是以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概念出现的.另一方面,当公共管理与“新”的定语固定地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又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是用来指称一场特定的政府改革运动的.
与 20 世纪初期发生在美国的市政改革及其市政研究运动不同,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场席卷了主要西方国家,并逐渐扩散到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的政府改革运动.尽管以胡德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为这场运动勾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寻找其共同的方面,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是不容抹杀的.因此,由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建构起来的公共管理概念也必定比形成于市政研究运动中的公共行政概念更加复杂,受到更多力量的影响.事实上,所谓 NPM 也并不像胡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型.比如,费利耶( Ewan Ferlie) 等人就指出了 NPM 的四种模型,分别是: NPM 模型 1,效率驱动; NPM 模型 2,小型化与分权; NPM 模型 3,追求卓越; NPM 模型 4,公共服务导向.其中,前三种模型都生成于 20 世纪80 年代,第四种模型则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NPM 模型 4 目前发展最不充分,但仍在展示其巨大的潜力.它代表了对私人与公共部门管理理念的一种结合,通过描绘出一种独特的公共服务使命来重新赋予公共部门管理者以活力,但又与源于私人部门并可以向公共部门转化的那种关于良好实践的高质量管理的公认理念相协调”[14]14 -15.在这里,如果说前三种模型仍然可以被放入胡德对于 NPM 所作的定义之中的话,那么,NPM 模型 4 则与胡德笔下的 NPM 大为不同,它更多地受到了公共行政研究中公共服务取向的影响.
这表明,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侧重面,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主题.具体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与公共管理的概念有着一股走向规范化的趋势.
1999 年,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道森和达吉( Sandra Dawson and Charlotte Dargie) 看到,“在过去十年关于新公共管理的讨论中,可以指出,尽管新公共管理最初是根据管理主义与理性选择而得到概念上的定义的,但随后的辩论则包含了关于伦理、责任、民主、规制以及公共部门内在本质的探讨.这一变化重新证明了可以被定义为传统“公共”部门概念和公共部门价值的事物的切题性.我们可以将新公共管理的这些发展解读为是对其在 1990 年代后期发展并扩展为一个更加鲜明的“公共”概念的一种明证”[13].也就是说,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发生了主题上的变化,学者们为这一概念增加了许多规范性的内容.这一点,在美国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突出了公共管理概念的规范性内容更可能反映出美国学术界的基本状况.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规范研究方面显得更为成熟一些,而且学科间的交往途径也最为畅通,在此背景下,公共管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吸收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增强了公共管理概念的规范性内容.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行政评论》在 1998年推出了一期名为“领导、民主与新公共管理”的特辑,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状况,对新公共管理的概念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说明.在这期杂志中,特里( Larry D. Terry) 认为,“企业家模型已经受到了怀疑,因为它的支持者没能针对民主责任这一难缠的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那些致力于民主理想的人对于公共企业家总是抱着一种怀疑,不相信他们能够或者愿意抛弃自私自利的行为而支持公共利益( 无论如何定义) .新管理主义者所倡导的公共企业家恰恰使这一问题变得恶化了,因为,蕴含在新管理主义之中的理论无法满足任何一种公共利益的观念.由于公共选择理论与组织经济学信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又由于自利是这些理论的核心,因此有理由怀疑,“公共利益”与“公共善”的观念在这些理论中不会具有什么思想地位……因此,新管理主义版本的公共企业家需要得到检讨.在民主治理的层面上,由于烦人的责任问题,公共企业家对民主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威胁”[15].其实,还不仅仅是理论取向上存在着这些问题,而且,新管理主义就实践自身而言,也存在矛盾,并经常性地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公共企业家肯定拥有的一种内在的自利、冒险与不循常规的取向,为倡导解放和市场驱动式管理的人制造了一种困境.一方面,这些品质是值得赞扬的,它们帮助公共企业家作出了创新和激进的变革.另一方面,这些品质又加深了许多美国人对官僚权力的忧虑.进而,这些忧虑又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需要对公共企业家作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限制,以保证他们对我们负责.”也就是说,企业家模型内含着一个创新与责任的两难困境,这使它在实践中往往会造成一些悖论性的后果,作为一种新的责任实现机制,它经常性地使民主责任的实现遭遇无法得到保障的后果.
应当承认,经历了工业革命后,国家与政府发生了分化,在此前提下,政府在直接的意义上主要考虑的是管理上的问题,但是,在整个近代以来的社会中,民主任何时候都被看做是一种上位价值.然而,新公共管理却呈现出了反民主的倾向,在回避对政治价值问题的关照中用实际行动为民主掘墓.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个时期内大获成功,但受到一些较为谨慎的学者的怀疑,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林恩( Laurence E. Lynn,Jr. ) 就断定,“尽管被赞美者称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新公共管理却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主题,很可能因为许多原因而走向衰落: ( 1) 激发了这一概念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最初形象最终将在政治更替中受到破坏,党徒及学者们都将在宣布新公共管理的蜕变或消亡中发现新的机会; ( 2) 随着跨越国家和部门的比较研究的不断累积,各种改革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将迅速地遮蔽其表面上的共性;( 3) “新的”一词将被视作对生成中的研究形式或对象的一个不便的修饰语; ( 4) 政治论辩将需要一个新鲜的主题,以吸引人们对于新一波的改革观念的支持.我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写新公共管理的验尸报告了”.尽管林恩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即将衰落,但他又承认,要彻底拒绝新公共管理的主张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是公共行政永远也不能缺失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应当做的只能是重构新公共管理的内涵,尽可能地使其与民主的上位价值相一致.在此问题上,道森和达吉也作出了相同的思考,“传统上将公共领域视为其保留地的学者们发现它受到了管理观念的入侵.我们可以将此解释为一个简单的选择: 要么批判与拒绝( 新公共) 管理的观念,去寻找一些替代方案; 要么把它接纳为一个属于自己的概念,并寻求根据公共部门的语境来型塑与调节其含义.1990 年代后期的概念探讨表明,许多评论者已经作出了后一种选择,这是因为,选择反对改进效率的立场就等于选择了工业革命期间破坏机器的卢德派的立场,因而,也就失去了他们想要影响的群体的倾听”.
我们知道,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表制民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基本标准主要在于其政治系统是否具有代表性.因而,要使新公共管理与民主相一致,就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也需要具有代表性.凯利( Rita Mae Kelly) 的设想是,“考虑到大多数公民---即使是作为政府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很少拥有如何选择的足够信息与知识,即他们拥有“有限理性”,公民们经常向同他们持有相同观点的领导者或代表求助,以在什么才是“最好的”决策的问题上得到指导.如果民选官员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职能,反而在官僚机构或外包机构中拥有可能体现他们观点的代表,那么,就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新公共管理结构之中,代表性官僚制与多元政治领导有助于消费者/公民接受这一观念,即关于一种特定政策及其执行的社会平衡已经得到了实现,公平正义也已经发生,尽管在特定情况下,特定消费者/公民可能并未得到如同他或她的邻居或敌人那样的同等对待”
.因此,“在一个具有地理多样性的民主政体中,代表性官僚制可以提高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等级结构的效率与效能.它们有助于在政治侵入了执行的时候实现被理性选择理论家视为必不可少的社会平衡,也可以在选定情境中帮助管理者强调竞争性和真正的市场条件的缺乏”.在这里,通过对代表性官僚制的一种实用主义解释,凯利试图发现新公共管理与民主之间协调的方案.
考察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新进展,可以发现,由于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代表性官僚制的引入,新公共管理的概念被纳入了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研究传统之中了,其甫一出现时的反公共行政内涵变得越来越稀薄了,或者说,新公共管理的概念出现了公共行政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概念的区别也就变得模糊了起来.比如,在进入新世纪后出版的一本考察公共管理历史的著作中,林恩就认为,“公共管理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与其之前的“行政管理”(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一样,争取其作为一个学术与实践范式的永久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了”相反,“在行政与管理的概念之间,无法作出决定性的区分,尽管许多学者都试图作出这一区分.我还主张,公共管理并不仅限于“管理者所做之事”,也不限于政府运作.因此,公共行政的历史---它包含了权威结构、“最佳实践”和制度化价值的出现与演化---同样也是公共管理的历史.换句话说,本书中关于被某些人称为( 法国、德国、美国以及英国的) 旧公共行政的章节与那些讨论近年来的 NPM与管理主义的章节是在同等程度上与公共管理有关的……尽管我在整本书中都被诱使而使用公共管理的概念,但这一用法无疑会激怒那样一些读者,他们往往认为公共行政的概念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具有历史正当性和准确性的.当我认为语境需要的时候,我选择了公共行政的概念.而在两个概念都可能 适 合 的 地 方,我 则 使 用 了 公 共 管 理 的 概念”[18]7.从林恩对他自己用词上的交代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已经实现了公共管理概念的公共行政化之后,是没有必要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分的.
不仅如此,在这本覆盖了从古希腊与古中国直到 21 世纪的社会治理思想的著作中,林恩还对公共管理作了一种泛历史主义的解释,即认为人类的社会治理史就是一部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的历史.在这本书中,林恩列举了历史上的“公共管理大事记”,比如: 第一项,公元前 4 世纪,申不害的行政原则; 第二项,公元前 124 年,西汉创立“太学”,以“教授公共服务的价值与观念”; 第三项,529 年,第一份查士丁尼法典公布; 第四项,1154 -1189 年,英国普通法形成……[18]8根据这一记录,“这一领域可能起源于古代中国”[19]29.林恩的泛历史主义解释在新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者胡德那里得到了回应,在1998 年出版的《国家的艺术》这本书里,胡德花了大量笔墨来讨论诸如“父权主义: 儒家公共管理思想”、“古希腊合唱队”: 公共管理中的宿命论”等问题[20],同样把公共管理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000 多年.虽然为一种现代现象去寻找远古模型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学者们的共同嗜好,比如,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为了证明民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就在古希腊那里杜撰出了民主的典范.但是,在公共管理的问题上,采取如此泛历史主义的做法究竟有何意图,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这既不符合科学讲究事实的原则,也缺乏政治动机.
公共管理概念的公共行政化和泛历史主义解释都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概念探讨中出现的新迹象,除此之外,胡德早期关于新公共管理的经典阐述也仍然拥有大批的支持者.事实上,到了 20世纪 90 年代后期,公共管理的概念已经变得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一样,具有了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内涵,关于它的反公共行政解释与公共行政化的解释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对峙之中.这表明,在经历了早期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冲击之后,公共行政学界中规范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平衡得到了恢复,因而,公共管理的概念也被纳入了这种平衡之中,并能够在这种平衡中得到多元主义的解释.林恩就描述了关于公共管理概念的三种解释: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经典文献将管理视为公共行政官员裁量权力的依法负责行使.根据这种观点,公共管理是一种治理结构,是旨在使政府有能力行使人民意志的管理裁量权的一种合乎宪法的、适当的正式化.相反,近来的文献则倾向于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技艺,即个体在行使管理职责时所展现出来的熟练操作.在公共管理者负责任地实践其技艺---他们尊重宪法约束,并通常能够体现出被广泛视为合法的与适当的( 而不是党派性的或自私的) 价值---的意义上,公共管理又意味着更多: 一种宪政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公共管理遵循“实践规则”,是对行为的实际限制或指导,这保证了它在一个宪政政体中的合法性.因此,公共管理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结构、技艺与制度:管理、管理者与负责任的实践.
其实,这里的三种解释都只是林恩的解释,或者说是林恩所理解的解释,实际上,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一样,公共管理的概念也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学者们若想对各种不同的解释进行通约进而整理出一种得到公认的公共管理概念,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关于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应当是有价值的,正如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建构也是有价值的一样,而这正是当前的公共管理研究所欠缺的.
在我们看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关于人类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探寻,也许可以在公共管理的概念下进行.如果说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概念有什么不同的话,恰恰是前者需要在人类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上来加以理解.因此,对公共管理进行全新理论建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理论建构是要走出既有的研究途径和思维模式的.
[参 考 文 献 ]
[1]Colin Duncan.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for the 1990s[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
[2]Donald F. Kettl. The Global Revolu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Driving Themes,Missing Links[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997,16( 3) : 446 - 462.
[3]Andrew Gray,Bill Jenkins.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Public Management: Reassessing a Revoluti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5,73( 1) : 75 - 99.
[4]J. A. Chandl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r Public Manage-ment? [J].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1988,8( 1) :1 - 10.
[5]J. A. Chandl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Discipline in De-cline[J]. Teach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11( 2) :39 - 45.
[6]R. A. W. Rhodes,Charlotte Dargie,Abigail Melville,BrianTutt. The Sta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ProfessionalHistory,1970 - 1995[J].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5,73( 1) : 1 - 15.
[7]Herbert Kaufman.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9,29( 1) : 3 - 15; David O. Porter,Eugene A. Olsen. SomeCritical Issues in Government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1976,36( 1) : 72- 84.
[8]Peter F. Drucker. The Age of Discontinuity: Guidelines toour Changing Society[M].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69.
[9]Amitai Etzioni . The Third Sector and Domestic Missi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3,33( 4) : 314 -323.
[10]Christopher Hood. A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J].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69( 1) : 3 -19.
[11]Christopher Hood. The“New Public Manageemnt”in the1980s: Variations on a Theme[J]. 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1995,20( 3) : 93 - 109.
[12]R. A. W. Rhodes. Introduc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69( 1) : 1 - 2.
[13]Sandra Dawson,Charlotte Dargie. New Public Management:A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UK Health[J]. Public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heory,1999,1( 4) : 459 - 481.
[14]Ewan Ferlie,Lynn Ashburner,Louise Fitzgerald,AndrewPettigrew.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 Action[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4 - 15.
[15]Larry D. Terry.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Neo-Manage-rialism,and the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8,58( 3) : 194 - 200.
[16]Laurence E. Lynn JR.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Howto Transform a Theme into a Legacy[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8,58( 3) : 231 - 237.
[17]Rita Mae Kelly. An Inclusive Democratic Polity,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ies,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8,58( 3) : 201- 208.
[18]Laurence E. Lynn JR. Public Management: Old and New[M].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6.
[19]Laurence E . Lynn JR . Public Management : A ConciseHistory of the Field [M ] / / Ewan Ferlie ,Laurence E .LynnJR . ,Christopher Pollitt . The Oxford Handbook ofPublic Manag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9.
[20][英]胡德. 国家的艺术: 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M].
综观世界资源型地区(城市)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期---资源大量开发引起的经济高涨期---资源枯竭而导致的经济衰退期---经济转型期的过程。素有德国工业引擎的鲁尔区也是如此。20世纪50-60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了鲁尔区的煤、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作出的新判断.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对于更好地解决和处理好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管理领域的问题,提高各级党政部门的社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
从小范围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的提高,但是在区域公共管理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大范围看,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程度的提高,国家之间的联系更为活跃,传统的内向型区域管理方式难...
一、背景分析.旅游产业作为旅游目的地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往往能够给旅游目的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旅游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同时也能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提供社会动力和文化动力.越来越多的景区、城市、国家正是看到旅游产业所能带来...
绿色会计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经济主体与环境的关系.绿色会计与普通会计不同,绿色会计所采用的计算形式多种多样的,例如货币、事物,而普通的会计只是对货币进行计算.游客是旅游企业得到利益的主要来源,所以一些旅游企业为了增加游客的消费,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在...
众所周知,流动人口的调查是对于国家基本情况,综合国力的进行了解的前提,对于国家政府制定相应的人口,教育,就业政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国家强盛的基础性条件.尤其在新时期,社会现象越来越复杂,人口流动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这无疑加大...
伴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使得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刻.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对于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研究的并不透彻,本文主要结合实践,就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开展了分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