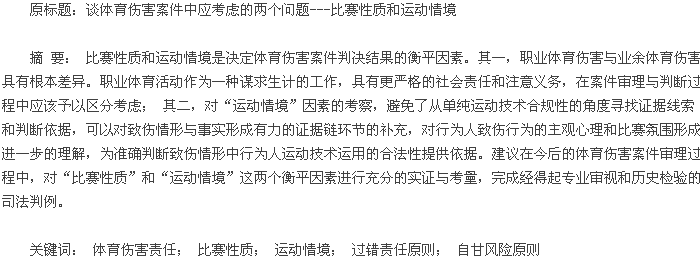
体育伤害与体育活动如影随形,犹如硬币的两面。很显然,体育伤害事故不能简单地与一般伤害事故划等号,体育的特殊性也应该在一般法律适用的层面上得到特别的考量与观照。体育伤害案件中“刻舟求剑”式的套用法律条文的司法实践,不仅有失公允,难以平衡行为人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保障公民体育权利与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法知名学者韩勇博士认为: “法庭判案的考虑因素以及涉及到的一些价值判断问题,至少包括项目本身特征、体育伤害事件发生时的事实和环境、体育参与者的特征、体育比赛的性质。[1]”这里就“体育比赛的性质”和“体育伤害事件发生时的事实和环境”中的运动情境因素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辅以“上海新泾公园体育伤害案”来深化主题讨论,具体案情与判决详见: 一审( 2014) 长少民初字第 18 号[2],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侯卫清法官转述二审( 2014) 沪一中少民终字第 29 号分析观点[3],与业界、学界讨论交流。
1 附加价值: 职业体育伤害与业余体育伤害的根本差异
关于职业体育伤害与业余体育伤害是否具有根本差异,以及在体育伤害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能否作为一个衡平( equity) 因素予以考虑,是学界、业界绕不过的理论探讨与实践问题。目前就此点并未达成共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主张二者有区别并要求将其体现在司法实践中的观点。如体育法知名学者韩勇博士就认为: “法院应区分案情进行判断,体育比赛的性质( 在不同性质的体育活动中) 这一因素应该予以考虑,例如在职业冰球比赛中在球门前双方运动员因推撞导致受伤可能认定受害人甘冒风险,而同样的行为发生在自发性的足球比赛中可能会认定加害人存在过错,而不能认定受害人甘冒风险。[1]”一些已判体育伤害案件也主张二者有区别,例如“上海新泾公园体育伤害案”二审判决评析观点认为[2],“受害人同意只适用于故意侵权领域,对于过失侵权行为并不适用,且业余体育运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与职业体育运动也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种是主张二者无需做出特别考虑的观点。
持此看法者直接引用职业体育中受害人同意原则或自甘风险原则这一抗辩事由与行业惯例,来证明业余体育也同样适用受害人同意原则或自甘风险原则作为主要的抗辩事由。笔者认为,持此观点者是通过平移职业体育的行业惯例,以及抹平职业体育与业余体育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偷换概念的论述手法,来达到证明观点之目的。例如,有研究者为了证明在所有的体育侵权案中可以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照搬职业体育的行业惯例作为主要的论述证据。“散打王争霸赛、K-1、泰拳、拳击、摔跤等直接针对人体本身的对抗性运动和比赛风头正劲,比赛自然是越激烈越血腥,越能获得商业利益,必然在规则上严格要求双方进行激烈的互相侵害。[4]”由此推理得出不论是职业体育,还是业余体育均可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观点。一些体育伤害案件的判决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南京足球友谊赛伤害案”二审判决评析观点即认为[5],“拳击比赛中拳击手每次出拳都是对对方人身的直接侵害,如果对该结果要依公平责任原则由出拳一方承担补偿责任,拳击这一职业必将无人问津,拳击比赛也不复存在。”
笔者支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职业体育伤害与业余体育伤害应该明确做出区分,应将比赛性质作为体育伤害案件的衡平因素,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以下补充一些新的论据,旨在深化对既有观点的认识。
职业体育是现代经济与娱乐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规则性。参与高水平的竞技活动作为一门职业和一项谋求生计的工作,具有更严格的社会责任和注意义务。正如“为观众负责”“为市场负责”和“为社会负责”所必须承担的谨慎注意义务,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世界反兴奋剂运动中的零容忍政策和运动员行踪报告制度。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研究者 Lev Kreft 认为[6],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WADA) 最严厉的反兴奋剂政策,遭致了道德和法律层面的质疑,诸如违反基本人权,导致运动员无法随心所欲掌控自己的身体等一系列批评,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职业性活动及所取得的体育成就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来源的生产性工作,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它属于一种生产性消费活动。职业运动员作为文化性“商品”的特征与事实,使其必须正视与接受自己作为商品所面临的一系列检验。人权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抗辩依据自然不适用。也有学者直白地指出[7]: “足球是一项职业,是挣钱的方式,职业体育人才希望将自己的才能转变成报酬。这是非常短暂的事业,但可以赚相当多的钱,金钱是球员从事 10 年、15 年职业足球运动的原因之一。职业足球运动员通过他们的体育劳动来维持生计,而随着近来欧洲足球劳工立法方面的变化,职业运动员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谈判或交易地位。”这也就意味着,职业运动员作为创造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需要为提高自身的工作质量以及确保文化产品的品质承担责任。职业体育中激烈的对抗性、冒险性和戏剧性是保障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创造高附加值的基础。
这为适用受害人同意原则作为职业体育伤害事故的抗辩事由提供了基本依据。
诚然,职业体育比赛中一般适用受害人同意原则也是有限度的,尤其在格斗类项目比赛中。加害人实施的违法行为只有获得规则的理解才能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受害人同意也只是在规则理解的范畴予以承认与授权。这充分体现了职业体育的高度组织性、规则性、商业化特征。例如,发生在 1997 年世界拳击协会重量级拳王争霸战上的泰森“咬耳事件”.泰森面对霍利菲尔德的针对性战术恼羞成怒,前后两次咬伤霍利菲尔德的耳朵,主裁当场取消泰森的比赛资格,赛后泰森还被处以吊销拳赛执照和300 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处罚。相同性质的案例发生在2014 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中的“苏亚雷斯咬人”事件。乌拉圭队明星球员苏亚雷斯丧失理性咬了意大利队后卫基耶利尼的肩部,当值主裁未能察觉并做出判罚,赛后国际足联追加严肃处罚,判罚苏亚雷斯四个月禁止参加和足球相关的一切活动,禁赛九场国家队比赛,以及10 万瑞士法郎的罚款。学界对体育伤害是否可以入刑,哪些恶意加害行为可以入刑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8-9].反映了学界对体育比赛中超出规则范畴和受害人同意原则框架的恶意伤害行为,超出职业体育“特殊性”赋予的伤害责任豁免范畴的争论所在。
职业体育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社会活动。职业联盟严密的组织性特征和职业俱乐部高度的企业化特征,让受害人同意原则可能产生的体育伤害风险,由赛事组织者、职业联盟、所属俱乐部、职业保险等以不同形式予以承担,由此逐渐形成了行业惯例与传统,也为保护与发挥体育行业的特殊性及其政治、商业与社会价值创造了舆论环境、体制机制保障和规则运行条件。职业体育中故意伤害行为的规制方面,一般适用于体育行业内部规则做出惯例处理。也就是说,泰森、苏亚雷斯等球员的故意伤害行为并未放在侵权法一般适用的层面上考虑,而是适用体育行业的特殊性予以“特别考虑”和“行业处理”.这是在运动员人身健康权与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之间的价值选择与实践平衡。职业运动员作为一种工作类型,职业体育联盟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在突出商业性与创造价值方面被赋予了更大的尺度和空间。这就使职业运动员让渡有限的人权保障成为一种行业惯例和传统,也就意味着,职业运动员选择这一工作类型就必须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而这种“牺牲”自我利益的行为具有明确的具体内容,当事人“知情”并明确知道可能产生的后果。这种切身权益的让渡是以可能换得更大的切身利益为目标追求,是由职业体育的特征所决定,也是体育行业内部规则和制度规制的结果。
与上述案例不同,“上海新泾公园体育伤害案”属于业余体育活动范畴,适用职业体育中的受害人同意原则显然过于牵强,因为行为人参与活动是为健身、娱乐之目的,并无附加之上的职业约束和更为严格的社会责任,参与健身活动的组织性、规则性无法与职业体育相提并论,在体育伤害保险制度、职业联盟保障等方面也无法与之相比。有学者在体育侵权案件中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理解[4],将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领域中发生的体育伤害案例及责任认定性质混为一谈,这是有失严谨的。尤其是业余体育活动参与健身与娱乐活动的场地属于开放式公共空间。它实际上解除了行业内部运行机制和规则的免责依据或某种意义上的“壁垒”,完全属于民法调整社会关系、人身关系的范畴。
诚然,既便排除了行业保护与惯例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体育活动中身体对抗性的特征必然形成伤害风险与事实这一体育活动的特殊性。这也是一些学者提出并主张的体育活动中的固有风险,即主要的默示自甘风险。行为人既使履行了一般注意义务,也仍然存在风险[1]的观点的依据,那么针对此,就需要在个人权利保障与体育活动特殊性之间寻求价值平衡。学界普遍认为业余体育伤害或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应该适用自甘风险原则,而体育活动本身也符合自甘风险原则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可以预见体育活动的危险性和风险性,本可以通过选择体育项目和体育活动形式予以避免,如果出于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心理发泄、追求刺激等获得某种利益的动机,行为人坚持从事具有较高或一定伤害风险的体育活动,便视为默示自甘风险,其理应承担合理伤害( 不超出体育规则框架的合技术性要求) 所造成的伤害结果及利益损失。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业余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恶意伤害行为,以及带有明确主观故意且超出体育规则框架之外的伤害行为,不能成为道德推脱和抗辩的事由。竞技体育并非法外之地,竞技体育中的恶意伤害行为也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伤害他人的工具[10].关于此也可以理解为,受害人愿意承担由自己造成的( 运动技术运用不当、自身体质原因等) 、体育规则框架范围内的、或由竞技体育中的固有风险或偶发性因素引发的伤害结果。但如果加害人属于恶意伤害行为和故意伤害行为,不得以自甘风险原则作为抗辩事由,而应由加害人承担全部伤害责任。
此外,也需要避免将自甘风险原则作为抗辩依据引发的全有或全无的抗辩与判案结果[1],将加害人是否存在过错简单区分为故意或非故意两种情形,因为这种全有或全无的抗辩结果很难促进双方的理解与和谐。而事实上,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由于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真实的致伤情形很难还原,对于加害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的判断是很难符合证据三性原则的。在此情形下,引入过错责任原则中的过失侵权概念与情形就成为一种可做出更好权衡的“中间地带”.如在“上海新泾公园体育伤害案”中,加害人跳起封盖,受害人在篮下投篮,加害人没拍到篮球,也未拍到投篮手,而是拍到了远低于投篮高度的受害人眼睛上。从篮球运动规则的角度而言,加害人侵犯了受害人作为比赛进攻方的圆柱体合法空间,属于典型犯规动作。从受害人眼睛受伤害程度来推断,加害人明显存在用力过猛的疏忽情形,即是俗语所说的“犯规动作过大”,而这一点又显然超出了业余体育中一般注意义务的理解范畴。当排除受害人无法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之主观故意情形( 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无法予以证明) ,加害人需承担的就是相应的过失侵权的责任。也就是说,行为人甘冒体育活动中可以预见的固有风险,但并不甘冒加害人因轻率和缺乏对其他人的考虑、以超出意料或违反体育道德的方式而导致伤害的风险[1].
由此,“上海新泾公园体育伤害案”中明确了职业体育伤害与业余体育伤害的根本差异。在考虑体育活动的特殊性并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业余体育活动中加害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最后判定加害人承担过失侵权的责任,法律适用正确,判决结果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