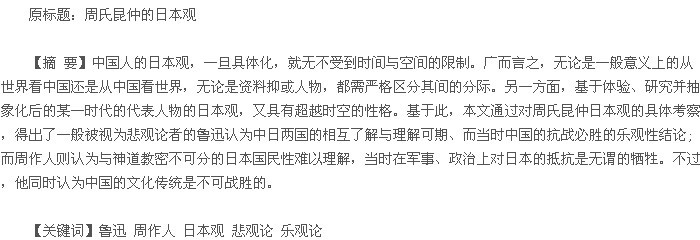
一、引言
鲁迅在《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中指出: “据说: 像日本人那样的喜欢‘结论’的民族,就是无论是听议论,是读书,如果得不到结论,心里总不舒服的民族,在现在的世上,好像是颇为少有的,云。接收了这一个结论之后,就时时令人觉得很不错。例如关于中国人,也就是这样的。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
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 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
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点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迷的国度’了。”
①鲁迅话锋一转,接着指出: “倘使长久的生活于一地方,接触着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触,感得了那精神,认真的想一想,那么,对于那国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罢。”
②而《活姿态的中国》的着者内山完造先生,恰恰“是二十年以上,生活于中国,到各处去旅行,接触了各阶级的人们的,所以来写这样的漫文,我以为实在是适当的人物。事实胜于雄辩,这些漫文,不是的确放着一种异彩吗……着者的用心,还是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
③虽然鲁迅认为在 1935 年中日交恶的年代,对内山先生的这本书,日本的读者看后所得出的结论肯定不同,但他的结论却是: “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
④不言而喻,鲁迅在这里强调的是,通过全面、深入的“接触”,直至能够“感得”了对象国的“精神”,是真正了解对方的前提条件与路径。虽然如黄遵宪、王韬等或有洋洋大观的日本记述、或也不乏真知灼见,但由于他们或身份、地位特殊,或有语言障碍等,很难真正深入地接触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底层的日本一般民众,从而“感得了那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对日本的真正了解,或曰中国人的接近实际的日本观———只有到甲午战后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才得以实现。
当时多数的留日学生生活是清苦的,所谓“下宿”的生活,使他们直接与日本的下层社会相接触。“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
①留学生的下宿供膳尚用热饭,而日本“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另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陶之。”
②至于当时的周氏兄弟,过的则是“完全日本化”的生活。这是“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外出,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的事情便无法深知的。”
③据周作人的回忆,他们两兄弟住的是日本普通下宿,上学时穿学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后来也改用高齿屐了。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盒饭。总之,衣食住各方面过的全是日本生活。他们不但没有感到什么不便,惯了还觉得很有趣。“这里不仅包含了对日本人民普通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且还是对日本生活中保留的中国古俗、中国民间原始生活方式的重温,从而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
④鲁迅曾为了专心学医而到远离东京的仙台,那里当时没有中国人,这样的环境,正如周作人所说,即便只在语言上,也使鲁迅的日语精进很多。而周作人后来也搬家到很少留学生且更加庶民化的麻布区森元町,与裱糊匠、剃头匠为邻。这种如同三等车厢一般的市井生活,使周作人对日本的体验更加“接地气”。
留学期间,周作人还常到被称为“寄席”的杂耍场去听“落语”,被这种曲尽世态人情的讲笑话的民间艺术深深感染,从中发现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等。
鲁迅留学日本八年,而留学日本六年的周作人中间未曾回过一次家,又与羽太信子结婚,多次声言视东京为第二故乡。周氏兄弟而外,像郭沫若、郁达夫、戴季陶等亦多如此。正因为他们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有深切的感受,所以他们的日本观与浮光掠影的臆断就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直到今天,周氏昆仲对日本的意见、戴季陶的《日本论》依然受到重视的理由。
诚然,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没到过日本的情况下,也写出了《菊与刀》那样的名着,但那毕竟是一种特例,而且对于真正了解日本的人来说,还是能从书中感觉出一种着者对日本的隔膜来。
另一方面,正如周作人所常提及的,他和鲁迅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他们昆仲所切身接触、所感得日本社会的精神,也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而且,两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东京,所以可以说是以明治末年的东京为代表的日本。周作人指出: “我的东京的怀念差不多即是对于日本的一切观察的基本……文学美术中最感兴趣的也是东京前身的江户时代之一部分。民族精神虽说是整个的,古今异时,变化势所难免,我们无论怎么看……如不是专门学者,要想完全了解他是很不容易的事。正如中国讲文化总推汉唐,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大抵是宋以来这一系统的,虽然有时对于一二模范的士大夫如李白韩愈还不难懂得,若是想了解有社会背景的全般文艺的空气,那就很有点困难了。要谈日本把全空间时间的都包括在内,实在没有这种大本领。”
⑤由此可知,所谓中国人的日本观,一旦具体化,则无不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所以,无论是从周边看中国,还是从中国看周边; 无论是资料,抑或人物,都需注意区分其间的分际。
从总体的代际上说,影响中国人之日本观的客观环境因素也在发生阶段性变化。自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中国青年再次成规模地赴日留学,而且与鲁迅他们那一代不同的是,相当多的留学生,他们十年乃至二十年留居日本,融入了日本的产业、教育等领域。长期的旅居生活所积累的对日本的实感,使他们的日本观更加贴近日本的实际。有关中国人的日本观的坚实而宏大的代表性着述的问世,应该为期不远了吧。
二、周氏昆仲日本观之同
通观鲁迅、周作人昆仲的日本观,在很大的差异中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归纳起来,大者可举出以下数端。
1. 对日本政治的批判和怀疑
周氏昆仲留学时期的日本观,无疑与当时他们所处的国际的、时代的、社会的环境密切相关。虽然周作人自己一再说他的日本留学生活一直是“颇为愉快”的,并没有遇到乃兄在仙台所遭受的那样的刺激。
但他同时也多次提及在日本所受到的两次震动: 一次是留学时期的所谓“大逆事件”,另一次为关东大震灾时的“大杉荣事件”。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追忆道,留学“期间,却遇见一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
这是明治四十四年( 一九〇一) 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时正在大学赤门前行走,忽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我就买了一张,拿来一看,不仅愕然立定了。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那时日本有没有共产党虽然未能确说,但是日本官宪目中所谓‘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只是那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和激进的主张社会改革家罢了。这一案里,包括二十四个人,便是把各色各样的人,只要政府当时认为是危险的,不管他有无关系,都罗织在内,做一网打尽之计,罪名便是‘大逆’,即是谋杀天皇。他们所指为魁首的是幸德传次郎( 秋水) 和他的爱人营野须贺。其实幸德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最有名,居于文笔领导的地位,所以牵连上了……这些都是检事小山松吉的杰作,其实也正是政府的传统的手法,近年的三鹰和松川事件就用了同样的方法锻炼成功的。他们将二十几个不相统属的人做成一起,说是共谋大逆,不分首从,悉处死刑。
次日又由天皇特饬减刑,只将一半的人处死,一半减为无期徒刑,以示天恩尚厚。这手段凶恶可憎,也实在拙笨的可怜。当时我所看见的号外,即是这二十四个人的名单。”
①此外,使周作人再次深感震惊的,“便是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震灾的时节,甘粨宪兵大尉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并及他的六岁的外甥橘宗一的这一事件”。
②周作人还曾为此专门写过文章。
由以上的事件,使周作人做出如下论断: “日本明治维新,本来是模仿西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根本是封建武断政治,不过表面上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迹象,但也逐渐消灭了。这一桩事,在他们本国思想界也发生不少影响,重要的如石川啄木、佐藤春夫、永井荷风、木下木太郎( 本名太田正雄,木太郎的木字本从木工二字合成) 皆是。石川正面的转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永井则消极自承为‘戏作者’,沉浸于江户时代的艺术里边,在所着《浮世绘的鉴赏》中说明道: ‘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 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
③其实对彼时的日本政治,周作人在1919 年第一次重游日本时的观感中,就已经表达了与此相近的看法。在 1919 年 11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游日本杂感》中,他指出: “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对自己也有害……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伤害……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中国,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
④待到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周作人对日本的政治更加失望,他的日本观和基于此的对日态度,也渐趋激烈起来。其在 1927 年所写的《排日平议》,集中反映了他对日本的看法。他指出: “非民治的日本,军人与富豪执政的日本,对于中国总是一个威吓与危险……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存共荣’,其实即是侵略的代名词: 猪肉被吃了在别人的身体里存着,这就是共荣共存……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要留心,不要信任他,要努力随时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这是中国知识阶级,特别是关于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现今中国所应作的工作,应尽的责任。”
①此外,在周作人对《顺天时报》的评价和态度上,也可看出他对日本政治的批判。周作人在回忆录中用了两节的篇幅叙述了当年的情形。“本来中国的报纸最初都是外国人办的,如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是如此,但那是外国商人,主意为的是赚钱,不像日本的乃是由政府主持……在北京的一个叫做《顺天时报》,在沈阳———当时称作奉天的一个叫做《盛京时报》,就名称上来看也可以知道成立的长久,和态度的陈旧了。日本是一个名称君主立宪,而实际是由军阀专政的国家,民国以来北洋政府虽然还很反动,可是民间有些活动显得有民主的色彩,这与日本人的观点是不大合得来的,其时便在报上大发议论,处处为反动势力张目,其影响实在是很大而且很有害的……结果乃由我单枪匹马去和这形似妖魔巨人的风磨作战。”
②及至中日全面战争来临之前,周作人连续写了四篇《日本管窥》,集中反映了他的日本观。对日本的武断政治、军人弄权的基本看法没有什么改变。当时周作人集中发表他的日本观,一是为了想搞清楚日本“非常时”行动的所谓理由所在,同时在此基础上意在寻求解决中日问题的道路。他的结论有三点: 一是因为日本对中国负了很重的“文化债”,也即长期受着中国的文化压迫,现在要来反一下; 二是他认为文化分精神和物质两种,“物质文化”———当时以长枪利炮等杀人器械为代表———虽是低等文化,但掌握物质文化的“英雄”们即是这现实世界的“实力者”,应多给予注意才行; 三是日本的“非常时”的行为与日本宗教,即神道教的狂热有内在联系。但作为缺乏体验的外国人,对神道教难以深入了解与理解。
周作人对日本的政治及政治文化的看法在当时应该说是透彻和明达的,但就是这样一位自命为“知堂”、被人们普遍誉为日本通的学者,在发表《日本管窥之四》不久而北京沦陷,他却很快堕落为他一直批判的日本军部卵翼下的华北教育总署的“督办”。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周作人的悲剧及其缘由,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今天依然如此。
鲁迅对于那一时代日本政治的看法,与当时周作人的观点大抵是一致的。对于日本军部的横暴,对于由此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的民族灾难,鲁迅一直都表示了极大愤慨,予以揭露。特别是他寓居上海以后,又亲身经历了“一·二八事变”,亲眼目睹了这一事变所造成的种种惨痛的后果。他在为萧红所做的《生死场》序言中说: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上,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
③萧红所写,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带来的惨剧。鲁迅曾就“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答文艺新闻社问: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 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④鲁迅对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看法,可由在他听说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在东京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当晚遭毒打致死后用日文所发表的,题为《小林同志之死》的悼念文可知: 「同志小林の死を闻いて」日本と支那との大衆はもとより兄弟である。资産阶级は大衆をだましてその血で界をえがいた、又えがきつつある。并し无産阶级とその先駆达は血でそれを洗って居る。同志小林の死はその実证の一つだ。我々は知っている、我々は忘れない。我々は坚く同志小林の血路に沿って前进し握手するのだ(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⑤此外,一些日本友人曾多次表示希望鲁迅能重游日本,鲁迅在 1932 年 4 月回复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信中指出: “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
①又如在 1934 年 1 月的信中,他表示,“然而现在到日本去,怕有麻烦罢。让便衣盯着去看樱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
②鲁迅在送别增田涉的诗中,也曾有“心随归槎忆华年”之句,他甚至也曾打算夏天带海婴去博多洗海水浴,都说明对生活过八年之久的日本,他还是怀念的。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的那些官宪的卑劣,只能放弃了。
2. 对日本文化的共同赏识之处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和看法,周氏昆仲在很多方面毋庸说存在很大差异,但也有共同欣赏之处。如对夏目漱石小说的喜爱,特别是对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两兄弟或介绍、或翻译,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等。对于活跃于明治、大正年代的一部分有特色、思想深刻的作家作品,他们或给予高度评价,或引为同道知己,他们共同翻译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选》,即是一个实证。
三、周氏昆仲日本观之异
就物质文化方面,如前所言,在周作人的日本观中,虽然他认为高级的、以艺文学术为代表的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的光荣,而物质文明不过是一个低级层次的东西,但也就是“实力”所在。具体到中日战端一旦全面爆发,他以海军出身( 南京水师学堂) 的目光,认定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防,海岸线又那么长,日本军队可以随处轻易登陆,一盘散沙的中国的抵抗是徒劳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军事上的失败主义的日本观,导致周作人严重的民族失败主义,这也是他在日本占领北京不久,稍作消极的抵抗,很快就屈服了的重要原因。
鲁迅身经“一·二八”淞沪抗战,感受到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与热忱。1936 年,病中的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言道: “在国难当头的现在……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阵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支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支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绝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③在鲁迅的心目中,当时的日本确实十分强大,是一个劲敌,但只要中国人民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战胜这个强大的敌人。而这实际上也成了他的遗言和遗志。
在文化一面,周氏昆仲对日本文化的认识、理解和选择,如前所述,虽有共同之处,但差异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周作人对他所处时代的日本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的作品都有接触乃至深入的探讨,从中总结和揭示了日本文学、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譬如日本衣食住文化中体现的崇尚简素、爱好天然等特质。另外,周作人对日本的通俗文学也情有独钟,从中体味出幽默、滑稽的趣味。他还从众多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探寻出日本文化中“游戏的心情”这样一种审美追求。他从浮世绘的艺术中,参悟出其中体现的“东洋人的悲哀”。以上种种,多数构成了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感知和理解。也正是因为较成系统地在广与深两个方面下过一番功夫,所以周作人还断言日本文化是“创造性的模拟”。这一论断对一向看不起日本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不言而喻自有其特别的意义。
鲁迅自称是贩卖日货的专家,他同时给自己的定位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窃火者”,对日本文化奉行的是剜坏苹果式的“拿来主义”。这样,一方面需要对日本文学艺术进行“过筛子”,也即有一个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甄选,将符合自己要求的,译介给中国的读者。因为重在后者,所以并不多见鲁迅关于方方面面的日本文学艺术的评价及结论,而我们从他所译介到中国的作品可知,他看重的主要在于文艺理论、文艺与社会之关系等方面。他激赏厨川白村即是由此。另外,他所欣赏的作家兼文艺论者还有岛崎藤村、有岛武郎及武者小路实笃等。而对片上伸教授,他表示“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由以上种种,可以约略窥知鲁迅日本文化观的倾向之所在。在艺术方面,周作人常说自己是门外汉,而推崇乃兄。鲁迅从小喜爱“图画”,对于日本的代表性艺术即所谓浮世绘,他指出: “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现在则是广重,其次是歌麿。写乐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最后还是不了解。然而,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的我想还是北斋。”①
四、简短的结论
对日本研究有素的周作人,在《日本管窥》的终篇,曾自嘲云: “平时喜谈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很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现状背驰……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迷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
②这是文化。在政治一面,他于《日本管窥之二》中指出: “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其终将沦为劣种乎,念之惘然……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相对于此,一直被周作人视为悲观论者的鲁迅,如前所引,“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
③而且他相信总有一天,中日两国能够“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适曾感叹像周作人那样能够赏味日本文化的,在中国并不多见。如前所述,对日本既有长期亲身体验,又有条件进行深入研究的周作人,在中日交恶之时,对日本并不看好,同时也深陷中国军事—民族失败主义泥坑,而最终选择以身事敌。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悲观论者呢? 在他的日本观中,有一点也是不能忽略的,也即他觉得唯一可以与日本抗衡并会最终奏效的,是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言而喻,这源于其对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清朝的看法———虽然“异族”在政治上统治了中国,但在文化方面最终将被同化。
质言之,对中日关系的现实与未来,鲁迅相信当时中国的抗战能够最终获得胜利,而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与理解可期; 而周作人认为构成日本人国民性深层的是难以以理性去理解的宗教,即神道教,中日两国国民很难相互深入了解; 而在当时军事、政治的现实层面,中国必败,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可战胜的。
科技文化源于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差异及其相互作用,正是在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片面到全面,从机械到系统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进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科技文化。这是完整的对现当代科技文化的现实理解,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