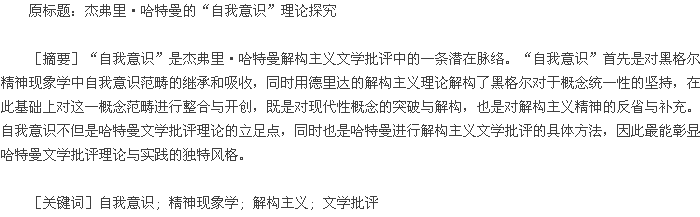
作为“耶鲁四人帮”中的一员,杰弗里·哈特曼在国内的译介和影响相对来说较为冷清。受解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哈特曼从来无意进行条分缕析的理论阐述,而倾向于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兴之所至的临场发挥。因为没有着意建立完整的理论和逻辑体系,再加上哈特曼因钟爱华兹华斯而滋生的诗人气质,使得哈特曼的着作具有驳杂繁复的特点,初读往往令人目眩。然而,哈特曼看似散漫晦涩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中,其实贯穿着“自我意识”这一潜在主题。“自我意识”不但体现了哈特曼的解构主义精神,而且也是哈特曼进行具体文学批评的独特方法。
一、自我意识的理论渊源
自我意识直接脱胎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自我意识如何产生、发展以及何为自我意识终点的阐释与论述。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的产生需要四个阶段,即感性确定性阶段、知觉阶段、知性阶段和自我意识阶段。这四阶段通过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步将感性功能扬弃和驱除,最终在自我意识阶段达到纯粹的理性,即概念。
黑格尔认为,感性是不稳定和虚妄的,纯粹的理想概念才是自我意识的最终圆满。在纯粹理性概念之中,自我意识不但能够与认识对象彼此敞开和呈现,而且能够将自身作为认识对象,用理性的概念把握自身。
从黑格尔那里转借自我意识范畴的同时,哈特曼还通过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冲破了黑格尔的纯粹理性与理性概念。德里达认为概念是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与占领,因此解构理性概念就要彻底打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是一体双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言语因为发出声音而直接地表达意义,因此言语代表了主体的在场,而文字只是表达和记录言语的符号。
言语能够通过主体发出声音而确定主体的在场,因此能够直接呈现主体,而文字只能通过对言语的记录呈现言语,从而间接的表现主体,所以文字比言语低了一等。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中主体的根基就在于主体的在场。如果语音呈现了主体的在场,那么解构主体就要从语音中心主义下手,打破语音与主体在场之间的同一。在传统语言学中,文字不研究对象,言语才是,文字只是语音的外在记录,是传达言语的符号,因此文字只是言语所留下的痕迹,因为其在语言系统中的外在性而与言语之间具有不可磨灭的差别。但文字作为语音的痕迹使得语音本身也有沦为存在痕迹的危险。如果说文字是言语的能指,因此是言语的痕迹,与言语之间存在着差别,那么言语作为存在的能指,也可能成为存在的痕迹。因为主体所获得的声音并不是声音本身,而是声音在主体知觉中留下的印象。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及其他》中提出,包括听觉在内的感觉就像印章在蜡模上留下的印记,不是存在的事物本身。而事物在感觉中留下的印记正可以对应德里达所说的“痕迹”。痕迹表明包括声音在内的主体感觉经验与事物存在之间无可弥补的差异和分延。“痕迹”本身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昭示了存在的转身离去,一方面证明了存在确实降临此间,并且留下足印,而根据雪泥中的指爪踪迹,有可能猜测出存在的大致路径。痕迹是曾经在场的证明,也是当下在场的否定,是过去在场的延迟,也就是分延。痕迹是过去的在场面向现在缺场的保留和推迟。“痕迹是延长与保留的双重运动的统一性。……痕迹扩大了分延和存储的可能: 它在同一进程中构造并抹去了所谓的意识主体性、它的逻各斯及其神学属性。”
[2]( P. 92)德里达将言语拉下意义的神坛,归化为无法还原的痕迹,语言成为了能指痕迹在差别中无尽的漂移和游戏。因此言语和文字一样,是主体的痕迹,言语并不能忠实地表达和呈现主体,在言语与主体之间存在无法还原的差异。
言语、文字与主体、意义之间,总是不断地推迟,极力贴近又总是无法到达主体的在场。在这推迟之中生成了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也极力想要呈现和表达主体想要传达的意义,但总是无法完全忠实于主体,为了尽量贴近主体本义,意义不断产生,不断贴近,但这些意义与主体之间永远存在差别,这些意义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为了不断靠近主体而产生的一连串具有差别的意义,就是语言的嬉戏,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分延。
二、自我意识的产生及特征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哈特曼将自我意识的出现比喻为“被阻止的旅行者”( the halted travel-er) 。在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哈特曼反对黑格尔按部就班、以纯粹理性为最终旨归的意识发展四阶段。从哈特曼对华兹华斯诗歌中诗人自我意识产生与浮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哈特曼认为诗人在日常状态中并不会保持反思自身意识并以自身意识作为意识对象进行把握的状态。
诗人的思绪通常如同流水散漫,这个状态类似于黑格尔意识发展的感性第一阶段,外界物象在诗人眼前流逝而过,但并没有在诗人心中留下特别的印象,而诗人自己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心中所想,如同黑格尔所说“自我仅仅是共相,正如一般的这时、这里、这一个是共相一样无疑地意谓一个个别的自我,但是正如我不能说出我所意谓的这时、这里,同样我也不能说出我所意谓的自我。”
[1]( P. 76)在黑格尔那里,共相是指感官认识的对象,虽然这些对象各自不同,但都只是虚无缥缈的感官体验,不具备理性概念的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感官对象都一样虚幻和不稳定,无法被理性确立为恒久不变的抽象概念,因此,感官对象都是共同的虚幻印象,彼此并无差别,即“共相”。可是,在对象与思绪的散漫之中,突然出现特别的事物吸引诗人的注意力,于是一切都变得不同。诗人在神思恍惚的漫途中被惊鸿一瞥的景象所吸引,意识围绕眼前之景萦逗不去,这时诗人所关注的对象不再是随机和任意的个别共相,而是具有神秘魅力的独特对象,与此同时诗人产生了独特的心情,而这一时一地的眼前之景与心中之情在诗人离去之后仍然长留记忆。哈特曼将诗人被特别之景吸引和打断的瞬间片刻称为“惊奇”,正是惊奇打断了诗人散漫无主的思绪流浪,使得诗人在与独特景象的素面相对中建立了自我意识。惊奇导致诗人对某个对象产生独特的心情与特别的关注,正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念对黑格尔现代理性的内部拆解。感官对象与理性概念之间的固有的虚无/确定的差别疆界就此瓦解。因此,哈特曼自我意识的产生本身就是对现代性传统中理性—感性这组对立概念的解构。
正是由于自我意识在现代与后现代、理性与感性之间沟通往复,因此自我意识具有两重性。
自我意识的两重性同时也是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将自身作为对象这一特征的解构性传承。在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中,自我意识产生以后,不但使得对象脱离了感性的随机任意与虚幻不定,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思与重认,自我意识产生的这一刻,不但感性认识对象变得独特而奇妙,自我意识本身也在自我的注视之中如同眼前的风景一般耐人寻味。虽然哈特曼在描述诗歌中的自我意识时并没有点明,但在他的文学批评思路中,自我意识其实已经一分为二,一体双生。哈特曼以华兹华斯的诗歌《孤独的割麦女》为例,诗中描写了一位在远远高原田野之中一边劳动收割一边白日放歌的陌生女子,诗中的“我”被歌声深深打动,难以忘怀。
“就像自我意识这一被分享的现实一样重要的,是每个诗人面对自我意识的方式。《孤独的割麦女》并不是通过沉思的分析去查询一种情感来源。诗人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他对高原上的女子产生如此强烈的回应,他的诗歌只是动用了他的回应的力量。展示了他被感动的现实之后,他允许这种情感具有自己的生命并且因为思想和感觉的进入而感到愉悦。”
[3]( P. 6)哈特曼认为,自我意识产生以后,诗人虽然将割麦女的歌声长久存留心中,但并没有对意识的对象即割麦女的歌声为何吸引他进行追究,反而回返自身,让意识在自身的感情中回荡。“具有自己的生命”并且伴随“思想和感觉的进入”的是诗歌中的自我意识,而观察和发掘这一自我意识产生生命、思想和感觉整个过程的也是自我意识,在这里,自我意识自身分裂为两重,一重是作为观察者的自我意识,一重是作为被观察者的自我意识。“诗歌开始于惊奇———一个普通的场景被一种不寻常的氛围所改变了: 割麦女是孤独的,并且她的歌声强化了本来应该期望热闹和愉快的丰收活动中的这种孤独———惊奇转化成了一种哀思,甚至挽歌。这里有一个内在的沉入,好像心灵被高原上的割麦女感动之后,现在被它自身感动了。这种神秘就在于对自我的突然深入,或者说对于自然和自我的双重震惊。”
[3]( P. 6 -7)“内在的沉入”正是双重自我意识的产生,割麦女的歌声因为激发了诗人的自我意识而成为独特的存在,而自我意识被自然中场景与声音所触发滋生以后,又将自然与自我一同作为了认识与观察的对象。哈特曼将自我意识对自然与自我的观察反思称为“双重震惊”,一方面暗示了自我意识的双重性,一方面也不动声色的将“自然”与“自我”置于了同样的地位。这是自我意识在解构了理性与感性矛盾对立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另一重解构:对于主体与客体对立关系的解构。在现代性逻辑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体现了掌握了知识与技能的人类对于自然的占据与支配。主体是主动的、索取的,客体则被动的被认识,划分入不同的分类体系,以供主体的掌握和利用。可是在哈特曼的文学批评中,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一同成为了自我意识的认识与体认对象,一同激发了自我意识在无意识思绪流动中的形成与浮现。在自我意识的产生过程中,主体失去了把握和支配客体的主动性,因为只有在特定自然场景的激发与触动下,自我意识才具备诞生的可能。因此在哈特曼的自我意识生产过程之中,自然这一客体从形成自我意识的主体那里分享了主体的主动性,不再被动依赖于主体的认识与开拓; 同时,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与作为客体的自然一同成为自我意识的认识对象。也就是说,在现代性思潮中应当占据绝对主导的霸权地位的主体,却在自我意识的两重性中成为了被动性的认识客体。在这里,主体—客体之间支配—服从的矛盾对立也被自我意识化解于无形。
如果不能理解自我意识在自身分裂出的双重性,就容易产生对文本中自我意识的极大误解。
例如,华兹华斯的诗歌《我像一片云一样孤独地徘徊》就曾经遭到严厉的批评。在这首诗中,诗人抱着一种孤身漂泊的心境在山谷徘徊,突然看到了一片金色的水仙。盈盈水仙在风中摇曳飘拂,如同起舞,让诗人抛开了先前的凄清荒凉,水仙这一视觉对象引发的惊奇使得诗人长久驻足。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诗人怀愁闷坐、倍感孤独的时刻,曾经令他流连忘返的水仙都会在诗人心中重现,与诗人的心灵一同舞蹈,让诗人的心中充满欢乐。
安娜·西沃德就认为,水仙的舞蹈以及日后水仙进入诗人的回忆并且使得诗人的心灵与水仙共舞这样的描写脱离了自然,是形而上学的自我主体塑造。西沃德认为,作为一首浪漫主义诗歌,应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人对自然的全情融入,而诗歌中不但把水仙拟人化,将水仙的风中招展描述为舞蹈,而且还凸显了诗人的自我感受,在这种自我感受中,原本具有自然属性的水仙被诗人的想象虚构化,甚至跟诗人的心灵共舞。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自我想象将水仙花的自然属性完全篡改,因此这是形而上的自我对于自然的对抗与推拒。但哈特曼指出,与水仙共舞的不是形而上的自我,而是打破了理性形而上与感性体验、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立界限的自我意识。“华兹华斯如此不稳定的,并且如此难以与自我中心主义分离的精神性因素,就是瞬间的注意……他很少细数郁金香的纹路,但他不断地细述他的心灵状态。当华兹华斯描写一个对象时他也在描述他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他自己的真实,一种获得自我的揭示。”
[3]( P. 5)华兹华斯不对自然中的水仙模物写貌,而是对自我意识穷情刻画,就是因为自我意识的二重身份与自然景观一样,都是自我意识的认识与体认对象。把握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华兹华斯的诗中真意恰恰与西沃德的理解相反,不是形而上的主体篡改了对象的自然属性,将形而上的抽象人格强加于自然的花卉,而是自我意识将自身融入自然,与自然对象一同分担自然属性。诗中不存在形而上的自我主体,只有分裂为主动观察者与被动观察对象的两重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的两重性首先是自我意识自我分裂为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为自我意识分裂为两重对立的自我,即过去的自我与这一刻的自我。哈特曼对《圣经·创世纪》中《雅各与神使者摔跤》一章的解读就展示了作品人物的自我意识所分裂出来的自我对立。雅各通过诡计夺走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地位和祝福之后逃离故乡,投奔舅舅拉班,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二十年后带着妻儿和舅舅的家畜财产逃回到故乡,企图与哥哥修好。在重逢兄长的前一夜,雅各夜间起来,打发妻儿使女和所有随从过河。只剩雅各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与他摔跤,黎明时分,无力胜过雅各的对手为雅各赐名以色列,代表神的祝福,因为雅各战胜了神。哈特曼认为,在雅各的整段人生经历中,这段插曲的出现十分吊诡,在这一夜之前,雅各与舅舅拉班决裂,准备回头面对被他欺骗和伤害过的哥哥以扫,并事先准备好丰厚的礼物打算向以扫赔罪,也已准备好万一以扫旧恨难消、大开杀戒时的逃离方案。在这一夜之后,雅各见到以扫,以近乎谄媚的方式获得以扫的原谅。如果没有这场突兀而神秘的夜间搏斗,整个故事会更加流畅和浑融。而雅各本人在这一半路杀出的搏斗中也发生了自身的刷新和突变,甚至得了神的祝福。在哈特曼眼里,受到上帝祝福的雅各不但毫无神性,甚至称得上狡猾无行: 早年在父亲临死之前假扮成哥哥以扫骗取本应该赐给以扫的祝福,之后又用类似巫术的诡诈夺取了舅舅所有的肥美羊群。可是,在与天使搏斗的那一夜,雅各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天使,名正言顺地获得了神的祝福。“雅各摔跤这一神秘插曲实际上给他机会证明他自己,他与神秘人搏斗并且胜利———虽然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他的父亲、哥哥和我们的道德感。”
[4]( P. 75)“我已经指出了关于雅各人格的令人惊讶的概括,从狡狯之徒、犹太人中的奥德修斯转变为神圣的族长,触动了上帝并被上帝触摸。然后这一插曲中还有突如其来的逆流……‘只剩下雅各一人’……对于当代读者来说一个令人迷惑之处就是那个‘有一个人’的突然出现。另外就是他希望日出之前离开。最后,这是一个对抗并击败神使的不同寻常的主题。”
[4]( P. 77)不管是被打断的完整叙事还是陡然突转的雅各人格形象,都能在冥冥之中指向哈特曼在解读华兹华斯诗歌时对自我意识的勾勒和形容: 被阻止的旅行者。而神秘人的出现就是阻止“旅行者”的“惊奇”,在被神的使者打断日常节奏的雅各打败对手之时也击碎了过往的诡诈阴谋,成为了通过自身力量获得胜利而被神祝福的以色列。在这个突如其来又恍惚而逝的夜晚,我们看到了雅各在与神角力中迸发的自我意识,使得过往卑劣狡诈的他在神赐之名中沐浴圣光。在雅各那里,雅各的自我意识分裂出卑劣的自我与神圣的自我。而卑劣与神圣的矛盾对立也在雅各这一人物的自我意识之中消解: 一个卑劣的人,可以在某个战斗的瞬间变得神圣。以此类推,现代性概念体系之中一切矛盾对立的概念都可以在自我意识的某一瞬间冰释前嫌。
三、自我意识在文学批评中的流动
自我意识产生以后并非凝固静止,而是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自我意识的流动状态是哈特曼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精神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运用,也是对黑格尔现代性概念的解构实践。黑格尔认为,意识到达自我意识的概念阶段之后,就是精神现象学的终结,自我意识将安住在自己单一性的最终形式之中,固定不变。而哈特曼的自我意识却不断在建立之后自身解构,沉没于潜意识,自我意识时不时的在潜意识中实现浮出水面、鱼跃龙门的那一刻,在刹那光辉之后又归于沉寂,又在沉潜已久之后重见天日。因此,哈特曼的自我意识没有终点,也不会长久持存,总是在建立与解构之中来回往复,无始无终。
文学批评中自我意识的流动首先体现在自我意识本身的产生过程是流动性的,这种流动性依托于记忆的延迟。在分析华兹华斯的诗歌《我像一片云一样孤独地徘徊》时,哈特曼强调了自我意识的灵光一现之后的记忆延迟与最终重生。诗中金色水仙这一视觉对象引发的惊奇使得诗人长久驻足,这时诗人虽然将水仙融入了内在精神,但并没有建立具有自我反观能力的自我意识。直到时移事易,在人生经历获得不断的丰富之后,诗人仍然牢记这副生机勃勃的自然图景,因此无数次再度感受到那种空茫寂寥的境况之时,金色水仙都会横空出世,进入诗人的回忆,这个时候诗人才真正实现了自身的自我意识,瞬间滋生出的自我意识终于能与自然风露中的金色水仙并肩共舞。也就是说,自我意识的这种自我揭示是在回忆被耽搁和延迟许久以后出现的。华兹华斯诗中“回忆”和“耽搁”可以对应德里达的“痕迹”与“分延”,水仙花的形象是大自然中水仙在诗人心中留下的痕迹,是空间在诗人心灵中的分延,也是时间在诗人记忆中的分延。诗中的金色水仙因为是诗人的回忆所以是不在场的,诗人面对的是自己心灵中的水仙痕迹,在痕迹中他重新面对了自我,在痕迹的分延之中瞬间的自我意识浮出水面,绽放光华。
与德里达不同的是,哈特曼倾向于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痕迹和分延,认为象征不在场痕迹和分延能够为文学作品带来更鲜活的生命和更为深刻的感染力,并凸显瞬间的自我真实,这种真实感虽然只在瞬间浮现,但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恒久流转,并且在不同的读者那里获得各具特色的千万种风情。同时,感性记忆的延迟也与弗洛伊德的前意识理论有关。弗洛伊德认为前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在于,前意识中储存着词表象,也就是知觉留下的记忆残余,并且在一定的刺激与提醒之下会再度进入意识。词语的残余首先从听觉中得到,同时视觉记忆残余也极具重要性。前意识虽然处于无意识之中,但是能够通过感性记忆残余的提醒再次进入知觉。正是前意识与感性记忆残余之间的关联使得瞬间的惊奇能够转为回忆,并且在适当的时间电光石火般重现。德里达解构主义将文本视为语言的嬉戏,但语言的嬉戏是否是完全漫无目的章法? 对于这一问题,哈特曼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之中给出了回答。语言的嬉戏并非彻底的散漫无凭,而是立足于前意识中的感性残余记忆,使得自我意识一方面能够自由的舒展生发,一方面又依托于现实在心灵中留下的记忆痕迹。
自我意识本身在浮现与沉潜之间流动,同时自我意识在文学批评中的展开也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流动,哈特曼将自我意识在具体的对立两极之间的流动称为“猜测”。哈特曼认为,通过诗人的猜测,一个形象会连缀起广阔的社会人生内涵,批评家则通过这种分析在解释形象的同时对形象进行了再创造。以《孤独的割麦女》一诗的第三节为例,诗人对割麦女所唱的歌曲进行了种种猜测:她歌唱的内容是讲述古代的战争还是倾吐今日平凡的哀乐? 这一猜测中包含了历史—现实、个人—社会这两组对立。哈特曼对此解释道: “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充满了意义……展示了这首歌是如何超越了它自身,引起诗人的浮想联翩。他对于读者的新的姿态混合了向外的情感和向内的思索。第三诗节包含了两个猜测,继续探索由孤身一人走向整个社会的冒险。这首歌是否向着与历史的过去或者与神秘的过去相关联的磨难流动? ……在如此偶然的一个形象之中出现的人类交流的力量及其无限的回响就能够被把握了。通过这个词或者这一转换,有限被消除了。”
[3]( P. 8)“孤独的割麦女”这一单独的形象,通过诗人自我意识的情感注入,在浩瀚的历史、无边无际的神秘与任何时代的现实生活这两极之间来回往复地流动,因此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有限的形象,而是在不同读者的自我意识的投入与感触之下,在无休止的猜测和联想之中获得了源源不绝的流动性以及永世不竭的无限性。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诗中的猜测是植根于自然现实的,并且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偶然的自然景象给诗人带来惊奇,诗人在由此而产生的自我意识之中对眼前所闻所见进行天马行空的推测和联想,为笔下的形象赋予了摇曳生姿的无限生命。而这些推测和联想都是在本应矛盾对立的两极之间展开的,现代性体系中本应彼此否定和对抗的对立关系在哈特曼那里却成为了自我意识实现流动状态的基础。
哈特曼认为,诗歌本身就是在流动的猜测之中展开的。
猜测不仅是自我意识在诗人创作之中的流动与丰富,同时也是文学批评中自我意识的展开方式。如果说诗人的自我意识是被自然的惊奇所阻止的旅行者,那么批评者的自我意识就是被文本中两极对立间的突兀与惊奇所阻止的旅行者。批评者不但要把握诗人在文本中明确设置的对立关系,同时还要进一步发掘表层对立两极背后更深层的矛盾双方。再以《孤独的割麦女》为例,文本中明确提出了过去—未来,个人—社会这两重矛盾对立,但哈特曼认为,这两重对立只是个别具体的,而自我意识流动所实现的文学批评应当挖掘出超越个别对立、能够沟通一切文本的终极对立。
因此哈特曼深入剖析了歌声吸引诗人驻足的深层原因。他认为,诗人之所以会对割麦女感到惊奇,是因为孤独的歌声与收割的场面本身就是矛盾的。通常的收获应当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丰收应当是欢乐的,但诗中的割麦女分外孤独,连歌声都带着凄楚。在这里,割麦女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形象,而是与过去传统的收割场面形成了对照,猜测就这样在流动之中将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连缀了起来,从而不断拓展自我意识本身的界限,使得自我意识上天入地,投身古往今来,获得无限广阔的生命。而诗中具体场景与传统记忆之间的差别对立又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索。收获中欢乐与孤独的对立导致诗人进一步联想到丰收的反面,如果丰收代表生的希望,那么丰收的对立面就是死的沉寂。对于哈特曼来说,生死大限正是自我意识中的终极对立。生存与死亡,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因此也是不同文本共同面对与思考的恒久对立。哈特曼在文学批评中最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自我意识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流动与分延。
可以看到,通过自我意识在生存与死亡之间的流动,文学文本已经与现实人生息息相通,现实人生是文学文本的基石,文学文本则是对人生问题的回应与思考。这与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内部自成世界,与外部现实社会毫无关联。因此,自我意识所面临的终极对立也是双重的,即生存—死亡的对立与文学—人生的对立。这一思路在哈特曼对于《俄狄浦斯王》的解读中得到了贯彻和延续。哈特曼认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就是俄狄浦斯在预言与命运之间的求索与抗争,而预言—命运这一总的对立背后,又展开了一系列人生的对立。比如,生与死的对立: 预言昭示必然失败甚至死亡的结局,命运则是俄狄浦斯对于预言充满生命力的反抗与挣扎; 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对立: 父亲给予儿子以生命,儿子却要夺取生父的性命; 亲情与爱情之间的对立: 母子之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为温馨慈和、最为包容和伟大的情感,却被迎娶生母这一乱伦行为所亵渎和玷污; 情感与理性的对立: 由情以观,俄狄浦斯作为弃儿被他人收养,根本不认识自己的亲身父母,弑父娶母,绝非本意,而他在位期间的勤政爱民,在灾难面前的痛心疾首,也表明他是一位明君,但是以理而言,正是因为他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之下犯了弑父娶母的滔天大罪,导致整个城邦陷入灾劫,所有的臣民都因为他的罪孽而受苦,因此他又必须受到惩罚。正是在生与死、父与子、情与理、亲情和爱情间的针锋相对中,自我意识来回流转,蜿蜒往复,使得俄狄浦斯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与批评家那里不断获得解读,万古常新。而所有的解读其实都是围绕文本背后所隐藏的一系列两极对立展开的。同时,许多不同的文本因为生死、父子、情理等共同的对立两极而获得了沟通呼应的可能,这正呼应了解构主义中的互文性理论: 所有的文本彼此之间都是敞开的,任何文本都不是单独的,而是与别的文本相关联。
但是哈特曼的自我意识理论同时还为互文性理论增添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敞开和勾连,是因为它们之中的自我意识面对着相同的对立两极。可以说,自我意识在两极之间的流动正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中“痕迹”与“分延”的语言嬉戏在文学批评中的实际运用,同时也克服了德里达解构主义专注于能指的漂流却过分散漫无依的危险,因为自我意识的流动虽然因人而异并具有天马行空的自由,但供自我意识来回往复的对立两极却扎根于文本,使得自我意识的流动始终以文本本身为依托。
四、自我意识中的想象
自我意识在猜测运动中达到的最高临界点就是想象。在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解读中,哈特曼首先指出,华兹华斯诗歌里的自我意识来源于自然为诗人带来的惊奇,因此自我意识的产生需要自然的引领。可是在自我意识的产生与流动过程之中,又可以不断的壮大、增强自身对抗自然的力量。而自我意识对于自然的对抗并非有意为之,相反,正是自然本身的神秘与广大导致了自我意识对于自然的重新认识与对抗。华兹华斯的《序曲》一诗,就描述了自我意识被自然所阻隔、蒙蔽又绝处逢生、反而孕育出对抗自然的想象力量的全过程。华兹华斯多年前攀登阿尔卑斯山,途中与众人走散了,只好自己寻觅登山的路途。披林寻路一番之后,华兹华斯在向当地人问路时才知道,他其实已经翻过阿尔卑斯山,但是在翻越的过程中却完全不知。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乐趣与成就感本身就在于向着顶峰的不断攀援与跋涉之后终于能够登临绝顶的快感,而这一切的期望都在不知不觉间错失。等待中的登顶与翻越已经在不清不楚的寻觅之中发生,可是如果发生的当时自己并不知晓,那么爬山的乐趣又在哪里呢? 在华兹华斯看来,曾经令他亲近不已、如同母亲一般的大自然,这一次却将他蒙蔽了,他发现大自然除了无私的美景之外,还有着神秘与未知,有着光明开阔背后的黑暗深渊。可是,被自然所拒绝和遮蔽之后,华兹华斯如同弃儿一般,在陷入孤立无助的状态之后获得了自我壮大的力量。《序曲》中充满激情的抒写到,当华兹华斯在大自然中迷失方向,他看到了想象的光亮。自然短暂的弃绝,使得自我意识获得自我成长的独立性,能够面对自然的神秘与黑暗。在想象的产生过程中,自然本身显示出了矛盾对立: 亲近与拒绝,光明与黑暗。如果说平日的大自然代表着生机勃勃,滋养万物的生命活力,那么令人迷失的大自然就代表着对于生命活力的封闭、排斥和拒绝,也就是死亡。可是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扼杀自我意识,反而让自我意识向死而生,独立于自然的拥抱滋养,自立自强。分裂为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自我意识这时发现自己本身具有源源不绝的力量,在这种力量发展到最高点的时候,自我意识能够脱离自然,在自然之外发掘自身内部生的生命能量。想象令诗人陷入死亡的恐惧,但随后又凭借想象的力量奋发精神,实现了对死亡恐惧的战胜。想象与自然进行对抗,最终达到与自然的平衡。在这里,自我意识同样是两重性的: 一重是对自然的依赖,一重是自我的独立; 一重是对死亡的惶恐,一重是对死亡的超越。在想象之中,两重自我意识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对抗,最终获得了第二重自我的暂时胜利。可以说,想象立足于自我意识的两重性与流动性,但却实现了对这两者的超越。
结语
哈特曼的自我意识可以说是借尸还魂,在现代性概念的躯壳之中注入了解构主义的精魂。虽然自我意识这一范畴本身来源于黑格尔,但在哈特曼的文学理论视域之中却将现代理性同一性与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思辨与文学批评沟通连缀了起来。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对现代性传统的拆解,哈特曼的自我意识却扎根于现代性概念范畴,从现代性概念的内部实现解构; 哲学力图以理性驱逐感性,哈特曼的自我意思却通过理性的哲学范畴认识和解读文学中的个人情感。因此,哈特曼所开创的自我意识这一跨越理论时代与话语领域的文论范畴,出自黑格尔的现代性却又经受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洗礼,来源于严峻的哲学思考却又驰骋于活泛的文学批评之中,集中体现了哈特曼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在传统与解构双方面实现的理论与实践突破。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 [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2][法]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家堂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3]Geoffrey Hartman,Wordsworth's poetry 1787 ~ 1814,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4]Geoffrey Hartman,A Critic's Journey: Literary Reflection1958 ~ 1998,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结语作为美国当代文学理论更迭的见证者,希利斯米勒曾受到英美新批评、意识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在诸多理论和流派的影响下,米勒对文学批评的认识不断更新,但有一点却从来不曾改变,那就是对文本多义性的探寻。在新批评的影响下,米...
洛特曼“符号圈”理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思想的活跃、批评话语的审美转向,在中国学界逐渐由被忽视走向被发掘、阐释和应用的。...
一、先锋溯源先锋一词最早记载在中国古代史书《三国志蜀马良传》中,属军事术语,指军队作战中的先遣部队。国外则认为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avant-garde一词,也是用来指军队的前锋部队。到19世纪30年代,由于傅立叶、欧文、蕾德汶等英法空想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