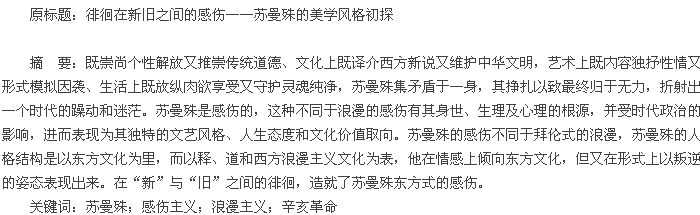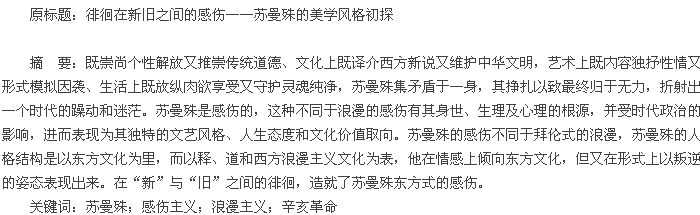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苏曼殊是不朽的人物,短短三十五年的生命传奇,演绎近代中国的政治、宗教、文化变迁的深层底蕴和斑斓色彩,小说家、诗人、画家、翻译家、和尚、革命志士,在曼殊身上不可思议地交融在一起,并在每一个方面都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许多似乎不可调和的东西奇迹般的被苏曼殊一个人的心灵承载出来,于是,苏曼殊成为辛亥革命前后时代风气的表征, 徘徊在新旧之间的感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曼殊,也造就了苏曼殊独具风采的美学价值。
一
苏曼殊的身上,处处充满了矛盾。作为文学家,有人把苏曼殊归结为旧人物,周作人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 谢冕称:“综观整个20世纪,用旧体写诗的所有的人其成绩没有一个人堪与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相比。……苏曼殊无疑是中国诗史上最后一位把旧体诗做到极致的诗人,他是古典诗一座最后的山峰。” 顾彬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 。而钱玄同则认为曼殊的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新文学的源头,“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 意谓苏曼殊开新文学风气之先。着名学者杨联芬教授指出,五四小说完成了中国小说由讲故事到表现(向内转)的现代性转化,但它的发端,却不能不追溯到民国初年的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小说主人公的自我表现、忠实于个人主义选择的主观化叙述,不愧为20世纪中国浪漫小说的先声。
作为画家,有人把苏曼殊归于传统文人画的南宗一脉,他的画多峰峦、危岩、孤松、垂柳、残月,以及荒凉的城垣、幽远的庙宇、村边的茅台、山间的断桥等意象,体现出一种空灵、平淡、意无尽的境界追求,体现了曼殊的古典文人趣味。他的女弟子何震说,他“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 而柳亚子对苏曼殊评价非常的高,“绘事精妙奇特,自创新宗,不依傍他人门户。” 陈独秀曾说,“曼殊作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匠之浪费笔墨”。 柳无忌则说,“他带给中国画一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性和构思,他的艺术是如此独特、卓越,观察起来比任何语言所能形容的都要好。曼殊的画,超越了自然和生活的真实,达到了一种在近代中国绘画里罕见的空灵的美。”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开派人物黄宾虹说,曼殊一生,只留下了几十幅画,可惜他早死了,但就是那几十幅画,其分量也够抵得过我一辈子的多少幅画!意谓苏曼殊启动了近代中国画革新之旅。
作为和尚,苏曼殊自幼就有浓厚的佛门情节,一生三次出家,三戒俱足,并“白马投荒”,远游南亚佛国,然而他于佛法并不能身体力行,谨守戒律,时而僧装芒鞋,终生守身不娶;时而青楼柳巷,终生暴饮暴食。精通佛理,出入尘世,更像旧时代风流名士的作派,“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个名副其实的和尚” 。然而,有人却说苏曼殊“懂得佛教最高深的意义”,孙中山当年把曼殊与近代佛教非常着名的佛教太虚大师比较,然后说,“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功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曼殊圆寂后,柳亚子这样哭他:“鬓丝禅榻寻常死,凄绝南朝第一僧。”
亦有人称曼殊是中国佛教的“马丁·路德”,意谓苏曼殊是开创中国佛教新局面的人物。作为革命志士,曼殊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却又与革命若即若离。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横滨暗杀团、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试图刺杀康有为,发表《反袁宣言》,大骂其为“独夫民贼”,他与孙中山、黄兴、陈独秀、章太炎等革命巨子结为挚友,孙中山称曼殊为“革命的和尚”。着名学者马以君认为,苏曼殊实在是一位“以革命为天职,以创作为余事,有心革命业绩不显,无意为文成效甚高的资产阶级民主志士”。 曼殊死后,革命团体光复会追认他为“文化导师”;但苏曼殊投身革命,却不“借革命以营私”。革命成功之后,苏曼殊欣喜若狂,也只不过想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光宗耀祖。
作为翻译家,苏曼殊最先倾心西方文明。苏曼殊与严复、林纾合称清末三大翻译专家,柳无忌认为,“在二十世纪初年,苏曼殊实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创始者,重大的功臣,诸如梵文的介绍,西洋文学的翻译,中诗英译的编集,有其辉煌的成就。” 他热情地介绍虚无党人的事迹、着作,他翻译兼创作的《惨社会》通篇充斥无政府主义言论,足证苏曼殊先于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很早即受无政府主义之深刻影响。姜东赋之《论苏曼殊》指出苏曼殊是“一个已经有所觉醒,已经获得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感染的知识分子”。 但后来苏曼殊思想发生明显转向,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日益反感,他不愿与欧美人同游,他与拜伦亦渐行渐远,意识到拜伦之信仰追求“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能安身立命的是什么呢?辛亥革命后的苏曼殊对东方文化的认同程度越来越深,从语言、文字、文学到礼俗、哲学、宗教,逐渐形成明晰之文化层级意识,以为印度文明优于中国文明,中国文明优于西洋文明。以致于周作人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 ”的确,苏曼殊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复杂体:集佛教、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浪漫主义、个性自由和封建道德于一身。在当代学者陈平原看来,苏曼殊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
有人因此而认为苏曼殊的社会人格是分裂的,他无法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社会的游离分子,任何既定的称谓都不能准确地界定他。他时而身着中式服装,俨然“保守旧道德”的遗老;时而一袭洋派十足的西服,又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教士;时而袈裟披身,似乎化身为悲悯众生的佛祖。社会角色的错乱使苏曼殊内耗了他的才华,最终难以有大作为。
但这只是表面的皮相,矛盾并非绝对的,复杂中有基本的底色。郁达夫总结说,“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浪漫,是苏曼殊的最明显的符号,然而,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讲,不是浪漫,而是感伤,浸润出了他奇特的生活风范和强烈的个性表现,并创造了不仅仅属于苏曼殊一个人的时代病。
二
辛亥革命前后,笼罩在在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文人们很少不表现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爱情的觉醒、命运自主性的觉醒,一方面又是觉醒后的无力、迷茫。无力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对自身命运的无力,迷茫是指在顽强的传统面前对未来前景的迷茫。这种感伤的情调,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人处于历史转折期必有的感情标记和心理氛围。
不过,苏曼殊的感伤不仅表现于文化、美学的层面,更有其身世、生理、心理的根源及现实政治的影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苏曼殊终身挥之不去的疑惑。苏曼殊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他的父亲苏杰生(珠海前山镇沥溪村人)曾经任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苏杰生一生曾经娶过一妻三妾,而其中一妾就是日本女子叫河合仙。
曼殊生母,据现在考证叫若子,有人把她称为河合若,她的身份是河合仙的妹妹,所以苏曼殊其实是一个私生子。曼殊出生三月,若子就离开了苏家,苏杰生将曼殊交其妾河合仙抚养,曼殊从此也就认河合仙为其生母,或许苏曼殊一生都不知道自己不是河合氏亲生的。
到了6岁那年,苏杰生撤离横滨将曼殊带回沥溪,但是河合仙没有一同回来。5、6岁的孩子离开了自己的亲母亲,那种孤独、不安一直伴随了苏曼殊的前半生。苏曼殊九妹苏惠珊回忆曼殊返乡后的生活说,“一父数母,各爱其子女”,“时或婶婶辈言语不检,人重此轻彼之分,使三兄感怀身世,抑郁不安。” 其侄苏绍贤回忆说“性孤特,与人罕言语。然闻人谈论,与其意不合者,辄抗声致辩,滔滔汩汩,必令人无可置喙乃已。” 13岁时,曼殊离开沥溪前往上海,从此以后曼殊就与珠海永诀了。
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血统,但是他又很怀疑,这便成为折磨他一生难言的心事,柳亚子说曼殊“而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 苏曼殊自己写给友人信中说“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每一念及,伤心至极矣!”所以以后他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身世就是“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 冰。”没有家可以归依,飘零以及与飘零相伴的伤感便成为苏曼殊的生存常态。
让苏曼殊伤感的另一大因素是他的身体。苏曼殊从小就瘦弱,身体不好,“九年面壁成空相,万里归来一病身。泪眼更谁愁似我,亲前犹自忆词人。”但终其一生,既极度贪吃又特别好色,沈尹默有诗描述说“任性以行淳,关心惟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 对此苏曼殊倒也并不避讳,顾彬曾指出:
“苏曼殊……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苏曼殊在上海常常出入于“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每天豪华豪宴,每次都是放开肚量,将各种美味吃到盘碟见底。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 柳亚子回忆苏曼殊的贪吃时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芋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
1907年前后,苏曼殊在日本与鲁迅有过一段交往。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到苏曼殊,对苏曼殊的诗文评价很高,对他的个人生活则不表恭维,他对一日本友人说,苏曼殊是“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与其说他是xuwuzhuyi者,倒应说是颓废派。”
对此,他的挚友陈独秀却说,“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 其实,速死的办法有很多种,何必非要如此呢?这种抑制不住的贪吃只能说是生理的病态,它导致与死亡的近距离,以及面对生命无常的感伤。
比生理病态更让人感伤的是心理的病态。男女情爱,是曼殊一生中最好的风景,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隐痛。苏曼殊的初恋对象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姑娘,很快便无疾而终。其后,他的西班牙籍英文老师庄湘愿将爱女雪鸿许配给他,他只能垂泪“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再后来,河合仙极力撮合曼殊与表姐静子成婚。他又以佛门未便论娶推掉。他到处以和尚自称,却经常出入青楼,为不少风尘佳丽写下情深意切的诗篇,然而,当花雪南、百助枫子等与他相爱的青楼女子最后要委身于他,他却决绝地走开了。
在日本时,他与凄苦、美丽的调筝人相爱是“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但最后同样分手: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他为情所困,为情所伤,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全身而赴,却又全身而返,始终未曾与一位女性有过真正的性爱。
对于苏曼殊的这种有些玩世不恭的行为方式,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不解人事”的“婴儿”。陈独秀曾说他“是大有情人,是大无情人,有情说他也谈恋爱,无情说他当和尚。”“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章太炎也说,苏曼殊“独行之士,不从流俗”。而国内外也有学者针对苏曼殊“热于恋爱而冷于结婚”,猜测他可能有生理上的缺陷。
不论生理上的缺陷是不是真的,心理上的缺陷却很明显。苏曼殊曾裸身闯进女弟子何震的房间,指着洋油灯大骂,表明他的精神已经出了问题。“忍见胡沙埋艳骨,休将清泪滴深怀。多情漫向他年忆,一寸春心早已灰。”苏曼殊面临的是爱无力,是心理上的阳痿,和尚的戒律只是一种托词。李欧梵曾说,“他那副和尚的外表仅仅是一种装饰罢了,并不能为他的生活态度提供多少正当的理由。倒是给他格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传奇的色彩吗?更多的还是无奈的色彩吧。
三
另一让苏曼殊感伤的一面来自时局。他对于自己长于斯的国土充满感情,大量的着作中倾注了祖国命运的忧怀,“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哀国家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苏曼殊积极翻译拜伦的《哀希腊》,希望用《哀希腊》这篇文章去唤醒国人振衰起敝的决心。
他认定,满清是造成国家衰败的祸首,要救国,就要反清。 苏曼殊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主张无政府主义,土地、财产归穷苦的民众享有,对极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美国女杰郭耳缦尤为推崇,特别翻译了她的传记。
1913年 7月 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痛斥袁世凯是嗜血恶魔。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正是它为苏曼殊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誉。
革命始终贯穿于苏曼殊的一生,但革命依然不是苏曼殊生命的主旋律。激情过后更多的是疲敝、是怀疑、是失望。辛亥革命胜利,革命党人的一些作为很使曼殊对革命变得悲观,他曾流露过对一些革命党人的不满:“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也不满那些只会“做几句歪诗的”志士。对于革命党人争相攀爬上位,争权夺势,苏曼殊给予了尖锐的讽刺和指责,即便是他十分敬重又大他十岁的章太炎。
鲁迅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曾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虽有革命要求,但他们“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可谓一针见血。不说袁世凯“革命”最后为当皇帝,即与苏曼殊交往甚密的革命志士中,有为个人目的而变节投敌的,如刘师培夫妇;有因局部利益闹意见的,如章太炎;更有许多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而飞黄腾达的,如叶楚伧、陈少白等。在这样的“革命”现实面前,对革命向无功利的苏曼殊的心情可以想见。
胡秋原说:“今日一般人很难想到民国成立后的幻灭心情。辛亥以前一般青年希望民国成立再造中国的命运。结果‘莽操尸位 ',一切成空。如果仅仅袁世凯之徒倒行逆施,其事尚小。然而一般新人物或革命志士,在清末已有变节者。至于民国,尤多趋于寡廉鲜耻,成为势利之徒,一种幻灭与绝望之情袭击当时的知识界。”后来胡秋原对曼殊和弘一的出家评论说,“他们的出家,不仅代表个人的感伤,也代表了社会的感伤,代表对社会腐败的反抗或逃避的一种绝望的心情,由于他们有一片最真诚热烈的心,这反抗的逃避或逃避的反抗取一种感伤至于极端的严肃悲凉的形式,即出家。”
四
出家还不足以平息曼殊的伤感,他要诉之于诗、诉之于画、诉之于小说,从而形成了曼殊美学上的感伤风格。感伤不同于浪漫,但又与浪漫相关。郁达夫说,贯穿苏曼殊诗、画、小说的气质,是浪漫。陶晶孙亦曾说过: “在这个文雅人办的‘五四’运动之前, 以老的形式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者, 就是曼殊。”这是误解了浪漫的涵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艺术都主情。浪漫主义艺术充满豪迈的、昂扬的激情, 感伤主义多伴随着苦涩的、低沉的忧郁。浪漫主义的积极一面是狂飙突进, 感伤主义则包容了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 , 旧事的留恋, 与宿命的嗟怨。感伤既意味着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对现实世界产生了不满, 并有了向现实和命运挑战的意愿, 然而一旦现实世界过于强大, 主体在面临挑战和困境的时候往往选择退却或者逃避。
苏曼殊的作品,就是如此。他的诗作富于才情、灵性。他以情诗见长,缠绵真挚。他写男女情事,却包含着僧俗的冲突,浓郁而克制的感情,沉着而宁静。每首背后都能看到他的深情与无奈,挣扎与痛苦。
郁达夫《杂评曼殊的作品》说:“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 此所谓“近代味”,主要表现为抒写感情的大胆坦然,和与此相应的语言的亲切自然。苏曼殊熟悉雪莱、拜伦的诗,他的爱情诗中无所忌讳的真诚放任,以及对女性的渴慕与赞美,融入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神韵。在当时那种陈旧的思想压迫开始被冲破却又仍然很沉重的年代,渴望感情得到自由解放的青年,从他的热烈、艳丽而又哀伤的诗歌情调中,感受到了心灵的共鸣。但比较西方浪漫主义, 他缺少排山倒海的气势。
苏曼殊的画也呈现伤感主义情调。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萧瑟下别有怀抱。 他前期的画侧重表达反清之执志,后期绘画的表现情趣则愈趋悲凉,刊载在《民报》上的《猎狐图》《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图》《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图》《陈元孝题奇石壁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无不借古喻今,或许最初起意为呼吁国人救亡图存,结果却是抒发其忧国之思。苏曼殊还曾作《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
最能体现苏曼殊艺术情趣的还是他的小说。 这些小说的共同特征是:爱情故事中间穿插讽刺现实的说教以及悲凉的气氛。所以,苏曼殊不仅仅是讲故事,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对人生的体验,“莫名之惑”,与中国传统感伤小说侧重于外部叙述, 强烈者呼天抢地, 柔曼者哀感顽艳相比,苏曼殊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性。苏曼殊的笔触更多指向人物的心灵。苏曼殊笔下的爱情悲剧主要源自人物的内心冲突。这种内心冲突是苏曼殊小说的基本模式, 也是人物的感伤之源。 他把个体的两难选择提升到本体的高度, 于命运的凄凉情调、苦涩滋味中传达出人的无力感。
李欧梵在其《现代性的追求》中,将苏曼殊与林纾郁达夫等中国现代作家中情感一派的代表来比较,分析他们书写情感的不同方式。指出林纾与苏曼殊确立了建立于情感基础之上的个性方式。认为苏曼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与西方的结合,跳出了林纾的“儒生”模式,而又不同于其后的郁达夫的以性为基础的情感模式。
但郁达夫认为苏曼殊的小说“实在做得不好”, 原因在于“缺少独创性, 缺少雄伟气”。“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的确点出了苏曼殊的特征,诗、画、小说均如此,这正说明 苏曼殊情感表现的力度、人物内省的强度、艺术想象的方式,与西方浪漫主义有质的差别。其情感内核和美学风貌主要表现为感伤,而非浪漫。
五
感伤把苏曼殊和西方文艺的感伤主义扯上了关系,尤其和拜伦、歌德联系了起来,苏曼殊常被人称为“中国的拜伦”。拜伦,这位异域的浪漫诗人,一度是苏曼殊崇拜的偶像。他与拜伦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苏曼殊毕竟不是拜伦,近似之处以外,他们有更多的不同: 拜伦笔下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是拜伦式英雄的典型代表,高傲而倔强,忧郁而孤独,神秘而痛苦,与社会格格不入并与之进行彻底的反抗。曼殊笔下的三郎是曼殊式和尚的典型代表,清高而犹豫,柔弱而多思,痛苦而自虐,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并最终以出世来化解迷惑。在艺术风格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更契合,但歌德的感伤仅关乎爱情,曼殊的感伤则是全部的人生。拜伦是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斗士,苏曼殊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充满感伤情怀的文人。苏曼殊最终告别拜伦不是偶然的。
苏曼殊的感伤,其内涵、特质不仅与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洋主流浪漫主义大异其趣,也与以卢梭为代表的西方感伤主义貌合神离。西方感伤主义是因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而得名 。感伤主义重视自然景物的描写,侧重刻画人的内心世界,认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不幸的生活遭遇,以唤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 。
苏曼殊对欧洲浪漫主义及感伤主义之了解均零散而不系统,他只是从自己的主观意趣出发,接受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和雨果。更奇特的是,苏曼殊的伤感有时竟与国粹主义纠结一处,其实质不是张扬个性,挑战古典,而是承载民族之精神重负。他的感伤不是西学东渐的直接产物,反而是固有文化生态发生结构变动之结果,骨子里仍然是东方式的。
近世以来,人们多注意到苏曼殊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面,对他的中国文化本位观则严重忽略。研究者多彰显其“新文学”,少言甚至讳言其“旧道德”。苏曼殊是一个西方式的个性主义者吗?显然不是。他对拜伦的推崇,对浪漫主义、个性解放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残缺人生的自我拯救和士大夫任侠济世的现实需要。他对西方文化却是选择性的接受。苏曼殊的文化取向,始终处于晚清东方文化派的思想阵营。 在《告宰官白衣启》中,苏曼殊反对世俗事务侵占宗教场所,肯定宗教的积极意义,为中国民间习俗和朴素的宗教辩护,反对盲目崇拜西学和民族xuwuzhuyi,以国粹文化激发爱国热情。他的“怪”,更容易让人想到了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视权贵,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痴”;他的“真”与“狂”则与唐寅、徐渭等在迷茫和矛盾中追求个性自由平等中的反传统神似。
综观苏曼殊的全部,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苏曼殊的人格结构是以东方文化为里,而以释、道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为表,他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学理上都倾向东方文化优越论,但又在形式上以叛逆的姿态表现出来,传统固无可挽回地成为过去,未来又无路可走。“新”与“旧”的冲突,在“新”与“旧”之间的徘徊,这一切造就了苏曼殊的感伤,这种深刻的伤感体现于他的日常生活,体现于他的男女私情,体现于他的艺术创作,亦体现于他的政治态度,他的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复杂,都只是因为他的东方式的感伤。这种感伤,不光是属于苏曼殊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既是属于革命前后那个特定的年代,甚至在当今时代也能听得到它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