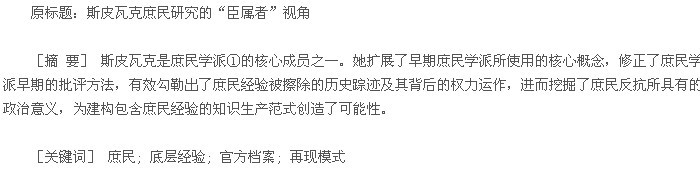
斯皮瓦克非常反感自己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庶民研究”被纳入“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体系中去。尽管斯皮瓦克一再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学界,她最着名的两篇论文《庶民可以说话吗?》与《臣属者的文学表现———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文本》却几乎无一遗漏地被编入各类“女性主义读本”或“后殖民批评读本”。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中国学界也一直以“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这样简化的标签来认识斯皮瓦克及其思想。那么,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
独特性在哪里? 本文将把斯皮瓦克有关庶民问题的讨论放置到庶民学派的学术思想架构中来讨论,重新认识斯皮瓦克庶民研究的独到贡献。
一、“庶民”与“庶民意识”
庶民学派有感于印度社会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用了葛兰西《狱中札记》中所采用的术语“庶民”( Subaltern) 来描述处于社会边缘的各类群体。但是在研究实践中,一方面,他们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一再重复自己所反对的学术研究范式,总是摆脱不了经济决定论; 另一方面,他们的批评范畴使用混乱,往往交替使用“被殖民者”、“妇女”、“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层”等术语,实际上架空了“庶民”这个批评范畴的所指。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斯皮瓦克加入该学派。斯皮瓦克的加入带入了文化研究的纬度,将该学派带出了僵化的经济决定论泥潭。同时,斯皮瓦克也利用自己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将该学派的学术思想带入了西方,第一次实现了第三世界学术的全球能见度,所以说“庶民学派”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传播与斯皮瓦克密不可分。
斯皮瓦克从本土社会权力图景出发,对庶民学派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庶民”作了重新界定,赋予了这个术语高度的流动性与情景化,从而将处于各种权力关系轴线末端的群体都纳入其中,使得建构容纳多元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知识生产范式成为可能。斯皮瓦克在一次媒体专访中对这个批评范畴作了进一步阐释,她说:我喜欢“庶民”这个词,因为它是高度情景化的。“庶民”这个词最初指军队里面的底层军官。葛兰西采用这个词对付检查制度: 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元论,把底层与社会边缘群体称作庶民。这个词语高度情景化的特点,可以避免僵化的阶级分析对于底层多元经验的遮蔽。
“庶民”与后殖民批评所使用的“殖民者/被殖民者”、女性主义者所使用的“男性/女性”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批评范畴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这倒并不是说斯皮瓦克追求学术时髦,而是说这些已有的二元对立范畴确实与印度社会历史与现实显得疏离,无法有效描述印度( 后) 殖民社会多元的权力关系以及边缘群体的复杂构成。在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设定的这样几组二元对立权力关系结构中,前者处于霸权地位,后者处于从属地位,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在印度社会的权力关系结构中,这样的二元结构并不存在,在某一权力关系轴线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放到另外一个权力关系轴线当中去,也许就处于支配地位,反之亦然。这是历经殖民的印度社会内部权力关系结构的独特性。
在这个社会中,现代与前现代权力关系结构并存,比如印度的封建王公,他们是被殖民者,可是在庞大的印度社会内部,他们又是对底层进行“内部殖民”的压迫者; 再比如印度的资产阶级好像处于支配地位,但其中可能有些人是通过自己奋斗发迹的低种姓人士,他们在诸多场合也遭受着形形色色的歧视隔离,甚至敌视。斯皮瓦克把这种状况称为“没有支配的霸权”( He-gemony Without Dominance)。因此,斯皮瓦克建议用葛兰西的“庶民”这个术语以涵盖不同的主体位置。这样的状况并不是说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权力关系之中,而是说这样的权力关系在西方并不具有普遍性。
有不少批评家将斯皮瓦克的这种分析方式称为“文化决定论”。实际上这完全曲解了斯皮瓦克的本意。斯皮瓦克并不排斥庶民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经济因素,而是说单一阶级纬度的分析可能会遮蔽基于种姓、种族、性别等其他层面的压迫。那么在界定“庶民”这个批评范畴的语境时,应该如何处理其中的经济因素呢? 斯皮瓦克建议将“经济”置于删节号之下: 保持“经济”的能见度同时消解了其决定性地位。斯皮瓦克修正了庶民学派所使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与理论架构,使它走出了狭隘的阶级分析范畴。斯皮瓦克实际上也克服了后殖民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僵化的种族或者性别纬度,从而能够根据研究对象与具体情境来赋予庶民临时的所指意义,以描述不同底层群体比如妇女运动、农民起义、部落民以及不可接触者的反抗斗争经验。
庶民学派的创始人古哈在《农民起义的主要问题》一书中以“庶民意识”作为另外一个重要范畴来分析印度各个边缘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斯皮瓦克批判这实际上是与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类似的一个概念,试图赋予千差万别的庶民斗争虚假的连贯性。她指出,这种所谓“有尊严的庶民主体”是精英话语的结果,完全忽略了这些群体内部各个群体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苦难经验以及与他们各自切身利益相关的不同政治诉求。斯皮瓦克一方面强调边缘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比如妇女这个群体之中有西方妇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差异,第三世界妇女群体中又有都市女性与农村女性,而都市女性中又有所谓上层社会女性、中产阶级女性以及底层社会女性。她们面对的问题,利益诉求以及表达诉求的方式,是有着千差万别的,更何况在“庶民”这个范畴之中,还有除了妇女之外的各类边缘群体,“庶民意识”这个概念显然无法一语冠之; 但另外一方面,斯皮瓦克自己又提出了所谓的“庶民性”( Subalternity) 这个概念,主张在特定边缘群体的研究中,应该深入到其文化秩序内部中去,描绘出这一群体的文化逻辑脉络,然后按照这个群体的文化逻辑来思考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与庶民学派其他成员不同的是,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庶民性”是一个流动不居的概念,是一个在差异化的情境中临时构建的一个思维框架,斯皮瓦克把这称为“策略性本质主义”( Strategic Essentialism)。虽然斯皮瓦克自始至终也没有说明白何为“策略性本质主义”,但是她在庶民研究重要分析范畴设定中的“臣属者”视角却给庶民学派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
二、庶民经验被擦除的踪迹
斯皮瓦克揭露了庶民面临的无所逃遁的现实困境,戳破了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幻象。进而,斯皮瓦克也揭示了庶民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被擦除的历史踪迹,为庶民经验进入知识生产创造了可能性。这是斯皮瓦克在庶民研究领域作出的另一个独特贡献。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中,庶民似乎可以通过现代国家的政治代表权来摆脱自己的从属者地位,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但是,斯皮瓦克对此似乎并不乐观。在《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中她指出,政治代表权并不能够保证庶民的利益必定得到认可与保障,也未必能够保证他们的声音被听到。斯皮瓦克批评德勒兹与福柯预设了这样的前提: 美学( 艺术、文学与电影剧本) 的再现与政治代表权制度都是意识形态或直接或曲折的表达,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式与运作机制。然而,斯皮瓦克指出,尽管两者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汇: Represen-tation,但是其实它们之间还是有着显着差异的: 艺术作品在对某个庶民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再现的过程中,通过特定媒介可以部分再现多样化的庶民经验、不同的现实困境与多元的利益诉求,虽然整个艺术再现的过程,按照后现代主义文艺观,并不能够谓之“真实”,但其间的差异性无疑是可以得到充分彰显的; 而政治代表权只能够通过整合起来的一个声音来代表所有庶民群体发言,无法呈现庶民内部的差异性以及庶民利益诉求的多样性。这是因为在印度这样高度分裂的后殖民社会,民族、宗教、种族、地域、阶级等现代与前现代身份纵横交错,无法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也无法建构一体的政治身份。这样,他们不得不把这种代表权让渡出去,让代理人来代表他们发言。斯皮瓦克通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关于政治代表权的论述来厘清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在这部着作中描写了 19 世纪法国农业社会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斗争。马克思认为,这些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状况阻碍了他们拥有阶级意识。因此,在政治机构中,小农的声音集体缺席,象征性地由来自于中产阶级的代理人或者政党来代表他们说话。斯皮瓦克据此认为,现代政治机构无法提供庶民表达自己诉求的平台,而是遮蔽了庶民多元的声音。
斯皮瓦克指出,这种政治代表权机制对于庶民声音的遮蔽同样适用于西方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全球姐妹情谊”———西方女性主义者试图代表第三世界妇女发言,表达她们的诉求。
斯皮瓦克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知识分子与第三世界的妇女之间建立平等的联盟政治是不可能的。她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者总是试图用欧美的女性主义理论来诠释第三世界妇女的经验,表达她们的生理与政治期许,代表她们发言; 有时候甚至第三世界本土的女性主义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自己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表达自己的诉求。斯皮瓦克认为,这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因为她们身处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历史语境,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挑战。
斯皮瓦克的研究揭示了当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人权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为庶民群体代言的虚幻性,戳破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斯皮瓦克指出,庶民的声音要被听到,首先必须要让他们的经验进入知识生产。这里的经验不仅仅包括现实的经验,也包括历史的经验。只有在这样一个立体的纬度中去观察,去思考,才能够立体地把握庶民的经验,进而确立有关庶民的知识生产的有效性。斯皮瓦克认识到了庶民历史经验在历史书写中的缺席,并努力发掘妇女在官方历史中消失的声音。她将文学研究中后现代叙事学研究方法与对于印度19 世纪殖民档案的细读结合起来。斯皮瓦克在《色目尔人的王妃》( The Rani of Sirmur,1985年) 一文就是其学术理念的具体实践,在这篇文章当中,斯皮瓦克揭示了妇女的声音消弭的踪迹。
在印度从东印度公司控制到英国政府直接控制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高种姓妇女起初被频繁载入殖民当局的历史档案,后来销声匿迹。
这其中的蹊跷究竟在哪里呢? 斯皮瓦克经过研究后指出,历史档案中高种姓妇女从“在场”到“缺席”的整个过程完全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与殖民当局的权力接管。斯皮瓦克所提到的色目尔王国位于土着印度( 英国完全控制的区域在历史上被称为英属印度; 土着国王控制的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土着印度) 的东北部山区。这一地区对于英属印度的政治与经济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 东印度公司重要的贸易线路与殖民当局对付尼泊尔抵抗者的关隘。
殖民者试图吞并色目尔,并最终侵占该地区,将其纳入英属印度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英国“废黜了不与英国人合作的色目尔国王佳玛·普拉卡什( Karma Prakash) ,理由是他太野蛮放纵,恣意杀戮臣民,沉湎声色,不理朝政”。在罢黜现任国王之后,“王后被确立为她的儿子———未成年国王法特·普拉卡什( Fatteh Prakash) 的摄政”,因为王室里没有英国人可以信任的其他皇亲国戚,而“女人显然更容易被控制”。斯皮瓦克认为“王后被推上权力的巅峰是因为她是前任国王的妻子而且是一个更好操控的工具”。在这个特定历史时刻,王后的特权地位从属于她的性别身份: 作为王后与太后。当王后对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助于英国殖民当局与跨国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时候,她就从殖民档案中消失了。
斯皮瓦克认为“只有在帝国主义扩张需要她的时候,王后才出现”。而印度后殖民国家的所谓民族解放叙事也概莫能外,对于妇女的记载一样从属于后殖民国家的民族解放叙事。斯皮瓦克综合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碎片还原庶民的历史,还原庶民被遮蔽历史经验的学术实践为庶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三、庶民经验擦除背后的权力
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历史踪迹,同时也揭示了庶民经验被遮蔽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及其后果。斯皮瓦克通过重读印度经典文学文本以及统治当局的法律文书考察了印度妇女的意志与切身经验被遮蔽的踪迹,同时也审视了庶民经验被擦除背后的权力运作。在讨论过程中,斯皮瓦克以“萨提”( Satee,寡妇自焚殉夫的行为) 为切入点。斯皮瓦克强调,在印度古代的宗教文本比如《摩奴法典》( 公元前 7—2 世纪左右成书) 以及《梨俱吠陀》( 口头文本,大约成书于前 900 年) 中,寡妇自焚被编码为一种高贵的牺牲行为,或者说朝觐,而不是一种自杀行为,她说:对于《摩奴法典》,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妇女自杀行为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它规定自杀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但是同时它又为某种特定形式的自杀留下了空间: 妇女为了保全自己的贞洁在丈夫死后而自杀似乎可以例外于教规。
传统上,无论婆罗门教还是印度教都反对自杀,除非它成为一种自我牺牲,一种宗教仪式。但是它又严格规定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享有这种“例外”特权,只有妇女在丈夫的遗体边自焚可以例外。这种“例外”建构了一种父权制主导结构。正如斯皮瓦克所说,“妇女毁灭自我同时又能够去除自杀恶名的唯一场所就是她死去丈夫的火化柴堆上”。斯皮瓦克指出,在萨提过程中,女性被重新定义为她丈夫财产的一部分,如同丈夫生前的用品如木床被褥等一样,必须火化。这个过程同时又被宗教圣典赋予了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性。在印度教文化中,寡妇自杀殉葬被界定为“好妻子”行使妇道的特异能指,是妇女美德的集中体现。
但是“妇女牺牲”作为“好妻子”的特异能指的意义在异质文化之间的传递过程中失去了: 殖民地官员持迥然相异的看法,他们将“萨提”看作是印度文化残忍野蛮的一个符码。在这样的逻辑中,白人的殖民就不再是入侵,而是传播文明的光荣使命: 瓦解野蛮的父权统治,解放被压迫的印度妇女。斯皮瓦克认真研究了英国学者兼殖民当局官员汤姆逊( Edward Thomp-son,1886—1946 ) 1927 年有关“萨提”的论述,揭示了殖民当局编织的有关寡妇自焚叙事文本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 英国殖民当局据此将殖民剥削和领土掠夺合法化为解放黑暗大陆的“文明使命”。斯皮瓦克指出,殖民者与本土知识阶层有关“萨提”问题的争论,并没有给深受其害的妇女们留下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在后来的反殖民斗争中,女性的身体实际上成了殖民者与本土民族主义者双方建构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场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斯皮瓦克说,“庶民没有可以说话的空间”,因为妇女的声音与主体性被埋葬在本土所谓父权制道德规范以及殖民当局“野蛮文化受害者”的论述中。
斯皮瓦克在对印度国家档案中有关巴都丽( Bhubaneswari Bhaduri) 的历史叙事所进行的分析中进一步讨论了“萨提”问题。巴都丽 1926年在其父亲位于北加尔各答的寓所内自杀。一直以来研究者都试图找出巴都丽自杀的真实意图。大约最近,人们才发现原来她是印度独立武装组织的一员,因为武装斗争所张扬的暴力与自己的信仰冲突,精神崩溃而自杀。斯皮瓦克运用叠加文本作比喻来描述巴都丽参与反抗殖民的斗争经验被另外一种叙事擦除并重写的过程。在篡改过的父权制主流历史叙事中,她在斗争中的英雄行为以及其非暴力主义的博爱理念统统被遮蔽,其自杀行为被重新编码为“非法之爱”后的自我毁灭————另外一种形式的萨提———并成为其家族后来几代人的耻辱之源。斯皮瓦克指出,巴都丽作为底层妇女,其反抗殖民斗争的历史经验“在历史叙事中被擦除,湮没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民族解放叙事之中”。斯皮瓦克通过反向阅读历史档案,勾勒出了女性的历史被遮蔽的踪迹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斯皮瓦克说:在庶民主体性被擦除的同时,性别差异的踪迹也被擦除了。在有关反殖民起义以及相关社会运动的历史书写中,女性参与反抗的历史被遮蔽了。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使得男性在历史书写中居于主导。如果说在殖民当局书写的官方文档中妇女没有自己的历史,不能发言,那么妇女在后殖民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则处于更深的阴影之中。
斯皮瓦克与“后殖民批评”以及“女性主义”批评不同。后两者关注前殖民地人民以及女性当下的经验与压迫背后的文化秩序,进而发掘并解构背后的殖民话语及父权制话语逻辑。斯皮瓦克认为这样的分析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姿态,她倡导从官方历史记载的历史裂隙出发,从碎片中进入过去,勾画庶民经验被擦除的历史踪迹,一方面重构庶民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指导研究者更好地进入庶民当下的经验,进而为庶民经验进入知识生产创造可能性。斯皮瓦克的目标不是要直接消解所谓的帝国主义或者父权制文化及其话语建构,而是目光下移,关注边缘群体的经验,进而将庶民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这在斯皮瓦克看来是为庶民赋权最关键的一步。斯皮瓦克的看法与数个世纪以前培根提出的“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权力”)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庶民反抗的政治意义
斯皮瓦克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向读者呈现了被消声的庶民阶层独特的反抗方式及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斯皮瓦克关于“庶民不能说话”向我们呈现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现实,但同时她也并不否认庶民的政治行动力以及政治反抗的能量。斯皮瓦克的结论: “庶民不能说话”引起了有关其理论模式局限性的讨论。批评家如帕里( Benita Parry) 认为,斯皮瓦克的理论描述了庶民面对历史与现实压迫的无力感,从而否定了庶民的主体性,进一步遮蔽了庶民的声音。帕里写道: “斯皮瓦克的主张限制了庶民的经验进入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也否定了重构涵盖庶 民 经 验 的 新 的 知 识 生 产 范 式 的 可 能性。”帕里的观点代表了当下许多人对于斯皮瓦克的质疑。
斯皮瓦克所谓“庶民不能说话”的论述总是被抽掉具体的语境,从而认定斯皮瓦克否定庶民的政治行动力与影响力。实际上斯皮瓦克的《庶民可以说话吗?》一文的观点并非如此。
斯皮瓦克在一次访谈中说“庶民不能够说话意味着即便是庶民拼命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不能够被听到”。可见斯皮瓦克并不是要表明,特定的庶民群体无法表述自我经验与政治诉求,因而无法进入主流历史书写中去,而是说他们的声音被主流话语遮蔽或扭曲,不得不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中来接受他们的从属身份。
斯皮瓦克实际上看到了庶民的反抗及其所具有的力量,但是她对于庶民的反抗方式及其政治意义的解读却是独特的。在德维的小说《黑公主》的英文版译者序中,她深入讨论了底层妇女的反抗以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力量。小说的背景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西孟加拉邦北部地区的农民与部落民起义。当时不堪剥削与压迫的底层人民揭竿而起。斯皮瓦克在译者序中凸现了这样一个情节: 一位叫做“黑公主”的底层妇女被俘并受到政府军的残酷折磨。小说第一部分的叙述者是政府军首长色纳那亚克。他大量阅读起义军的宣传手册,试图了解起义军的政治动机,但是这些小册子并没有给色纳那亚克关于起义军政治目标的任何信息。尽管他努力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读物,但是他在这些册子中无法找到起义军政治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任何蛛丝马迹的联系。色纳那亚克在册子中只能读到一些神话或者民间故事片段。
这些年代久远的东西在印度家喻户晓,色纳那亚克无法从中嗅到任何的政治气息。斯皮瓦克推测说,也许是他的精英位置决定了他无法理解庶民还停留于久远年代的思维,无法进入起义军的心灵世界。起义军貌似完全无关政治的宣传手册拒绝被纳入精英主义的文化符号系统,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效的抗拒手段。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黑公主”同样是一个谜。在审问中涉及起义的内容,她拒绝使用印地语,操着政府军无人能懂的部落语言。在双方貌似一问一答的审判中,色纳那亚克无从知道其参加起义的经历,也无法了解她所吟唱的革命歌曲所表达的政治意义。这里“黑公主”在审判中对于语言的选择也可以看作是她的一种反抗。
斯皮瓦克也认为,故事与印度古代史诗《摩珂婆罗多》形成互文的效果,这样的叙事安排彰显了“黑公主”的反抗力量。我们知道,在史诗中,同名主人公“黑公主”嫁给了般度家族的五个儿子。在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黑公主”最年长的丈夫在色子比赛中输掉了妻子,敌方的首领伸手来抓她的沙丽,由于神克里希纳的神迹干预,“黑公主”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和荣誉。而神之所以伸手相助,是因为她奉行了“法”的标准,也就是恪守了妇道。史诗《摩珂婆罗多》以神话的方式呈现了妇女恪守妇道从而发生神迹,进而借助( 男性) 神的力量得救的故事。其中父权制结构借助在印度社会具有崇高地位的史诗将妇女所尊崇的“法”神圣化。
德维的故事戏仿了《摩珂婆罗多》中的这一幕,由于色纳那亚克的纵容,“黑公主”遭到了看守士兵的强暴。但是“黑公主”没有在所谓神的帮助下得到救助,她拒绝穿上衣服,坚持在公众面前一直赤身裸体。“黑公主”蔑视性暴力,赤裸裸血淋淋地展示自己饱受折磨与蹂躏的身体。
斯皮瓦克认为,尽管“黑公主”受到了政府军的性侵犯,但是她拒绝穿衣服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其反抗的标记。“黑公主”展示饱受蹂躏的身体对色纳那亚克代表的父权制国家的权威性构成了挑战: “‘黑公主’用伤痕累累的乳房去冲撞色纳那亚克,第一次,他站在一个没有武装的目标前害怕了”,“黑公主”挑衅地质问对方: “这些衣服有什么用? 你可以剥光我的衣服,但是我要看看你如何再给我穿上? 你是个男人?”斯皮瓦克认为,“黑公主”的诘问强力扭转了审判双方的位置,动摇了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
斯皮瓦克指出,庶民群体带有前现代色彩的政治诉求表达方式似乎对现代国家政治没有直接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反抗就完全没有政治意义。殖民者与独立后的民族国家权力机构迫于大众暴力反抗的压力,会进行虽然缓慢却持续的政治改革与改良,这本身就彰显了庶民反抗所具有的力量。斯皮瓦克进一步提出,庶民研究应该努力去探求: “庶民”的历史是如何通过精英话语建构起来的; 如何去发掘庶民在以往的历史书写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书写中被遮蔽的历史经验; 庶民群体反抗斗争的碎片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如何挑战了主流的历史叙事。
五、结 语
斯皮瓦克扩展了庶民学派的核心概念“庶民”与“庶民意识”的意涵,揭示了印度本土庶民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以及复杂性; 同时,斯皮瓦克勾勒了庶民经验被遮蔽的历史踪迹,揭示庶民经验被擦除背后隐蔽的权力运作; 最后,斯皮瓦克也发掘了庶民反抗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斯皮瓦克上述研究实践的核心目标是将庶民的经验纳入知识生产,走出为庶民赋权的第一步。
在研究中,她引入了文学文本叙事学研究范式与文本细读策略,并灵活运用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等西方先锋学术话语。可见,无论从研究方法、研究目标还是研究实践来看,我们都不能将斯皮瓦克学术研究简单归入“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或者“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范畴,更不能将她的研究看做上述学术体系的一个分支。用霍米·巴巴的话说,斯皮瓦克的庶民研究离不开她的“臣属者”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