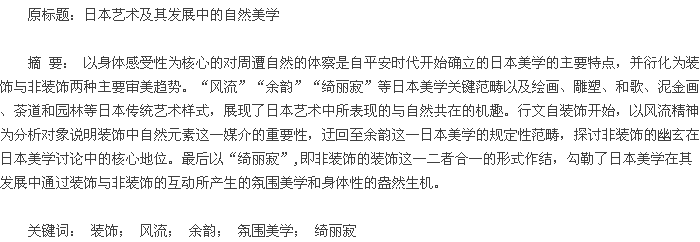
“风流”是日本传统美学的精髓,它与四季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饰り”是装饰的同义词,但在艺术和艺术工艺中被更多地理解为“风流”精神的视觉化。这一概念强有力地促成了公元 10 世纪日本风格的产生,也促成了当时和歌和假名字母的创作,日本本土文化的特性开始绽放。这一潮流在 12 世纪,即平安时代的末期达到顶峰。
一、装饰和风流精神
武笠朗指出,风流主要用于以下范畴: ( 1) 自然特色和花园,或者花园设计的幽趣; ( 2) 用于仪式、娱乐、节日、佛教及其相关活动的服装、马车或陈设的装饰;( 3) 用于仪式和娱乐等活动的产品,它们是由金、银、多种丝绸布料和天青石装饰而成的[1]( P181 -187) .
这种华丽装饰的精神进而转入到佛教雕塑、绘画卷轴和金漆作品中,即日本风格的创新流派。《荣华物语》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文献,不仅对于行为方式和习俗的历史是重要的,对艺术欣赏也如此。这部书共 40卷,其中关键的 30 卷写于 1033 年。该书据传是由一位叫赤染卫门的宫廷女子所撰写,她是当时的权贵,藤原道长之妻的侍女。该书描写的是生活历史、趣闻轶事、年度重要事件,也包括仪式和服装。
这部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视角,即佛教雕塑之美并不仅在于作品本身,同时也与雕塑的自然要素和所处环境有关。如其中言: “佛像在池塘中的倒影重现了佛的影像,这无限的高贵。”“月光普照,佛像被佛堂的虔敬之光点亮。”“水面反射着佛的圣洁影像,佛堂、藏经阁和钟楼也是如此。呈现给我们佛的世界。”[2]( P275 -310)这些景象描绘的是藤原道长 1022 年修建的法成寺。这座寺院已然不在,但其子藤原頼道 1052 年所建的平等院提示着我们完全相同的景象。平等院凤凰殿的阿弥陀佛像是雕塑家定朝的代表作,他确立了日本经典佛像雕塑的风格,反映出心灵平静的、柔和的面部特征和身体结构的平衡。虔敬之光和月光在这里也至关重要,不仅穹顶上有 8 面镜子,从穹顶向下还有多达66 面镜子,以给予充足的光源来保证佛像在水面上形成倒影。寺后溪水所产生的水波广为人知,溪流撞击人工沙滩上的石头,形成类似佛教西方世界中宝相花图案的水波形态。正如这一例子中所展示的,水、光等自然要素是造就动人艺术设计的媒介。
在这一时期,自然要素在每类艺术和艺术工艺流派中都超越了物质存在本身,如大和绘( 日本风格的绘画) 、和服、泥金画工艺品等。12 世纪前叶由藤原公任辑录的《三十六人家集》被视为当时最具原创性的装饰设计。不同种类的彩染纸由手工切割装订,给予作品触感。自然主题,如折枝、鸟及水波等被安排得韵律十足,使其似乎蔓延至观者。与这些主题相平行,非对称布局的假名字母处于流动之中,从而使整个设计在视觉上更为生动。
这种装饰特性延续到江户时代,如处于离心运动中的《鹤下绘三十六歌仙和歌卷》。古田亮在分析装饰艺术时说道: “作为艺术的装饰性并不仅是视觉刺激的问题。通过展开内在于人类和自然的 DNA 似的韵律或图案,装饰性增强了其价值。这也与这样一个事实相关,即一般说来,日本的装饰艺术植根于自然。”[3]( P229)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日本美学显然并不仅关于艺术作品本身,也相关于其环境要素及周遭氛围。主题依据光、影、风、水,也就是自然的运动,呈非均匀的韵律式设计。进而言之,这里可以强调的一点是,空间意识是由作品和观者的互动衍生出来的( 例如,观者在观赏佛像时,感受到自身正处于与佛像相同的光影氛围中: 作品和观者共有空间) .因此,身体性、连同感受性或感觉,在日本文化对艺术的理解中是不可分的。
相似的特性也体现在绘画卷轴中。当时的绘画卷轴分为两种流派,即“故事( 物语) ”和“叙述( 说话) ”.“故事”是段落式的( 每个场景独立于其他场景,同时又是整体的一部分) ,主要体现在装饰、情感特色上,而“叙述”则是由具有动态连续性的情节组成的。《伴大纳言绘卷》是较为知名的一部“叙述”型绘画卷轴,该作品描述的是政治主题,其高潮是火烧応天门,这一场景写实性地表达了好奇地围观大火的民众不同的面部特征和神态①。“故事”流派更合乎这个时代的装饰文化,完成于 12 世纪前半叶的《源氏物语绘卷》基于 11 世纪清少纳言所撰写的着名传说,以极为精致的彩色背景描绘了贵族生活。
在这部绘卷中,房间是没有屋顶的,呈完全开放以利用整体性的鸟瞰视角展示人物及其环境的细节。在“东屋 1”这一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寝殿造样式( 平安时代贵族寓所的代表性建筑风格) 的房间并没有严格区分内外的边界。内外只是由竹帘区分开来,每一个隔扇和布屏上都绘有自然风景的浮世绘。在另一处场景“玉鬘 2”中,内廷中开放的樱花遮盖了玉葛家的众公主们,她们互相比赛来赢得樱花。与自然共处是日本传统生活的根本思想,为了这一目的,即使室内也会有自然元素的装饰。艺术找到了这一视角,也找到了如何明确表达“亲近自然”这一思想的方法。
二、余韵
与日本美学相关联的关键词有很多,如雅、哀婉、幽玄、无常、侘寂、别致等。久保田淳认为,除了这些词语以外,余韵大量出现在艺术理论中,并渗透至日常生活中,对日本美学形成规定性。《方丈记》的作者鸭长明在其和歌理论《无名抄》中写道: “幽玄体就是余韵,即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和无法看到的风景。”久保田通过现代思想引入这一概念,如在小说中余韵一词的使用,夏目漱石在其《草枕》中将余韵视为露骨的对立面,及日本文化对模糊感的钟爱[4]( P47) .
余韵也可比对世阿弥在其着作《风姿花坛》中有关能剧的“秘すれば花”理论,即“真正关键的是明白这二者之间的区别,隐藏起来的真正的花和展示出来的不是花的花”[5]( P279 -283) .这一概念指出潜藏的艺术技巧可以意料之外的深刻印象打动观众。当然,对这一概念的解释还有很多,但下面这一说法似乎更为合适,即: “展示出来的仅是一部分,这就为潜藏起来的那部分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空间。”[6]( P16)日本文化对于“余韵”的品味也体现在艺术技巧中,比如円山応挙的画作《骤雨江村图》中那迷蒙的氛围、快速隐没的风景,只有气候环境的力量能被身体性地感受到。还有《冰图屏风》中作为无之高潮刻在纯白屏风上的几条线。这一意象是有意为之的,屏风本身为的是在进行茶道时为宾客带来几许凉意。图像本身确实只是现实空间的一个部分,但其意象却直达屏风之外的观者,演化为清凉的氛围。
云对于余韵的明确表达也有着重要作用,但更多的是其另一些显着功能。比如在土佐光吉的《源氏物语图屏风》或狩野永德的《洛中洛外图屏风》中,金色的云笼罩整个风景或场景。日高熏认为,这里金的云,一方面通过忽略其他不必要的客体来引导观赏者的视线,另一方面将不同的时空汇合在一起,同时推进装饰,也即风流的功能[7]( P22 -25) .
正如这里所示,装饰和余韵更像是在一种互动关系中加深各自的特色。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其散文《阴翳礼赞》中将这种关系和指示性视角理解为在黑暗中观看金漆工艺品。如其所言,古时工艺师在这些器具上涂以金并画上图案时,一定在头脑中想到这样黝黯的居室及处在微弱灯光中的效果。奢侈地用上金色,也是考虑到要在那“暗”中浮现的情景与灯光反射的程度。装饰成金色的漆器在那光亮的场所是不可能立即洞观其全貌的,必须在幽暗处观赏其各部分时时、点点地放射底光的情景,其豪华炫丽的模样,大半隐于“暗”之中,令人感到不能言语的余情韵味[8]( 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