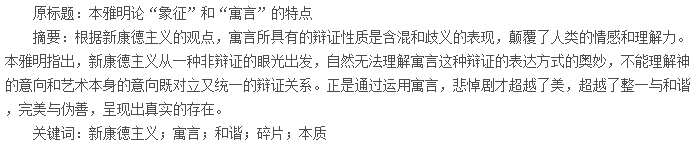
本雅明认为,温克尔曼《罗马宫殿里的赫拉克勒斯雕像描写》就属于巴洛克艺术作品中成功运用寓言形式承载永恒意义的例证。在这一作品中,作者以和古典主义明显有别的写作方式细碎的描写了雕像的各个细部。在巴洛克艺术家眼里,或者说按照寓言理论,没有形象的整体,只有形象的碎片。虽然是或正因为是碎片的集合,形象承载着形象之外的更深远的意义。于是我们不再从形象上看到象征概念里所强调的美。在神秘的意义或理念或真理的光芒投射到形象上时,虚假的、整体的、世俗的美的表象不见了,其上的各种修辞手段失效了,原来的意义关系破裂了,只剩下神秘的破碎的整体,等待有心之人进行深刻的研究,从而探寻出后面的意义。这在古典主义看来当然是离经叛道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它所宣扬和极力主张的正是自由而非确指、完善而非破碎、实在而非神秘、优美而非严肃。但是巴洛克艺术理念却毫不留情的指出,古典主义理念所推崇的艺术形象的光明正大外表之下有更深刻、更本质、更有价值的东西等待发掘。与之相比,光鲜的外表和显露的意义黯然失色。
然而,新康德主义美学家和本雅明的观点相左。根据这一派的观点,寓言这种巴洛克艺术所推崇的表达方式所具有的辩证的性质反而被认为是缺陷,是含混和歧义的表现。“然而,寓言的基本特点是含混和多义性;寓言,以及巴洛克,都以其语义的丰富为荣。
但这种含混的语义丰富是奢侈的丰富;而自然,据形而上学,实际上还有机械学的陈规俗套,则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含混始终是意义的清晰和统一的对立面。”
意义的清晰和整一是第一要务,在清晰和整一背后,不应人为引发出过多的含义,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属于有闲阶级的奢侈行为,没有价值,纯属多余——寓言是失败的表达形式。另一位新康德主义美学家,上述观点持有者赫曼·科恩的学生——卡尔·霍斯特,则从另一个角度贬低寓言。他在《巴洛克问题》一书中指出,即便把寓言限定为是非常具体的表达方法,基于其本质所决定的属性,在运用过程中还是会造成造型艺术向修辞性艺术的过渡或渐变,从而使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性质处于骑墙的尴尬状态,显得不伦不类,既不像严肃的艺术品,也不像实用性(如演讲词)一类的东西。
如果说巴洛克所看重的寓言在其他领域如生活中的运用尚可接受的话,那么在艺术中的大量运用在新康德主义美学家眼里就纯属灾难了。其恶果就是,使得造型艺术作品如音乐艺术作品般多解而歧义,使得最复杂多变的人类表达方式受到非情感、非人类的侵扰,颠覆和取消了人类的情感和理解力,造成对艺术创作和艺术规律的干扰和瓦解。即便恶果如此严重,新康德主义美学家郑重指出,许多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却好像对其恶果视而不见,浪费许多精力,运用寓言进行创作,从而污染了许多本来应该更伟大的作品。
本雅明对于新康德主义美学家的责难进行了反驳,虽然这种反驳很简洁却很直接,直指新康德主义美学家的一个死穴:不能够辩证的看待寓言问题。他指出,新康德主义从一种非辩证的眼光出发,自然无法理解寓言这种辩证的表达方式的奥妙,不能理解神的意向和艺术本身的意向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当然不是一种无冲突的关系,而是一种在上帝的威严之下达成的和平共处。
在举证并驳斥了新康德主义美学家的观点之后,本雅明指出,寓言虽然如同思想领域里的废墟,和古典主义所标榜的完整、协调大不一样,但却有其存在的强有力根据,而不仅仅是靠着辩证法的光环自证。“正如悲悼剧的例子所示,当历史成为背景的组成部分时,它是作为书写而做到这一点的。‘历史’一词以瞬息万变的字体书写在自然的面孔之上。悲悼剧舞台上自然——历史的寓言式面相在现实中是以废墟的形式出现的。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在这种伪装之下,历史呈现的与其说是永久生命进程的形式,毋宁说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的形式。寓言据此宣称它自身超越了美。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这说明了巴洛克艺术何以崇拜废墟的原因。”
历史之所以能够融入悲悼剧之中,是因为它甘愿化为背景,以寓言式的表达方式悄无声息的存于其中,而不是自我标榜和宣扬其主体性,因为其自知自身的虚假性,看似有规律的、自我演进的历史实际上只是重复,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其放弃了虚假的存在价值,向上帝投诚,因而当它虽然只是作为配角被挂在悲悼剧的墙上成为背景之时,却也获得了足够的补偿——成为永恒的自然的一部分,不再挣扎在虚妄的、瞬息万变的道路上。悲悼剧中自然和历史的辩证统一的现实对应物正是废墟。正是以废墟的形式,历史才得以打破自身的整体性神话,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运用寓言表达形式的悲悼剧就超越了美,超越了整一与和谐,完美与伪善,呈现出真实的存在。把现实拆解为废墟,从废墟中寻找真相,是巴洛克艺术和其表达方式寓言的共同策略。
于是我们在巴洛克艺术中看到的就是颓废的强壁、崩塌的石柱等残存的迹象。这些迹象和遗物并非没有价值,而是历经风雷电雨的见证者。它们作为证据和奇迹保留下来,证明自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证明任何世俗社会的人工产物在自然伟力面前都将化为废墟。它们同时又是作为古代社会的遗产留下来的,如同历史的尸体,残缺不全留存至今,供人观看——或作为巴洛克悲悼剧中的背景和道具被随意摆放在舞台上,起到某种指示作用。
本雅明通过构建以“悲悼剧”概念为中心的悲剧思想,力图摆脱古希腊悲剧的羁绊。在他看来,悲剧的概念已经过时,在苏格拉底被悲剧性的判处死刑的时候,悲剧和悲剧英雄就走向了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无言的忍者通过默默抗争打造的后希腊的悲剧形象。然而对于这一点,人们并未自知,而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依然追捧悲剧的概念。殊不知,悲剧已经早就和围绕在它周围的三一律、伟大、荣誉、英雄事迹等等概念一起变成了历史遗迹,取而代之的正是悲悼剧。尽管德国悲悼剧本身缺乏广泛的说服力,但是本雅明认为西班牙的卡尔德隆和英国的莎士比亚通过伟大的戏剧实践,证明了悲悼剧的优越性。
当然,在本雅明那里,悲悼剧不仅仅是文艺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哲学概念、宗教概念,具有终极追问的意义,关乎人类的思想拯救。通过赋予“寓言”这一概念丰富的、辩证的色彩,来研究悲悼剧、提倡悲悼剧,是为了从浮华的历史中撇去变动不居的成分,还历史一个永恒的真实面目,并将之固化为风景,成为悲悼剧上演的背景。从这个价值角度衡量,古希腊的悲剧自然稍逊一筹,与悲悼剧相比对于历史的关注缺少宏观和超脱的眼光,当然也就缺少终极性的意义。
今天的悲剧,或者说包含悲剧因素的艺术作品,虽然对于某些题材的挖掘不够深入,但是所涉及的题材是如此的广泛,思考的问题是如此的具体,恰恰缺少了本雅明所重视的对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其中甚至人文关怀的成分也不够多,不够深入。本雅明的寓言思想,对于思考当下艺术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