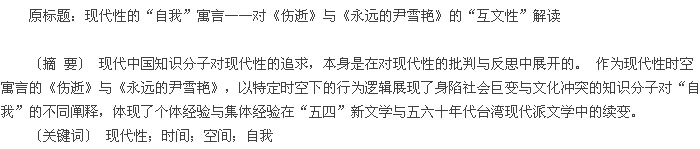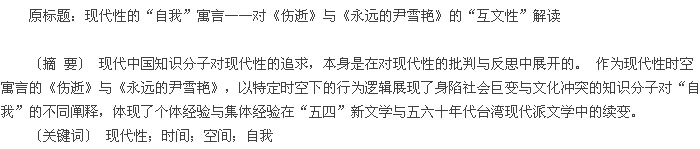
一、现代性的时空寓言:《伤逝》与《永远的尹雪艳》
“五四”新文学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表达方式,鲁迅的《伤逝》可以视为对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的寓言性再现。 把鲁迅对涓生与子君的塑造作时空的寓言性区分时,在现代社会中“觉醒”的涓生代表着时间性的喻体,而为“传统”所“桎梏”的子君则具备了一种空间性的喻意。 在这种区分中,可以看到鲁迅探入历史构造的方式具有特定时空下历史的行为逻辑。 当时间性的涓生与空间性的子君相遇后,时间并没有如现代性勾画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进程继续前行,而是被空间圈禁。 将子君带离家庭桎梏的涓生,并没有实现共同的精神前行,反被“吉兆胡同”中种种衰败的空间性意象所围困:庭院、租房、油鸡、昏暗的油灯……扬言不断前行的现代性时间最终被圈禁在一个封闭式的空间中, 呼吁着精神前行的时间因此成为一只“笼中鸟”,最终为“由家到局、由局到家”的狭小空间所扼杀,为“‘川流不息’的吃饭”所替代。
时间与空间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那里,同样可以作寓言性区分。贵生、洪处长、壮图……这些拥有着如其名般响亮人生的人们却最终敌不过时间线性进程,如果将他们视为一种时间性的喻体,那么无论时间如何轮换,仍在原点冷视人们来去的尹雪艳则具有空间性的喻意。 “尹雪艳总也不老”,此时尹雪艳实际已演化为一种凝固的空间性存在,“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 空间性的尹雪艳如同见证历史繁华的旧地,那些古物是为时人提供记忆往昔的唯一凭证。 “尹雪艳自然是宋太太倾诉衷肠的适当人选,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宋太太那种今昔之感。 ”
对那些经历着时间性的人们来说,空间性的尹雪艳是见证他们过往的唯一抚慰。
当我们以“时间”为切入点来审视现代性之于中国时,这两个同样以时间围困空间为开端的故事,呈现了“现代性”与“历史”的冲突关系。 在宣扬着未来已经开始的现代社会以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将“历史”打碎,现代性以无坚不摧的理性气势破坏了感性传统时,在这两个故事的开始,我们看到了作家对现代性的怀疑:鲁迅让空间性的子君围困了扬言要携同她精神前行的涓生,白先勇让空间性的尹雪艳作为凝固的“过去”抚慰着经历着时间的人们的伤痛。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
在鲁迅反复发出历史重演的感叹时,可以看到他对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不确定的矛盾态度。 同样,白先勇的小说“在可见的历史事件外,他的小说毋宁更以戏剧性的笔触,彰显一辈作家面对时间,尤其是‘现代’时间的形上焦虑”。
显然,“现代性”与“历史”的撕扯在知识分子的思考中并非现代性的完全取胜,现代性经验在中国的复杂性正是因它与“历史”的无法割裂的关系,而身处其中的“我”首先思考的就是“过去”在与“现在”、“未来”的张力构造中应被置于怎样的位置。
在这种思考中,具有同样开端的故事在最后呈现了不同的结局。 在《伤逝》里,如果说空间性的子君曾围困了时间性的涓生,最终的结局却是时间性的涓生的留存和空间性的子君的毁灭。 涓生所代表的精神的开放和自由,及朝向未来的姿态,对以他为代表的“五四”青年来说永远是第一性的。 即使精神的前行最终以牺牲“个体”为代价,鲁迅仍旧选择让时间性的涓生留存。 当然,以子君的毁灭为代价换来的现代性精神的幸存,留给涓生的未尝不是一种反讽。 这是一个表现启蒙和现代性经验在中国的复杂与多重性的故事,而在鲁迅构造历史的逻辑中,所暗含的正是与“历史”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内在矛盾。
而在《永远的尹雪艳》里,行进的时间最终为空间性的尹雪艳所扼杀。 不论是在“不老”的尹雪艳身上感受不到时间的行进,还是寓意着时间的三个男人被认定为是因“煞星儿”的尹雪艳而死,现代性时间的线性进程在尹雪艳这里被阻断,冷眼旁观着人事变迁的尹雪艳一如她那人潮轮换的尹公馆,在迎来送往中凝固成一种意象式的存在。 尹公馆这幢“崭新的西式洋房”中放置的是“桃花心红木桌椅”、“老式大靠背沙发”、“黑丝鸳鸯戏水的湘绣靠枕。 ”
这座中西合璧的尹公馆在现代性的外壳里裹挟着的都是“过去”的填充物。 “现在”在最终留存的时间性的子涓那里继续行进,却在扼杀了时间的空间性的尹雪艳那里停滞不前。 然而,如果真有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存在,只能是一种意义上的“过去”本身,只有逝去的东西才得以定格与不朽。 因而当空间性的尹雪艳凝固在时间坐标的原点时,她实际上已成为“过去”的象征物。 白先勇曾认可尹雪艳是死神式的存在,这同样也是一个讽刺的寓言,它告诉人们他们所追求的永恒是死亡的象征。 在白先勇那里,不断演绎的今昔之别淡化了未来的镜像,他以一种回首的姿势将时间在某种意义停滞在了“现在”,而同时,被斩了首的时间使去掉了未来的“现在”被停滞。
二、“过去”与“现在”:生命断裂处的“自我”书写
以“启蒙”为题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次现代性的尝试,当历史的进步观许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未来的乌托邦时,线性的历史成为知识分子构想民族国家的前提。 相比过去,“五四”作家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思维方式。 他们在体验和表达世界时,强调的是个体即“自我”的存在。 然而,在以“启蒙”为目的所划定的民族国家的外框之下,宣扬着“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学中所高扬的“自我”背后存在着一个隐性的集体意志。
不论是阿 Q 的“救命”,还是狂人的“救救孩子”,都可以说是一个形而上的文化断裂和历史起点。 在这个断裂点,中国近代历史的痛苦体验直接导致了对“过去”的批判与悬置,这种批判既包含了以“未来”之“新”取代“过去”之“旧”的现代意志,也是对“传统”进行“偶像破坏”式的全面批判。 在“五四”以“未来”之名全盘否定“过去”来为“现在”扫清历史的障碍时,现代性的时间因此成为一种革命的时间。 在这个革命的时间里,“过去”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寓言图景,以此返照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让“现在”以“未来”之名把自己从“过去”拯救出来。
因而,如果在白先勇那里,“过去”的不断被唤起使“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被停滞,那么在鲁迅那里,时间的停滞正是他所恐惧的。 因此历史的停滞虽然同样存在于他的小说中,却被寓言性地变成了历史运动的革命性前提。 《示众》中的退化为“物”的“看客”,这种死寂的麻木是鲁迅为唤起革命性动机的设置,他列举种种不堪的“过去”,正是为了让“现在”将“过去”弃置。 因而,当“过去”作为一种构造因素加入到“现在”的新文学进程中来时,成为革命性前提的“过去”在鲁迅的书写中具有开始的意味。 同样,在《阿 Q 正传》里作为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旧中国”,最终以其内在的自我瓦解为一种新的伦理道德扫清了道路,一种新的历史主体因此获得了到场的契机。
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对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来说,是一个事关语言实践内在本质的问题。不论是对文学本身有效性的思考,还是同历史进程无法分隔的现代性自我意识,都意味着现代性时间的印记已深刻地烙印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写作中。 而“历史”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二者的内在对立在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和形式内部被赋予了革命的企图。 在这种企图之下,任何在“私人语言”范围内重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努力实际都是以革命性为前提。 因而,最终作为“自我”的外在规定的社会历史现实,同“自我”的内在价值冲突时,这个与外在规定相冲突的“自我”只能成为历史的表象。
不论是打破固有的秩序重建新的体制,还是战后体制秩序的重建,对一代人来说都是一个十分压抑的过程。 只是对于前者而言,被囊括于体制化建设中的“自我”,“个体”的局限不易被觉察。 而对于后者,在战争苦难的阴影中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文化的废墟,最终只能返向自身。
五六十年代,置身于孤岛隔绝、历史离散和西方现代思潮涌进之中的台湾知识分子,“自我”与文化一同在向深渊坠落中失落。 在这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中,台湾知识分子重新寻找生存的意义,当他们向内在寻找人性的资源时,“自我”拥有了一次再界定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台湾现代派文学可以说是重新亮出了“五四”关于“自我”的题旨,“现代主义”的叙事中同样指示出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在历史的分崩离析中企图以自己的内在经验打下时代的印记。 这同样是生命与“过去”出现断裂的一代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被迫与“过去”分割的一代人。 面对“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断裂时,“过去”在台湾现代派作家那里不再是唤起革命性的动机,而是成为与停滞的“现在”形成对比的美好往昔。 “过去”才是生命的源泉,“现在”只是躯体的受锢地,作为生命凭证的“过去”为他们在迷失了“自我”的“现在”找回身份认同。 《永远的尹雪艳》里以吴经理为代表的那些过了时的人,过往成为他们自我身份的确认,他们只要一进到尹公馆,“大家都觉得自己重要,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地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诰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
这些历经人世沧桑的人已不再寻路,也不再扮演着领路人角色,他们只是意在将自己与他人的那一些生命的情绪展示出来。 此时,“过去”不再是时间向度上的与现在、未来在有着一定连续性的存在,其立足点及归宿点是与其形成对应的“现在”,从而真正突显了存在于“现在”的“自我”的生命困境:没有“未来”,仅有的“过去”也是对应于“现在”而存在。 在“过去”与“现在”的生命断裂所形成的张力中,“自我”的叙述获得了原动力,叙述着在宏大的历史之下的个人心灵。
因而,如果说“自我”在《伤逝》中最终牺牲在了革命性的历史前提之下,那么在《永远的尹雪艳》里“自我”则记录了一代人时间的伤痛,“个体”在与时间的创伤的对抗中,这种反抗性因一种精神突围的姿态而显示出积极性。 当白先勇把时间变成意象进行写作时,历史此时已被还原为一个凝视者的对象,成为历史观照者的“个人”因此拥有了主动性。 在战后的台湾,当“自我”不再被赋予确定的价值指向时,“如何勇敢面对赤裸孤独的自我”便真正成为这一代知识分子需认真思考的主题,在此意义上的叙事所结构的不仅是一个主体,更是这一主体的内在经验,正是这种专注的内视写作使台湾的现代派文学诞生了一部部知识分子的“心灵自传”、“精神私史”。
因此,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主体”的位置和功能是倾向于一种“集体意志”,那么台湾现代派小说中“自我”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则显现为一代人的自我形象的积极活动,展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集体经验”。
三、“我”与“我们”:自我意识与集体性经验
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提出,台湾的现代主义是“五四”新文学“文学的启蒙”传统的一种延续。 从“五四”新文学到台湾现代派文学,如果不是单纯从现代主义技巧出发来探讨两者的共通与区别,而是从一种反叛传统,或者说与历史断裂的“先锋文学”中折射的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来探索“自我”的续变时,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
在 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启蒙的观念通过革命变成社会现实,但革命只有在“立人”的个体实践中才能获得价值确定性。 “五四”新文学作为世纪初的“先锋文学”,“过去”在被激烈地“当代化”时,社会生活的远景也被浓缩为个人经验的悲剧冲突。 就在这样的文学机制中,作为社会主体的创作者与叙事呈现的“自我”合二为一,最终呈现的“自我”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 阿 Q 是来自“黑暗的闸门”的一个未及发出的“心声”,《阿 Q 正传》也是关于整个中国的一个民族寓言;《呐喊》的自序传达不是纯粹自传性的个人信息,更是整个近代中国集体经验的一个缩写。 “五四”作家在书写一个“我”的故事,但明确“我”指向一个集体性的经验后,这实质上也是一个“我们”的故事。 “五四”文学的重个体、追求个性解放与它重整体、强调民族政治文化重建的诉求从来都是相辅相成,这种个性与集体性的张力也是“五四”留下的宝贵遗产。
而又一个集体经验断裂的再次到来,台湾现代派获得了新一轮的“启蒙”在观念的空间里再次展开的机遇,虽然它已指向存在于新文化统一体中的个人,但是个人生存的背后同样潜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分裂的不幸。 “文学创作恐怕是由于对现实生活有些不满,所以才自己去创造一个世界。 ”
当台湾现代派在个体经验的具体性层面上力图重建生活世界时, 精神既作为现实的对立面寻求对现实的克服和超越,同时又在这种克服和超越过程中寻找和界定自身的现实性。 来自不同背景的《现代文学》的创刊成员的最大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他们共同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时光未明充满了变数的新世界”,他们“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十字路口”,并且要在“这股激变的洪流中,探索前进”,而他们建立的全新的个人概念,他们对新的自我意识的探索,同样也隐含着一个集体形象,这个集体形象昭示着这些现代派作家同一代人的共生关系。 “白先勇小说中的社会性格可能是最明显的,不论是‘大陆人’在台湾的‘流落不偶’(《台北人》系列),还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无根飘泊’(《纽约客》系列),他关心的都是‘一群人’,而非‘一个人’。 ”
只有表现“个人”的作家能够以文学担当起集体性历史境况的矛盾,表现共同生活体中的大多数生息与共的生命时,“个体”的生活才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上自觉的生活,“自我”也因此在集体经验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崭新的主体性价值。
在 20 世纪的中国,精神每一次前行都伴随着同旧日的观念世界的决裂。 而其中挣扎于“过去”与“现在”之中的生命经验,呈现出的是一种成长的历史。 吕正惠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中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台湾现代主义只是表面的类似,以此作出“台湾现代主义是对‘五四’精神的背离”的判断。而这一判断忽略了二者在内在精神上的关联性。 台湾现代派小说虽然在形式上扬着西方现代主义的旗帜,在经验上却仍有着“五四”意识的痕迹。 只是这种意识在时空的断裂中已被多大程度地改造,又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它的当代经验是无法确证的。 作为主观内省式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形式,如果说台湾现代派小说独特的语言技巧与结构形式表现出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心灵镜像,那么这种全新的个体经验和写作者自我意识的表达,也应该被理解为“过去”提供的集体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变形”。
如白先勇所说:“如果说‘五四运动’的白话新文学是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第一波现代化的结果,那么20 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可以说是第二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
50 年代中期,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中潜流断续的现代主义文学推到了文学的中心地位, 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一个新的土壤里实现了富有实绩的革命性传统和传换。 “‘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 ”
正是这种“五四”气质影响了一批台湾知识分子发起了《现代文学》杂志。 事实上,当知识分子的经验曾为一个时代所浸染,那么他们的创造性就不可能与这种经验彻底分隔。 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并不存在“五四”时反传统的问题,因为传统已被强行割断了,可是恰恰是被割断的传统以另一种隐性的力量不断地影响着这批移居台湾的中国知识分子。 当现代性把人们从对曾经麻木的生活中解放时,也带来“传统”的断裂,可以想见此时经历着个体身份的一贯性为现实境遇中断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境。 在本身便是一种矛盾的现代性中,这种矛盾心境本就是现代性的宿命。
在此基础上回应“伪现代派”的质疑时,可以看到:不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都不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回声,并且在文学中展现的“个人”背后同样存在一种集体性的东西,而这种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经验紧密相联的个体性,以叙事的突破及自主的叙事逻辑,记录了一代人的经验的历史的生成。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全集》修订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白先勇.台北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白先勇. 第六只手指:白先勇散文精编[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6]白先勇. 二十世纪中叶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J].香港文学,2002(4):5-7.
[7]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8]朱立立.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台湾现代派小说的一种解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9]王德威.游园惊梦,古典爱情———现代中国文学的两度“还魂”[J].现代中国,2005(6):159-175.
[10]陈晓明.“没落”的不朽事业:白先勇小说的美学意味与现代性面向[J].文艺研究,2009(2):3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