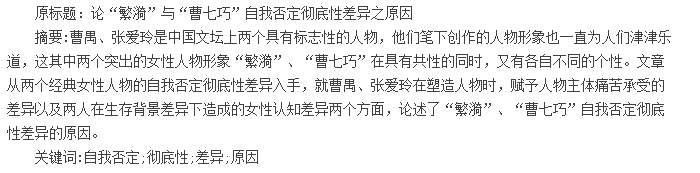
在中国文学创作的源远长河中,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历来是众多作家的呕心追求之一。在纷繁、众多的作品中,他们或她们的名字总是与作品中那些血肉丰满,引发情感共鸣的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鲁迅与其笔下的阿Q、祥林嫂;钱钟书与其笔下的方鸿渐、苏文纨;老舍与其笔下的祥子、二马等等。在对人物创作的追求中,富于情感与纤弱之特性的女性形象从古至今历来都是经典人物创作中的一个闪光点:情感炽热的崔莺莺、抱恨投河的杜十娘、命途多舛的“金陵十二钗”、丧子孤寂的祥林嫂、倔强孤傲的颂莲,他们无一不上演着多情脆弱的女性情爱悲喜剧,无一不在男性“纯洁”的绳套中,在绳套上那些美丽伪饰的迷惑中,从生理和心理上对自身进行着痛苦、残忍而又“自愿”的否定。到了近现代,女性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以一种貌似觉醒的形态,撕掉柔弱、羞涩、圣洁的外衣,“变形”的出现在大众面前。这当中,“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曹禺《雷雨》中的繁漪并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性格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三大女性形象”。之所以如此说,多是因为,他们身上既浓缩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情爱悲剧,同时又勇敢打破女性传统角色固守的圣洁、美好、温柔、贤良的模式,回归到原始、自然、复杂和现实的人性情感中。而其中对繁漪“变态”的情感捆绑,阴鸷的性格以及她那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描写;对曹七巧自我束缚于金钱枷锁,以求内心安全感和情感依托,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至亲至爱的描写,其发展脉络之清楚,性格描写之细腻,心理剖析之直接和犀利使得这两个女性艺术形象在现代文学中更是被推崇至“人性与女性结合的最突出体现”。在二者的身上,我们不难找到“情感上的受挫与自残,行为举止上的疯狂与变态,情绪上的压抑与转移”等等诸多共性。然而无论其相似的程度有多大,她们终归是两个人,她们的身上总有体现自身特性的地方,她们的身上总能找到解释二人命运相殊的本质根源———那便是“自我否定彻底性”的与否。
一、主体痛苦承受的差异
张爱玲在其自传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她们不是英雄,只是这时代重负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不彻底,但他们是认真的。
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只是一种启示。”
正是基于曹七巧的这种失爱后对情感世界的彻底否定,因此我们对她投射的更多是一种同情与憎恶混合的情感,对她的同情更多侧重在她的冷漠无情与情感上的麻木荒凉,可以说她的痛苦更多是存活于旁观者的眼中和感受中,而对于其自身来说对“金钱”的狂热、变态的追求、高度聚焦的投入,已麻木了她对周遭人事的关注和情感的倾注(当然涉及金钱则例外)。她的精神家园已完全被具体的物质所吞噬,在她的精神家园里没有友情、爱情甚至是亲情,有的只是金钱,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七巧是用金钱代替情感构建了她的“精神乐土”。因此可以说七巧在她的思想领域中是“快乐”的。她承受了姜家上下对她的鄙夷与排斥;她抵御了季泽的引诱与挑逗;她“战胜”了媳妇对儿子的“拉拢”;她识穿了世舫“觊觎”家产的贪图。总之,在她的“清醒意识”下,她守住了她的那份家产。七巧对金钱的偏执让身旁之人痛苦、寒心甚至是恐惧,人们为她而悲,为她而伤,为一个活生生充满激情的女人,最后情感诉求不成,导致扭曲的灵魂放肆贪欲的种种劣迹苦叹不已。在封建社会伦理对女性的压抑中,七巧寻找到了“拯救”内心的“良方”———她用金钱的存在来代替自身存活的意义。用金钱否定爱情,用金钱否定亲情,甚至用金钱否定自身意识。七巧认为在金钱的国度里,她找到了精神的“乐土”,于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她畅游在自己的“快乐”当中,从此结束了精神的苦旅。自我的迷失与麻木,使得“丧失自我,灵魂扭曲”的痛苦转嫁到了“清醒者”的思维意识中,使读者成了七巧悲剧命运的痛苦承担主体。
想较曹七巧来说,繁漪是更加不幸的———“生来是个女性,命运已给她终身的不幸。如果没有知识,浑浑噩噩像牛马般地过了一世,倒也令人省事,最不幸的是也去吃了“智果”,从模糊中清醒过来,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人,从而有了情感上的‘欲念’。”
繁漪正是这样一个偷吃了“智果”的不幸女人。她在情感上对周萍的依赖成了读者同情她的情感要素,同时也成为她痛苦的本质根源。正是因为这种不彻底性,她一次又一次地燃起被爱的希望,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在周萍的不忠与玩弄中承受患得患失的精神和心理折磨。在阴霾、沉闷的周家大院,繁漪否定金钱,否定权势,否定亲情与友情,否定世俗伦理道德,甚至否定自己作为女性的矜持与自尊。然而知识女性对男女之情的浪漫追求,对享受被爱的渴望与向往却使她无法否定人类的原始情感之一———情爱。于是“情爱”这根绳索便成了她否定一切后,倾力抓住的一根“救命草”。相比之下,可以说繁漪的痛苦更多体现在本体,而非旁人的单一感受。
她在情爱上的欲念,使她无法摆脱痛苦的纠缠,她大胆冲破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美丽、温顺、贤惠、贞洁期望的行为,使她在封建社会中无法逃脱成为悲剧角色的命运。因此对她的同情更多带有被动性、方向性,对七巧的同情则更多带有主动性、自觉性和替代性,也可以说对七巧的同情是一种清醒者替麻木者的生存承受苦痛的彻底、自我的同情。
二、生存背景导致的心理差异
在生活的大背景中,抽象的说张爱玲与曹禺更多存在的是一种共性,那便是封建大家庭里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情感精神的“空虚”之间的强烈反差。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都能抓住封建大家庭里不幸女子的敏感神经,都能将这部分女性的言行举止、情感变化,心理活动刻画得淋漓尽致,细致准确。但大环境的类似掩饰不了具体生活环境中细节因素的差异。
可以说,家庭生活的影响带给曹禺的只是一种苦闷、忧郁的补充。他似乎一开始就已带着文学家特有的忧郁气质和浪漫感伤情绪而降生。
“曹禺从小就有着不少的苦闷,好像生来就是一粒苦闷的种子。他上中学时,才不过十几岁,她的父亲就对他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
幼年丧母,是造成他同年孤独苦闷的一大原因,他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直到他自己已是古稀老人,但凡每每提到生母,依然内心怀念伤悲之情难以释怀。“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了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的深处。”
除此之外,在宣化的日子,也是曹禺孤独感空前蔓延的一个时期,“据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非常敏感,我总是坐在城墙上,听那单调却又十分凄凉的号声,偌大一个宣化府,我一个孩子,又没有了自己的母亲,是十分孤独而寂寞的。’”
从曹禺的家境来说,他从小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生活,住在小洋房里,家里一干负责各式活计的下人,拉车、做饭、打杂,一应俱全,日常生活还有保姆打理。也许也只有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曹禺才能在平和的家庭生活中享有忆念生母,蔓延孤独的“权利”,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曹禺才能主动、“刻意”的营造出那种感伤浪漫情怀的心境。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痛苦与孤独是不纯粹的,也是不彻底的,是带了浓浓文艺色彩和情感的“凄美”色调的。
反观与之相比,张爱玲则显得不幸得多。家族里对以往繁华的留恋,对现实的回避,使得整个家族都处于一种混沌与不清当中,正如余斌在《张爱玲传》里说的那样“张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先人的阴影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没落贵族的情感被华丽的色彩、温暖的色调、高贵的气质所涂染覆盖;另一方面,家道中落的残酷事实折磨、打击着自命不凡,纨绔无能的贵族遗少。这种种的矛盾纠葛使得现实的生存也变得畸形起来,人的遭遇与苦闷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张爱玲尚不满二十五岁,但似乎已是饱经忧患,她肯定不止一次地回首前尘,油然生出难以名言的沧桑感。向来是‘登临意无人会’,谁也无从体验那惘然中蕴蓄的复杂况味。……她那位身在海外,眼下不知落脚何处的母亲;那位吸鸦片、娶姨太,曾经声言要打死她,现已断了来往的父亲;她的不得志郁郁而终的祖父;她那个漂亮的然而不争气的弟弟。甚至她也许还会想到更远,想到没有见过面,而常在亲戚口中听到的外曾祖父或是‘相府老太太’。”
如果说曹禺幼年丧母是他苦闷、痛苦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对张爱玲来说,母亲———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存活则带给了她更多的精神困惑。一方面她视母亲为希望、依赖,把母亲作为逃离父亲家庭里的冷漠和暴力的避风港;然而另一方面,面对母亲沉痛的警告,面对“思想失去均衡”走入“自我怀疑”的精神痛苦,她又对母亲失望,渴望逃离。可以说张爱玲面临的精神与肉体的必然受损,在做一种无奈、痛苦的选择,而这个痛苦抉择必然经历过一个对自我全盘否定的心路历程才能从中挣扎出生存的可能,也许也正因如此,张爱玲才能使曹七巧的自我否定变得如此彻底。如果说曹禺生母的去世留给曹禺的,是一份也许生母能排遣、理解内心苦闷、孤独的希望,那么张爱玲父母的存活所带给她的冷漠则将她内心曾存留的希望彻底带向了绝望。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曹禺的痛苦与郁闷是一种诗人、文学家的附属品,充满了浪漫的色彩,它是一种心理情绪的转化,具有一定的主题自动性;而张爱玲的苦痛则更多来源于周遭环境的压迫性施与,她的接受是被动的,是无从反抗的,从而一旦选择也就是彻底的,根深蒂固的。
另一方面,曹禺在其学习过程中,不断接受的新思想、新理论,使其不论对人本身或是世界都抱有一种不断探知,以求改造,解救的态度。“他的家庭,他的周围熟悉的人事,都引起他的不平和思索。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
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潮流来说,他是“入世”的,他具有一般知识青年的热情和激情,正如其所说那样“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拼杀一下”。对社会的责任感,对人类痛苦的探索,这些精神上的联系明白告诉了我们,曹禺是在“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都成了他的领路人,正是源于这种“入世”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使他对未来抱有一种希望,于是他宁可将繁漪推向痛苦的边缘,成为“一片浇不息的火”,“一柄犀利的刀”,一个最富“雷雨”性格的人,也不忍彻底否定她的精神与肉体,成为一具没有情感知觉的躯壳。
与曹禺的“入世”相比,在时代的动荡中,张爱玲显现的是一种“出世”的平静与淡漠。亦如她自己所言,她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她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更放恣的。”
(女人保存和体现了人的真正本性,在此得以体现。)这种“出世”的气质与其生活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无不有着莫大的关系:“张爱玲一九二一年九月在坐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里出生,以后她在大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租界的地面上度过的。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又是外国人管辖的地盘,与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喜欢寻绎巧合与象征性事件的人或许愿意从中生出丰富的联想: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也有一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复杂情结;对应于租界三不管的边缘位置,她也是永远立于一切潮流之外的边际人。”
这样的生存环境使她拥有了保持独立的客观条件。而在主观学习上,她的学习更多带有自我性,而非社会性,也正因如此她既能保持自己“俗不可耐”的生活情趣———拜金、贪享安逸、慵懒,同时也能避开俗世中的思想主流,继续自己的寂寞与孤独。“随着年龄的增长……孤独与寂寞将自尊心琢磨得愈加灵敏纤细,而愈是如此,她就愈是不能放过来自外部的对于心灵的哪怕是极小的伤害;将种种被伤害的感受做了放大的处理之后,她更加意识到环境的不可靠、不安全。张爱玲敏感内省的气质与冷漠的家庭气氛对心灵的窒息,这二者之间相互发生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张爱玲性格成长中的恶性循环。”
她不断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浮沉,她对自我的封闭,使她断了挣脱痛苦,燃烧希望的退路,彻底将自己放逐在了个人的空间里。
无论是七巧的彻底性也好,繁漪的不彻底性也罢,我们都不难从中找寻到作者自身的意识痕迹。因为曹禺本身的社会性,所以其剧作的人物,既具有独特的个性,又具有明确的社会性,因此繁漪不能纯粹彻底,也不应纯粹彻底,反之张爱玲对人性本源的探求,则使得七巧更多展现了其个性魅力,没有世间时事的干扰,七巧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她能纯粹能彻底,能允许彻底的毁灭!
参考文献:
[1]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3][4][5][8][9]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6][7][10][11][12]余斌.张爱玲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
自《雷雨》问世以来,曹禺及其经典剧作的研究从未风平浪静。细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这5大经典剧作,凌驾于主题挖掘与结构审视之上,剧作张力的构成研究似乎更见功力。话剧内部的张力关系表现为各种戏剧矛盾因素在文本中对立,或与...
钱谷融先生说: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现实。《雷雨》的作者曹禺正是通过这样对人物的不断探索和研究来展现这深刻的社会主题的。剧中的中心人物周朴园是一个丰富的、立体化、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他具有两重社...
题目:《雷雨》中蘩漪的人物形象评述目录摘要(详见正文)关键词第1章前言第2章雷雨性格2.1残酷的爱2.2不忍的恨第3章悲剧的成因3.1家庭环境3.2新旧交织的女性意识3.3无意识领域第4章我眼中的蘩漪总结致谢注释参考文献以下是正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