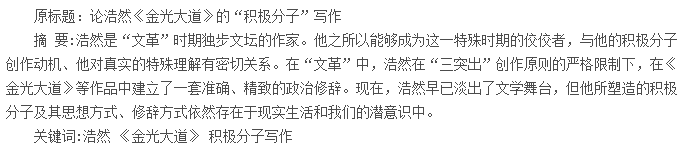
“文革”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噩梦,然而,作为成名于“十七年”的浩然来说,这场众人的“噩梦”竟然是他独享的文学时代。1966 年 5 月“文革”爆发前一个月,浩然的首部优秀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三部)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发行,作为一颗文学新星,浩然本可以平静地迎来他的创作高峰。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浩然无法按原有的方式写作。在 1966 年 6 月到 1970 年年底的将近五年时间里,他除了零星的文学评论和新闻特写之外,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到了 1971 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运动的后期。面对无序、粗糙的群众文艺状况,周恩来总理对国务院“出版口”的负责人说,“1971 年再不出书就不像话了”。1971 年 8 月后,期刊出版工作开始出现转机,一些停办的刊物开始复刊,还创办了少量刊物。据统计,“全国期刊出版种数,由 1970 年的 21 种,上升到 1971 年的72 种,1972 年又上升到 194 种”。
随着部分文学杂志的复刊和创刊,小说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文学创作活跃起来。
一时间,凋敝的文坛突然被数量庞大的工农兵创作所充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创作质量之低,连文革派自己都不能满意。虽然上海负责文学评论的写作班子“任犊”曾为之做了一点政治辩护:“恐怕在资产阶级老爷们看来,里面有的作品是很不合‘章法’的”,“不合章法也是一种章法,一种新的章法”。然而,这毕竟不能改变事实。因此,文革派不得不考虑重新启用专业作家和编辑来参与小说创作,为创造小说的“样板”作品提供可能。为了既能利用专业作家,又能有效地监控他们的写作,文革派重新推行 1958 年文艺“大跃进”时期的“三结合”集体创作方法,以“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方式生产了《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作品。
而浩然同时具备政治过硬和业务成熟这两方面的优越条件,作为工农兵作者中的佼佼者,他获得了那个时期非常难得的独立写作的资格。在某种意义上,浩然在“文革”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并非完全由政治力量的介入造成,他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拉上文学舞台的。浩然机遇的到来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浩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作为革命的受益者,他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完全要感谢党的教育和培养。他说:“象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这种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生的职业,如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苦人搞革命,政治上得解放,经济上闹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浩然的亲身经历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农民,社会主义的兴起,已经救了农民。”
正是这种翻身农民的“感恩”心理与情绪,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浩然曾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被墙报上的散文诗吸引的情形:“那带韵的优美文字所表达的当时农民对解放后新生活心满意足的情绪、对更美好日子的向往,却因激发了我的共鸣而深深地印在脑海。”
除了朴素的阶级情感之外,“文革”中关乎切身利益的派系斗争也使浩然对文革派心存感激。在“文革”初期,周扬要赶他下去参加运动,而江青却留他下来继续写作。
因此,他认为“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我从黑线的压制下拯救出来的”,“他觉得是这帮人救了他,自然感激他们。感恩图报,感谁的恩便为谁做事……”
于是,在这种“感恩”心理的支配下,浩然积极响应文革派的极“左”文艺主张,并将之视为政治觉悟的体现。他说:“从来没有想过回避或摆脱党的方针政策和正发展着的各种运动对我创作的影响力;正好相反,作为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作家,总希冀配合得更紧密些、完好些。”至于作品的优劣,他也完全赞同“政治标准第一”的工农兵文艺观,并以此来解释他本人和他的作品在“文革”前后的荣辱沉浮:“反映了成功经验的,就站住了,这是大多数的篇章,因此我沾了光;有的跟失误的弯转有所牵连,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背了黑锅。”
非常吊诡的是,在“文革”结束后,浩然本人从不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作品违背真实。在 1980 年代,他曾经表示,他一直将“写农民,给农民写”视为他的创作理想,并进一步解释说,“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志愿和决心,因为我是农民出身,……农民同我保持着天然的密切关系;我是在农民帮助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不断从农民身上和生活中吸取创作素材。”
如果说这一理想在他的《艳阳天》时期曾经成立过,但是到了“文革”中,浩然的写作重心发生了偏移。他不再关注现实中的普通农民,而是转向塑造理想中的农民英雄人物。如果说,他笔下的高大泉、朱铁汉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农民呢?
在 1994 年《金光大道》重版之际,浩然在序言中明确地指出,高大泉、朱铁汉就是当时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积极分子”。并且,在涉及《金光大道》的构思过程的多篇文章中,他也不只一次提到,《金光大道》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有当时京郊的农民积极分子王国福的影子。
这些“积极分子”来自工农兵,但政治觉悟又明显高于普通的工农兵群众。
对于“积极分子”,浩然一点也不陌生。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浩然十四岁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在扩军工作中,因为变相强迫“动员”一个青年参军,结果,“这个青年入伍不久负了伤,传说牺牲了,他妈就找我拚命。等到土地改革的时候,为这件事我受到报复,被当成土改的障碍给搬了‘石头’。”
在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浩然承认自己“有浓厚的狭隘的偏激情绪。”他曾经认为,“不应该分给地主富农们和我们一样平均数量的土地,认为应该让他们尝尝挨饿的滋味儿”,“不应该给俘虏们号房子住和购粮购菜吃,应该杀掉他们,报仇雪恨。”
到了“文革”时期,浩然在运动中依然活跃,在斗批改过程中,他又被选为积极分子,参加市里的下放干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当时的积极分子高大泉、朱铁汉等等,都是我的依靠对象和战友”,“他们对幸福明天的热烈向往、顽强追求,以及为达到目的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当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也铭记在心头”。
所以,当大多数在政治上被打压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对“三突出”原则深感束缚的时候,从一个积极分子逻辑出发,浩然甚至认为“三突出”原则还执行得不够彻底:不仅要在写作中强调,还要在生活中强调。他说,“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深入生活开始就强调‘三突出’。”
如果说,在写《艳阳天》时,浩然还没有忘记像韩百安那样勤劳本分、胆小怕事的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的话,那么,到了《金光大道》时期,他不再关注普通农民的利益和情感,一味地在作品中回味自己在建国初期所体会到的“蜜月”般的“幸福感”,对60 年代中国农村严重的经济危机视若无睹。在“文革”中,浩然的创作动机发生了严重蜕变,已经由“为农民写,写农民”变质为“为积极分子写,写积极分子。”
在“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余年中,浩然从没有真正地反省过这种极端狭隘的“积极分子写作”严重扭曲了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因此,也就无怪乎在 1998 年,他还会公开宣称对自己在“文革”中的创作丝毫不感到后悔,甚至认为自己当时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由于找准了“积极分子写作”的定位,浩然对文革中强调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做出了不同一般的“正确”理解。
就“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言,浩然充分领会了“革命的”这个修饰语对“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中“作品”和“世界”关系的修正作用。经典的现实主义强调作品对世界的模仿。而浩然却从根本上颠倒了这一关系。在他看来,作品不应该模仿世界,相反,世界应该按照作品所揭示的真相来改变自身。他认为,创作的第一要义是“改造”,即“把不正确的和落后的东西,用我们的原则精神、正确的思想标准加以改造,同时把与之对立的正确的、先进的萌芽状态的东西加以发扬———把不合尺寸的原材料,加上钢,放进我理想的‘模子’里溶解,脱出个全新的‘型体’,树立一个榜样”。这种改写现实的做法被浩然看作是作家“正确认识”何谓“真实”的能力的体现。也就是说,当作家看到现实中存在严重的缺点时,他必须要学会辨别主流与支流,本质与表象。什么样的认识才是“正确”的呢? 浩然说,“我们应当认识到:某些缺点虽然严重,但它不是我们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比起成就、总的形势,它是微不足道,不起主导作用的。”因此,对支流的忽略,对表象的改造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可以“让做了错事的同志看了以后有所启示,有所自觉,而且效仿它。”
就“革命的浪漫主义”而言,浩然也同样做出了“革命化”的改造。尽管浪漫主义强调作品是对世界的表现,但它并没有取消世界的客观性,并没有割断作品与世界的联系。而在文革派眼中,作家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它只是事物的表象;而作家应该关心的是事物的“本质”,因此,世界不是作家认识真理的出发点。那么真理在哪里呢? 真理就是被教条化了的“毛泽东思想”和文革派所鼓吹的种种政治理念。它是外在于世界的,高于世界的绝对真理。因此,“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经典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作品不是对世界的表现,而是对意识形态的表现。这就涉及到作家的创作态度———“歌颂还是暴露”———的问题。在浩然看来,歌颂还是暴露,“并非仅仅是写作形式和方法;它是革命作家与非革命作家的分界线。”
1966 年 2 月,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做的发言中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新文艺”的构想。
1968 年 5 月 23 日,于会泳应《文汇报》之约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样板戏的金科玉律———“三突出”原则,并于 1969 年 11 月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提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个创作原则的提出使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文艺”观念具有真正的可操作性。
在“三突出”原则限定下的小说创作很难避免“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但是,当时的主流批评家却一再要求作者克服作品雷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浩然凭借其文学才华,以及对文革派文学观的准确把握,为“三突出”原则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性。在《金光大道》中,最能体现作家才情的段落,应该是小说的“引子”部分高大泉出场一节。在主人公出场之前,作者先描写了他们一家分离的场景:动身的那天早晨,好多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凑到高家的小土屋里;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说的都是一些让人宽心的吉利话,祝福他们从这一步起,就时来运转,诸事如愿。
弯在床上的男人颤颤抖抖地抬起他那枯瘦如柴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小儿子二林的头顶,看不够,亲不够。他悲愤地向儿子,也是向妻子和邻居诉说自己的不幸。他说自己白给地主“积善堂”卖了三十多年命,病倒了三天没干活,就被赶出大门;他说自己耿直本分,勤劳半生,如今却落下两手空空,妻离子散;劝妻子不要惦记他,嘱咐儿子听娘的话,长大了当个有志气的人,要替他报仇雪恨。他说着话,流着泪,又很费劲地转动着脑袋问:“大泉呢? 过来,过来,我再跟你说几句话。”
这个场景中,尽管人物众多,但是除了因为行文需要而顺带提到高二林的名字之外,所有人物都处于无名状态。作者只以“男人”、“女人”、“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来指代他们。作为普通的受苦人,他们只是面目模糊的一群,没有名字,更没有声音。所以,当“男人”,也就是主人公的父亲,向大家诉说他的不幸的时候,作者甚至没有使用直接引语,而仅用间接引语。这个高度概括的形式,大大降低了次要人物的音量,为主人公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因此,“男人”诉苦的申诉变成了平静地陈述,而他喊长子到跟前来的一句平常的呼唤,却被隆重地加上了引号———“大泉呢? 过来,过来,我再跟你说几句话。”在一片无声的叙述中,突然发出了声音。一个关于命名的叙事,使英雄人物从普通的受苦人中脱颖而出,从而在“无名”的群众与“有名”的英雄之间构造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不可改变的秩序。
这里不能不称赞浩然的艺术才能,高大泉的第一次出场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意义。当父亲呼唤他时,高大泉并没有应声而出。在短暂的静音中,叙述的速度被巧妙地放慢了。高大泉的缺席,反而激发了读者对他更加强烈的期待。接着,读者跟着大泉娘的视线开始寻找主人公。
她(大泉娘)又抬头朝远处看看。破烂的街道,荒凉的野地,都是静悄悄的,没有行人和声音;忽然,一群鸟儿叫唤着,从远处大水坑西边的小树丛里飞起来,接着走出一个男孩子。
显然,高大泉的出现给死寂的荒野带来了生气,其中的象征意味不言自明,而作者巧妙的布置仍能带给读者阅读的愉悦。而后,高大泉的具体形象逐渐显现:这个男孩子,细瘦的个子儿,上身是开了花的破棉袄,下身是条条缕缕、辨不出颜色、看不清形状的灯笼裤子。他提着一只大瓦罐,摇摇晃晃地往这边走来,两只光着的大脚丫子,“吧嗒”、“吧嗒”地拍打着路面上的浮土。
与前面精彩的铺垫相比,人物的正式出场却让读者感到明显的失望。这段详细的外貌描写所包含的信息是那么的贫乏,以至于除了报告主人公的阶级出身外,人物的个性没有得到丝毫展开。比起正文中朱铁汉的外貌描写,高大泉的亮相的确逊色了许多。虽然作者曾说,高大泉和朱铁汉一样,是他所熟悉的积极分子,但是在小说中,作为中心人物的高大泉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比朱铁汉更加完美。而浩然在外貌描写中对高大泉性格刻画的回避,或许就是在不经意中暴露出作者在塑造高大泉时的力不从心。
所以,为了丰富“高大泉”的形象,浩然不得不在单薄的外貌描写之后,再追加一个直接展现人物性格的语言描写,通过高大泉与地主“小少爷”的争吵来补充主人公富于斗争性的英雄品格。
在《金光大道》中,还有一种无所不在地运用“三突出”原则来创作的方法,这就是“典型化”。《金光大道》中的“典型化”显然借鉴了“样板戏”的经验,在小说中,无论是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以至于环境描写中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具有鲜明的形式感和象征意味。
小说中有多次关于“道路”的描写。在“引子”中,最先出现的是“逃荒的道路”,作者写道:那弯曲不平的道路正反浆,不是泥就是水。一群一伙的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破衣拉花;那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一双双无神的眼,好像有千愁万苦无处诉说,也用不着去诉说,都压在心头,化成了无声的反抗,不息的追求;……一辆罩着锦锻绣花围幔的小轿车飞奔而来,又疾驰而去;鞭抽铃响,泥水溅在步行人的身上;几个人躲闪迟慢了一点儿,肩上挨了鞭子;轿车过后,留下的是难闻的烧酒气味和女人的尖笑。远处残碑枯叶树下边的乱坟中间,有几堆崭新的黄土,青烟升腾,风扯挂纸,接着是一声声凄凉的哭啼……无疑,这段景物描写意在说明旧社会富人走的都是阳关道,而穷人只有死路一条。而在新中国,高大泉遇到昔日的穷伙伴、今天的革命军人雨田,在雨田的指引下,他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于是“两个伙伴迎着太阳,肩并着肩,在那朝向正东方的大道上迈开了步伐……”。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金光大道》中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描写仅此一处。似乎除了“正东方”的修饰语外,根正苗红的浩然也不敢轻易对新中国的道路妄加评论。
与对社会主义道路惜墨如金的描写相对,在“陷在泥水里”一节中,浩然频频借助环境描写对资本主义的泥泞险途发出警告。首先是天气的突变,大晴天突然下起了大暴雨,象征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怕局面。接着冯少怀和他的大车出现在暴雨中:“西官道完全改变了本来面貌,……它像一条弯曲浑浊的小河,滚着水,飘着被风雨掠下的树叶;冲来的粪沫子,在泥水里翻跟头、打旋转……”而冯少怀新买的大车和骡子也全无了威风。“一辆新胶皮车,象一口从老坟里扒出来的半截棺材,胶轮深深地埋在泥水里。辕上的骡子,后腿坐着,前腿支着,脑袋歪着,长嘴巴尖在浑水上喘着气,吹着泡泡。它浑身湿淋淋,毛儿贴在皮上,好象一条刚从大坑里捞上来的黑鱼。”
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浩然将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手法推向了极端,使之呈现“功能化”特征。在《金光大道》中,没有一个细节不为“阶级斗争”的主题服务,细节被当作政治修辞的零件,随意装配,成为“阶级斗争”主题的装饰物。
然而,“三突出”对文本的全面渗透并没有到此为止。在“老周忠挂帅”一节中,还有一个英雄人物的身体特写———“手”的特写:“一盆炭火,围着四个贫农老人,八只被绳索和木器磨得皮肤粗糙、指头弯曲的大手,像观赏,像比较似的,一齐伸在火苗上。那手上的折皱和老茧,是奴隶的伤痕,也是创造者的光荣标记。”
这一身体特写表明《金光大道》已经将抽象的“阶级意识”外化为可供观赏的身体特征,以求现实生活、文学形象与意识形态的政治修辞的完全合一。
“三突出”原则在文本中的无限扩张,最终导致了“文革”时期小说中“叙述人”的权力空前加强。
在“文革”时期的小说中,叙述人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之外,还具有“评论功能”,而且,时常出现“评论功能”压倒“叙事功能”的情况。为了保证主题的鲜明和清晰,作者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议论侵吞故事的正常叙述。在小说《虹南作战史》中,叙述人对作品的干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小说的每一章都围绕着一、二条“主席语录”展开情节,而且,议论和表态文字泛滥成灾,据统计,理论阐释的内容占到了作品篇幅的八分之一。
由此可知,在“文革”小说中叙述人既不代表作者发言,也不代表人物说话,而是站在意识形态的高度,以一个阶级主体的口吻,用全知方式对作品中的所有人、所有事进行政治评价。实际上,叙述人是那个抽象的工农兵的阶级代言人。因此,在《金光大道》里,我们经常发现一个奇特的场景,就是叙述人直接和主人公对话:高大泉坐在猛进的火车上,在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里,陷入了从来没有过的奇妙的严肃的沉思里。
高大泉哪,你这个在血与泪里挣扎了几千年的劳动人民的后代,那个灾难深重、罪恶无边的旧社会所反复重演的一切历史悲剧,你都亲眼看到,你都亲身遭遇,然而,这些已经彻底结束,因为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了;那么,从今以后,在那更伟大,更艰苦的斗争“长剧”里,你,还有你的伙伴们,将怎样担负起历史使命,又将怎样行走你们的人生道路呢?你快觉悟,你快回答!用你的心,用你的脚步回答吧!
在这个奇特的对话中,叙述人的声音好像神谕,完全来自故事之外的空间。它以权威的语调不断地引导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试图将高大泉的阶级觉悟推向更高。除了叙述人高亢的声音之外,我们根本无法知道高大泉的想法,或者说,叙述人的想法完全取代了高大泉的想法。在它的高音压制之下,文本中的人物也好,作品的作者也罢,都不过是名存实亡的傀儡。作家根本不可能通过人物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即使是政治上最过硬的英雄人物高大泉,也没有机会展现任何个人的情感。在《金光大道》的“引子”部分,叙述人仅用 208 个字,就将高大泉的恋爱、结婚、生子一笔带过,没有给人物留下任何私人空间。因此,在“文革”小说中,“阶级,才是革命叙事的真正叙事人”,无论是人物还是作家,都“只是一个被抽空了‘我’的被叙述者。”
“文革”小说中的叙述人在文本中的作用,与曾经发表在《朝霞》杂志上的一篇短篇小说《特别观众》中的那个剧场里的声音监听师非常类似。监听师警惕地在剧场里四处查看,时刻防犯着播送样板戏的音响出了故障,导致声音的失真和走形;而叙述人则随时处理各种意义的解释工作,以防止不必要的歧义的发生。在“文革”小说中只有一种声音,就是叙述人纯洁而高亢的声音。人物的语言只是陪衬与附和。英雄人物让高音更高,反面人物让低音更低。小说刊印时设置的醒目的黑体字,象征了叙述人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是叙述人的无上权力的证明。
1975 年,浩然被卷入“四人帮”阴谋夺权的政治斗争,他奉江青之命,写出了为她歌功颂德的《西沙儿女》,又以打击“走资派”为目的写了《百花川》(又名《三把火》)。而这些作品在“文革”结束后立即被定性为“阴谋文艺”。他曾经的辉煌成为日后的污点。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作品被遗忘了,但浩然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心路历程作为一种历史教训的总结,还是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1]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J]. 编辑学刊,1998(3) .
[2]任犊. 农场的春天·代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浩然. 我是农民的子孙[A]. 孙达佑、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4]陈徒手.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J]. 读书,1999(5) .
[5]浩然. 发扬敢闯的革命精神[J]. 北京文艺,1975(1) 增刊.
[6]李德君. 危险的道路 严重的教训———评《西沙儿女》作者的变化[J]. 北京文艺,1978(10) .
[7]浩然. 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A]. 孙达佑、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8]浩然. 写农民,给农民写———《他和她在晨雾里》编后记[A]. 孙达佑、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9]浩然. 怀胎,不只十月———漫谈《山水情》的酝酿过程[A]. 孙达佑、梁春水编. 浩然研究专集[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10]浩然. 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A]. 浩然. 金光大道[C].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
[11]卢新宁、胡锡进. 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N]. 环球时报,1998 -09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