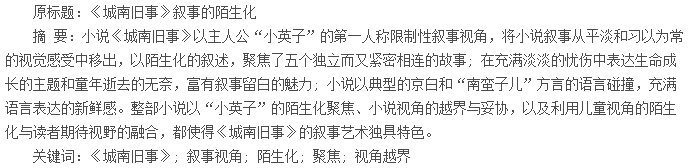
《城南旧事》是作者林海音以主人公“小英子”的独特视角,再现作者自小随父母旅居老北京城南的童年趣事,借以表达作者对童年逝去的无奈和成长中不可避免的哀叹。小说叙述了《惠安馆》、《我们看海去》等五个故事,这部“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的小说,有着成功而出众的叙事艺术。
陌生化视角作为小说叙事不可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探讨。“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所谓陌生化,就是将对象从正常的感觉领域移出,通过施展创造性手段,重新构造对对象的感受,从而扩大认知的难度和广度,不断给读者以新鲜感。
而《城南旧事》的小说叙事,正是以一种陌生化的儿童叙事视角,回顾并展现了小英子“看到她温暖的小世界后面,一个错综复杂的悲惨的大世界。”
其作品时时晕染着一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同时也表达了生命成长中不可避免的哀叹。
一、《城南旧事》陌生化视角的来源
《城南旧事》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英子”,其叙事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一个七岁孩童的视角单纯而明净,总可以忽略掉生活的沉重、压抑和不公,使小说洋溢着新鲜而陌生的新奇感受。《城南旧事》的这种儿童视角首先就决定了文本所描写的有限视域是局限在主人公“小英子”的视野中的。作者林海音先生写此书时已年过半百,其本身的人生历练与小说文本中“小英子”的纯真视角相互碰撞,以一种童稚和不成熟的表达,与读者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因此给读者明快而延长的视觉上、心理上的新鲜感。
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之所以需要陌生化,有两个目的:一是抵制审美疲劳并消解日常生活的‘机械性’,二是增加艺术感受的难度进而延长这种感受。”
小说《城南旧事》中写“我”去找惠安馆的疯子秀贞玩时,描写了“我”在等秀贞时发生的趣事:“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这一情景极具生动逼真的画面感,令人读来捧腹大笑,同时,又使人觉出“小英子”的童稚与可爱。不了解作者的人很难想象“小英子”这一形象会出自一个老年游子的笔下,而“小英子”的儿童视角又充满了好奇心和对外在事物的感知欲,这或许更体现出作者林海音在回忆性自传中的巧妙之处:把陌生化巧妙地杂糅进儿童视域,透过一个七岁主人公“小英子”的眼光把生活中的种种繁杂和矛盾进行过滤,使整部作品从人物到故事情节都充满着“淡淡的伤感”,又时时透露出成长中的好奇和新鲜感,从而大大提升了读者对于小说故事的期待感。
林先生做此书时的确切心境我们已不得而知,然而,透过这种陌生化叙事的笔法,或许我们可以猜想,林海音先生一生的豁达开朗,聪慧秀敏,以及先生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思考。其女儿夏祖丽在为母亲立传时,曾经这样记录到:“母亲善感却不多愁,她下笔很淡,感情很浓。”
这一评价十分中肯,也更加使读者确信了《城南旧事》“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绝非矫揉造作,而是出自作者的本真和个人特殊的成长经历。
二、“小英子”陌生化视角的聚焦
“小英子”的视角是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是叙述者以故事主人公一人的眼光叙事,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文中的主人公。同时,儿童的眼睛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和求知欲,所有生活中的事物一经“小英子”这双儿童眼睛的“过滤”,就可以把小说社会背景下的生活、事件从正常和平淡中“移出”,并赋予极具主人公个性色彩的童真童趣,使得整部小说变得格外清新和纯净,这也就是《城南旧事》中主人公“小英子”式叙事视角的陌生化所在。主人公“小英子”的眼睛对世界的认知有一个独特的、陌生的聚焦方式,这不仅是基于作者林海音先生的童年记忆,也是基于小说主人公“小英子”不断成长的经历。《城南旧事》中小英子叙事的陌生化聚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叙事内容陌生化:串联五个故事的成长
法国学者热奈特曾就叙事视角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聚焦”观点,《城南旧事》的“内聚焦”也就是“小英子”的陌生化聚焦,它更多地表现在主人公“小英子”作为叙述者兼主要人物角色,她通过自己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心理活动,别具特色地展现自己身居北京城南的童年生活,这其中既蕴含着“小英子”个人童年的欢乐,也时刻蕴蓄着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淡淡的悲伤。《城南旧事》透过“小英子”的视角,独特地展现了作者童年生活中的人、事、物。
《城南旧事》采用片断式的记忆形式,记录了五个独立又紧密相连的故事。《惠安馆》写秀贞和小桂子为寻思康而被火车轧死;《我们看海去》写“小英子”偶然结识的大朋友为生活所迫偷东西被捕;《兰姨娘》写旧中国一个美丽女子饱受男权凌辱并最终走向勇敢追寻自由的道路;《驴打滚儿》写不得已随丈夫黄板牙重新回乡生养的宋妈痛失孩子;《爸爸的花儿落了》一章中写“小英子”在爸爸离世的悲伤中成长。
《惠安馆》一章中,大人眼里的疯子秀贞在“小英子”的眼中却无比正常,“小英子”甚至被秀贞的故事感动,热心地帮助秀贞和小桂子相认,还不计后果地偷出妈妈的金镯子给这母女俩做盘缠;《我们看海去》中被人人唾弃的坏人小偷被抓,“小英子”觉得无比伤心,还决定以后一定要写本书怀念友人;《爸爸的花儿落了》中面对爸爸的离去本应无比伤心难过的“小英子”,却表现得十分淡定和坦然……小说中所有这些人事物的表现,都极其符合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内心的心理变化和性格特征,并印证着儿童视角的陌生化心理。
然而,这五个似乎并无关联的故事,实际上是以小英子的成长、童年的逝去为线索,串连成了一串美丽而富于光泽的珍珠,就像作者林海音先生自己说的那样:“这部小说是我以愚马矣痛心的眼光写些记忆深刻的人物和故事,有的有趣,有的感人,真真假假,却着实地把那时代的生活形态如北平的大街小巷、日常用物、城墙骆驼、富连成学戏的孩子、捡煤核的、换洋火的横胡同、井窝子无意中写入我的小说。”
作为文学接受的一方,我们又总在寻找“小英子”生活的足迹。小说有趣又充满了淡淡的悲伤,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回味和美好。这既是本书的主旨,也是作品完整而充满趣味性的关键所在。整部小说突出了“小英子”的视角关注也随着成长的哀叹和童年的逝去而不断转移。例如,《惠安馆》时,“小英子”六岁,正准备着上小学。到第二章《我们看海去》,读小学一年级的“小英子”七岁;《兰姨娘》一章,兰姨娘叮嘱三年级的“小英子”要认真读书,不能惹妈妈生气;《爸爸的花儿落了》一章,十三岁的“小英子”小学毕业。由此可见,这五个独立的故事实际上又以时间为线,饱含童年逝去的无奈和成长不可避免的哀叹。
(二)叙事结构陌生化:《城南旧事》叙事的留白艺术
整部小说在《爸爸的花儿落了》一章中结束,文风朴素而悲伤,童年逝去的无奈和成长不可避免的哀叹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每一个故事的结束,又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读者的期待并不随着故事的结束而降低,反倒是一步步更加高涨,有一咏三叹之感,是一种叙事的留白艺术。
在每一个故事结束的同时,“小英子”的视角关注也在静静地发生变化。从糊里糊涂帮助儿时的玩伴“小桂子”寻亲,甚至偷出妈妈的金镯子给秀贞和小桂子作盘缠的善良;到与大朋友小偷相约看海,“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太多了,很难分。……你分得清海跟天吗”的率真;再到偶然看到爸爸跟兰姨娘的暧昧,隐约觉得妈妈的悲苦,并鬼灵精怪地凑成了兰姨娘和德先叔的姻缘,解除了妈妈的危机的机灵和智慧;再到“小英子”小学毕业时,爸爸在病中离去,留下母亲和英子以及众兄弟姐妹,从此担起了“做大人”的勇敢和责任,开始“闯炼闯炼”的成长。“小英子”这一主人公的性格也在一次次离别和结束中发展、成长,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小英子”开始关注和思索亲人的悲苦,虽然很多时候“小英子”想不明白,似懂非懂,但读者却更能在这种陌生的不成熟叙事中体悟人物和反思自我。聚焦的视野和视角不断在各种协调和处境中变换和转移着,实际上,作者的聚焦转换十分自然,“不同的聚焦就象是来自文本内部不同方向的强烈光柱,把主人公照耀得里外通明,这种不定式内部聚焦的效果,有点象复调音乐,它由许多独立对等的弦律构成,但最终又在多声部、多层次的变化中,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强度和气度,共同营造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
可见,孩童视角的成长变化主要体现在,作者并没有拘泥于故事的简单叙述,而是在叙述中表达出成长和变化的主题。
(三)叙事语言陌生化:典型的京白语言与台湾语言的碰撞
《城南旧事》叙事视角的陌生化之处还在于叙事语言的陌生化。这是来自长在北京城南的“台湾人”的儿童成长记忆,既富有北方“京味儿”的质朴,又有“南蛮子儿”客家歌谣、福佬仔的回味。两种文化积淀的融合、摩擦,更能烘托出生活的本真和乐趣,在身处另一种文化的铺叙中激发出更多新鲜而跳跃的语言活力,大大提升了读者对于小说叙事的期待感。
“小南蛮子儿”的京片子记忆的特殊之处,更多地表现在小说中北京人与台湾人双方的称呼、生活习惯以及饮食特色上。一方面,是“南蛮子儿”对北京方言的不适应。《惠安馆》一开始,作者就讲明来自台湾闽南的妈妈还是讲不好普通话,“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却讲成“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再比如,“小英子”与秀贞初次相识时,秀贞的妈妈叫小英子“小南蛮子儿!”,“小英子”当时却想起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叫他们“北仔鬼”,可见这种由于地域不同而造成的精彩的语言碰撞。
另一方面,是“小英子”这个“小南蛮子儿”对京片子的无限热爱。爱吃佛照楼的八珍梅,喜欢打糖锣挑子上的酸枣面儿、印花人儿、山楂片还有珠串子……还包括“小鱼上大串儿”等一些极具京味特色的方言。
这两方面的特殊叠加,使得“小英子”这一角色身份别有个性,给读者期待以很大的新鲜感和想象,笔者读文时,觉得“小英子”这一角色实在可爱淘气,惹人怜爱。甚至脑海里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眼睛大大的、水汪汪的,留着齐刘海儿,有些微胖的小女孩儿站在面前,冲你眨眼睛,扮鬼脸。《城南旧事》中多次提到了作者自己作为一个台湾人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的种种乐趣,正如作者本人在《城南旧事》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
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这就是《城南旧事》中独特的语言艺术吧。
三、陌生化叙事视角的优与劣:《城南旧事》小说叙事视角的“越界”与“妥协”
“陌生化”理论在叙事学的研究中一直颇受争议,主要原因在于陌生化叙事有一定的片面性,它过分强调叙述对新奇视像的追求,从而忽略了叙述的真实性和逼真感。所以,一部成功的叙事作品,总是能够拿捏好这其中的度,达到言语表达和叙述内容之间保持新鲜感的最大契合点,《城南旧事》的陌生化叙事处理实际上就是在陌生化基础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小英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她既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所以这一角色更“透明”,也更易得到读者的认同和理解。
这种陌生化视角的优点在于,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时常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预期的读者,并且按照预期读者心理反应来写,而《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既是作者,又不是作者,“小英子”的有限视域一方面充满了儿童的纯真和善良,另一方面在面对善恶、好坏时,主人公“小英子”又时常觉得不理解和困惑,而这些不理解实际上恰恰符合了人物的身份和形象,因此,这更加突出了“小英子”的可爱和机灵。
当然,作者的这种有限视角的选择,也不可避免有一定的缺点。“小英子”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事视角,也是叙述者的视角。主人公“小英子”的角色身份成为限制人物在小说中的一言一行的关键,这就给作者在完整而生动形象的表达小说故事上其实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如果仅仅是以“小英子”的视角来写,那《城南旧事》可能就变成一部完全是成长中孩子的不成熟视角,很多涉及到社会背景、人物遭际的叙述将无法表达,这将给这部小说结构的完整带来很大的被动性,如果只采用孩童的视角,那我们今天读到的《城南旧事》可能就不会那么精彩生动了。
事实上,在《城南旧事》的陌生化叙事视角中,作者为了避免单方面地透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展开叙述这一弊端,采用了一些“非常手段”以达到一种全知全能视角的效果,这就是笔者标题中提到的“视角越界”。所谓“视角的越界”现象是指,“文章的叙述者超越了内视角的边界,侵入了全知视角的领域。”
《城南旧事》中“小英子”的叙事视角既有依凭其身份限制的有限性,同时,叙述者又跳出故事文本,从小说叙事的整体结构出发,能动地让主人公“小英子”通过一些具有偶然性和符合个性特征的行为来完成小说的补充叙事,使整部小说在叙事内容和结构上充分合理又别具个性。小说中的“小英子”就是凭借自己的“听事儿”和“看”来介绍其他小说关键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从而达到小说的全知全能叙事的效果。
首先,写英子的“听”。例如,《惠安馆》中借写英子的“听事儿”来介绍疯子秀贞的身世:“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后来呢?’‘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又听事儿,你。’‘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说谁?’‘小桂子她妈。’‘小桂子她妈?’宋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我也哈哈大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
作者巧妙地把“小英子”的有限视域拓展开,把“偷听”来的不理解的事件作为小说叙事的补充,无形中既是刻画“小英子”天真可爱聪慧形象的点睛之笔,又是保证小说完整叙事的必要补充。
其次,小说通过“小英子”的心理活动来补充叙事。
比如,在《兰姨娘》中,爸妈就是否应该把兰姨娘留在家中起了争执,妈妈让“小英子”去买豆蔻,“小英子”当时的心理活动:“豆蔻嚼起来凉苏苏的,很有意思。兰姨娘在家里住下多么好!她可以常常带我到城南游艺园去,大戏场里是雪艳琴的‘梅玉配’,文明戏场里是张笑影的‘锯碗丁’,大鼓书场里是梳辫子的女人唱大鼓,还要吃小有天的冬菜包子。我一边跑出去,一边想,满眼都是那锣鼓喧天的欢乐场面。”
再者,写英子的“看”:《兰姨娘》中写妈妈为了兰姨娘吃醋:“爸挑了一色最浅的,低声下气地递到妈面前说:‘你看这料子还好吗?是真丝的吗?’妈绷住脸,抓起那匹布的一端,大把地一攥,拳头紧紧的,像要把谁攥死。手松开来,那团绸子也慢慢散开,满是绉痕,妈说:‘你看好就买吧,我不懂!’”
从上述的例子中,很容易就能发现,《城南旧事》中类似这样的叙事还有很多。作者在陌生化叙事的同时,又借助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视角观察等行为来使得小说的叙事更加充分。
总体来看,《城南旧事》的视野越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结合了“小英子”的偷听来补充说明小说叙述必要的人物背景和生活遭际。如,在《惠安馆》中,“小英子”借偷听宋妈和卖火柴的老妈子的谈话,向读者介绍了惠安馆的疯子秀贞的悲苦经历,也为下文“小英子”撮合秀贞与小桂子相认作了铺垫,使得读者在充满悬念和好奇的基础上不断读下去。二是,作者借“小英子”的“看”来描写其他人物的行为活动,以充分反映人物间的微妙关系。例如,在《兰姨娘》中,写“小英子”无意中看到兰姨娘和爸爸一同躺在床上抽烟,爸爸捉着兰姨娘的手,“小英子”看到这一幕,隐约觉出母亲的悲苦,从而为下文“小英子”有意促成兰姨娘和德先叔的姻缘,解除母亲的危机埋下伏笔,同时揭示了小说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社会地位低于男性的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城南旧事》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是不同于通常所讲的全知全能视角的。这是因为通常所讲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是一种上帝式的视角,叙述者的叙述无时无刻不处在一个评价和设定标准的高度,知晓他人所不知晓的事,同时也会与读者产生较大的距离。
然而,《城南旧事》中的全知全能视角是经过非常手段处理的、与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相结合的视角,读者无时无刻都对下文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关注度,也因此读者与文本中的人物保持着密切交流的关系。小说常常借大人讲话或者是表明宋妈等人的错误以及小英子心理活动等方式,突破了简单的小英子视角的角色性限制,使小说婉转地变成了一种全知全能的叙述,同时又保持了小英子儿童视角的特点和可爱之处。
这其实是《城南旧事》小说叙事陌生化的妥协之法。
四、《城南旧事》叙事的成功:陌生化视角与读者期待视野的结合
《城南旧事》叙事的成功,不可忽视儿童陌生化视角下的小说叙事与读者期待所产生的摩擦。叙述者在叙事中既迎合作为文学接受的一方的期待视野,又使其不断地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受挫,即所谓的期待受挫,二者交互作用,促使读者达到文学接受的高潮。《城南旧事》中主人公“小英子”的有限视角不断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充分利用了“小说具有运用、转换叙事视角的最大自由度和可能性”,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和作家的一致喝彩。
作为文学接受者的读者们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有了所谓的道德判断和价值标准,本来很明白的事情在小英子那里却偏偏行不通了,这种文学形象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更延长了读者的好奇感,使得读者内心寻求“共鸣”的阅读动力更大。
小说叙事的魅力往往在于故事本身并没有激烈的冲突,冲突却在小说文本中张弛有度。《城南旧事》的叙事蕴含着淡淡的忧伤,是一种平淡的、来自叙述者“小英子”成长中童年逝去的美丽,这种叙事的美丽,沾染着无奈,又蕴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就如美脱离不了社会历史而存在,美本身就具有了时代性和社会性一样。也正因为如此,《城南旧事》并非一部简单的儿童文学,也并非一部满怀回忆和向往的自传文学,它更是一部展现蕴含人文美的叙事文学。
《城南旧事》以主人公“小英子”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视角,将小说叙事从平淡和习以为常的视觉感受中移出,以陌生化的叙述,聚焦了五个独立而又紧密相连的故事;在充满淡淡的忧伤中表达生命成长的主题和童年逝去的无奈,富有叙事留白的魅力;小说以典型的京白和“南蛮子儿”方言的语言碰撞,充满语言表达上的新鲜感。整部小说以“小英子”的陌生化聚焦,借助儿童视角的局限性和小说叙事视角的越界与妥协,促使陌生化与读者期待视野相融合,从而成就了小说《城南旧事》独特而出众的叙事艺术。
参考文献:
[1]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林海音.城南旧事北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林海音.林海音文集·生命的风铃[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5]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6]申丹.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引言胡学文是我国当代文学非常优秀的一位作家,从1995年处女作《骑驴看唱本》(《长城文艺》1995年第1期)开始,他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胡学文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先后在诸多文学刊物,如《北京文学》、《长江文艺》、《小...